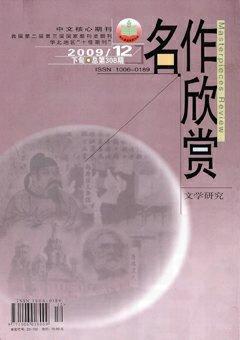论叶兆言小说的“反高潮”
关键词:叶兆言 叙事策略 反高潮
摘 要:叶兆言的小说在“平常”的外表下蕴涵着先锋的意味,这种先锋意味如果从形式层面而言就体现在其小说对叙事策略与叙事技巧的重视上。新的叙事时空的开拓,叙事的各种可能性的探索,尤其对高潮的预示和闪避,以及虚实相间的场面处理,确立了叶兆言个人化的叙事风格。
在叶兆言的作品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故事进入自然流畅甚至急遽紧张的时刻,叙述者马上会转入另外一种语气和文字,冷静地讨论和沉思这种叙述和叙述对象的距离,告诉你一种虚构的迹象已经出现在叙述中。此后,叙述人重新调整心态、视角,再次进入故事。这种叙述上的化出和化入,无形中给叙述带来了形式上的美感,那就是叙述的节奏和故事的节奏。这种力图回到“真实”的推敲,无形中增加了小说的张力,使得小说衍生出多种可能性。并且他小说的结构,好像都是随意开始,平和过渡,在没有高潮的故事讲述后结束,整体体现出无结构却有秩序的张弛层次。这种写法,即为“反高潮”。
“反高潮”,既是语言修辞手法又是篇章结构技巧的运用。用陈华、何晓曦二位先生的话说:“当你心神贯注,为故事情节所吸引,喟然而叹,抚颊沉思,感慨动颜之时,小说忽然激流直转,出人意料的结局奔突而出。但在惊奇之余,若将通篇仔细玩味,又能悟到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必然。正是由于这种结尾的提挈,通篇小说才隐端毕露、真相大白,生动传神,令人读来如橄榄在口,余味无穷。”①
本文试从叶兆言运用“反高潮”手法对小说具体情节处理及效果加以分析,希望可以看到叶兆言叙事技巧的一隅。
一、采用“反高潮”的缘起
叶兆言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叶圣陶是著名的现代作家,父亲叶至诚是南京的藏书状元。叶兆言本人是南京大学的文学硕士,他的学养是当下当红作家中较高的一位。读书条件得天独厚的叶兆言读书之多,在其同辈中几乎无人可比;又由于他父亲的藏书绝大多数是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这就使叶兆言以后的文学创作不可避免地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像荒诞小说《绿色咖啡馆》就是这种影响下的产物。巴尔扎克、卡夫卡、福克纳以及张爱玲都是叶兆言本人提及的创作受其影响较大的作家。
叶兆言的小说多写平民生活。他以一系列描写平民市井的小说,构筑了自己在文坛的地位。他的平民意识是骨子里的,其间透露着关注的热情、平等的理解和温和的同情;因而他笔下的生活是为大多数读者所熟悉的生活。几乎每一个人都能从其平淡的叙述中找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形成一种关照或产生一种情绪。这种对平民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书写,使得他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更深厚的意蕴,以及如何提升作品的吸引力。这里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作家张爱玲。如王德威评价,叶兆言描写俗世生活的源头有两个,“一是张恨水、李涵秋等人领衔的鸳鸯蝴蝶派;一是张爱玲独家炮制的海派传奇”,“叶兆言的《半边营》刻画了一个年华老去的华夫人与她的三个子女的怨怼关系,摆明了是对张爱玲《金锁记》的敬礼之作”,“《十字铺》颇有些张爱玲的《五四遗事》的讽刺趣味”②。张爱玲的小说较少因果分明的逻辑安排,每当情节即将接近高潮的时候,她总不肯轻车熟路地滑入读者期望的高潮场面而是克制地宕开一笔,以别具慧心的隐喻和象征暗示了人物命运的陡转。正如她自己宣称的:“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③艳异空气的制造即是她所擅长的隐喻象征,已有研究者指出,镜子、月亮、水缸、玻璃……是属于张爱玲的私人意象,在她的小说中一再出现,其功能“和整个故事结构、人物有关系,有时是嘲弄,有时是一种暗示性的道德批判……”④而在叶兆言看来,“到了高潮就不往下说了,乘胜追击是读者的事,再好的话也不能多说,要有节制”。等到读者明白过来其中的缘由恍然大悟之时,便会陷入深深的沉思和回味中。在谈到短篇小说的创作时,他特别强调自己不喜欢欧·亨利的小说,这种向大师挑战的论述并不是他的本意,他的意思是,短篇小说不是为轮胎打气,打足以后让它爆炸,在叶兆言看来,“写短篇应该像打气”,“好的小说应该是一只充足了气的轮胎,它载着读者驶向小说的彼岸”,“结尾有时候并不一定重要,重要的常常是造成结果的过程”(《叶兆言文集·作家林美女士》中之作者自述)。他的小说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在看似平淡的叙述形式下,通过“反高潮”等手法的综合运用,使得小说中有大量空白需要让读者去填充和想象。在这种“智力游戏”中,读者可以获得对生活的多重感悟。无疑,在“反高潮”上,叶兆言是师承张爱玲,虽然二者的运用不尽相同。
二、对“反高潮”的运用
叶兆言喜欢不动声色、冷静客观地讲故事,叶兆言的小说给人好读的印象,因为它们披着故事的外衣,这也可以看做是叶兆言争取读者的策略和手段,但显然他不真正属于传统的“讲故事”作家之列。虽然几乎叶兆言所有小说的开头都给人一种阅读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错觉,但是人们一旦带着这种期待视野进入故事之后,阅读期待几乎大多落空,他在叙述过程中常常把故事予以打乱或解构,而且较多运用“反高潮”的手法,他的小说在形式上没有多少特别的讲究,好像是随意开始,平和过渡,在没有高潮的故事讲述后结束。事实上他对小说形式中过分突出的结构意识不以为然。叶兆言的一系列创作在“反高潮”的运用上探索出的“有意味的形式”也给文学创作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叶兆言对故事情节的反高潮处理,有两种主要形式:
一种表现为外在情节的突变,大多出现在故事将要结束的时候,对于高潮的解决往往出乎读者的意料,以结局的奇特、出其不意而令读者回味无穷。
如小说《艳歌》中迟钦亭和沐岚婚后生活索然无味,濒临离婚,这时迟钦亭恰好又碰到自己单恋过的初恋情人庞鉴清……迟钦亭到底说了什么不得而知,庞鉴清有什么样的内心波澜语焉不详,待到一切挑明后二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小说也未曾述及。这个结尾一直让读者唏嘘不已,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对庞鉴清的暗恋促成了迟钦亭和沐岚的婚姻,可是小说中单单略去了关于二人在庞鉴清单独居住的家里会面的情形。被描写、叙述出来的文本图式化方面,只是表达言内之意的主要方式,而文本的空白和沉默,则是达到言外之意的重要手段。这种叙事省略了许多笔墨,掐断了许多线索,留下了大片的想象空间,召唤读者去填充和确定。
又如《枣树的故事》结尾处这样描写:
岫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找老乔。正下着春天的细雨,空气湿漉漉沉甸甸,挤得出水,压得人心烦。仍然还是过去的门牌号码,远远地望过去,一切都旧了些。她没有贸然敲门,却远远站在那,举着伞,十分犹豫。一切都像预料中那样精确。老乔和夫人果然打着伞迎面过来,步伐悠闲,节拍合标准的慢。很显然,老乔已经看见岫云。当那伞与伞擦边而过,当那伞下的人本能地重心向外移,岫云的心口突然抽紧起来。她觉得老乔一定会停下步,扬起熟悉的手势。等老乔走过去了,又无望地觉得他可能会回过头来。那黑的雨伞忠实地保护着主人,钢丝骨架锃锃发亮,黑伞下老乔夫妇挨得更近更紧。眼见着到了门口,老乔让夫人照应伞,掏出钥匙来,门不重不轻地关上了。雨依然自顾自地下,岫云举伞的手有些酸。她想象中的自己已经跟进院子,登堂入室,名正言顺。……老乔的家就在眼前。岫云步履蹒跚,走向那熟悉的碰上和涂了漆的木门。她像读一本书似的,注视着木门的漆纹,注视着门牌上的阿拉伯数字,无形的手指戳向门铃的红揿钮。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转过身去,毫无知觉地往回走,无论哪条都是回那破旧简陋的小屋。儿子勇勇还躺在小床上,小铁床一翻身吱吱咔咔直叫……
这段结尾在情理之中,但是又出人意料,令人回味。女主人公岫云在失去了宝贵的人格、尊严和名声后加速了堕落的步伐,企图征服玩弄男人于股掌之间,甚至以征服老实人老乔为能事,而事实上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尤其是儿子勇勇患肾病企求老乔的帮助时,岫云虽然看到老乔看见了自己,但老乔却走过去了。这样的陌路之感恰是对岫云的一种讥讽。作品中虽然没有明确交代却由层层铺垫可以轻易地推断出勇勇是老乔的儿子。
另一种对“反高潮”运用的表现形式则是情节设计的偶然性。叶兆言把看来偶然的沿着时间先后顺序出现的事件进行精心组合,表现了事件发展的意外、人物命运的无常和死亡方式的奇异。它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叙述手法,也展示了这个可能的世界。作家所进行的这种探索不仅是对以往传统的继承,更是作家自己所进行的创新:情节安排并非遵循传统的因果律,而是一种作家自己的个人律。
以《我们的心多么顽固》为例来看叶兆言在叙事过程中对人物命运的设计是怎样主动出击推翻或是扭转先前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尽管这种选择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
开篇叙述主人公老四蔡学民对阿妍一见钟情,经历诸多艰难困苦虽然蔡和女知青谢静文有了肉体关系,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深爱着阿妍。后当期待已久的两人终于最后走到一起,蔡学民却发现与阿妍结婚之后的生活与想象的完全不同。“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⑤家庭生活空间的不如意、家人之间相互的利益纷争、性欲望无法获得满足、最希望有个孩子结果变成永远的奢望,最终无法忍受现实压抑的蔡学民一次次地将性的发泄转向其他的女人。
一个作者要想取得文本上的成功,他必须使文本与读者的预想不断出现矛盾并产生激烈的反映,也就是要留下与传统观点相悖的空白。叶兆言小说总是让读者的预想与文本产生矛盾,如反高潮的情节处理。故事在这里展开了一个细节,就是老四不断地带着不同的女人去做人流,次数多到他做医生的朋友感到厌烦。这个细节只是为了表明老四对阿妍的不离不弃。
随着读者为他们关系的逐渐稳定暗自庆幸时,小说又冷静地展开了另一个情节,当蔡学民发现在自己面前永远没有激情的阿妍与干儿子的性关系之后,不能生育又加上背叛丈夫,阿妍的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作者却让蔡学民选择了忍受痛苦而坚守爱情的阵地。这样安排是作者对芸芸众生及其生活的微讽,对生活荒诞意味的揭示。
小说中最具偶然性的情节是当蔡学民与阿妍在异地他乡相聚,面对对面楼上的大火两人紧紧拥抱泣不成声。且不管这是否是作家有意制造的一个神话,单单是两个饱经沧桑的夫妻最终重新相依相伴的结局便是对于爱情的一种独特的理解和阐释。
再如小说《别人的爱情》,以大学老师过路和女导演钟秋的偶然相识引出了和钟家有关的一系列人物,叙述中线索较多却不杂乱,每个人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其中关于钟夏的故事最具“反高潮”意味。
钟夏是这部小说中唯一的完美男人,他身上有着诸多美德,然而恰恰是这些美好的品质造就他的人生大起大落,因为信任下属而被人欺骗丢了官职直至坐牢,出狱后一无所有再创业,苦苦追求的陶红却成了小混混的妻子。他执著地追求着事业和爱情,命运对他总还不算太吝啬,他的事业逐渐蒸蒸日上,心爱的女人也逐渐接受他。就在读者为他高兴的时候,他的命运陡然逆转,忽如其来的车祸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者冷峻的笔触,一切都那么随意,仿佛没有任何立场,这是叶兆言惯用的叙事,作家的主体意识隐匿,使文本排除了激情,没有大爱与大恨的宣泄,没有对人物故事的品评,使作品呈现一种距离,一种多义的模糊状态。这可以说是作者的一种“故意”是一种叙述上的反高潮,这种故意是为了把价值思索归向于多元。
“反高潮”的情节处理,构成了叶兆言小说的召唤性,使人们既定期待视野与其小说之间出现了不一致。其作品的接受就可以通过对熟悉经验的否定或通过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层次,造成“视野的变化”。视野的变化体现了文学的功能,“阅读经验能够将人们从一种生活实践的适应、偏见和困境中解脱出来,在这种实践中,它赋予人们一种对事物的新的感觉……从而打开未来经验之路”。
新的文学经验赋予人们新的感觉方式,建立新的期待视野。这种反高潮的情节处理不仅能在感觉领域内具体化为对审美感觉的刺激,也能在价值领域具体化为对道德的召唤,向读者原有的道德观念发起冲击,且通过新形式突破人们日常行为。
作者简介:熊延柳,南阳理工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① 欧·亨利:《四百万》,陈华、何晓曦译注: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8:2。
② 王德威:《艳歌行!叶兆言新派人情小说(代序)》,见《叶兆言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5。
③ 张爱玲:《流言》,中国科学公司,1944:28-30。
④ 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大地出版社,1973:47-49。
⑤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度》,华夏出版社,2004:11-12。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