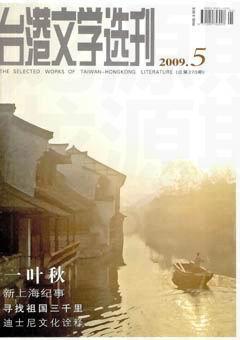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
我是一个从远方来的客人。每一回来到内地,不论是哪一个城市,面对的是我的朋友,或者是陌生的人,尤其是连媒体记者在街上碰到都跟我握手,听到南腔北调,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因为语言丰富的土地、方言多样的土地,一定会有比较多元的、比较复杂的,也可能会有比较激烈震荡的语言活力。这种活力在一个开放性较强的社会,或者流通性较大的社会,当然会伴随着大大小小的生活冲突而形成对这生活的观察和反省。
我就是依赖这种活力讨生活的一个人。今天就从近代中国一次巨大的语言活力萌生的背景上说起。
我们知道在上世纪初年,有一次非常大规模,而起码在历史影响上,我们自己觉得非常深远的一次运动—— 一个“五四”爱国运动。也因为这个爱国运动,稍早已经萌芽的白话文运动甚至还侵夺了“五四”这个符号,而为我们今天所从事的文字工作奠定了新的基础。白话文运动的细节,不容我在这里野人献曝。我这样一个“依赖语言活力讨生活的人”今天能够稍微谈谈的,则是在白话文运动——或称“新文学运动”之后,在现、当代文学本质上带来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重大影响。
到今天为止,包括在座有我尊敬的作家李锐,包括我自己,我们所写的是什么呢?大体而言,是小说。是什么样的小说呢?一方面,从语言最表面的特征上看,我们以为我们写的是“现代小说”,这是有别于印象中六朝志怪、唐人传奇,也不同于历代文人于公牍私启之余撰写而成的笔记故事。这些老古董,至少在轮廓上是用旧式语符连缀而成的,是用文言文写的。
撇开文、白差异不说,从另一方面看,即使是宋元话本乃至于连篇成套的明、清章回故事,大致已经是语体之作了,似乎也和今天我们所写的、而且称之为小说的东西迥然不同。形式、情感、主题、结构,但凡有关叙事的一切质素,两者都不一样。
我——还有今天也在现场的李锐、蒋韵,以及千千万万不在现场的华文作家——过去近百年来究竟在做什么呢? 请容我提出一个根本的疑问:我们是不是都在用汉字写西方小说呢 ?
或许,当我们在使用白话文、语体文的同时,已经自动接收了正好就是在新文学运动同时大量输入中国的西方叙事传统。“现代性”这个词的意义,可能更大程度地在我们的小说之中,成为一个被辨认、被理解、被认同,以及被模仿而传承的特质。
为什么我说是用汉字写的西方小说呢?首先请看:我们都是个别的作家,而个别作家拥有他个别作品的创作权。光是这一句话里的两个元素——我的作品是出自“我”的“创作”,这就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而且是纯粹西方输入的概念。当然,所谓“特质”还不只如此,更多可以解析的,譬如说:在我们惯常书写的作品之中,往往会出现大量心理的描述,用以“深化”、“支撑”、“体现”我们在过去传统小说里常看到的动作性的细节,作品不再满足于戏剧性的张力或者是离奇的遇合,取而代之的是作品中的主人公几经人生的转折(或许尽管相当平淡)之后,对自己的处境、命运、性格或者是情感,有着非常大的转折。一般我们称这样具有启蒙色彩的转折为“神悟”、“顿悟”,一个词epiphany。往往在故事接近尾声之处,我们会看到一次主人公特别的发现——这种发现当然不是动作的,不是外在的,不是杀了仇家,娶了爱人,打败了敌人,获得了官诰而已,而是往往跟随着作者自己想要提出,或者是想要呼应的某种思想息息相关。
如果从这个书写上的异变看起,也就是从将近一百年间输入并成形的这个传统往回看,大概它和西方近五百年来整个小说的工业的发展,以及它的终极关怀是密切不可分割的——我暂时不提它,只在这里稍微点明一下。对我而言,我更关心的是,过去三十多年以来,我所从事的工作,是否根本上是一个误会呢? 姑且不细论在台湾,或者其他华人地区,有多少人读过我的作品,或者是听过张大春这个名字,他们是不是也误会了?大家说我是台湾小说家、中文小说家,是吗? 或许应该还我一个本来面目:我不过是一个用汉字写西方小说,而出生在台湾的中国人呢。这是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讲题——“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的缘起。
在大概四岁左右吧,我的父亲把我放在膝盖上,他是一个六尺高的大汉,总在把我安置好了以后说:“咱们来说个故事吧!”一说从我四岁、五岁、六岁,说到我小学二年级,说的不是一般的故事,说的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等大部头的章回,一路说下来。我记得上小学第一天的时候,我的父亲跟我说:“你已经是小学生了,今天庆祝你上小学,给你讲两回吧!”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讲的是《水浒传》开篇的两回。那天听故事的兴奋远超过我成为小学生的兴奋。
当这样的一个经验,从四岁左右开始慢慢地进入我的生活之后,我发现有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办法分辨,我今天听到的故事跟上个月听到的故事,甚至我今天早上和昨天下午的生活,说直了,就是那些故事会带来种种微小的骚动,形成某些轻盈的扰乱。故事的情节应该是源出于狭小不及七八平方米的起居室里,梦幻的场景却可以推拓到无限江山之外,而千古风流与万里刀兵却可以长驱而入,侵入我们眷村那一整排鼓荡着虫鸟之声的纱窗。
也许为了要理清这个错乱,我会刻意在回忆自己生活的时候,把现实掺和到小说里。梁山泊下,朱贵放哨箭的水亭在辽宁街巷口的五洲面包店,而大水寨就在几百米以外的长春市场。似乎是为了不让自己感觉在听故事以后,跟自己的现实生活产生错乱; 在这个动机之下,我让它定位得更清楚——其实却错乱得更厉害。让我们在这个错乱的起点上,进入今天所要讲的“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中的第一个传统。
第一个我要谈的是“史传”。过去大家都知道,它几乎是研究古代文献也好,或者是考古材料、器物的材料也好,只要回到古代,我们总习惯性先回到被书面语记载的史传,它是真的吗? 我一直以为是。
在我念大学的时候,进入中文系,我的第一堂课就是《史记》,老师从本纪往下讲,第一篇是《项羽本纪》。我的老师李毓善先生十分仔细地分析着项羽的身世、性格和种种遭际得失,以及他与刘邦的比较,阐释了作为一个悲剧英雄的诸般特质。可是在那一堂课上,我却受到了一个大震撼,原来我们一向以为足以相信、凭靠的史料,和我四岁、五岁的时候,那种混杂着想象、虚构和现实材料的故事情境并无二致。
《史记》如此记载:项羽被困于垓下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士,这时他留下了那句流传百世的名言:“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为了表现他的善战,还高声说:“你们看 !我一定要连胜汉军三阵,为了你们,我要突破重围,斩汉将、搴汉旗 !”而汉军则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发动合围,项羽的确做到了他所说的斩将搴旗,但是,之后再辗转退到乌江西岸,在杀了百数十人之后,项羽终于在绝望中自刎了。
接下来项王几乎是被分尸的。可是这一段经常让我纳闷。因为现场从高坡之上下来,到他整个军队被歼灭,他自己被分尸,这一整个儿的过程是在哪一个原始的材料上有记载呢?在汉武帝那个时代,司马迁靠着什么样的现场材料得知项羽说过那些话,做过那些动作?当时没有录音笔,没有摄影机,它是哪来的?我的老师说,这就是史家“操纵之笔”,这个对我来说是太不可思议的。司马迁跟我们这一行的人说来实在太像了。然而,这个《项羽本纪》绝对不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次“操纵之笔”。我甚至觉得当一个史家在描述历史现场诸般细节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实证,以“国史”如此慎重的载记,仍然允许史官运用各种材料,以及技法,来发动一个具有现场感、临即感的故事。所以我们的史传从最基础的表现上,就认同一个自我悖反的努力:以虚拟之笔还原现实。不管《史记》或者日后的史传里,到底有多少内容看似无根底、无来历,可疑,至少大约可以这样去判断,中国的史传是容许掺杂着史传作者的虚拟之笔的。
第二个对我来讲也一样构成震撼,而且有强烈影响的,来自于“说部”。不管是长篇章回,或者是笔记小品,包括《客窗闲话》、《子不语》到《三言二拍》、《聊斋志异》这一类的作品,不论是来自曲艺,或者是来自连伴奏乐器都没有的说白,说部大多分享着一种奇特的氛围。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的老师高阳,是写历史小说的一位作家。
高阳有一天喝了酒,喝得差不多了,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写小说,比不上人家讲书的,也比不上搞说唱的那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读了些书,能够掌握史料,功夫深的还能做些小考证;可是,我们实在不能跟‘人家比。”不能比说书人? 这种话突然出在高阳嘴里是不可思议的,对他而言,当代还有谁能跟他谈历史小说的表现艺术呢? 他本来是在吹牛的,吹着吹着,居然说起我们比不上说书人来了,接着他又说起扬州出了一个说书人。
他说那位扬州人有一天说书了,说的是《武十回》,就是《水浒传》里以武松为主角的故事。而且这个说书人特别有名的段子就是《狮子楼》——狮子桥前酒楼的一个简称。说书人把它简称为狮子楼。这就回到《水浒传》的文本。在文本里,武松杀嫂,为兄报仇,这一整个段落并不长。换言之,一个定本的《水浒传》,按照一字不漏地说,两三段说完。但是说书人有自己的门道,高阳所说的扬州的说书人,有一天坐在书场里,说:“今天说到这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他说到了武松一抬腿,要进狮子桥前酒楼,见西门庆,他能杀得西门庆吗? 各位去翻一翻《水浒传》,这一次说书人没停在回目分隔之处,他停在准备要钱的地方。就这样,今天不说了,要听明天再来。
说书人一回头到后台,来了个人,先拱手捧上一包银子,说我是你的粉丝,特别喜欢听你的武松打西门庆,可是我是个商人,我今天要赶到杭州去做生意,我去一天回一天,办一天事,共三天。你好不好给拖一拖,三天以后我回来了,如果能让我听到了武松杀西门庆,我再给你原样的一包银子。
据高阳说,三天以后那说书人惊堂木一拍,开场讲了,商人也回来坐在那儿——“话说武松登登登就上楼了!”这中间有三天的时间。高阳跟我说,你知道他怎么办到的?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你知道吗? 他说他也不知道。高阳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没有另外一个说书人,能知道这说书人是怎么拖过那三天的——也许我们还可以想象,但凡现场有其必要,某个说书人甚至可以丢本子拖过十天。可是无论如何这个说书人的活儿,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我就幻想,说不定说书人一回头到第二天一拍惊堂木,要上楼的时候,突然一抬腿,后面有人喊了一声“武二哥 !”
我在一本小说论《小说稗类》里面,曾经以李逵独劈罗真人为例。宋江派李逵陪着戴宗下山,中间就发生了枝枝节节的事,李逵去管闲事。我就纳闷为什么中间会冒出跟正文无关的段子?我回头想,这个罗真人,很有可能就是现在在我们台湾很流行的大法会主讲人。一场法会要开讲了,有各种奇诡的设计,会让现场观众产生类似法力幻觉的布置。比方说:活佛一进场,偌大一个体育馆顿时凉爽起来,没有人计较这是忽然把冷气开大的效果,还以为是活佛带来了满室清凉。这种大法会让我想起来:也许罗真人这个段子的来历或灵感,就是千年以前的某个说书人,对他周遭所发生的这种场面的一个小小的嘲弄,我们读到罗真人如何施展法术的时候,说不定就已经遁入《水浒传》的作者在第一度的生活经验里面所接触到的实务,而产生了一种同理可证之感。后世的读者只知道李逵脾气火爆,迁怒要劈罗真人,而真正的罗真人到底是什么背景? 早就已经失去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回到了说书人的身上去讨论一个叙事,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也就是跟刚才的史传略有不同的,是我认为中国的小说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作者,运用一个单一的文本,形成一个单一的创作所有权,甚至它跟个人创造、个性创造这几个形而上的概念,是无关的。它是你用,我也可以用,武林、江湖、门派、宝剑以及技击之术,通通是各代作者、讲者彼此分享的。
说部的作者一向不以为自己拥有或独断了作品的内容,也不以他人运用了自己的“创作”元素为忤,同时也不认为自己借用了前人或同行的文本作为材料就是什么抄袭剽窃。在这个我们姑且可以泛称之为“民间”的叙事场域里面,情节、人物、道具通通是可以相互流通而无碍的。
相互流通而无碍的作品是不讲究创作权的,“创作”只是个人融入一个巨大叙事传统的小小步伐。那么,会有人不甘心吗?会有人觉得:创作活动里的那个“我”,更应该被认识吗?也许,在不同身世、背景、价值观的书写者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关切。
这就引起我们注意到了第三个传统。中国小说或者中国的叙事传统里,还有一个我认为,多年以来没有被大家注意——也许注意到了,但也不把它当做是一个显著重要的领域:“笔记”。我所知道的台湾的史学界,在过去十年间,很多学者付出相当多个别的努力,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历代流传的“边际材料”——笔记。
当我们打开那些笔记,一定会感受扑鼻而来的酸味。说句不同于化学家定义的话:笔记基本上是“酸性”的产物。为什么酸呢?我们注意到写笔记的人,大部分笔记作者,我所读到的,要不就都是考场不得进取的读书人,要不就是公余赋闲的佐吏,要不就是退休致仕的官僚。他们能“文”,也就是有书写的能力。但是,在刘勰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第三》)以外,应该还有经书以外的内容,具有“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这样的性质。
笔记的作者可以议论时事,发表公共言论,不过,他们更可能处身于大历史的角落之中,撷取些“大叙事”(grandnarrative)所无暇顾及的琐碎。我曾经在一篇讨论笔记小说的文字里如此写道:“中国古典之中的笔记何啻万千? 述史者有之,论文者有之,研经者有之,记实者有之。异方殊俗之珍闻轶事者,辄笔而记之;骚人墨客之趣言妙行者,辄笔而记之;某山某水有奇石怪木者,某诗某曲有另字旁腔者,亦不得不笔而记之。王公贵族,是不免要入笔记的,贩夫走卒、妖僧侠丐也往往厕身其间,点缀着一则又一则动人心弦的人间灯火。笔记之庞杂、浩瀚,之琳琅满目、巨细靡遗,连‘百科全书一词都不足以名状。总的看来,笔记可以说就是一套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生活总志。”
然而之所以酸,乃在于这种生活总志与庙堂经典的旨趣不能相容——它是“野”的,也是“在野”的。这些写笔记的人都有两个基本心态,第一个要传。即使不能附会于庙堂经典,然而一旦成为文字,就有流传的机会,就有“为后世所见”的机会。
清人笔记里有这么一则,说的是康熙朝在京师有一群诗友,经常做文酒之会,他们是查夏重、姜西溟、唐东江、汤西崖、宫恕堂、史蕉饮等人。这些人聚在一起,常相互期勉:“吾辈将来人各有集,传不传?未可知;惟彼此牵缀姓氏于集中,百年之后,一人传而接传矣 !”这不仅仅是好名而已,恐怕正道出了借由书写而得以与史传主流分庭抗礼的一种期许。这和前面所说的民间说部,恰恰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撰写笔记的作者,往往希望借由笔下所记的故实,而得以名其人。然而,笔记作者还可能有不止于扬一己之名声于后世者的写作动机。我所谓另一个基本心态就是他们有在“史外立史”甚至于“史外造史”的企图。
我们知道在南宋,这个国度是很怪的,从康王渡江以后,准备定鼎南京,然而不到一年,就被轰到临安去。南宋在杭州有根据地,在温州也有根据地,在金人无暇统理管辖的许多小城市都还保有统治权,但到底它有多少领土,几乎可以说是不明确的。质言之:南宋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拥有多少国土的国家。可是北方呢? 金朝的统治者立国以后,就开始打一个算盘,他们认为要统治汉人,得用汉人那一套。所以金人大量起用没有南迁的士人,而且发展儒学,那一套儒学因为汉人历史正统的关系,所以到现在还必须依靠非常少数的考古材料去建构。
南宋既然是这样一个偏安的局面——老实说,说偏安都有点惭愧,应该说是“碎安”——可是却出现了许多笔记,在讨论、追忆、补述北宋神宗、哲宗的时候,就是北宋中期,文化活动最剧烈的时期,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我称之为“人人争说苏东坡”。苏东坡在他自己的时代,并没有为自己打造任何神话,反而是在他过世之后,他的弟子,他的弟子的弟子,以及渡江之后,南宋的诸贤不断地复制出来的一个具有辉煌、鼎盛的光环的伟大文教时代,有人也因此而发明亦发扬了一套“正统论”。
在我看来,甚至不乏像司马迁写项羽那种笔法的,安插一些情节,让这些情节归属于某一个伟大的人物。在此,让我们想起苏东坡 !
打从南宋开始,甚而一直到明人乃至清人的笔记,都还有新鲜出土的、关于苏东坡言行的笔记之作。这让苏东坡成了一个胡适之先生所谓“箭垛子式的人物”,但凡有不俗之见、特异之说,皆可归诸苏学士、东坡先生。为什么这样?在南宋学人或文人而言,是为了要重新塑造一个文化灿烂的故国,以维护自己这个小而碎的朝廷在文化正统上面的一点点优越感。我们在笔记上看到,这话是苏东坡说的,那话也是苏东坡说的,我以前非常喜欢这些故事,可是越想越觉得像集体舞弊,就是一整群在政治上携带着巨大失意和焦虑的读书人,在重新打造北宋文化想象。我刚刚举苏东坡的例子,是要说明集体的焦虑,或者是自卑,或者是不安,也极有可能透过笔记的写作传统,悄悄地撼动文学表现或者是叙事内涵的重大意义。
“史传”、“说部”、“笔记”,我分别说了三个词。这三个词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我产生对于中国小说或者是中国式的叙事传统的一个重新认识呢? 我要回到个人写作经验上说一个不足为奇的故事。
在一九九九年,我写了一半的《聆听父亲》,由于我儿子的诞生而停顿了,这一停大概到二O O二年,期间我的第二个孩子都出生了。大概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古典笔记,同时也在电台担任说书的工作。原本说的是前人或我自己写的长篇,像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以及我自己的《城邦暴力团》等等。
但是从二O O二年到二O O五年,我改变了策略。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早上写一则短的故事,或者是一篇小考证。差不多就是三千四百字,这个字数刚刚好够我每天下午在一个小时的说书节目里讲;上午写,下午就讲这三千四百字。这些稿子就扔在电脑里,再也没有回头看过,也没有要另谋发表之意。于我,这样的写作没有一丁点儿“借由印刷形式流传”的意图,可以说是养成了一个不发表的习惯。
这个“不发表”,犹如我先前说过的,是一种在说部里面的情态,不发表,就无所谓所有权,就无所谓智慧财产。已经讲过的故事、写过的文字,就是在风中流逝的话语,“它”不是“我的”。
我的说书,可以是一个随时制造,也随时丢掉的东西。我不要把它想成是什么“作品”。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传统,教导我不一定随时随地做一个拥有著作权的作家,做一个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奖牌上带回家的作家。我所继承的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提醒我,倘若我能够丢掉个人创作这一个概念,我可能就丢掉了很多在写作之外极可能困惑我、骚动我、烦乱我的东西。
我能不能丢掉打从十几、二十多岁我一开始写小说时就引领着我的那个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的腔调呢? 我不断地追问着自己:我能否回到一个说部或笔记作者的位置,不去和我所处身的当代阅读环境沟通和协议呢? 我“宅”在自己的书写状态里面——也可以说是“躲在家里面”,锻炼自己对所有繁琐细碎的古典知识做一点一滴根本性的爬梳和吸收。
可是我终于在人生即将走到五十岁上的时候——连我第二个孩子都上小学的阶段——我开始体会到:如果我不会去做那些整理中国古代许多没有名字留下来的小东西、小的段落,并且把它重新整编,使它们看起来可能还有一些作用的工作,那么过去二三十年来,我闯荡江湖,在台湾享有一点小小的名声就反而是一种浪费。所以接下来在《聆听父亲》之后,我做了一个更奇怪的决定,我写了一本书叫《认得几个字》,这本书就是教我的孩子怎么认字,讲“买卖”的“买”字、“练习”的“练”字、“背书”的“背”字,从语言学、文字学、声韵学这些看起来只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才需要教育的内容从头学起,想办法找一些小故事,让我六岁跟九岁的孩子能够有兴趣,能够听。
最后我想结束在两个类似笔记的故事上,来概括我写这本书的心情。这两个故事分别发生在上一次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发生在我自己的家里,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却显现了今天我所谈到的三个我所继承的叙事传统——有史传材料,有说部元素,也有笔记趣味。它不是小说,是两篇已经发表了的小品文,也是我的生活实录,却具现了我创作中最深沉的关切——
局
小兄妹把两条跳绳相衔接绑紧,从三楼梯口垂下来,上端压上一只绣花鞋,下端悬空,要让楼下经过而好奇的陌生人去拉另一端。我听见他们在布置这陷阱的时候低声说:“我们不要玩很可爱的游戏,要玩恶作剧才行 !” “对呀! 一定要玩恶作剧才行。”然而,家里面有谁是陌生又有好奇心的人呢 ?
过了不多会儿,哥哥来到我书桌旁边:“你要不要经过楼梯一下。”我说不要。“你要不要看看我们家出现一个奇怪的东西?”我说不要。妹妹走过来大声对哥哥说:“你这样讲他当然不会被骗呀 !”接着转脸冲我说:“你想不想被很软很软的鞋子打到头呢?感觉不错哟 !”
“我不是笨蛋,休想叫我入你们这个局。”
“入什么我听不懂。”妹妹说。
结果他们入了我的局了。通常这一招十分有效;当我希望他们学习某一个单字、运用某一个词汇、锻炼某一种句法的时候,总是先让他们听不懂我说的话,当他们觉得这个字、这个词、这个句子值得探究,甚至是大人们想尽办法,刻意隐瞒,不欲使孩子得以接闻的那种神秘知识,就一颗爆发的好奇之心而言,只有“沛然莫之能御”足以形容。
我随手扯张纸,画了个弯腰驼背的老人,驼曲之处特别画了个圈儿,告诉他们:这是弯曲的脊椎骨。妹妹自觉眼尖,说:“你在画奶奶吗 ?”算是吧?我说。
“局”这个字本来大约就是个佝偻之人的模样,不论是病老骨弱的生理问题,还是委屈难伸的精神状态,此字大约就是从体态之写实而来的。由弯曲、委曲而表狭隘、仄窄,似乎顺理而成章。但是我猜想几乎就在橐驼之义形成的不久之后,“拘限”、“囿域”、“范畴”这一个意义群也出现了,显然是佝偻这形貌能够引起的第一度联想所致。接着而来的便是“权限”。
在指称一个特定的行政单位,比方说前清的“外事局”、“文化局”;到今天的“刑事局”、“新闻局”、“教育局”……这都是从一个“分别和限定事权”的观念出发的。至于在中古六朝时代就已经出现的泛称“当局”,其“拘执”、“偏见”的语意就更值得一论了。
“当局”二字无疑从对弈而来。这个从汉代就开始运用的词汇一向是和“旁议”对立,而且总强调着一种眼界清明与否的差异——“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觉悟因傍喻,执迷由当局”。对于谁看得清楚问题、谁看不清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几乎有一种宿命的成见,认定“博(下局去赌)者无识”而高见反而来自局外,结构中人不能自反而缩,远见也好,洞识也好,都不能从酱缸里捞取,而得靠旁观、靠异议。
“局”安的变化尚不止此。正因为“拘限”、“范畴”以及“权限”,使得它还具备了“按照一定规则从事”的意义。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大名著《百年孤独》里,那个元气淋漓的老布恩迪亚不喜欢下棋,因为他觉得“定了规则的游戏还有什么好玩儿的?”所以棋局、赌局、政局、骗局之同质者在此——都是设计出一套使人认真经营、以身相许的规矩,不自外也不能见其外的游戏。
这一天,我说了很多“局”,小兄妹一直耐心地听着,不时看看纸上那个奶奶,似乎对于“局中人”流露出些许的同情。但是,妹妹的结论很直接,她挑起双眉,指着楼梯口垂下来的跳绳握把:“你要不要去拉一下 ?”
橘
已经过了橘子结实的季节,再想要闻到新剥绿橙皮的刺鼻香味,还得等上好几个月。孩子无意间的一个玩笑,让我怔怔地忆起那香味,好半天回不过神来。那是因为张容在应用“入局”这个字的时候,说的是:“张宜! 我要设计一个橘子让你进来倒大霉。”
“橘子那么小,我怎么进得去呀?你真笨 !”张宜笑着跑开了。
我尽可能摆脱了对橘子香甜滋味的怀念,在一旁插嘴了:“是有人能跑进橘子里去的故事,你们都过来。”
那是唐代牛僧孺所写的《玄怪录》里的一篇《巴邛人》。这个巴邛地方的人,不以姓名传世,我们只知道他的家里有一片橘园。一年秋霜之后,橘树结满了果实,大多形体如常。个中却有两只大橘子,每一个约有容积三斗的瓮那么大。巴邛人十分好奇,便叫人上树摘下来。
说也奇怪,那么大个儿的橘子,居然和一般的果实差不多轻重。剖开之后,每橘之中出现了俩老头儿,鬓眉皤然,肌体红润,四个人两两对坐,正在下象棋呢。老头儿们身长只有一尺多,对弈之际谈笑自若,橘子剖开之后,一点儿也不显害怕,依旧相与决赌。
赌完了,一个老头儿跟战败的对手说:“这一局,你输给我海上龙王第七女髲发十两、智琼额黄十二枝、紫绢帔一副、绛台山霞宝散二庾、瀛洲玉尘九斛、阿母疗髓凝酒四钟、阿母女态盈娘子跻虚龙缟袜八緉,后日到王先生青城草堂还我。”
另一个老头儿接着说:“王先生答应要来,竟等不到——说起这橘中之乐,还真不亚于商山呢! 可惜不能够深根固蒂,被个蠢东西给摘下来了。”
又一个老头儿说:“我饿了!来吃点儿龙根脯罢?”随即从袖子里抽出一枝草根,方圆约可寸许,形状宛转,像一条比例匀称、具体而微的小龙。这老头儿说时还真掏出一把刀子来,一刀一刀削着那龙草吃,而“龙根脯”随削随长,也不见消损。吃完之后,老头儿忽然喷了一口水,把那“龙根脯”噀成一条巨龙,四个人便一起骑乘而上。但见脚下的白云泄泄而起。须臾之间,风雨晦冥,转瞬即不知所在。巴邛这个地方的人都说:“这事儿传了几百年,可能原先发生于南北朝末期的陈、隋之间,但不知真确的时代而已。”
故事里始终没能出现的王先生之所以姓王是有趣的。“王”字不消说是统治者的代表。这是为什么其中一个老头儿会感叹“橘中之乐,不灭商山”的缘故。
“商山四皓”是一个常见的典故。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四位秦博士,原来都是那个好侮慢读书人的刘邦所不能罗致的名贤,长年隐居在商山之中。却因为张良的建言,由吕后“卑辞厚礼”地征聘,成为保护太子刘盈的羽翼之师。这是汉初政局初获稳定的一个关键。
但是《玄怪录·巴邛人》的故事却用两颗大橘子讽刺了这四个老人的隐士面目:原来再孤高的隐者都还是能罗致到“局”中来逞一逞对博之势,并获取相当乐趣的。“橘(局)中之乐,不灭商山”就是这样一个感叹。质言之:如果不是经常冒着被贬逐杀戮的危险(“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愚人摘下耳”),又有什么好隐的呢?
你从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人类生而就注定是局中人,争胜、争强、争名利、争是非,争一切可争之物——而所谓“隐”,几乎要算是不正常的了。
例句:张宜:“好! 现在,为了父王的荣耀,我要发动连环攻击了!攻啊——半瓶醋小叮当来了!”哥哥这时纠正他:“是半瓶醋响叮当!” “明明是半瓶醋小叮当!你不要乱讲,以为我不知道……”
我始终觉得:作为一个占了小说很多便宜而能写作的作者,既然继承了许许多多的教养,我总得找个志业来继续从事吧。甚至可以这样说,借着我对中国叙事传统小小的粗浅的理解,以及我自己的感受和觉悟,我觉得许多写小说的人,可以不见得完全放弃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而是多一步回头审视一下曾经滋养过我们,并且一直处于和其他文本相互分享状态之中的这些笔记、说部,以及偶尔或者经常会撒谎的史传。当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过一遍”这些琐碎,才能确认我们是不是能说自己故事的人。
或者,我们根本一直就在远方呢 ?
(本文初稿由楼伟珊记录整理)
(本辑均选自台湾《印刻》2008年第4卷第12期)
·责编马洪滔 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