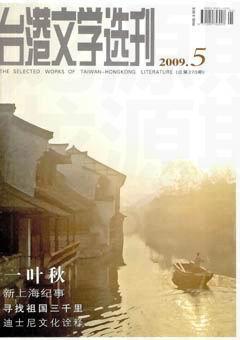穿越时光的回响
安鼎岙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形象的确立,台湾进一步掀起一股投资、移民上海的热潮。据两岸统计,2000年在上海台商约三十万 ;截至2005年,上海的台商已逾越五十万 。“上海的快速发展,成为淘金梦的新乐园。” 与此同时,“台湾人在上海累积的时间与人数” ,①也渐次成为台湾作家笔下上海题材的来源。2000年后,台湾知名报刊《联合文学》、《皇冠》、《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等,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上海的散文、随笔,尤其《联合文学》、《皇冠》、《中国时报》还推出了多篇以上海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作者都拥有多年在上海生活的体验,内容上握扣台湾人在上海的竞逐打拼、爱欲情迷、沉浮沧桑,手法上多客观写实,并能穿越台湾人在上海鲜华、风光的表面,进入其内里或绵软纯一或纠缠辨证的深处,对台海两岸分离半个多世纪、大陆改革开放约三十年以来,台湾人在上海种种复杂的社会心理进行历史的叩问和思考。因此作品一经刊出,即受到文坛不小的关注,著名作家李昂将此誉为新世纪“台湾文坛最特出的现象”。②
囿于资料,2000年以来笔者就管见所及,迄今能够读到的相关作品不少,印象深刻的为五篇小说。其中成英姝的《上海迷宫行》想象大于写实,本文暂并不列入评介范畴。
张蕙菁的《和平饭店》最早连载于2001年7月6日至10日的《中国时报》,后又入选台湾九歌文库《2001年小说选》,《台港文学选刊》2004年第9期转发。小说讲述了一个叫查理的台湾企业干部,受公司委派到上海去收拾日益凋敝的残局,尽管前后只有两次,而且每次停留的时间不长,但是上海日新月异的面貌、勃勃生长的商机,令他震撼不已。查理在上海,不计个人得失,大刀阔斧精减冗员,然而他回到总部后,公司并没有再给他赴上海续职的机会。他也没有自己再回上海创业的打算。可是,查理在台湾,“和所有人聊起上海,便说那里是下一波经济发展的焦点,市场太大了,到处是机会,先前去投资的现在开始回收,现在不去就迟了”。小说还设置了两个细节:一个是查理第二次离开上海前,为了俯瞰全上海,登上了“全中国最高”的建筑——八十八层楼的金茂大厦;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位蜘蛛人,“他原来只是去参观大楼的,突然毫无预警地,他脱下了外套……”“一个钟头后他攀抵楼顶,被公安带走。他泪流满面地告解,为自己的违纪行为懊悔。”“夜里查理在旅馆的房里看完那段新闻报道,(却)默默地将电视关了”,那时“他的心理也充满了蜘蛛人的虚荣。”但这个人物也有另一面:“查理在上海只待了不到两个礼拜,却去了和平饭店五次以上。每次都是晚上去,去听老年爵士乐”,而查理却是个音乐的外行人,“老实说,他的生活如果少了这些音乐电影之类,搞不好连他自己都不会发觉”,查理受感动受吸引的是和平饭店的“气味”,因为 “上海一年一个样,每天早上它又抛弃了昨天的预言。只有和平饭店守着它的老迈,它的爵士乐还会在上气不接下气当中吹奏下去。”整个结构,作者采用蒙太奇叙事,情节交错推进,于人物心理的时空变换之间,抽丝剥茧般逐渐引出对台湾人“新上海热”中之非理性的冷静思考。一方面,作者肯定了蓬勃成长的现代化大上海中孕育着多种多样的发展机会,表达了对台湾人普遍到上海谋求发展的想法的理解,另一方面,借主人公不断的追忆、上和平饭店,同时又暗示出上海在深厚的历史和崛起的新锐之间也是充满了挑战性,不是那么容易征服的,“有成功,就有失败”。作者多年在上海台资公司负责,感受自然非同一般。从而,它不止针对台湾的上海热,也对大陆广大的同胞注入了一剂清醒剂,发人深省。
《十八香》系一长约四万多字的中篇,见《皇冠》2004年3月号,并被列入当期“推荐小说”,作者符芝瑛。该小说主人公名叫季林,任职台湾一家较大型公司经理,事业顺遂,家庭、感情一向平平稳稳。后因公司到大陆谋求发展,而季林“业务娴熟,加上带点亲戚关系,比较可靠”,小老板征调她到上海去筹备新公司。在人生地不熟的上海,秀林殚精竭虑、黾勉从事,历经八个月的艰苦拼搏,新公司终于如期在上海风光成立。但是,鲜为人知的,秀林赢了事业,却搅进了一段暧昧不明、似有若无的情愫;讽刺的是她在台湾的“后院”也“失了火”,老公同时卷入了婚外情。这个小说看似十分通俗,其实却深刻表达了作者对现代社会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强调所谓精彩人生而遗忘了传统伦理美德的一种忧伤。由于全球化,西方情欲泛滥的影响无远弗届,古老的、诗意的东方价值体系一天天走向式微,人类泊靠的家园也逐渐受到挑战。但是小说到最后,作者写道,秀林当下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回家吧!”秀林的姐妹淘阿珍,经历过十几年的青春轻狂,也开始收心“想结婚了”。作者对未来仍然葆有自己的理想。
《敢问马大嫂》和《插队》两个短篇小说作者都是章缘,最初分别发表在《联合文学》2006年第9期和2009年第8期。《敢问马大嫂》叙写了一个随家从美国到上海来生活的、夫姓邱的闲太太,学说上海话,也能尽力适应上海的习俗人情,但是由于种种的误解,往往给自己造成莫须有的焦虑。《插队》中心人物叫彼得汪,曾经在美国留学、工作十年,表面看上去一切顺顺当当,实际上却备尝艰辛和寂寞。后因受雇于一家台资公司,彼得汪来到了上海,出乎他想象之外的,由于精通英语和同时是华人,这种双重的背景立即使得他光芒四射,不仅普遍受到上海本地人的看好、西方人的尊重,而且离弃过他的一位美籍犹太女子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这种前后径庭的对比,深深刺伤了彼得汪敏感的心弦。终于有一次在多喝了点酒失控之后,彼得汪面对一位自以为是的英国佬,他的愤懑、苦楚、委屈像火山一样喷薄而出。两篇作品实际上都在探讨一个困扰华人或台湾人许久的身份问题。相对于“差异性”,就人来说,“身份”是人在组成社会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③按照英国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的看法:“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又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做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④ 《敢问马大嫂》中的邱太太,雇了一个本地钟点工马大嫂,帮她“买小菜、汰衣裳、烧饭”。在家她是主人,马大嫂是客人;走出房子,她又成了客人,总是受到本地人的注目。由于身份不断地转换,最后邱太太自己对自己“是什么人”也模糊了。“夜深人静时,她戴耳机闭着眼睛”,“问一大堆私人问题”:“假如侬是上海人,吾就是台湾人,假如侬是中国人,吾还是台湾人……错了错了,吾实际上是美国人,华裔美国人……”混乱、尴尬,心里“觉得毛毛的”。《插队》里面,彼得汪更清楚意识到,当本地人高攀他的时候,那并非因为他是“汪”,而是他是美国人“彼得”;当外国人赏识他的时候,相反同样也不是因为他是“彼得”,而是“关系,各种关系”。这样,彼得汪一直不停地总在“插队”,身份没有定所,处在焦灼之中。
可以说,不同的作品,作者都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不同的观照。相近的题材,思考的问题却各有关注的焦点。而有趣的是,这些新上海纪事,相较于对祖国大陆其他地域的书写,台湾作家笔下的上海台湾人,共同拥有一个相似的特征:无论生活或工作,在上海的台湾人大多为居住者,已若明若暗地融入了上海社会,而非如到内地别处去的观光客的姿态。《十八香》中秀林到上海以后,“不知不觉中,秀林这几个月好像快被上海同化了,讲话变得直来直去,生机勃勃”,“回到(台湾)公司述职,同事七嘴八舌问她上海生活怎么样,还有人说她越来越像大陆妹,连口音都不太一样了。”
思想者爱默生曾说:“哪里有美好的事物,哪里就是他的家。” ⑤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对于彼岸台湾人以及全世界,都以她的“美好的事物”,彰显着独特魅力。
①②见李昂《想像台湾》,载2002年台湾九歌出版社《“九十年”小说选》。
③转引:钱超英《身份概念和身份轶事》,载2000年第2期《深圳大学学报》。
④见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罗岗、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208页。
⑤转引:刘再复《新哥伦布的使命》,载2004年第10期《台港文学选刊》。
——近自然造林开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