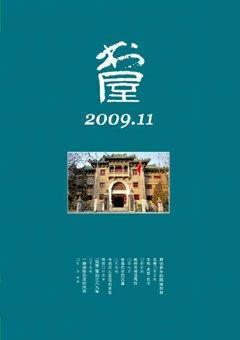红楼漫论(五题)
徐振辉
对宝玉的“多称现象”
顽石玲珑认未真,各将褒贬称斯人。
入山远近高低视,方识千姿万态春。
一个人生在特定的环境中,家庭成员和社会上各种人对其都有个称呼;当这个人成为各种人关注的焦点时,人们凭各自的尊卑亲疏关系和情感程度,作出多种称呼,我们可以名之曰“多称现象”。生在贵族大家庭中的宝玉就有这种“多称现象”。对他或詈斥,或嘲谑,或尊崇,或俏骂,其称呼大多以比喻表述。作家通过“多称”特指的语义符号,既反映各种人际关系,又展示人物内在精神的多重组合。
“多称现象”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描写中是少见的。《水浒传》中及时雨宋江、智多星吴用、霹雳火秦明之类的绰号,只能让性格行为定格在一个层面,即使有多重性格的人物也只能以一个诨名限定,如黑旋风李逵、豹子头林冲等等。所以“多称现象”不同于人物的绰号,它包含了性格精神的多种寓意。
宝玉在家长口中是什么样的特殊称呼?“畜生”、“蠢物”、“孽障”、“混世魔王”、“祸胎”、“呆根子”,这些称呼既有疼爱之心,又有恼恨之意,足以画出宝玉“行为偏僻性乖张”的傻狂形象。
在仆人眼里宝玉是“小祖宗”、“爷”,在众清客眼里是“我的菩萨哥儿”,袭人称他“皇天菩萨小祖宗”、“呆根子”(显然是种昵称),玉钏称他“凤凰”,赵姨娘称他“活龙”,园中老婆子竟称他为“老人家”……这样富贵尊荣的公子哥儿,只有用最崇敬的比喻来称呼了。
最有意思的是黛玉对他的一种称呼——“我命中的天魔星”,她对宝玉交织着又爱又恨又怨的复杂感情,这与贾母说他们“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含义是一致的。
在诗社为每人起别号时,宝钗给宝玉取名为“无事忙”、“富贵闲人”。他还有个别号叫“绛洞花主”(周汝昌先生从戚序本上考证出“主”应是“王”)。这些别号倒是宝玉的真实写照,不夸大褒贬,稍有讥讽,俗中见雅,宝玉也乐于接受。
对宝玉的“多称现象”不是小说中的孤例。贾母在众人眼里也有各种称号:多数人称她为“老太太”,刘姥姥称她为“老寿星”,凤姐称她为“老祖宗”,僧尼称她为“老菩萨”,都能切合身份,措辞得体,各尽其妙。对凤姐的称呼,也同样颇具特色。所以,《红楼梦》中“多称现象”可以说是人物的多视角展示,宝玉、贾母和凤姐的多称,正是他们在大观园中处于众星拱月的显赫地位所致。
上述的“多称现象”,实质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系统。俄国符号学家洛特曼说:“一个语言符号如果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使用得长久了,它就会结合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许多历史文化背景,就成了一个文化的语码。”对宝玉的“多称现象”,我们的确能看出《红楼梦》的一些历史文化背景。其一是浓厚的佛教色彩。“畜生”、“孽障”、“菩萨”、“魔王”、“冤家”等都是佛教名词,这种宗教观念千百年来已积淀在人们的深层意识之中,佛教词语与汉文化词语已融为一体了。黛玉所说的“天魔”,为欲界之王,其率无量之眷属,常障害修佛道之人。从这个称呼中也可窥见宝玉形象的某个侧面。其二是对族权的无尚崇敬。“祖宗”之称,正是封建宗法社会权力至上的一个象征,在贾府只有贾母和宝玉能高居此地位。其三是对神话传说的敬畏心理。如称呼中的虚幻现象“龙”、“凤凰”。从这些历史文化背景上多侧面地描写人物,正是作家天才创造力的表现。当然,人物如果缺乏丰富的个性和复杂的精神内涵,就不会出现“多称现象”,也不能深刻展示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了。
念佛语言符号化
念佛村婆万谢恩,老尼口舌污空门。
潇湘一语卿休笑,多少惊魂伴泪痕。
佛教从东汉时从印度传入中国,至宋、明以后,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并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
本文所说的念佛指口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意为无量寿、无量光,是大乘佛教的佛名,为佛教宗派之一的净土宗的主要信仰对象,信徒专念“阿弥陀佛”名号。《陀经》说,念此佛名号,深信无疑,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后来所谓“念佛”,多指念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名号。由于这是最短最容易受持的经咒,所以这项修行方法简单易行,中唐以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流行。唐代有本笔记叫《宣室志》,内容宣扬佛法,说到“群鱼俱呼佛号,鸡蛋亦喊观音”,证明生灵皆信佛教,反映中唐时自皇帝到士夫,从官宦到百姓信佛的盛况。明末净土宗的莲池大师说:念一佛名,换彼百千万亿之杂念也。指出念佛的作用可以排除妄想杂念,是断绝烦恼的最快速的方法,一直坚持下去,便达到“即念即空,居然本体”的禅境。这是《愣严经》中的重要观点。
从《红楼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清代的佛教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刘姥姥说他们那里庙宇最多,可见在农村佛教也很盛行。作为贵族家庭的贾府,为了贾妃省亲,专门聘买了十二个小尼姑,还在大观园中建了个栊翠庵;办秦可卿丧事,请了一百零八个和尚做斋事,灵柩还停厝在庙中。另外,僧俗之间常有来往,甚至还有感情纠葛。
佛教对社会的广泛深入影响,必然会反映到风俗习惯、文化心理及语言习惯等方面来。尤其是本土文化对佛教词语的吸收更为突出。《红楼梦》的主旨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所以字里行间到处见到梦幻、孽障、轮回、禅关之类词语;而像“无中生有”、“无我”、“缘分”、“天网恢恢”、“一尘不染”等词,已融入了汉语词汇,人们在使用时似乎已忘了它们的佛教文化源头。
小说中用得最多的佛教词语是“阿弥陀佛”。这个词的使用可以看出几个特点:首先,用此词语的都是女性,她们不分贵贱、老幼、文野,从中尤可看出佛教对女性的深刻影响。其次,阿弥陀佛的涵义极广,如表示惊叹、感佩、喜悦、庆幸、遂愿、委屈、罪过、无奈、虚饰等等,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汉语词汇能有如此的多义性和含混性。一个外来宗教词语的符号化,造成内涵无限延伸的有趣现象,是中外文化交融的一个生动例证。
《红楼梦》中写到念阿弥陀佛的人至少有近二十个,念得最多的是刘姥姥。她到贾府,见周瑞家的答应为她引见凤姐,就不住地念佛,见到螃蟹宴如此靡费也念佛,听到宝玉说若玉这样的人虽死不死也念佛,“阿弥陀佛”成了她表示感激、惊叹、醒悟等众多意思的口头禅。贾府送了很多东西给她,“平儿说一样刘姥姥就念一句佛,已经念了几千声佛了”。一个乡下老妪的朴素、感恩,似乎只能如此表达了。
而出自空门的老尼净虚却是口中念佛,心存歹毒,她求凤姐破坏了一桩婚姻,从中牟利,结果害了一对男女的性命,“阿弥陀佛”在她嘴里只是个掩盖罪恶的幌子。《西方确指》中觉明妙行菩萨说,念佛最忌讳的就是夹杂。夹杂,心就不清净,不是净念了。而净虚之作为竟是不净不虚之勾当,确是有污空门。
令人好笑的是黛玉也爱说此佛号。一次宝玉与她嬲笑时突然头疼,她说:“该,阿弥陀佛!”当宝玉病危转安时,她急忙念了声阿弥陀佛,还受到宝钗的嘲笑。黛玉并不信佛,念佛只是一种口头禅,意在表达难于明言的复杂情感,因为“阿弥陀佛”已经语言符号化了,已经渗透到她的潜意识之中了。
杀风景:诗情画意的颠覆
晒裤花间足污泉,焚琴煮鹤更痴颠。
若无画意诗情伴,享尽荣华也枉然。
“杀风景”是个俗语,意思是有损美好的景物,败人兴致。李义山《杂纂》卷上举例十二则,曰“花间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却垂杨”、“花下晒裤”、“游春重载”、“石笋系马”、“月下把火”、“妓筵说俗事”、“果园种菜”、“背山起楼”、“花架下养鸡鸭”等。另一说为“清泉濯足”、“松下喝道”数种。古人的审美观念有别于今人,但基本精神还是接近的。冯梦龙辑的《笑史》有“不韵”一卷,所载的亦和上述“杀风景”的事例类似。如《沈周》篇:苏州太守求善画者,左右推荐名画家沈周,太守便出传票把他拘捕来,并让他立在侧屋中作画。沈周画了幅《焚琴煮鹤图》以进,太守说:“亦平平耳。”焚琴煮鹤即是鲁莽庸俗的人对美好事物的摧残,沈周讽刺太守毫无文化素养,太守仍懵懂无知。
诗情画意和杀风景其实是事物美与丑、雅与俗之两端,小说描写真实的生活和人生,作者的理想和美学追求,势必描写这些内容。《红楼梦》第二十四回,有个老嬷嬷来传凤姐的话说:“明日有人带花儿匠来种树,叫你们严禁些,衣服裙子别混晒混晾的。”这就避免了“花下晒裤”式的不韵。凤姐虽有些粗俗,不比大家闺秀,但在内务管理上,还不乏尊贵与文雅。
《红楼梦》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世界,其中很多美好的人物与景物可以入诗入画,如葬花斗草、折梅抱瓶、隔墙听曲、月夜品笛、赏菊持螯等等。但是,也有很多杀风景的人和事,且举数例:
造景勉强。在观察大观园一处茆堂时,贾政认为是天然景象,宝玉大发议论道:“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此犹“背山起楼”也。
园中斥子。宝玉在大观园为景点题名,面对如诗似画的美景,他吟出几副韵味悠长的对联,然而贾政全无褒扬之语,屡屡斥为“畜生”、“无知的孽障”。此犹“松下喝道”也。
骚扰美色。凤姐走在大观园,见“黄花满地,白柳横坡”,边走边赏幽情雅致,藏匿在假山后面的贾瑞突然拦住,搭讪着说些肉麻的话,不堪之致。此犹“花下晒裤”也。
草包胡扯。薛蟠把唐寅画上的署名说成“庚黄”,宝玉纠正后他笑道:“谁知他‘糖银‘果银的。”云儿唱曲时他胡乱插嘴,轮到他行酒令时满口脏话。此犹“妓筵说俗事”也。
情种蠢举。刘姥姥胡编了一个漂亮女孩雪里抽柴的故事,宝玉信以为真,派茗烟去找,结果找到一位青脸红发的瘟神爷,化美为丑,令人笑倒。神话故事美在虚幻缥缈,硬要落实即是蠢笨之举。此犹“苔上铺席”也。
此外,“杀风景”的事例还有刘姥姥在省亲别墅旁内急欲便,夏金桂“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贾赦的蠢俗笑话等等。“杀风景”是文化素质和个人品格的缺失,是对诗情画意的颠覆,所以它是一种“反文化”,与诗情画意造成强烈的不和谐。作家借此对亵渎斯文者作鞭挞与喟叹,也让读者从喜剧色彩中获得快感。
上述杀风景事例,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撕毁,让人看到粗鄙俗野,产生嘲笑或感叹的喜剧效果。但是,也有的杀风景具有另一种美的价值:或展现人物之情性,或暗示主题之深意。前者如晴雯撕扇,反映其恃宠任性和倔强的个性;多姑娘调戏宝玉,衬托宝玉晴雯之间纯真的情谊。后者如刘姥姥醉后四叉八脚地躺在宝玉床上,显示富贵温柔必将为贫贱粗俗所取代。
笑话的改造
笑语精编妙一心,开颜捧腹佐千斟。
借来冰雪寒枝艳,化作梅花月下琴。
《红楼梦》中有好多笑话,大多是从生活中提炼而出,也有的是对现成的笑话加工改造,达到比原作更有趣味和思想内涵更深的艺术境地。
第五十四回凤姐讲的聋子看放鞭炮的笑话,源自冯梦龙《笑府·形体》,但比原作具体生动,而且完善了笑话结尾“抖包袱”的结构。“只听‘扑哧一声,众人哄笑而散了。抬炮仗的抱怨卖炮仗的做得不结实,没等放就散了”。这时穿插湘云的问话:“难道他本人没听见响?”凤姐说:“这人原是聋子。”这里突出“散了”这个关键词,显然隐喻贾府“树倒猢狲散”。
第七十五回贾赦说的孝子为娘治病而请婆子针肋条的笑话,是借鉴金天基《笑得好》中《心在肩上》,由原作的拳师教徒弟出手不能打人肩上,改为孝子与婆子的问答。孝子担心针到心上,婆子说:“不妨事,你不知天下做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作者让贾赦当着贾母说出如此露骨、蠢笨的笑话,对刻画其性格提供绝妙的细节。
从古代笑话中引发出新意,这是曹雪芹独具匠心的创造。第八回写黛玉到薛姨妈家,见宝玉与宝钗在一起,便含有醋意地说:“嗳哟,我来得不巧了!”接着她所作辩解说:“要来时一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很像是受了唐代艺人黄幡绰(小说第二回“奇优名倡”中提到他)的一则笑料。黄曾为安禄山圆梦。安说梦见衣袖拖至阶下,黄解为“垂衣而治”,安说梦见殿中槅子倒下,黄解为“革故鼎新”。后唐玄宗诘问他,他却说:“非也,逆贼梦衣袖长,是出手不得;又梦见槅子倒,是糊不得。”黄因人而作二说,黛玉也心口各有一套,机警伶俐如此,一语双关的话中有绵里藏针之妙。
宋代党进是个不学无术的武官,一次一个说书人见他,党问他说什么故事,对曰“韩信”。党即把他打了出去,左右问是何缘故,党曰:“对我说韩信,对韩信亦说我矣。”第六十五回兴儿向尤二姐介绍凤姐的险恶,尤二姐笑道:“你背着她这等说她,将来你又不知怎么说我呢。我又差她一层儿,越发有的说了。”这段对白可能由党进的笑话脱胎而来。原作并没有多大深意,而尤二姐的这段话,对刻画她的忧虑和坦率,揭示潜在心理,确是传神写照的化工之笔。
打破“话语霸权”
瓦釜铜钟听判然,污泥亦可出清莲。
心声如鹤排云起,各占风情一片天。
《红楼梦》既然在写人上打破“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传统旧套,那么在语言上也必然排斥好坏分明的简单化模式。
写“坏人”的假、恶、丑,并不排斥其语言中有价值的内容。这是因为他们在观察世间事物时也有真知,在人际交往中也有善言,只要人性尚未泯灭,其语言也有被人认同的可能。小说家安排人物说什么样的话,可以看做是一种“话语权力”,如果照好坏分明的脸谱化、简单化的人物塑造法则,必然会让“话语霸权”损害形象,曲解生活。在《红楼梦》中,那种“非好即坏”的两极思维已被打破,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多样化也打破了这种“话语霸权”。从这个角度看,小说的语言不仅是个技巧问题,也关涉把握和描写人物的真实性程度,以及理解和反映生活的深刻性程度。我们只要赏析一下王熙凤的语言魅力,就能领会这个道理。
第四回贾雨村判冯渊官司时,门子以“护官符”提醒,要他因私枉法。贾为此人命案思虑未决,门子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大道理”而行不通,在潜规则盛行、关系网复杂的社会中,确是官场要诀。门子虽是个“教唆犯”,但不能不说他“世事通明”,言之凿凿。
第七十五回写邢夫人之弟邢德全,他吃喝嫖赌,“手中漫使钱”,因此人称“傻大舅”。一次喝酒,他醉露真情,对贾珍拍案叹道:“怨不得他们视钱如命。多少仕宦大家出身的,若提起‘钱势二字,连骨肉也不认了。”这是他对金钱社会、达官贵人的真知灼见。第二十四回贾芸向他舅舅卜世仁借钱,卜很吝啬,但他告诫外甥的话也不无道理:“你只说舅舅见你一遭儿就派你一遭儿不是。你小人儿家很不知好歹,也到底立个主见,赚几个钱,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看也喜欢。”对年轻人也是有益的告诫。
李嬷嬷是个居功、自私、唠叨惹人厌的老婆子,然而她也有识人察性的眼力,话也说得尖锐泼辣。第二十回她斥怪袭人对她不敬,说道:“谁不是袭人拿下马的!我都知道那些事。”袭人虽有忠心、尽责的一面,但她打小报告夸大“敌情”,致使王夫人驱逐丫头、抄检大观园,造成几条命案,以及宝、黛婚姻的悲剧,袭人都难辞其咎。小说中只有李嬷嬷才淋漓痛快地揭其一生隐恶。
《红楼梦》不仅没有剥夺“反面人物”的话语权力,而且让他们的语言表现力更为增强,从艺术的角度看,他们语言的粗鄙化、生动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生活中不能因人废言,在小说艺术中亦当如此。铜钟奏大雅之曲,瓦釜也能鸣木铎之音,作家不能因对人物的道德评价而在语言设置上厚此薄彼。泾渭分明的“好人”“坏人”观,必然不能反映人物的全部真实性;如果认为这是一种“典型化”,那就是误解了现实主义的语言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