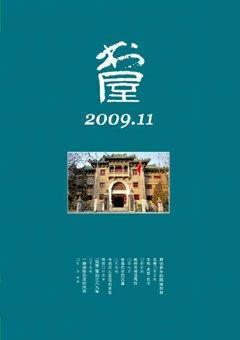畅销书闲话两则
雷池月
《蟹工船》的红火不是一种文化现象
2008年,日本十大流行词语中,竟然包括了“蟹工船”这样一个当代人根本不知所云的生僻字眼。这是因为年初再版了一本名为《蟹工船》的小说,该书上半年销量就突破了六十万册,到今年春天,发行数已累计百万册以上,高居畅销书榜首。小说的畅销又带动了改编的热潮,漫画版本销量达数十万册,由偶像派和实力派明星合作演出的电影也于今年夏天上映。上述空前火爆的形势自然在全世界产生了影响,首先是欧洲,《蟹工船》一书强势进入市场,被推为“working poor”的必读书目,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中国反应也颇快,译林出版社于今年一月就推出了中文版本,只是在学界和市场似乎都并未引起太大的动静,这一现象可以让人产生多方面的思索。
《蟹工船》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成名作,是一部反映劳动阶层的痛苦与抗争的书。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尚处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为了争取更多的外汇,兴起了捕捞并加工海蟹主供出口的产业,附有加工设备的捕捞船就叫“蟹工船”。海蟹产于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北方海域,那里气候寒冷,远离陆地,船工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非常艰苦,所招募的工人大多是赤贫且并无一技之长的临时工,由于船主和工头们的刻薄和残忍,船工们团结起来和雇主展开斗争——《蟹工船》所反映的就是这些船工们生活和斗争的一个断面。作品具备当时左翼文学最基本的特质,即通过揭露社会黑暗的现实来唤醒被压迫者的阶级意识,促进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从而推动社会革命的进程。
这部书为小林多喜二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可就在此书问世后不久,小林于1933年2月在狱中被军警拷打致死。当时世界左翼文坛反应十分强烈,纷纷表达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暴行的谴责和声讨,鲁迅代表“左联”发出的唁电在中日两国都很著名。由于1932年的军部政变后政治环境的险恶,《蟹工船》一书并未在日本继续产生影响,而战后日本进入了由所谓“神武景气”所带动的资本主义高速发展时期,劳资矛盾由于劳动者处境的改善而相对缓和,正如有位评论家所言:“日本人把蟹工船转移到国外去了,他们自己成了吃蟹的国家。”于是,小林多喜二和他的《蟹工船》长期地遭遇了冷漠甚至遗忘。
《蟹工船》在问世八十年后的今天大受欢迎,据说“最大的理由是日本的‘新贫人口从中找到了折射自己受穷的一面镜子”。“新贫人口”即指那些在当今西方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中涌现的极其贫困的群体。由于长期的不景气,业主越来越不愿意雇佣正式工,因为那要负担诸多的社会保险,不像临时工可以随时解雇,这和《蟹工船》里老板招募工人的情景十分相似。日本今天的临时工已占劳工总数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四点一),这些临时工被解雇以后,常常“流落街头,日食面包二个,在网吧过夜,走投无路,或因患病无钱救治而自杀”。《蟹工船》的读者大量的就是出自这个阶层,日本偶像作家雨宫处凛说:“《蟹工船》里写的与现在自由打工者的状况非常相似。”“现代打工者和《蟹工船》里的渔工在情绪上是相通的,他们的不满一样地集中在两个方面:工作环境的恶劣和管理者态度的恶劣。”年轻的读者反映说:“我很羡慕小说里工人团结一致面对敌人的做法”,“船上的工人都是我的兄弟,就在我的周围”。
有评论家指出,“蟹工船”的火爆彰显了日本从未有过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现在的“新穷人”生存状况有的还不如当年蟹工船上的渔工。这个说法或许失之夸张,但可以肯定一点,与《蟹工船》的红火密切相关的是,“新穷人”现象的恶性发展确实导致了日本政党生态的极大变化。以日本共产党为例,自上世纪中叶以来,面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连续繁荣,日共的政策一直左右摇摆不定,实力和影响日趋减弱,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低潮的到来,生存状态更是每况愈下。世纪交替之际,日本经济随着泡沫的破灭走向衰退,日共才终于获得了喘息和复苏的机会。到了此次金融危机,竟可说是好运连连。他们不失时机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站在维护穷人权益的立场,向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根治的各种社会弊病(包括“新穷人”现象)进行猛烈的揭发和抨击。日共的这个态度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底层群众的拥护,一年多来,《赤旗报》的订户逐月上升,每月平均新增党员一千五百人,党员总数已达四十余万。日共在国会的议席已经超过曾经是日本第二大党的社民党。社民党控制工会的传统局面也早已根本改观。所有这些都说明《蟹工船》的火爆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并非一种单纯的文化现象,它确实是当前日本经济、政治、社会诸多危机交相作用下,在文化这块屏幕上产生的鲜明投影。
左翼文学在取得主流地位之前,由于它所坚持的批判立场所决定,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程中,确实作出过重大的贡献。《蟹工船》一书的命运似乎也可以佐证这一点。但在取得主流地位之后,由于“工具论”之类的误导,在权力的干预下,左翼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往往产生质的变化。以我国的情况而言,就曾经留下过或者“假、大、空”,浑身虚胖(如大跃进时期);或者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如文革阶段)的史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政策的变化,出现了一段由批判精神引导的文学的繁荣,但左翼文学不仅未能高举批判的旗帜掌控话语主导权,相反听任自己被逐渐边缘化。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两极分化和劳资矛盾一类社会问题出现了,这本来是左翼文学可以大施所长的时空条件,但人们看到的却是它近乎失语的状态。想一想欧洲,曾经产生了多少表现资本家和工人这两大阶层各自的生存状况和相互间关系的作品和大师?而在我们这里,能拿得出一本真实地(不求其深刻地)反映这一当代最重要主题的书么?“富二代”和“农民工二代”之类新名词已经正式进入媒体和日常语言系统——产业工人做到“第二代”还被称为“农民工”,这叫什么话?这后面潜藏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能不令人忧虑吗?从前我们常说“蛋糕做大了,问题自然解决”,现在,“蛋糕”已经大了几十倍,而问题却还在继续发展并拖累着国家前进的脚步,只有因为丧失信仰而麻木不仁的官僚才会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关于资本反人性的本质,马克思早已明喻于前,今天,矿难和黑窑一类事件又佐证于后,有志于建设和谐社会的人,都会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可是,在这方面承担着特殊重要责任的文学呢,它在哪里?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包养着一支数量不小的文学大军,媒体上有时能看到他们听到他们在角落里嘀咕,说: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不能只有马悦然一个人懂汉语,只有委员会改组了,中国人才有希望获奖云云……
令自己难堪,让他人尴尬
尘封了三十多年的张爱玲遗著《小团圆》不久前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很是对书市造成了一些刺激。香港的情况最火爆,台湾就比较一般,至于大陆,则远不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倾城之恋》带来的那种震动了。海峡两岸比较一致的反应,其原因也大概相同:这本书的自传性质过于明显了。广大的张迷们喜爱的是张爱玲驾驭文字、描摹心理、营造气氛的能力,而不是她个人古怪的性格和荒谬的情感经历。《小团圆》的失败之处,就在于她坚持要把自己生命中理应努力加以遮掩的部分,充分向他人展现。她或许是希望读者能从纯粹的文学或审美角度给予她理解。然而这实际上是绝无可能的,因为在中国人有史以来的所有政治高调中,民族大义向来是被摆在第一位的。很多喜欢她的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涉及她个人往事的追索和评析,如今她自己竟直接走上前台来讲解,无论如何妙笔生花,那结果只能是:令自己难堪,让他人尴尬。
据说,张爱玲曾经交代她的遗嘱执行人宋淇,《小团圆》书稿要销毁。但这只是一句话,书稿一直保留在她本人身边。宋淇的儿子小宋(也已经年近花甲了)说,整理张的遗物时发现了这部稿子,由张爱玲本人工笔誊正,装订也很考究,足见作者并不真想毁掉它。小宋认为不该让这本书就此湮没,公开出版,不惟广大张迷能享受到阅读的愉悦,同时也算是完成了作者的遗愿。她地下有知,当为之欣慰。小宋先生的话大概是可信的,因为,他已经将大部分版税捐赠给了香港大学的某个基金会。那就是说,没有牟利的动机。
张爱玲堪称一代才女,除了情商有点问题,语言功力、艺术感觉都无疑可以让她置身于新文学重要女作家之列,只是还没有到达夏志清所认定的那样一个高度。她确实不能和鲁迅、沈从文比肩,有些研究者把她和萧红并论或作比较,其实也是很不相宜的——倒不是什么高下之分,而是两人差别太大。萧红是传统的(请看她是如何为端木蕻良忍辱负重)、平和的(既不是勇敢的斗士,也不是驯服的顺民)、良善的(她无负于她爱过的每一个男人);而张爱玲则是现代的(嫁与西人作妇当时仍属罕见)、偏颇的(只服从感性的支配而拒绝理性的思考)、冷漠的(除了男女间的一时苟且,举目世界何处曾寄托她永久的爱!)。作为一个作家,张的精神世界的某些缺失是致命的,这使她放弃了对所处时代最起码的社会担当,有时候甚至于是丧失了一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
龙应台指责张爱玲“冷血”,当否且不说,至少这个“冷”字一针见“血”!张本人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冷傲”,至于“冷漠”、“冷酷”以至“冷血”云云,这类对她常见的评价,都可谓“虽不中,亦不远矣!”她的“冷”,自然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她经历和性格相互作用的结果。她出生于腐朽而没落的清朝遗老世家,先人的煊赫早已随时光飘逝,后人的不肖则堪称“与时俱进”有增无减。从她懂事起,骄傲而敏感的内心,想必从未接纳过她那些病态的、浅俗的亲属,当然她可能也没有从亲人那里得到过情感的温暖。她有许多作品都使用了自己的家庭作为背景材料,以亲属做人物原型,但其中找不出一处细节或场景能给人带来光明、温暖或希望的感觉。她叫自己的母亲为“二婶”,形容自己的舅舅“像酒精缸里的孩尸”,亲属们这个吸毒,那个同性恋,还有她并无根据的对他人乱伦的猜想……这些揭露的后果当然很严重。早在她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以后便和亲人基本断绝了来往。冷漠从少年时代就渗透进她的灵魂深处。
张爱玲很早(不过二十岁)便走上了文坛,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她的才华吸引了许多崇拜者,而她却将崇拜者的胡兰成选做了自己崇拜的偶像。她知道胡兰成的汉奸身份,却让自己高傲的头在胡的面前“低到地底下去”。以她和胡兰成夫唱妇随的关系,她也是可以按汉奸治罪的。何满子先生就主张将她定性为汉奸作家。也是种种原因,战后他受到了宽大待遇(当时大汉奸金璧辉的男宠、某李姓伶人就曾被捉将官里去问罪)。1947年,总算和胡某离了婚,但也是明离暗不离。此时胡兰成如丧家之犬,生活无着,要依靠张爱玲的接济(对此张的解释是过去自己用过胡很多钱)。解放后,因为有柯灵、桑弧甚至夏衍这样的大人物罩着,张的情况还不错,不过经过“三大运动”之后,她也明白了此地不可久留,便跑到了香港。当时香港的情况不好,大量难民还在饥饿线上挣扎,何况她这种国、共两方面都无法投靠的人,生计更是艰难,于是于1952年去了美国。她的英文不错,可以进行写作,但想成为主流作家以卖文为生却绝无可能,只能找些资料员、管理员之类工作糊口。虽然她的才气在聂华苓、於梨华这些人之上,但生存状况却无法和他们相比。经济的困窘一直到她的书重新在台、港打开局面以后才有所缓解,而当时她连回香港办理出版事宜的机票钱都颇难筹措。在艰难的日子里,她的心境可以想见,大约除了以“冷漠”自励,以“冷傲”自慰,还有就只可能是对自己遇人不淑的懊恼,这种懊恼,用《小团圆》里盛九莉那悲凉的自况来表达,就是所谓“汉奸妻,人可戏(欺)”。
晚年的时候,张爱玲在两岸三地都已是暴得大名,但她的心却似乎已经由冷漠而归于冷寂,连追逐名利的本能都趋于麻木了。对于红颜才女,年华的老去和才情的消逝总是构成正相关的。而且,由此导致的萧索的心情和对外部世界的疏离感更是相辅相成。她越来越封闭自己,过着基本与世隔绝的生活。由于题材的枯竭,偶有写作,也局限于对早年记忆的搜索(如《小团圆》之类)。丈夫赖雅去世后,她身边没有亲友,以至于死在公寓里好几天才被人发现。回溯她的一生,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是个贴切的写照。
《小团圆》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主要角色都有原型可以对号入座。张爱玲当时的创作动机,就是要就自己的过去向读者(世人)作些说明。因为其时胡兰成出版的新书《今生今世》引起了台、港传媒的热议,张说她“不能让别人垄断了书写这段爱情的权利”,要“不惜打一场笔墨官司”。于是《小团圆》出炉了。她将书稿寄给在香港的宋淇,让宋联系出版。宋看完之后劝阻了她,因为宋觉得,出版此书,一是会给胡兰成制造更多的炒作机会,二是会令反日情绪高涨的台湾读者产生反感——他们不会接受张爱玲迂回表达的观念,那样一来,刚打开局面的市场就将前景难卜。宋的意见令张爱玲犹豫不决,《小团圆》就这样搁浅了三十多年。说要“销毁书稿”,那是在回答宋淇的诤言,但始终舍不得“毁”,因为其中有她自己很想交代明白的观点。
什么观点?不是民族大义,更不是政治正确之类,她不会企图把自己说成“曲线救国”的义士,也不会像陈璧君一样强辩“汪先生也是为了救国”。在书里,她其实只说明了一点,就是她在《色·戒》已经表述过的:一个女人被男人征服了(用她的原话,这征服是“通过阴道”进行的),从此,所有的伦常大义、是非标准于她就都失去了意义。她的这个表达应该是真诚的,但这毕竟只是她个人的观点。所以当李安在《色·戒》影片里对这点作出真实而充分的演绎时,并不为所有观众所接受,连台湾的中统老人也出来为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抱不平,说影片“玷污了爱国义士的英灵”,号召进行抵制。也许只有“易先生”(丁默村)才会从正面叫好——凭着自己超强的性能力,竟然让一个身负使命的敌方女特工甘心为我所用,对丁默村这个摧花辣手(他玩弄过的良家女子和娱乐明星不可胜数)来说,没有比这更令他惬意的事了。不过《色·戒》所取的是一种客观叙事的角度,作者和读者都可以见仁见智,匪夷所思的情节反而让广大张迷不会受到多大震动。《小团圆》就不同了,读者很快查找出角色的原型:盛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人们或详或略都知道他两人的故事,也知道胡兰成是个很龌龊的小人。所有爱读张爱玲的人,大概都不大愿意接触到张的这段历史,因为人们多半不忍心看到张被胡玩弄、欺骗和背叛的细节和场景。在胡兰成眼里,张的分量还不及另一个情人——流氓汉奸吴四宝的老婆佘爱珍,这不能不令张迷们痛恨和惋惜。而《小团圆》竟还要翻开沾满污渍的旧账本,披露作者的那份自觉的卑微的爱——你自己即使不觉得难堪,也应该想到“粉丝”们的尴尬。孜孜矻矻研究“张学”的教授对此只能毫无底气地解释:“小说就是小说,不能够在生活中对号入座。”多为难啊!此稿当年不毁,是失策了。
据说,张爱玲晚年曾有意研究丁玲。张一生眼界极高,甚至表示过不能接受冰心和她相提并论,何以会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和她完全不同的丁玲感兴趣?想必是发现了彼此相通的某个心灵的节点。这使我想起五十年前在大学资料室里读过的一本书,叫做《劳者之歌》(或《劳动者之歌》?),是三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合编集。内有丁玲作品《续莎菲女士日记》,讲述了她和冯达在南京时的一段恋爱故事(这本书和这篇作品解放后都未再版过,因此,读过此书如今还健在的人肯定不多了,但张爱玲应该是读过的)。冯达是个变节分子,丁玲和他相爱了,同居了。丁玲为自己的这段爱情所付的代价是很惨重的,从延安时期的“审干”到解放后的“肃反”、“反右”等历次政治运动,反复受到猜疑盘问、批判指责,冯达成了她一处永不能愈合的溃疡。她对此事一直保持着低调,虽然解放初期(自己刚获得斯大林奖金,正炙手可热)在被周扬逼急了的时候(竟公然在大会上就“历史问题”不点名地威胁),也曾挺身而出表示抗议,但终究不敢正面接招,再没有当年写《续莎菲女士日记》时的勇气。丁玲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和她为爱所承受的委屈,张爱玲想必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才会动了“研究”的念头,如果不是这样,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能把这样两个完全挨不着的人联系在一起。张爱玲和丁玲,情感遭遇或许有近似之处,后来的处置态度却迥然不同。丁玲懂得回避,尽管还是为此经历了无数的坎坷(虽然另有除此以外的诸多原因),最终却总算获得了盖棺论定的荣誉。张爱玲却不然,对于理应回避的往事,却偏偏不肯放下。我有时设想,她也许是忘记了焚毁书稿,而且又没有估计到自己的突然去世,那么,如今她若地下有知,恐怕就只能够喟然长叹:“小宋误我!小宋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