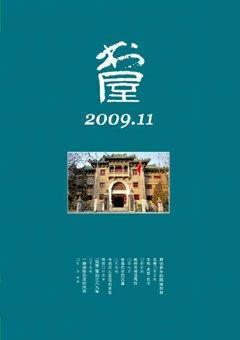穿越历史的沉重
吴增辉
日本人中野孤山百年前的中国游记《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今日读来仍能给人以强烈震撼。在这本小书中,初到中国的中野孤山具体描述了他从上海到成都沿途所见到的人情风物,呈现了晚清中国衰败没落的图像。书中细致描述了中国人状貌言行的猥琐及生活习惯的种种落后,居高临下地表示出对中国人不幸命运的悲悯,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优越感。
一
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连续的重大胜利使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迅速膨胀,现代国民意识迅速形成,他们相信日本民族已成为唯一可以与白种人分庭抗礼的黄种民族,而中国人则已沦落为一文不值的劣种。甲午战后,日本媒体进行了歇斯底里的宣传,把这场胜利定性为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意在通过对中国人的践踏抬高日本人的地位,从而使日本名正言顺地步入“文明”国家之列,拥有与西方“文明”国家同等的地位。在这种生为黄种人的自卑心理的驱动下,日本人以起劲地大肆贬低中国人来获得自身优越的证明,中国人几乎成为野蛮人的代名词。据当时的日本媒体报道,中国战俘在东京游街,一路遭到日本市民的羞辱和谩骂;但大部分战俘无动于衷,似乎毫不知耻,以致一位妇女跑出来对着游街的战俘大喊:“如果辫子军就是这个样子,我也能杀好几个!”日本人对中国人普遍的鄙视心理由此全面形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野孤山来到中国,开始了他在成都为期三年的教习生活。
中野踏上中国领土,首先感受到的便是中国人肮脏落后的生活及其迥异于日本人的猥琐不堪的精神面貌。中野在上海登陆后,便被蜂拥而上的中国苦力所震悚:“他们手脚的皮肤很特别,是由污垢堆积而成的。他们疮疥满身,褴褛蔽体。这些苦力不是探头探脑地挨个客舱窥视,便是在客人的残羹剩菜中翻找肉食的蛛丝马迹,一旦寻得,便咋着舌头津津有味地大口咀嚼。其情景之恶心,无人不为之震惊。”
这类文字在百年之后的我们读来,也会受到相当的刺激。
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完全可以表现于精神面貌。近代化后的日本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教育普及,道德提高,智慧发达,整个民族自我认同感空前加强,呈现出勃勃生机。先行一步的日本反观仍然在君主制的泥潭中裹足不前的中国,鄙夷之情油然而生。这些苦力们猥琐的样子是近代中国贫困、愚昧的生动写照,这固然与西方殖民者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有关,它更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及其所长期实行的愚民政策的产物。将中国近代的衰败落后简单归咎于西方的侵略,与其说是一种浅薄,不如说是一种无知。
与欧洲乃至日本不同的是,中国的专制是一种彻底的专制,所谓彻底是指君权从中央直接伸入地方,以绝对的权力支配调用全部的国家资源,将强大的国家意志凌驾于兆民之上,以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中国底层民众处于被任意搜刮的境地,而统治者的贪欲使得这种搜刮永无穷尽。在多数时间内,底层民众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遇到灾荒年月,大批饥民只能四处逃亡,而官府的赈济往往是杯水车薪。不愿坐以待毙者,或者易子相食,或者揭竿而起。中国历史就在这种治乱的循环中周而复始。
日本学者古濑奈津子在比较了中、日两国的朝贺仪式后认为,“唐代的朝贺是全国规模的,中央地方官员齐集于中央共同举行。与此相对的是,日本的朝贺是二重构造的,在中央以天皇为中心,在地方以国司为中心分别举行。两国的国忌仪式的差别也大抵相同,一是全国规模的,一是以都城为中心的。这都明确地显示着,皇帝权力是可以浸透至地方的,而天皇权力并未进入地方的最低层”。“唐朝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日本则由于朝廷所委任之国司的权限较大,地方较独立,其独立性也得到了朝廷的承认”。这种专制程度的不同使得中、日两国的农民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状况。日本在中世末期以后,形成了具有很强的地方自治特征的社会形态。尽管德川幕府建立后强化中央集权,但仍然保留了村落自治。领主分派下去的税收不是如中国那样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村为单位。村政权要自己决定如何在村民中分摊这种税收义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农民利益,保证了地方的经济积累,造成了日本江户时代(即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农村经济的繁荣,进而带动了文化的昌盛和政治的觉醒。日本后来的明治维新能够迅速取得成功与这种中央政府与基层村落分立型的社会结构无疑具有极大的关系。
回头再看中野笔下的中国苦力,我们就会明白,他们饥不择食的贫困与龌龊不堪的样子实则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日趋强化的恶果。“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惜乎中国历史上“仓廪实衣食足”的时代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因此杜甫才会在《忆昔》二首中深情追忆盛世光景:“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盛世昙花一现,接踵而至的便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即便在所谓的盛世,灾荒也是连年不断。生存尚且艰难,礼节荣辱之类自然无从谈起,愚昧麻木成为中国下层民众的基本特征。兼以中国的统治者历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搞愚民政策,更使穷而且愚的民众莫知所以了。因此,中国人最终的悲剧和日本人最终的幸运其实早已潜藏在历史的细节之中了,最后的结果不过是历史逻辑的自然发展而已。
二
中野自然也注意到中国饭店餐具的不卫生,他写道:“擦餐具的擦碗布和擦鞋台、凳子等的抹布不加区分,擤了鼻涕的手在衣服上擦,然后又用衣服擦餐具。诸如此类不讲卫生的现象,华人毫不在乎,而在我们看来,完全无法忍受。那些掌管炊事的幺师身上穿的衣服之肮脏,令我们惊诧无比。”这种不讲卫生的陋习时至今日依然随处可见,如许多饭店餐具的清洗消毒极不严格。
中国人不注意卫生的习性举世闻名,遍布世界的唐人街之肮脏杂乱往往在当地独树一帜。中国人的这类习性究竟是古已有之,还是如京戏等国粹一样后天产生,确实很难考证,谁也无法看到古代中国人的生活细节。中国人对自己的生活习惯习焉不察,各类正史杂史鲜有记录。诚如陈寅恪所说,“中国历史多是政治史,社会经济、民风民俗等方面的材料极少”。就日本人而言,虽然自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曾向中国派遣约二十批遣唐使,但这些人在中国期间究竟经过何地,经历何事,有何见闻,鲜有记载,目前所见只有唐代日本遣唐使释圆仁的旅行记《入唐求法巡礼记》。但该书主要记录了唐代与佛事相关的内容,如各地寺院的规模特色,各类法会的举行过程,武宗灭佛的历史见闻。此外亦涉及朝贺、国忌、乞雨等各类仪礼,也记述了唐代的一些风俗,如除夕、元宵节举国欢庆的盛况。其中对唐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涉及不多,以致我们无法了解唐人的生活状况及日本人的观感。大概因为当时唐王朝国力强大,文化先进,日本人高山仰止,即便唐人有某些不洁的毛病,恐怕也不会受到日本人的挑剔,大概文化整体的先进性可以使一些局部缺陷忽略不计。
总之,日本人直到近代才开始大量描述中国人生活细节上的种种陋习,表明近代中国已严重落后于世界。而日本人只有在居高临下地俯视中国时,才可能注意到中国人的细节缺陷。细节的落后往往透露出本质的落后,无论开埠后的上海如何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无论远远望去如何光华富丽、歌舞升平,只要还存在着那些大嚼垃圾中的食品的苦力,只要旅店客房仍然臭虫横行,乃至尿迹遍地,只要饭店伙计对碗布及汗巾不加区分地混用,那么,这个城市的文明只能是一种徒有其表的伪文明,恰如中野所说:“该国虽然看起来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实际上,它已年迈体衰、丧失活力,五亿人民落后于世界文明,即将成为野蛮的民族,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中野的悲观固然出于对中华民族肤浅的了解而形成的短见,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中国现实的清醒认识。真正的文明首先是精神上的,精神的猥琐与贫困将抵消任何物质的富有。近代上海只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幻影,它只是照搬了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的繁华奢侈,而近代西方文明的内在精神,诸如宗教精神、法律制度、民主体制、道德意识、责任感及作为人的教养与尊严一概无从谈起。因而,近代上海只不过是一个贫血的美人,随时都可能晕厥死去。
中野孤山笔下中国人生活细节上的种种陋习实则中国长期权力至上的畸形社会的必然产物,而非如鲁迅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因为它并非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东西,实在是中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使然。只要民众被压在最底层,除了苟延残喘的生存,没有任何其他权利,那么诸如卫生习惯、绅士风度之类具有现代意义的国民素质都将不会形成。长期恶劣的生活条件自然使人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长期低下的社会地位及被呼来喝去的奴隶生涯使他们自然不会追求人的尊严和风度,这类精神性的素养只有在平等的社会中才能形成,只有在感到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时候,一个人才会追求“人”这个神圣概念原本应有的东西,而对“人”的完整意义的追求在深刻意义上也是一个制度问题。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都强烈地感到了中国人对政治的冷漠,原因在于,中国的老百姓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凡事都取决于上级乃至官长的意志,个体诉求无法得到表达的机会,当然会形成政治冷漠。而所谓政治,最核心的意义即在于管理公共事务,最高效的管理是民众的自我管理。民众只有参与到政治中去,才能培养出自我管理的能力,进而培养出相互关爱、遵守秩序等现代文明观念,不至于成为一盘散沙。而对专制统治者而言,他们最害怕的恰恰是民众的团结合作,“聚”就有谋反的嫌疑,“聚众谋反”、“啸聚山林”之类短语核心词即是“聚”。所以中国历代统治者对老百姓一向是“分而治之”,只有把百姓分化成一盘散沙,才能高枕无忧。从近代中国的状况来看,这一目的显然是达到了。
中野孤山笔下的中国人行事不守秩序,没有公共意识,自由散漫,各行其是,恰如一盘散沙。如中野乘船到达九江时,“未等轮船停稳就有商贩接二连三地跳上船来,也有跳下船去的乘客。开始装卸货物时,苦力一拥而上,那混乱嘈杂的场面,就像是暴乱开始了一般”。此类情景现在仍然时有可见。
三
作为对中国文化有所研究的日本人,中野孤山自然会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与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及精神状态之间的关系。中野注意到,“学校里一定设有祭祀孔老夫子的圣坛,这已成为华人道德观念的中心点”。“无论去哪家看,都有一个上书‘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大字的位牌,这是家家户户的道德观念的中心点”。尽管学校和家庭都将儒家道德作为“中心点”,中野却很怀疑其实际的效用,“但不知这些对中华民族之道德观念是否真正具有感化的功效”。
显然,中野通过对中国人日常言行举止的观察发觉中国国民的道德素质并没有体现出儒文化教育的功效,中国人言行之粗鲁怠慢与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教诲相去甚远,这无疑是一种教育的失败。因而,中野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中国人这种对儒文化道德的恭敬并非发自内心,既非发自内心,自然谈不上对精神的濡染。
中野并且注意到了成都乃至于中国的牌坊,“牌坊不仅是蜀都,在中国各地都有。牌坊的最上方有金字写的圣旨或圣旨旌表,圣旨的下方横书‘节孝或‘故某某节孝坊或‘贞烈坊等具有标榜颂扬意义的文字”。中野对此批评说:“与丈夫殉情,果真应该旌表吗?更何况,这么大的纪念物并非官建,也非政府出资,而仅仅是从圣上那里求得一美名,最终还得由自家人掏腰包去修建。这似乎是在吹嘘自家的富有,说起来,不过是自我标榜罢了。因此,穷人家即使出了贞女烈妇,要修建一座这样的牌坊也是无能为力的,其结果,她们只能从这个世界上销声匿迹。如此这般,旌表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旌表,它只是一种个人行为罢了。”
中野显然并不理解中国表彰节妇的深意。中国的统治者们建造那些高大的牌坊其实并非是给女人看的,而更主要的是给男人看的。女人守节不守节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男人效忠不效忠,女人尚且做节妇,男人自当做孝子忠臣。孝要愚孝,忠要愚忠,唯此当权者们才能高枕无忧,肆意狂欢。
四
作为教育工作者,中野孤山敏锐地注意到了中国学生的精神状态与日本学生的极大不同,中野写道:“学生身着长衫,怎么看都像业平(业平:在原业平,日本平安前期的和歌作者,六歌仙之一。阿何亲王的第五个儿子。原作者注)一副公子哥的样子。他们无忧无虑,悠闲自在,不慌不急,与日本学生的活泼向上、精力充沛形成强烈的反差,简直就像是些老头。”
中野孤山所看到的成都新式学堂里那些老气横秋的“像是些老头”的学生是中国儒文化最后的影子,“在进入现在的学堂之前,除汉文书籍以外,什么也没有学过,《论语》、《孟子》等讲义非常精彩,《史记》、《左传》等读解也绝顶透彻,但关于理化、常识、数学等知识,他们却一窍不通”。虽然他们也在学习西方的科目,但不可能真正了解并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是怎样的落后,面临怎样的危机,他们的心灵没有受到强烈的震动,自然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并自觉汲取外来精华,以重塑民族精神。也许他们仍然在以传统的夷夏观念看待中日战争,说不定还在做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美梦。作为蜀人的郭沫若留学日本后才写出了像火一样猛烈燃烧的《女神》;鲁迅也是在留日期间心灵受到震动而弃医从文,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批判;邓小平也是在日本的新干线列车上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直观的感受胜过任何声嘶力竭的呐喊。
中国人不仅将儒文化的仁德观念作为自身修养的准则,而且将其上升为国家政策,企图以道德教化怀敌附远。我们无法证实或证伪儒文化仁义至上的普世价值,但如果一种文化首先不能维持一个民族的生存,则其普世性就值得怀疑。西方人在坚守基督教人道精神的同时,又不放弃利益争夺,乃至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悍然发动侵略战争,义与利、善与恶那样不可思议地统一在西方文化中,正因为这样,西方人才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而不必像中国人一样总是为自己的逐利行为扯上道德的遮羞布。也许中国人自小便套着道德枷锁,所以年纪轻轻却像暮气沉沉的老头。鲁迅与中野孤山有相似的发现,在《从孩子照相说起》一文中,鲁迅写道,“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活泼好动是孩子的天性,与民族国别无关,而中国孩子的驯良显然与大人的调教有关,而大人如此调教则显然又受到传统的潜移默化。对中国孩子所表现出来的驯良,鲁迅说,“驯良之为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面对这样一群缺乏生命活力的学生,中野孤山也流露出恻隐之意,感叹说:“从总体上看,这些学生缺乏活力”,“一想到将来支撑中华民国的是这么一些国民,不禁心生悲凉”。这位日本人的悲悯或许有真实的成分,但似乎更有对日本摆脱了被殖民化的命运而顺利驶入近代国家的庆幸。中野在长江湖北段看到运送铁矿石的铁道后说:“我们使用这些铁矿制造清朝向我们订购的军舰和武器,也就是说我们把产品返销给他们,这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从前,我们将我国有限的钢铁运往外国,在那里造出钟表发条后又数百倍的价格买回日本,如今情形正好相反,但愿诸事如此。”日本刚刚摆脱了被殖民化的噩梦,便转而以更野蛮的方式侵凌中国,并在对更弱者的施暴中得到快慰。这种心态既显示出这个岛国民族逆境求生的危机意识,更暴露出其民族性的阴暗与褊狭。尽管历史上的日本人曾从中国广取佛经,并在本土广建佛寺,但踏上中国领土的日本人除表现出对中国物质财富、文化遗产的贪婪外,远远没有表现出佛教的大爱与慈悲。他们究竟从中国文化中得到了什么?
中国之落后固然令人触目惊心,但中野孤山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肤浅的了解使他不可能对中国的前途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以悲观的语调断言:“该国号称‘中华‘中国,曾极尽繁盛强大,但如今却每况愈下,陷入退步落伍的境地,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如果孔、孟复生的话,或许还有一线希望,但就目前来看,孔孟的复生是做梦都不可能的事情。”中野笔下所呈现出的中国人的肮脏、丑陋和麻木的确令人震惊和痛心,然而以此断言中华民族“即将成为野蛮的民族”,“陷入退步落伍的境地,已经没有回天之力”,则无疑表明中野孤山对中国观察的草率及以中国文化了解的浮浅。
中野孤山的中国游记尽管距今已百年之久,但作为遭受过无数屈辱的民族,绝对不能忘记昨日的伤痕。我们还是应该经常重温历史,看看我们百年前的模样,知耻后勇,不断反思,奋力进步,以使中华民族永远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以战争时期中野重治为标本的考察
——中野重治诗歌作品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