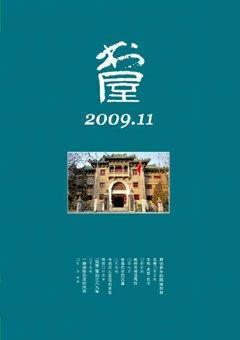喜忧参半的网络民意风暴
蔡永胜
(一)从两个案例看网络监督已成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河南省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联体别墅和楼中楼。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就此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时,逯军副局长质问采访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言论一出顿时天下大哗,媒体讨伐声一片,有些网民的发言十分尖锐。
我们先不讨论逯军副局长究竟是捅破了某些官员的潜意识,还是他违背了中国大陆官员本应遵守的意识形态,单就他的言论受到广泛的批评以及批评导致郑州市纪委不得不介入调查此事件来看(据悉逯军现已被停止工作),“民意”已经不是一个小觑的字眼,它在新技术的武装下已经变成了现实的强大力量,直接地对政府行政权力实施了影响。
在“邓玉娇事件”中,更是彰显出普通人的话语一旦通过网络汇集起来就能形成强大的监督力量。邓玉娇在娱乐场所遭受人身侮辱奋起反抗,将一名镇政府官员乱刀刺死,由于舆论对该事件的关注以及网民对邓玉娇英勇行为的高度赞扬,法律最终对邓玉娇作出了免于刑事处罚的判决。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性都有其弱点,人们不能因为一个官员出入娱乐场所而最终丧命就放弃对他非正常死亡的起码同情而漠视他作为人的尊严,法律也不应该超过自身的规定性而对被害者转化为杀人者的结果之审判中丧失公正。然而既往的事实主要在于,在中国,官员是强势阶层,他们行使权力时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监督,这样就造成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滥用权力,甚至在滥用权力中变得十分骄横狂妄、不可一世,这样,“民意”的“矫枉过正”就显得很必要。理性的人应该尽力使自己保持公正,法律没有主见地跟随“民意”并不是成熟的公民社会应该有的现象,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的运作特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意”通过网络来形成一定的力量对政府官员的行为有所监督乃至制约就是社会政治走向成熟所必需的。在“邓玉娇事件”中,如果不是邓玉娇心理和性格的特殊性,那么受害者就不是她杀死的官员,而是她自己了,而后一种情况在中国不是个别的。
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现实社会的另一种普遍情况,中国虽然已经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然而真正贯彻起来还是受近代意识形态的很大影响,比如关于北京老城区的改建,开发商往往与政府官员合谋强令居民拆迁,给予居民的拆迁费用又由开发商与政府一方来确定,被拆迁户就完全处在被动位置,没有任何自主权可言。显然,这里的“强买强卖”既与公平的市场经济背离,也就谈不上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了。如果是涉及地铁、学校等公共建设,那么这种形式的拆迁尚且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政府协助开发商强迫居民拆迁后,开发商却是进行商业性开发,开发商因此获得的巨大利润并不会与被拆迁的百姓共同分割。这里且不论有多少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在这种“官商”利益合谋中被消灭或破坏,仅就利益的分配来说,就造成了官员与权贵资产者合伙起来共同损害公民利益的现象普遍性地发生,某些官员在“公仆”伪装下,是玩弄权力而获得个人利益后的窃喜。由于监督力度的极端薄弱,权钱交易可以以不易被察觉的方式悄然进行,这样就出现了集团利益与公民利益的看似微弱而实则激烈的冲突。其中的利益算计之不同于商人在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中逐利的算计在于——某些官员将想尽办法不露痕迹地将权力换取个人利益视为一种做官的技巧,如此行政权力的滥用造成了社会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出现变态性配置,从而使社会丧失了应有的公正性。官僚阶层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虚假:一方面是大肆宣扬的道德夸饰,一方面是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中国历代王朝在其末期几乎都是在出现类似的吏治崩坏而在天灾导致的民变作用下走向灭亡的。我们应当牢记这个教训。
所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的这句话其实诚实地道出了某些官员的潜意识,是一种直来直去的胡说。尽管一种变相的胡说与一种直来直去的胡说之间其差别在本质上其实是很小的,但网民只懂得批评直来直去的胡说,而不懂得批评曲折的胡说。其实那些不受监督的官员及其权力总是以“为人民”的名义损害人民的利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二)对网络监督的前瞻
在以权力监督权力不力的情况下,舆论监督可以先行,尤其网络监督可以先行;而实际上网络监督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十分强劲的监督力量。在中国,新兴的网络具有传统传媒所不具备的优势,由于网络信息传播非常快捷方便,“言论自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现。
在纸媒体的时代,由于掌握表达思想工具的人相对较少,因此任何有违政府意识形态之“正统”的言论都能被行政手段很容易地消除掉,然而网络提供了可以将思想立即转化为语言的平台,一个敏感的信息可以在数秒内迅速传播到成千上万人的计算机上并得到即时性的评论,任何力量都无法应对如此巨大的语言能量流,所以采取堵塞言论的做法在技术上是完全不可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实在没有那样的警察队伍可以给予数万人乃至数百万人实施旨在破坏大脑左半球语言功能区的“外科手术”;建立“黑客部队”配备同样多的黑客攻击网民的计算机又容易造成对国民经济的强大打击,因为人们上网的计算机即使很大数量都属于个人,而其上承载的信息却往往关涉他所服务的机构;而语言信息虽然也可通过过滤软件对敏感词句有所限制,然而如果国家强迫使用过滤软件而该软件过滤词语过于苛刻则将使一般日常语言表达受到限制,从而会给任何人造成不便。总之,欲在技术上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是难于做到的。全球化时代一旦开始后,再想回到封闭时代就不具有可能性了。
既然网络语言的自由性一定程度上使政治丧失了很多专制时代的能量,就可以主动地设想如何使网络监督发挥到更高的境界。就网民方面而论,“网络作家”目前阶段还没有达到传统作家的影响力,他们的作品的文学性似乎普遍地有待提高,基本上只适用于匆促的阅读而缺乏长久魅力。窃以为文学作品需要精心构思,网络传播只能是辅助性手段,而“短平快”式写作不适合于文学创作,这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初期那种文学之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作用,看来不大可能在现代中国社会再现了。“网络评论家”有所发展,我们能注意到某些评论家的个人博客充分发挥了网络语言快捷传播的优点,比如中国大陆的网络评论家王干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中关于汉字的议论就很有可看之处,他关于简化字属于“山寨版”的议论甚至得到了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的响应。我们能否设想,中国的网络媒体也能产生出西方独立媒体培养出的著名的评论家、名记者那样对世界政治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呢?回答是——哪里有自由哪里就会有出人意料的发展,“网络精英”很可能在中国出现。我们能注意到西方议会中,某人的慷慨陈词得到国人的侧耳倾听,我们也可以设想将来中国的网络评论家的言论受到中国人广泛的关注从而对中国社会发生积极影响。就政府方面来说,如果新兴的网络媒体吸引广大民众的注意力,那么政府也就自然会通过网络渠道宣传自己的施政纲领,而涉及一方人民切身利益的事件——如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建设核电站、化工厂,就不能无视公众的意见。在网络时代,政府过去施行的那种“暗箱操作”越来越困难,几乎不可能了,信息传播的无孔不入会使任何涉及公民利益的事件得到强烈反响。这样政府的作为就必须更加透明和公开,否则其执政的合法性就会遭到普遍质疑。
由于人类社会生活是有机整体,新技术的革命意义并不完全局限于技术本身,它总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深远的影响。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没有被发扬光大(而是逐渐灭亡)与技术的限制是分不开的,而古罗马的民主受技术限制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古罗马比古希腊的城邦国家要大得多。我们假设古罗马人有现代人的通讯、电视、网络技术,那么它也许不至于从民主制逐渐转化为帝制了。我们因此设想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借助于新兴网络媒体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因为借助网络,民主政治会获得良好的技术支持。古希腊时代,雅典的公民为了就一项决议投票必须集合到广场上,而古罗马民主政治时代,罗马城以外的罗马帝国行省那些获得罗马公民权的人士要想参与罗马政治,则需要跋涉千里到罗马城中,否则就难以对罗马政治发挥直接的影响。然而现代社会,公民的表决可以通过网络立即实现,只要在虚拟电子票上的“是、否、弃权”三项中作出选择就行了。当然这里忽略了细节——比如如何避免一人多投选票问题等,不过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在什么样内容的决议上设置“是、否、弃权”才是最重要的,而网络技术并不能包办一切。在当代中国社会,既然网络选秀能顺畅地完成,那么网络选官也当然是可行的,其实这里并不存在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的所谓大是大非,民主政制不过是一种政府运行模式的合理性改进而已,随着网络民主的发展,窃以为公推直选等民主形式逐步在中国推广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三)网络自律——建设文明的网络监督语言
任何一种极端主义都是有害的,“网络民意”也有自己的局限,以为“人民意志”绝对正义且绝对正确是迷信,民主的现代意义是权力制衡,而不是“民意”崇拜。而且民主的适用范围不是无限的,比如对于某些科学技术中的专门问题就并不是民主所能解决的,对于一个科学理论的论证不存在多数性原则,不能认为同意的人多就是正确的。即使在人民能够了解和评价的问题范围内,也不是“人多势众”就代表正确方向,人性的弱点之一就是往往急功近利,无条件地顺应“民意”就可能走向民意的反面,因为人民在非理性的激情状态下所作出的决定往往违背他们理性状态所理解的利益。实际上“人民”的意义不仅包括现代人,还包括死去的古代人,古代人的“民意”就存在于我们现代人所遵循的道德与法律之中,我们不能在猛兽之中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而只能听凭它们的丛林法则,盖因它们不理解我们祖先所领悟的道德与法律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学会如何做一个光明正大的君子,依然是建设成熟而理性的公民社会的基础,而民主只能建立在成熟而理性的公民社会之上,而不能建立在极端主义的“暴民社会”之上。然而网络在使言论自由获得解放的同时也使人性的弱点前所未有地暴露出来,由于许多跟帖可以不必署名或署假名,这使网络语言极端地“爱憎分明”:凡是自己同意的观点就膜拜性地赞美,凡是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则极尽侮辱之能事。陌生的网民之间本来无怨无恨,然而由于无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本来可以商量讨论的问题一旦出现观点对立,就立即变成了没有任何游戏规则的“论战”——以市井的污言秽语互相攻击。中国近代杂文家鲁迅虽然也有极端主义“爱憎分明”的弱点,但他攻击传统文化的语言毕竟还吸收了传统语言的典雅,李敖的嬉笑怒骂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学养功底,然而现代中国大陆许多青年人除了满腔的怒火之外看不出什么修养,对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深思就咆哮起来。这种网络浮躁现象实在令人担忧,因为这些极端主义的“愤青”似乎有回归丛林法则的迹象。比如关于简化字与正体字的使用问题,本来是可以深入讨论的学术性(乃至延伸到政治学)问题,网民通过此讨论也可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然而许多讨论此问题的网民似乎缺乏必要的理性,没有对那些与自己有不同观点的人的起码尊重。显然,关于是否恢复中国传统正体字的问题,通过网络投票的“民主”方式来裁决是很不适当的;其他方面,比如我们也不能就是否废除私有制投票,或者就是否继续奉行或废除孔子的人生哲学投票。现代民主并不是就一切问题施行投票并按多数性原则作出决议,即所谓多数人的当家做主并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意义;通过监督而防止统治者演化为专制独裁者,这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意义。人民选举出自己的统治者统治自己,这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明确的,统治者的荣耀是他的聪明才智和公正与理性在被统治者面前获得赞誉,而不是获得作威作福的资本,被统治者在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中获得的利益是——他们不必为国家日常的公共事务太过操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并非是矫饰性的“仆人”与“主人”的关系,国家宪法给予被统治者的权力是——他们有权确定统治自己的统治者。
网络监督只有在适当的范围内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力量,而且是要在传统道德的约束之下。因此网络监督也有一个自律的问题,即网民必须在“战国时代”的纷乱中逐渐建立起语言规则,即表达自己观点的语言首先是文明的。我们中国古代的文言文是世界上最文明、优雅、成熟的语言,因为文言文经过数千年的持续发展,淘汰掉了糟粕而保存了精华,适合于表达庄重的情感、理性的论辩、谦恭的态度,然而却不适合于表达轻慢、猥亵、粗暴无礼的情绪。现代白话文则融会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市井语言,加之鲁迅杂文言辞刻薄、思维简单的文风在现代乌托邦时代的独尊,以及近三十年来英语口语作为商业性粗糙语言对中国语言的污染,极大地扭曲了中国现代汉语。由于近代一系列旨在破坏传统文明的运动使中国文明的连续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裂断,中国古典时代文言文的优美、毛笔正体汉字的典雅,现代人已经难以领略,更何况实践了。
“网络监督”的自律意义就是,网络中要形成一种风气,就是谁如果动辄污言秽语就会遭到网民的普遍谴责,每个人在书写自己的文字时都要想到自己不是在不受任何道德约束的阴暗角落里,而是在古圣先贤的墓碑前,无数正义的灵魂在注视着自己,并因此逐渐地形成网络语言的禁忌,谁使用不文明的语言谁将遭受厄运。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我们日常交往的语言不能做到起码的文明,我们就不配享有自由与民主,因为奴隶性的本质在于:某些人只有在压迫中才能保持温顺,而自由与民主不是被他应用在理性的发扬上,而是用在非理性的狂暴凶恶之发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