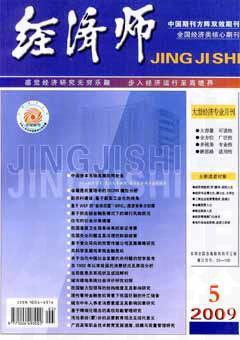浅论易经《蒙》卦的启蒙教育观念及现代意义
摘要:易经《蒙》卦中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观念,它包括启蒙的对象、主导者、启蒙的方法和手段,对于现代转型社会的启蒙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和现实意义。文章针对现代启蒙教育中的对象范围问题、学生兴趣问题,以及教师的惩罚权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主导权教师惩罚权教育手段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05-115-02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这是一部独特的哲学著作,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但究其内容而言,又不是空洞无物的。经过现代学者的研究和发现,我们更加认识到它不只是单纯的卜筮之书,而是中国古代先民从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等全方面的经验和实践总结。其中《蒙》卦中的教育启蒙观念直接影响到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发展进程。笔者试将此教育启蒙观念抽取出来,在时代背景下来阐发出新的涵义,使这一观念更具有借鉴和现实意义。
一、易经《蒙》卦中引申出来的教育启蒙观念
首先我们来阐述一下易经《蒙》卦中的教育启蒙观念,这主要集中在蒙卦中,归纳起来有:
1教育启蒙中的对象问题。周振甫先生在《周易译注》提出“启蒙”的对象有两种:一种是人刚刚初生长大时的蒙昧幼稚,即《蒙》卦辞称的“童蒙”;一种是由于没有受到良好启蒙教育而蒙昧无知触犯刑律的“刑人”。另一方面,从蒙卦的卦辞来看,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教育启蒙的范围是广泛的,并不单单指国民教育领域,而要推广到法律等更宽泛领域。可以说,这是宽广范围的启蒙,具有更深一层的社会意义。
2教育启蒙中的主导权问题。作为教育工作者,笔者认为启蒙教育不仅要熟知教育对象,还要把握好教育中的主导权问题。《蒙》卦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噬告,再三渎,渎则不告。”黄寿祺和张善文两位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并非我求有于幼童来启发蒙稚,而是幼童需要启发蒙稚有求于我;初次祈问施以教诲,接二连三地滥问是渎乱学务,渎乱就不予施教。同时,我们还要更加认识到,启发教育对象的工作,主导权应该在教育工作者手中,幼童虚心求教,双方志趣相通,才能达到启蒙效果,否则只会扰乱启蒙教育的正常秩序。
3教育启蒙中的方法问题。针对蒙昧幼稚的教育对象,如何进行启蒙教育,既要注意到对象接受新鲜事物和知识的能力,又要考虑到他们的智力发展程度。《蒙》卦曰:“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黄寿祺和张善文认为,启发蒙稚,利于树立典型教育人,使人免犯罪恶;要是急于前往必有遗憾惋惜。此段话也告诉我们,在启蒙教育时,要善于树立典型,使受启蒙者有法则示范,这样才不至于陷于错误中,同时也不可急于求成,否则就会造成“困蒙”,导致对象远离启蒙教育者。
4教育“启蒙”中的手段问题。《蒙》卦曰:“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黄寿祺和张善文认为,猛击以启发蒙稚;不宜于施用暴烈过甚的方式,宜于采用抵御强寇的方式。我们从这段话中看到,启蒙教育手段上应该严厉,因为人在初生之时愚昧无知,不得不采用“猛击”的方法来启蒙。《程传》中也讲到:“九居《蒙》之终,是当蒙极之时;人之愚蒙既极,如苗民之不率,为寇为乱者,当击伐之。”但是又讲“上不为过暴,下得击去其蒙,御寇之义也。”指的是启蒙教育不应该过于简单粗暴,以免伤害启蒙对象。应该采用“御寇”的方式,。即扫清愚昧,包容教导,同时又保护对象,避免伤害。即卦中讲到的“包蒙”。
二、易经《蒙》卦的启蒙教育观念的现代解读
通过对易经《蒙》卦的分析和阐述,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先民在启蒙工作中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启蒙者主导思想以及教育手段和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作为当代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借鉴古代的启蒙教育经验成果,结合国内外的启蒙教育理论,创造出一套适应中国特色的启蒙教育方法。笔者抛砖引玉,提出一些观点,和有志于启蒙教育人士一起探讨。
1教育工作者要具有独特的启蒙教育理念和创新教学实践。《蒙》卦中讲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指的是师生双方志趣相同,才能达到教学效果。孔子在论语中也讲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的意思就是,教育学生,不到他心里想知道而不能做到的时候,不到他口中想说出来而不能做到的时候,就不去启发他。启发学生,举一而不知其三,就不再告诉他。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致的,教育启蒙重点在于学生的自我认知,而不是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因此,教师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启蒙教育思想,国外学生启蒙教育多在于教师引导下,这样学生更有创造性和积极性。
当然,独特的教育理念,并不是凭空想象,一意孤行的,而是融会了传统教育启蒙思想和国内外先进教育创新理念,形成的自己在实践教学中行之有效的独特教育观念。在教学中要不断创新,突破陈旧的教育理念。
2现代启蒙教育对象和内容要具有更大范围的社会性和广泛性。《蒙》卦中谈到的教育对象,即“童蒙”,它有多重含义,既指个人出生时期的童蒙幼稚状态,又指蒙昧无知没有经过启蒙教育的国民。而启蒙教育内容则侧重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国家法令、政治军事制度等各个方面。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新世纪的转型时期,在方方面面都有很多新鲜事物不断涌现,现代社会要远比传统社会结构复杂的多。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以及社会道德建设方面也更需要多一些的启蒙教育。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对于道德的教育非常重视,表现出各个领域内的“泛道德化”,如以法律为例,传统社会提倡“德主刑辅”,道德扮演的角色要超过法律的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秩序上对道德的宣传和教育更为普遍。在现代社会,我国相继提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总体上讲对法律的传播和宣传还远远不够,往往公民在犯法之后,才会意识到学法和守法的重要性。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有学习法律的义务。但如果没有组织专门的法律学习和培训,法律意识势必不强,同时传播范围也势必不广。而且法律要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必须以通俗化的形式进行。与其他人文、社科部门知识相比较而言,法律具有更强的专业性甚至艰涩性。法律只有通过传播才能获得普及,法律也只有普及才具有其本来的法治意义与制度价值。
再以科学教育为例,当代社会,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但是也有一些腐朽迷信的东西换上了精美的“科学”外衣又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这种伪科学更迷惑人,而且不易识破。国内曾经出版了一套反伪科学“四大恶人”(即于光远、何作庥、郭正谊、司马南)丛书,它搜集了“四大恶人”近年来针对伪科学的各种演讲以及发表的文字,语言简洁生动,让普通读者了解更多科学的真谛。“四大恶人”的身份有中科院院士、作家、科普工作者等,他们的本职工作并不是专门揭露和批判伪科学,但是却去从事最一般的科学普及的基础宣传工作,其中的真正原因正是现代中国社会在
科技启蒙教育上的不足。
3现代启蒙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要具有实效性和可执行性。现代启蒙教育学生,讲究从兴趣方面人手,这样可以极大地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增强创新意识。因此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要从启蒙教育的方式方法、手段改革。但是考虑到我们社会中所面临的现实教育问题,又不得不陷入困境之中。现在的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生活在温室之中,单靠他们的兴趣学习,远远不能满足我们目前社会的教育需求。为使学生更适应现代社会教育的要求,教师应该树立良好典型,以使学生具有明确的示范准则,这些是国内做得比较好的。但是也有教师抱有“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在实践教学中使用惩罚学生的方法和手段,给受教育者造成严重伤害。如果处置不当,还会带来负面效果,极大地挫伤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继而对学生不闻不问,懒于教育,忽视教师职业责任。
针对国内教育中的惩罚问题,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们应该谨慎小心,但是也不能避讳不谈。有些学者认为要照顾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发育的特点,不该采用惩罚的方式,应该说服教育。这种说法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没有效果,或者收效甚微。《蒙》卦中讲到:“击蒙”,正是因为人在初生之时蒙昧无知,不知所措,没有正确的认知观念和能力,才需要采取严厉手段猛击,以破除蒙昧,达到启蒙效果。在我国法律中,严禁体罚学生,但并不意味着教师对学生没有惩戒权,体罚和惩戒学生这是两个问题,急需解决;教师惩戒权,是一把“双刃剑”,需要立法严格界定。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参考国外的教育处罚制度。
韩国通过《教育处罚法》,处罚规定十分详细明确;日本法律规定,必要时可以依据监督机关的规定,对学生实施惩戒,但不得实施体罚,并对哪些行为属于体罚做了较明确的说明;美国教师惩戒权包括:言语责备、剥夺某种特权、留校、惩戒性转学、短期停学、开除;瑞士学生无故旷课,瑞士法院就要对他提出诉讼:一般都要处以罚款;英国教师的惩戒权包括:罚写作文、周末不让回家、让校长惩戒、停学等,还专门制定法律,允许教师以身体接触的方式去惩罚学生;新加坡制定了体罚学生的《指导原则》;澳大利亚学生违反校规校纪,会被叫到警戒室,由专门的教师依照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惩戒。
可以看到,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仍然采用体罚制度,这对学生教育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我们教育学生时不应该采用暴烈过甚的方式,甚至于造成学生身体伤害、重伤以及死亡等严重后果,这是严禁的,也不能达到教学效果,反而造成学生的逆反心理,厌恶学习。马振彪在《周易学说》中提到:“包蒙者主宽,击蒙者主严,宽严相济,治蒙之道备矣。”这段话的本意就是既需要“包蒙”,宽容对待学生,又要有具体严厉的教育措施来达到启蒙的目的。
三、结语
易经蒙卦中的启蒙教育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教育思想的影响意义是深远的,提出了启蒙教育者的主导性原则、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和教育,方法手段上“宽严相济”等。在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吸收传统教育观念和国外教育理念,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改革是有益的,也是符合科学的教育规律的。我们目前需要在教育的社会领域的广泛化以及教育手段的创新方面下手,同时需要在探索中立法设立教师惩罚权,使教育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马振彪,张善文同易学说[M],花城出版社,2002。
2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修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周振甫,周易译注[M],中华书局,1991。
4刘大钧,周易概论[M],巴蜀书社,2004。
(作者简介:朱亚辉,福州大学阳光学院人文系讲师,厦门大学中国哲学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福建福州350015)
(责编: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