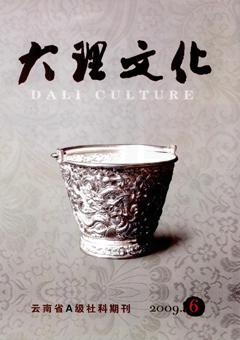石像蕴灵
左家琦
在太极山顶环视四周,群山倍显矮小,顿然觉得视界清明,真乃藏仙蕴灵之地。太极山顶土层很薄,随处可见裸露着大小各异、沐风淋雨的石头,坚硬光滑的踏级、巨大雄峻的台基和厚实牢固的石墙以及石头修造的建筑和庙宇,古老而充满灵性。在“药王殿”,我看到安放石像的庙宇并不高大,十几尊石像或许只是四散流落之后的聚首,他们集体蹲坐在小庙里,显得非常拥挤,很显然,这并不是石像原初的住所。
我心里老存有一种虚幻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投向石像的眼神中被生硬的反弹回来。手在疑惑和不解中悄悄抚过粗糙冰冷的石像,石像断截的头部、残损的肢体和头部规则的斜面,可能源于无意的损坏,也可能源自石匠的精心雕琢,目的不仅仅为了膜拜和观赏,也许为了替代残酷的杀戮,也许为了规避无辜的屠宰。
有一尊特别的石像,头的后部被规则的削去了一个椭圆形的斜面,我的目光被他冷峻而坚毅的面容所吸引,看不出有痛苦和狰狞的表情,似乎还隐藏着一丝浅浅的微笑。真正惊人的美,会有一颗期求极高的心灵,我在此刻被深深震撼,看着一尊尊原始质朴不断吸纳灵性的石像,犹如在欣赏一尊尊温暖古老的面孔。
石像,被最虔诚的姿势朝拜了千百年,她可能触发过悲悯的恻隐、可能宽恕过罪恶的诅咒、也可能拯救过善良的灵魂。在蛮夷边地,古时候祭司的地位一定很高,舞者的功劳一定也不会小。守望在太极山的神界之上,太极山的高耸和险峻,便于祭祀的祭司讨好神灵,也便于人神之间通过请神、祭祀、狂欢或者舞蹈进行广泛的交流与沟通。
我想起上山爬行过程中可以感觉山通神界,石有魂灵,庙遗仙风,磬存道骨。还可以闻到散落一地的花香,浸染一身的凉意,我拼命呼吸着甜美如蜜的空气,犹如母亲怀里饥渴吮吸的婴儿。山上酱红色的泥土,因为身在神境而倍显鲜活;山下重峦叠嶂、农舍若隐,犹如饱蘸墨汁的画笔在宣纸上渲染出来的山水画作。
石像在充满神秘与神性的太极山顶,汲取阳光仙气,悟道巫术精华。石像身体里拥有坚硬如铁的肌肤,温软神秘的灵性;石像承载过亘古绵长的黑暗、狂怒燃烧的闪电;石像注视着四处漫延的瘟疫、部落族属之间的征战。祭祀的祭司、狂欢的舞者、转圈的群众和过往的路人已经逝去了无数的面孔,古老的屋宇依然迎着山风和朝霞伫立。
转石阁,地势险要,三面临崖,用许多巨大的石条砌筑在凌空的山体之上,当地群众还保留着绕石三圈,然后念咒狂欢,向着悬崖深处抛撒纸钱的祭祀习惯。太上老君神像所在的屋宇没有门窗,整个屋宇是一座敞开着的石头建筑,借助缭绕的香火,阳光贴着光滑的石壁自由的晃动着。在道士“念念有词”的导引声中,我钻过石洞,绕着太上老君的神像转了三圈。在石头神案面前,当手和脸触及到冰凉巨大的石头洞壁的时候,我清楚的看到石壁上刻有“至诚感神”四个鲜红的大字,洞体布满浓密的苔和藓湿润的水痕,感觉异常的阴冷神秘。
摇钱树遒劲有力的枝干上爬满了厚厚的苔藓和叫不出名字的寄生植物,在山风中一如飘动的祭旗。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沉重地射在年代久远的石道之上,不时有道士的咏唱和祭祀的经声传来。
当道士做法的爆竹响过之后,我在想,先人请神做法、磕头祭祀、或者祈祷许愿目的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驱走邪恶瘟疫、佑护族人顺利平安,先人选择离天很近的神界和净土,太极顶作为与天对话,与地交流,布法祭祀的平台,祈祷的信众焚纸烧香想让天看见,祭祀的祭司念咒狂舞要让地感知。
当祭祀的乐器和急促的芦笙响起、当长长的经幡和猎猎的灵旗迎风招展、当古老的祭歌和神秘的咒语开始咏唱、当垂老的祭司和虔诚的舞者提脚抬腿,所到之处,见锅掀锅,见灶蹬灶,一切都为祭祀的队伍开道,为狂欢的人群让路。我在想,那一定是个神秘之夜,不眠之夜。
山顶一块古老的祭祀场地上,还有当地群众烧火做饭的灶痕,打歌踩踏的印迹。就在此时,我隐约感觉似乎有先人祭祀做法的背影闪动、万民狂欢的音乐飘来。在庙宇神坛炉烟的熏陶下,在大红公鸡喷涌的血浆和挣扎的嘶叫声里,翻山越梁,四面赶来的信徒,南来北往,匆匆远去的路人,连同虔诚的祈愿一起镌刻在了石像坚硬饱满的肌肤里。
石像肃穆的表情把我引向历史的深处,表情中还空留着上苍的召唤。
独赏斜阳,感觉是在聆听石像沉寂很久的脉搏;剪断烟雨,好像是在深情阅读石像的脸谱。
近观石像,上面有许多纸币粘贴后遗留的残片,油烟熏涂后没有抹去的痕迹。听住寺的道士说,这里成为“药王殿”以后,香火渐旺起来,神像也顺便兼职了“治病”的差事。听着道士津津有味的讲述,我没有想用纸币和香油去擦拭或者涂抹石像,当触及神像温凉身体的瞬间,双手在石像的身体上滑行,从一尊滑向另外一尊,我仿佛触摸到了逝去许久的历史。
那一定是个美丽的清晨,祭祀的祭司和众多的信徒怀着虔诚激动的心情聚集拢来,阅读石像陌生的面孔,感受石像丰富的表情,她们铁青、酱紫,色彩深沉而冷峻,体态凝重而粗犷,隐退了繁华的色彩,渗透着古老的粗野和神秘。
据万历《赵州志》上记载:“传说南诏始祖细奴罗曾在太极山中避过难”。虽然是传说,很巧的是,太极山的部分石像与我在剑川石宝山石窟和在巍山(山龙)屽图城遗址塔湾石场出土时看到的石像,无论从题材、造型、石质、色彩和线条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站在太极山顶,可以远眺细奴罗在巍宝山的耕牧之地。我悠然的想着夜色庇护下在太极山避难的王侯,躬耕的牧牛还待在山坡上吃草,后院木楼打开的门窗里,琴声从古老的草房传来,讲述的是无法遗忘的蛮王。
屋宇仍然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无法听懂石像之间被历史和岁月囚禁起来的“遗语”,在神像的身体里,也许有无数寄予厚望的祈愿蕴藏。石像身体上深深的刀痕,沉沉的锤迹让我感觉,暮雨朝霞、浓荫掩映,古老的石匠并没有走远;石像经幡、古寺半藏,似乎还有一串串叮铛、叮铛的声响,从石像的身体里生动地迸出。
一只小虫飞过,山风吹走了我心灵的燥热和身上的尘土。脑海里闪过一尊尊石像的时候,太极山的蓝天和白云丰富了我的视线,石像饱含远古的张望,身上沾染着松树的芳香,眼里蓄积着阳光的味道。
古老的祭司和舞者,借助太极顶的日月与星辰,纸钱和炉烟将无数先人诚挚的祈祷和信徒美好的心愿带走,徒留一份遥远的无告和着孤独的山风悄然起舞。远逝的王侯和黎民、曾经的祭祀和狂欢,美好的希望和梦想,无论是向着天堂还是地狱,都一起沉寂于太极山无色的梦里,山风后面追赶着的是山风,石头里面住着的依然是石头。石像在通灵和神性的光环中,从坚硬僵化、司空见惯的一块石头,成为原始灵性、形象生动的形象载体。
我深深的感到,在石像的身体里,一定有过恒久的魂灵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