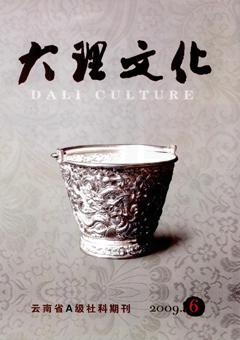水圈儿
龙 静
雨发出各式声响,舞动的韵律,在清晨,把世界轻轻晃醒。渐渐,人群如蓊郁葱茏的植物在院里、在街巷生长起来,手里的伞水中落花般漂流各处。夜雨、闲暇时间的雨又如眠曲。喜悦的雨,似舞者环佩琮(王争)作响。悲伤的雨,如离人恸哭着,伤感漫过山峦、原野,汇入溪流、沟壑。哪里是快乐的源头?哪里又是悲伤的归宿?是来自天国的乐音吗?我们还能听到那袅袅飞升的灵魂在歌唱,有力度的、柔美的、空灵的、能与神明交谈的,在这风花雪月的所在,和人世的嘈杂混响在一起,谁能撇开一切,聆听你的纯善?雨是明亮的,明亮的雨天是受洗的婴儿,雨珠是一群戴着白色手套,挥舞着荧光小魔棒的小仙女、小精灵在松针、栎叶、发梢、眉际跳舞,顽皮的贴在窗格的玻璃上往里张望,挤着脸,一不小心,就碎成了沫。一切如擦净的玻璃,樱桃红的如珠珞,树叶如琵琶轻拨的串串音符。草又长了几寸,蒲公英星星点点开了不少。雨后的阳光如耶稣,经了炼狱之痛,却奇妙地有着人性中的纯净和超越自然的璀璨光芒。纤细的雨如衣袂窸窣,铅笔在纸上滑动,小猫爪子抓挠的轻响。
“梅子黄时家家雨”,大理的雨,梅果还青,就陆续来着了,雨珠落在握着青果的梅树上,梅叶轻颤,像掉泪的眼不住扑闪着睫毛。今年旺势的雨是从端午开始的,节前很是热了一些日子。节假里,小男孩儿随家里的大人走亲戚,他是一个爱丢石头的小孩儿,刚刚过了三岁生日不久,每当石头扔进水里,扩出一个个水圈儿时,他便止不住“咯咯”笑出声儿来,我们暂且就称他为小水圈儿吧。他们来到小镇街面上吃中饭时,便感觉到无处不在的炙烤。到了小山中的亲戚家,凉快一点儿,没想,太阳微移,阳光倾注到院坝的水泥地面上,热浪便越过廊檐,从屋门的珠帘直逼进来,只好把风扇打开。务农事的亲戚说再不下雨,浇水这些事儿有的忙了,“无声雨润春霖早,村后山前唱俚音,新麦应时抽穗绿,应歌今岁庆丰吟”,应时的雨是农人的期待。院坝筑在高处,视线很好。晚上,水圈儿看到月亮像金色的涂料滴到宣纸上晕开,这就是民间所说的“月亮披蓑衣”——月晕。有闪电在山尖如蟠龙般掠过。大家一夜好眠,早晨醒来,雨淋湿了地,半夜下雨了。看到院里青柿带着叶子掉了很多,人们才知道雨有多大。雨又下起来了,小男孩一家还是决定冒雨出行。雨很大,天地间似演奏着一曲交响乐的华章。白羊河恣肆撕扯着褐黄色的卷发。路边分了台的湿地,水自上而下汩汩的流淌着。一天后,归家时雨小了,湿地的水也不见了,一段高坡上遇到了浓雾,对面除了车的雾灯外,什么也看不到。
雨总是下下停停,一月之内,一天之内,一个时辰之内都如是。雨下雨歇都让人猝不及防。在有雨的薄暮带着伞出来走走,抬眼望去,苍山翠微朦胧,笼着的雨就像聚集着一群振着透明翅羽的飞虫,你忙把伞撑起,脚下浅浅的水洼里,积水次第漾开一个个笑涡。当苍山半坡上的水雾散开,你又可以把伞收拢。几场稀疏的“飘风雨”把小水圈儿家窗前的花浇了个透湿,几天没有关注,最后发现草莓已伸出的长长茎蔓枯萎了,而花下竟开了小小一朵毒蕈,想像着风雨与阳光的交替催生满山的菌子,让人忍不住垂涎。
几仗雨后,西洱河水又涨了几篙,把下岸登船的水泥石阶淹了三两级。凝云墨染的天气,没有云气的蒸腾,风且住了,波翻浪涌之后,西洱河困了,静静地蜷曲着,任周遭车马喧哗。
河面长长的飘过来一道浅浅的水痕,像深色瓷器上映出幽暗的微光,又像梦中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两岸绿柳扶荫,夹碧桃粉白嫣红,妈妈抱着水圈儿沿着河堤玩耍,指着河面倒影对水圈儿讲:“河中有树,有花”。偶遇船家,铁皮船搁在岸边,网挂在栏杆上斜拉着清理杂质,岸上摆着几个盆,装着刚捞上的糯色的虾米、小鱼和一些碎碎的螺。时辰还早,听说大的鱼已经卖完。水圈儿很是好奇,全然不畏惧一只盘旋的黄蜂,拉着妈妈蹲着看了半天,又和船家两个小孩嬉闹了一阵。老大爷捞到一只蚂蟥,吸在手上,倒挂着垂下来。蚂蟥褐背黄腹,有勺柄那么长,粘乎乎的,放到水盆里,一会儿回缩成肉鼓鼓的一团,一会儿缓缓伸长,妈妈把它翻过来,只见白色的吸盘,活像吹的簧嘴。水圈儿的奶奶说,曾在牛身上捉过一只蚂蟥,用杵捣碎,结果出来无数个小蚂蟥,只好用纱布包好挂在树上暴晒……晚间的西洱河边多了几个垂钓的人,岸边一个个的灯在河面上幻化出一串串的魅影。
水圈儿也很爱花,这个季节里窗前的茉莉开了,他喜欢爬上窗台把大的花朵摘下。出去玩儿不时带回一朵缅桂花,别处叫它白兰,把儿兰。一天上古城,爸爸妈妈特意买给孩子几朵,他用细细的小指头勾着缅桂花,在手里绕着把玩,小鼻头一耸一耸嗅着。
雨季间歇的晴天,水圈儿随着父母来到了滇西的一个小城,小城被一条清澈的河流切分,四围的高山和谷底的河使整个小城看起来就像一个底部有裂缝的青瓷碗,旅店的窗外传来阵阵涛声,望下去能看到那条清凌凌的河,水圈儿挥着小手跃跃欲试。于是他们从大路一侧下去,绕过一座刷着白色石灰,拱顶的房子,来到河边,他们乘车来时知道,河的上游是一个水电站,虽然这段时间陆续经过几阵大雨,也许是上游蓄着水,宽宽的河床上水并不满。河水一坎一坎的往下流,下了一个坡,平缓一阵儿,又接着下坡。水圈儿一家往河的来路张望,那儿河水还宽,几个半大孩子光着身子在游泳,到了这儿,河床向对岸倾斜,河里的水汇到一侧,成为窄窄的一股,当然,水流更为湍急。他们这一头是河底光洁滑溜的石头,水圈儿欢呼一声,便被大人抱着放到了河中的石头上,他挪动着,来到河水面前,河水仿佛轻轻抖起的一袭朦胧、青薄的纱篷,水底潜着的石头,高的,水冲不到顶,破成几绺纷披下来,矮的,底部受阻,水面脉脉的起着波纹。水泥筑就的河堤上面,丛生的芦苇挺拔青翠,夹杂着很多竹节般纤细的草枝。稻田埂上,几个身着短打的孩子站着、蹲着、或弓着身子正对着秧田打探着什么。水圈儿看了一会儿水,就捡起石头一个接一个的往水里扔,石头“扑通”“扑通”在水上蹦达着落下去了,他越玩越有劲儿,“咯咯”的笑声起来,在这正午微热的空气中荡漾开来。
两只苇莺从上方飞过,嘴里衔着筑巢的枝条,小男孩丢石头的水声惊动了它们,“刮!”一只苇莺的枝条掉到了河面上,打着好看的旋儿,被水冲走了。它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已经迁徙了好一阵子。杜鹃常常借它们原来筑的巢孵蛋,外来的杜鹃蛋会影响苇莺自己后代的生存,所以它们离开了,想寻找一个适宜安家的地方。当那草枝随着激起的水圈儿漂出大截大截的路时,它们看到了前方湖中一望无际的芦苇荡,那儿有许许多多苇莺,是苇莺的快乐家园。
小男孩欢快地笑着,一个女孩也不由自主的把石头扔到水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水圈儿里潋滟的波光似乎也美丽的在她的脑海中闪烁起来。她迈着轻快的脚步回了家,收到了朋友寄来邀请她加入校友社区的电子邮件,无忧无虑的玩伴、青葱岁月的同学仿佛在向她微笑。她从小随父母不断辗转奔波,成年后工作在远离父母的地方,每一次的分别,思念都深深的在她心里沉淀。那一圈儿一圈儿泛起的涟漪似乎让这不由人的生活起了亮色,接着,她把父母最需要的关怀放到邮包里寄了出去,并且,要每年如此。
我们再回到那条河上,在那里,水圈儿妈妈让爸爸打一个水漂儿,爸爸好久没有打过水漂儿了,爸爸可以在水面打出三四个漂儿,水道窄,第二漂儿弹起时砸到了堤坝上。但他们都感到,那些欢乐的日子又回来了。晚饭时,一家人来到一个小饭馆里,小男孩肠胃不好,不想吃饭,爸爸抱着他,买回一些虎皮蛋糕,帮他脱了鞋,让他把脚平放到两个拼在一起的长条木凳上。水圈儿小口小口的吃着蛋糕,饭后,他们来到桥上散步,一个瘦削的,腰板直直的,留着白胡子的老爷爷推着一辆童车经过他们身边,车里的婴儿把下巴搁在车沿上,转过来,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爸爸向它耸了耸眉头,挤了挤眼。他们过了桥,来到县城的灯光球场上,那儿人们手拉着手在打歌……再从桥上往回走时,桥头已亮起了晕黄的灯,水圈儿甩着手大步走着。停了一下,回头问爸爸:“今晚你领我睡,好不?”。忙碌的爸爸很长时间没有领宝宝了。回到旅馆,上楼梯时水圈儿不让妈妈牵他,把手愉快地递给了爸爸。
也许,光阴能够倒转,当我们在某个时候,在某条河丢下一块石头,扩出无数个水圈儿时,那些曾在生命中下过的期许,那些曾经美好的时光,正奔跑着、跳跃着,向我们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