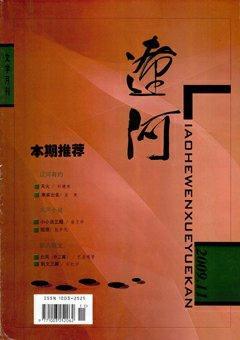故乡四题
李忠义
故乡上梁
在故乡,上梁是项古老的传统仪式,那庄重热闹的气氛不亚于小伙子结婚娶媳妇。童年记忆里,每次上梁都会热闹整个村庄。“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和木匠师傅的吆喝声宛如一曲没有节奏的大合唱,乐坏了的不单单是新房的主人。
故乡上梁多在早晨,房主一家最先打破了全村的静谧。男人扒拉着指头数算着帮工的人数,一趟又一趟倒弄着上梁用的家什;女人手忙脚乱地打点着该准备的饭菜,哈欠连天地不时伸几下懒腰。“他娘,小饽饽装好了?”男人问道。“还得再借几斤烧酒。”女人自言自语。好不容易盖几间房子,他们可不想上梁的时候掉链子,儿子等着娶媳妇呢。村庄升起袅袅炊烟,街上有了走动的人影,主人也收拾得差不多了。那年代村里一年盖不上几幢房子,上梁的消息立马风一样传遍全村。扛着铁锨前来帮工的男人、吐口唾沫抹抹头发的女人、睡眼蒙眬顶着鼻涕的孩子,不约而同地涌向尚未完工的新房。房前屋后全都是人,最兴奋的还属那些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的半大小子。成年累月碰不着件喜庆事儿,他们跃跃欲试地等候着热闹时刻的到来。我第一次经历上梁是我们自己家盖新房,我依稀记得那个寒冷的冬晨妈妈抱着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热闹,记得爷爷用皮袄兜着个大饽饽乐颠颠地往家跑。那年我四五岁。上梁的讲究很多,找人看好上梁的日子时辰摆在第一位。上梁前,新房中央的供桌上摆着大饽饽,有鱼、佛手、神虫,据说各有各的讲究。男主人点香、烧纸、磕头,祭天、祭地、祭祖,真有点过年的味道。那虔诚庄重的神色,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大人大声呵斥孩子,生怕破坏了这烟雾缭绕的氛围。供桌旁那块叫做脊印的木头上蒙着红布,像准备出嫁的新娘静静地等着良辰吉时。鞭炮声起,木匠师傅成了主角,开始粗犷响亮地唱梁,先是——
一头高,一头低,
好像凤凰展翅起,
凤凰不落无宝地,
今天落到你家里。
……
脊印木缓缓地拉上房顶,木匠师傅“啪啪”两斧头结结实实地按在两边的梁架上。红布随风摆动,众人齐声喝彩。此时,放鞭炮的人最神气,擎着荡拉着鞭炮的秆子在屋檐上走来走去,等到还剩下三四个鞭猛地把秆子扔到屋下。众人四处躲闪,大人粗野地嘻骂,孩子满脸欢喜地弯腰拣鞭。木匠师傅接着唱——
三支香烧的强,
一辈出个状元郎。
烧了香,快点酒,
日子过得年年有。
点完酒,就磕头,
一年一座大高楼。
直唱得主人眉开眼笑,旁观者阵阵叫好。木匠唱梁其实没有固定的词儿,嘴巧的木匠很多时候也现编现卖,只要押韵合辙顺口好记就能赢得掌声。就说我们村里的贫困户李洪俊家上梁吧,木匠就唱:“华主席领导强,洪俊也能盖新房。”那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当主席,木匠的唱词赋予了新内容。不过木匠唱到这分上,人们明白最具代表性的扔饽饽仪式就要开始了,这是上梁过程最火爆的场面。你看,木匠提溜着红布包着的大饽饽唱开了——
当家的注意啦
东不打西不打
先打当家的头一把
抱着饽饽往家跑
一步一个大元宝
主人张着长长的衣襟老早就在下面仰头望着,大饽饽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稳稳当当地落在衣襟上。“快跑、快跑……”在人们的叫喊声中,主人双手抱着大饽饽头往家跑,步子迈得比什么时候都轻快。
“快扔,快扔!”等急了的孩子们齐朝木匠喊。
“往这边扔,往这边扔。”唧唧喳喳的女人不甘落后。木匠倒是不慌不忙,东瞅西望,故意吊人们的胃口。木匠把四个稍大点的喜饽饽使劲地扔向四个方向,人们猜摸着喜饽饽落地的位置“呼啦”地抢过去。万一木匠“使坏”饽饽扔进泥窝里,把不住步子的人一准弄个泥水淋漓。胜者为王,扬着手里的饽饽引来诸多羡慕的眼光。小饽饽一把一把分散地扔下来,人群一阵欢呼,眼准身高的跃身去接,更多的还是得去争抢。孩子们跑来跑去活跃得要命,抢到的紧紧攥在手里生怕被人抢去;就要到手的小饽饽冷不丁被别人抢走,懊恼遗憾的神情刻在脸上。那年那月小饽饽数量依男主人的年龄而定,也就五十个、六十个的景儿。近水楼台先得月,木匠装几个、屋顶上的人讨几个,剩下的才会扔出去。如此,抢不到小饽饽的孩子还是多数,看着木匠斗口朝下表示没有了的举动,孩子们吧嗒着嘴悻悻地散去。村里上梁我必去, 十有八九是高高兴兴去满身泥水空手而归。还好,疼我的奶奶每次都事先为我准备块饽饽,让我破涕而笑。后来,三叔成了木匠,偶尔捎给我三两个小饽饽,一度成为我骄傲和炫耀的本钱。
上梁蕴涵着村人数不清的祝福。忙忙活活抢什么?要的就是个喜庆,图的就是个热闹,盼的就是那个吉利。听说故乡现在上梁比以前还庄重,木匠唱梁的词儿更鲜亮。主人准备的小饽饽成百上千,扔的还有烟、糖和硬币。不过,来抢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故乡的冬天
风少了往日的温柔,渐渐变得干硬清冽起来,夹杂着沙土枯叶在故乡或长或短或宽或窄的胡同里兜来兜去。该收的都收了,该种的也都种了,农活绝了。田野空旷,草木枯萎,麦苗成了人们视野里少有的绿色。冷不丁就在某个早晨,屋顶、树枝、院落里的家什都挂上了白色。人们哈口气冒“白烟”了,出门得抄着手了。冬天,就这样走进了故乡。
故乡的冬天长长的,九九八十一天。树叶先落,路旁的杨树、墙外的梧桐、河边的垂柳,几场霜下来叶子便落了精光,剩下的只有些瘦骨伶仃的枝条了。如同人脱光了衣服,在瑟瑟的寒风中飘曳、摆动。劳燕业已南归,唯有“喳喳”叫的麻雀,这些灰褐色的小精灵或展翅飞翔或四处张望,或啁啁啾啾唱一支欢快的曲子。也有两三只在一起戏耍,互相啄吻着,或挠痒痒似的钻进另一只的羽毛里不停地蹭来蹭去.这也算是冬天的一道风景了。“一九、二九不算九,三九、四九冻破石头”,说的是气温的变化。石头不见得冻破,待到三九、四九,气温却骤然降了下来,凛冽的硬风贴着地皮直往人的裤腿里钻,抄着手的大人孩子不时呵两口热气揉揉耳朵。屋檐上瓦棱下吊出许多半尺长的冰棒棒,调皮的孩子举着棍子戳下几根,像夏天里“咯嘣、咯嘣”地吃着冰棍,少不了招来大人的呵斥。晴天,晌午,冰棒棒冒着缕缕“热气”消融,屋檐下汇起浅浅的水湾。偶有几根“吧嗒”掉到地上,引来孩子们的你争我夺。早晨,井沿上是人最多的地方,全是些挑水的汉子。“天真冷!”“可不是嘛,广播里说明天还冷呢。”你一句,我一句,问答极随意,可都离不开天冷这个话题,像是彼此的问候,也像是对天冷的感叹。拔水,挂钩,上肩,粗犷的汉子身子多了些许笨拙,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滑滑溜溜的冰层。遇到那些心急的站不稳,刚拔上来的水桶“咣”地歪倒,立马“水漫金山”。“他娘的,倒霉。”哈哈手,接着再来。一个早晨,你走了我来了,一拨又一拨。井沿上的冰又厚了许多,十天半月化不了。
下雪的冬天最有味道,没有雪的冬天让人乏味。故乡的冬天总要下几场雪的。瑞雪兆丰年,庄稼人眼里的雪花是好兆头,雪越大越能象征来年好收成。面对漫天飞舞的雪花,他们郁闷的心境变得开朗,开始盘算起又一个忙碌的好年景。雪常常在冬夜悄然而至,一夜工夫,整个山村便白了。屋上白了,树上白了,墙头上白了,柴火垛上白了,院子里、胡同里、原野上全白了。远处的山川河流,近处的田野树林,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远远望去,“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意境油然而生。庄稼人对雪是虔诚的,即便扫起的雪也要堆在树下,或是推送到麦田里。太阳出来了,雪镶上了一层金边。缺少闲清雅致的庄稼人也纷纷走出村外,走向田间小路,领略自然风光,追忆起那纯朴天真的童年梦,忘掉了一切繁琐杂务,忘掉了一切烦恼忧愁,心里一片纯净,一片空明。他们的希望,好像就蕴藏在这一场场或大或小或厚或薄的白雪里。
没风没雪的日子,故乡会出现难得的好天气。冬天的太阳温和,即便打着眼罩向上望,一点也不耀眼。红红的日头翻过村东那座山,一点一点地上升。阳光照下来,村头巷尾的麦秸垛就金灿灿一片了,暖融融的。老人喜欢在这样的天气出来晒太阳。看惯了自己的牛吃草嚼料的贪馋样,听惯了驴儿咀嚼草料的咯嘣咯嘣的脆响的声音,厌烦了老婆子无休止的唠叨,整日憋闷得慌。于是,他们叼着旱烟袋出门,三三两两地往朝阳的地方聚拢。晒太阳的老人无定数,三两个,四五个,再多的时候也有,或蹲、或坐、或倚。旱烟叶子是少抽不了的,吧嗒吧嗒连吸几口,粗粝呛眼的辣味儿就和着浓重的烟雾升腾起来。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谁家的猪昨晚下崽了,谁家的孩子出息了,自己看到的、道听途说的,自己认为新鲜的就有心无心地说出来。有趣的话题,引来阵阵夹杂着咳嗽的笑声;有时候,你瞪眼睛我竖胡子的争论也避免不了,老人们熟谙彼此的秉性就像谙熟自己手掌里的老茧。忆昔日的艰辛,叹时光的短暂,一片青天下一方水土里一起出生,当年光着屁股下河甩了汗衫上树摸泥鳅套知了,如今头白了腰弯了,声声叹息:“唉,老了!”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故乡的冬天,有着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
故乡过年
进了腊月门,故乡的大街小巷便开始弥漫着过年的气息。猪年说猪鼠年话鼠,新年眼瞅着一天天近了。庄稼人停下了地里的活计,大姑娘小伙子大包小包地往家赶。男人忙碌着置备年货,女人则该洗的洗该浆的浆,新年仿佛就在眼前。
乡村的集市热闹。设摊摆点的商贩,你来我往的人流,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庄稼人难得闲暇,辛辛苦苦耕耘,勒紧腰带积攒一年,图的就是腊月集上潇洒一阵。鞭炮、对联、年画、蜡烛不能少,土香、烧纸祭祖时必备。五天一个集,夜里睡不着觉,就划算着要买的东西。给孩子扯身新衣裳,为老人买顶棉帽子。天暖,鸡、鱼、肉的,挨到最后一个集也晚不了。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珠忙着呢,瞧瞧这摸摸那,恨不得把整个集市搬回家。鞭炮市上摆起了擂台,“点了,正宗的潍县大鞭!”、“看啊,咱的八十响!”摊主声嘶力竭地极力显摆自己的货色。你放我也放,鞭炮声此起彼伏,瞬间烟雾一片。“二大爷,置得挺齐全呀。”老汉捻着稀疏的胡子:“呵呵,过年嘛。”
过了腊八,年味渐渐浓了。挑个没风没雪的好天气,屋里屋外收拾个干净。屋里的盆盆罐罐条凳茶几全搬到天井里,仔细擦拭;竹竿上绑着笤帚,天棚屋顶扫个遍,边边角角里的蜘蛛网、老鼠屎荡然无存。腊月二十三是辞灶,点上香、烧上纸、摆上供品,恭送灶王爷升天,期盼他老人家能“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保佑一家老小平安。此后几天才真的是忙年。女人开始做过年的大饽饽,用力地搓用力地揉,这样做出来的饽饽才白才有劲道。男人自然也不会闲着,自家养的鸡、鸭宰上几只,拔毛剖肚拾掇得利利索索,挂到屋檐下的橛子上冻着。猪下水乃下酒的好菜,猪头上的毛择得光光的,猪肠子洗了一遍又一遍,清水大料一起在锅里“咕噜、咕噜”地翻滚,满屋很快飘溢着诱人的肉香。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对联贴上门,大大的“福”字贴在影壁墙上,大红灯笼高高挂,门框上花花绿绿的“过门钱”随风飘曳。这营生多在腊月二十八九进行,对联早就准备中了,集上买的或是特意请人写的,全是赏心悦目的喜庆词。“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户户金花报喜,家家紫燕迎春”,蕴藏着庄稼人对来年的希望和祝愿。“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捣弄生意人家的对联别具一格;猪圈、牲口棚,墙上的“肥猪满圈”、“六畜兴旺”赫然在目。“人过年,牲畜也过年啊!”老者叹曰。
腊月三十过大年。这天的人们分外忙碌,顾不上贪恋热乎乎的被窝,早早起床了。男人挂祖影挂财神扫院子,水缸挑得满满的;女人开始准备新年的吃食,翻箱倒柜找出孩子们的新衣裳。清闲的是那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兜里装着小鞭,满街地找伙伴们炫耀,不时地传来一声脆响和阵阵的笑声。落雪的年,便多了一份踏雪寻梅的野趣和雅趣,多了一份琼楼玉宇的纯情和深情。大人少了往日的严肃,不住地叮咛孩子,过年要说吉利话,“死”呀“完了”之类的话千万不能说。日头刚落山,荒郊野外、山坡岭地上的人多起来,那是先人们居住的地方。同宗同族的人点香烧纸磕头,祭拜先人。庄重,肃穆。一时间,鞭炮齐鸣,炮仗震天,临行喊上几声:“老爹老妈,回家过年啦。”
晚饭后守岁。“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下象棋玩扑克,兴趣盎然地嗑着瓜子看着赵本山们的“忽悠”,就等着新年钟声的响起来。满心喜悦的孩子眼睛睁得大大的,一会儿可能便哈欠连天倒头睡去,梦里还等着大人的压岁钱呢。十二点不到,村里响起零星的鞭炮声,心急的人家开始“发纸”了。先是一家、两家……很快便是鞭炮声一片。大红的蜡烛映照着主人虔诚的脸,插着大枣的饽饽摆在眼前。作揖,磕头,告诉列祖列宗过年了。热气腾腾的“古扎”(饺子)端上饭桌,地地道道的年夜饭。碗筷撤还没撤下桌,拜年的人就进屋了:“爷爷奶奶,过年好!”“好好,坐坐。”满脸的笑容。一拨又一拨,问候的话一遍又一遍。拜年讲究大着呢,先拜辈分最高的,再拜跟自己父母平辈的,同宗同祖的所有长辈拜下来,差不多得到第二天上午。
新年,到处是喜庆到处是欢乐。锣鼓敲起来,秧歌扭起来,年味变得更浓。“初一初二拜姑姑,初三初四拜丈母”,趁这空闲趁这时间,走走亲访访友。啦啦知心呱,叙叙节日情,喝个过年酒,路上走亲戚的络绎不绝。
“耍正月,闹二月,痛痛快快到三月”,这俗语在故乡人的嘴上挂了多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如今的故乡人惜时如金,不出正月十五,就下地的下地,打工的打工,热闹了一阵子的乡村回归于平静。
故乡的光荣灯
一盏灯在心里亮了多年,一段情让我久久难忘。忽明忽暗的灯光如星星闪烁在空旷的田野,“咚锵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震撼着我幼小的心灵。我迎着刺骨的寒风和飘曳的雪花,把光荣灯紧紧提在手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故乡,每逢过年村里都要给当兵的人家送灯。那年月当兵特吃香。也是啊,原本土里爬土里滚的庄户小伙子到了部队,三年两年回来探家样子就变了。随便走到那里,腚前腚后满是看光景的孩子。草绿色的军装板板正正,见人说话“撇腔拉韵”,连挑水的姿势都耐看了。偶有谁从部队捎回几个子弹壳或炮弹皮,更能轰动全村。一向装腔作势的大队干部也会主动上门,酒盅一端,小酒一喝,毕恭毕敬地听人家啦外面的世界。也有闹出笑话的。在村里喂牲口的李老汉去部队看望儿子,回来就提着儿子的乳名嚷开了:“俺家虎,骑大马,‘咯哒、咯哒到越南了。”一个上学的孩子问:“大爷,越南在哪里?”老汉无言以对,其实他儿子在河南当兵。农村人重实际当兵的好找媳妇,在家种地找媳妇困难,当上兵提亲的保准挤破门,我二舅是个例子。那年月当兵的人家叫光荣人家,灯自然就是光荣灯了。当兵成了庄户小伙梦寐以求的事儿。
送灯安排在大年三十傍晚。灯自然要提前做好的,精心扎制的架子,红纸糊的罩子上缀着穗子,煞是好看。这还不算什么,难得的是那锣鼓声增加了过年的喜庆气氛。落满灰尘的锣鼓家什找出来,双双握惯锄把子的手敲打起来,先是参差不齐,后再慢慢上套,听起来也蛮像那么回事。祖坟上完,晚饭吃过,天已傍黑,送灯就开始了。寂静的山村热闹起来。村人出奇地默契,不约而同走出家门,喜欢热闹的大人孩子加入送灯行列,行动不便的老人乐呵呵站在门口观望。大队干部领头,敲锣鼓的跟上,提灯的孩子……足有长长的一溜。路线没有章法,走大街、穿小巷,一路欢笑一路热闹,连狗叫的也跟往常不一样。灯送到人家大门口总会热闹一阵,此时的锣鼓敲得更响。最最开心自豪的是当兵者的家人了,早早候在外面笑呵呵地接受着村人的祝福和祝愿。尤其那些辈分小的人家,光荣灯接到手,光荣牌钉到门框上,笑得皱纹都平了。遇到接着立功喜报的人家,笨嘴拙舌的干部也会喋喋不休地说上些过年话,好像人家当兵沾了大多大的光,俨然立功的就是他自己。一家再一家,挨家挨户送完,整个村子也差不多转遍了。
僧多粥少。村里当兵的大概有七八个,光荣灯自然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记忆里提灯的都是干部以及他们近亲好邻家的孩子,那份光荣、那份荣耀,羡慕的我要命。更多的孩子只有凑热闹的份了,放个“二踢脚”、使劲地跺几只摔鞭,引来不少的笑声。我属凑热闹的之列,亲手提提光荣灯曾是我的梦想。终于还是有过唯一的一次机会,那年村里又多了个当兵的。他家住在远离村子的一个山沟里,大概有三公里多。那天的雪下得大,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走去路来“咯吱咯吱”响。不知道因为路远怕冷还是时间太晚,那个提灯的孩子把最后一个光荣灯递给了我。热闹的人群剩下稀稀拉拉的五六个人,依然响亮的还是那锣鼓声。如同酷暑天喝了碗凉开水,那种舒坦啊,我恨不得蹦几个高。任凭雪花扑面,温暖的是我的心窝。周围村落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地响着,回家的时候可是真正的除夕了,满家人都在等我吃过年饺子呢。
此情难忘。光荣的当兵人家,诱人的光荣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