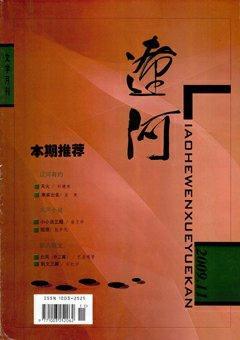离家出走
吴 亮
实在是恶俗的一个开头。想来点新鲜的也不行。
这个让陈广荣敬畏了二十一年的女人,就在这午夜时分像天外来客一样,不可思议地出现在他们床前。李艳茹是一个少有的沉着镇定的主儿,她目标明确地冲上来,第一件事便是一把抱起床头柜上的一堆混乱的男女衣物,直奔窗前,像发放救灾物资一样将它们毫不犹豫地泼到外面,一时间,女人的胸罩、男人的内裤飞舞在空中。李艳茹对这对刚刚被惊醒坐起、目瞪口呆的奸夫淫妇很轻蔑地浮出一丝冷笑,转身走了。
到中午的时候,从外面回来的李艳茹发现陈广荣不见了。当然不见了的还有保姆美菊。
李艳茹怔怔地在卧室大衣柜前面立了半晌。这里一片狼藉,像是刚刚被打劫,留有搏斗痕迹。电话适时地响了。
电话那头没人说话,但能听到嘈杂的市声。
李艳茹面无表情地说:“你想怎么样?”
陈广荣在电话那头说:“我要离婚。”
李艳茹冷笑一声:“那还要看我高兴不高兴呢。”
“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一定要离。”
“做梦!死都别想!”
“好,好,”陈广荣咬了咬牙,坚定地说,“你一天不答应,我一天不回去!”
李艳茹刚要吼一声“你以为你是谁”之类,电话已经重重地扣下,把她愤怒的语言生生卡在了嗓子眼儿里。她要崩溃了!她要崩溃了!她浑身冰冷,把电话重新拿起来,用颤抖得厉害的手指拨了几个熟悉的数字,那头传来一声甜美的女孩声音:“爸!”
“你那不要脸的爸跟保姆跑了——”李艳茹本来是想富有震撼力地向女儿宣布这一可恨的外遇事件的,可不知怎的竟带上了颤音,连自己都听出来了,她想哭,她想哭啊!索性,她拉开了嗓子,像没有文化的市井女人一般号啕大哭起来:
……
打完那个要求离婚的电话以后,陈广荣就拖着个大皮箱茫然地站到了街沿上。心里有些惴惴不安。这冒险来得太突然太干脆,也许早就在心里盼望着,但从来没想过付诸行动。就因为昨晚的疏忽,把十几年的犹豫一脚踢开了,他终于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离开那个家,离开李艳茹,离开她的控制范围。
没想到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
美菊匆匆跑来,她找到了一个熟识的小姐妹,可以暂时投奔的。陈广荣虽有朋友,却一个也不敢联系,怕李艳茹找上门去,也怕朋友不理解,惹出些是非。既是出走,就要走得干净,和自己的过往完全了断。
他们并没有走远,仍然在这座城市里。一座城市的容量是如此之大,大街大楼之外,有无数毛细血管般的小巷、偏僻的角落、沉默的旧房子,陈广荣发现有太多细节隐匿在城市深处,而在这里待了十几年了,自己却从未察觉。
美菊的小姐妹叫莎莎,在一家名声不太好的发廊做事,染黄的头发打理成乱草模样,左边耳朵套了五个亮闪闪的小耳环,睡眼惺忪地在前面带路,一边抱怨他们这么早就把自己吵起来,而她通常是下午三四点钟才起床的。走的是条夹缝样的小巷子,路窄,两边的房子差点门脸碰门脸,垃圾堆在路中间,一位强悍的妇女从屋里冲出来,把一桶形迹可疑的水泼到路上,然而也有“滋滋”的炒菜声与香气扑面而来,还有麻将声,小孩的哭声……莎莎一直在走,一直在唠叨,跟在她后面走的时间越长,陈广荣就觉得自己藏得越深,所谓“大隐隐于市”啊。
最后他们来到一扇门前,这门属于一幢一楼一底的旧式木楼,这楼像是硬掐进来的,在左邻右舍的夹击下挤得很费劲似的,都有点倾斜了。从门里出来一个勾腰驼背的小伙子,歪着脑袋盯着他们。莎莎说:“二皮!你个狗日的今天还老实喔,没出去死晃?”二皮就嘿嘿一笑,做了个打哈欠的动作:“哎呀,昨晚上把钱输完了,拿个卵子本钱出去晃哟。”莎莎指指美菊他们:“这是我的结拜姐妹,那是她老公,两个人刚从老家过来,还没得地方住,你把楼上姑婆那间屋租给他们怎么样?”二皮仗着和美菊不相识,直截了当地问:“给好多钱?”莎莎“啪”的一巴掌拍到他肩膀上:“死二皮!三百顶天了!”末了讨价还价,终于说好月租三百五十块。
楼上那间屋是二皮的老姑婆生前住的,屋里留有老年人特有的陈腐气息,家具物件黑沉沉的。陈广荣不自觉地皱皱眉,美菊却已经喜滋滋地收拾开了,扫地除尘,抹桌铺床,她很有兴致似的,因为这次不是为雇主干活,而是为自己,为刚刚展示在眼前的新生活。
陈广荣像被人打过一顿,软绵绵地趴在窗台上。他不像美菊那么容易快乐,而难以适应从昨夜到现在这十几个钟头内的变化。昨天他还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有二十一年婚史,有老婆有女儿,名下还有家小饭店,完全由老婆打理着,他是个有闲钱有闲情的大老爷,顷刻之间,他变成了一个婚姻的叛逃者,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一个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经济上都要从零开始的中年人。若不是被李艳茹泼洒衣服的壮举给刺激了一下,也许他一辈子也不会离家出走。
“……他做了亏心事,我一没打,二没闹,可倒好,他居然敢跟我提离婚!他敢哪!”李艳茹死死捧着一个纸巾盒,像捧着杜十娘的百宝箱,伤伤心心地对着它诉说,对着它号哭,不停地从盒子里抽出面巾纸擦眼泪鼻涕。
女儿陈佳敏坐在靠墙的地板上,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
“……老不要脸的跟小不要脸的跑啦!呜呜……他以为他才十七八岁啊,还私奔!呸!”
佳敏感觉到难以名状的烦闷,像初夏时期突如其来的溽热,憋得人心慌。她用双手抱住腿,头也不抬地问:“你真的就没有吵?没有闹?没有冲上去打人?”她脑海里浮现出三个胖男胖女打架的场面,有如重量级拳王争霸赛。
李艳茹的哭声收住一点,委屈地点点头:“就是没有么。”
佳敏心里说:这可不像你啊。
她妈妈像是听到了,辩解道:“我只想警告一下他们,叫他们晓得,我不是被蒙在鼓里的!”她又放低了声音,“我又没想和你爸离婚。”
佳敏敏感地想到了家里开的饭店。“仁和酒家”。好名字。招牌菜是“淑女四喜”。小有名气。怎么说也是两口子早年共同创下的基业,就算现在只是老婆一人在管理,好歹也是夫妻共同财产。依着李艳茹的脾气,要把这酒家分一半出来,倒不如拿刀把她脖子抹了。
“放心,他那个胆子,走不远的,再说他离了你,哪有钱啊?不出一星期就得回来。”佳敏很肯定。她所担心的是,回来以后又怎么办?
佳敏是请了假赶回来的,只待了半天就得回学校了。在对她妈千叮咛万嘱咐之后她走出了家门。在楼下,她蓦然看见对面一幢平房的房顶上,办展览一般躺着几件男女衣物,其中一件水红色的棉睡裙,是她妈妈淘汰下来送给保姆美菊的,现在这睡裙惨兮兮地卧在那儿,有家也回不去的样子,用另一种语言向佳敏申诉。
傻不傻啊?佳敏在心里怪她妈,这一招比打他骂他还狠,他那张脸,在这家还撑得下去?
转念她又想,不对啊,明明是他陈广荣犯了错,凭什么要给他面子?
陈广荣比他女儿估计的生存能力要强很多。
一周过去了。
又是一周。
然后是一个月。
这些日子他们几乎就关在租来的小屋里,很多时候,他们把门窗紧闭,吃的喝的备好放在床头,像馋嘴的小孩一样,整天整天地黏在一起。以前有李艳茹在家里,两人难得搂个腰亲个嘴的,做什么都像做贼似的,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任意发挥了,都觉得这是私奔的最大意义所在,都很兴奋很疯狂。
高兴的时候他们便理想化地勾画未来的蓝图。按陈广荣的规划,等哪天和李艳茹把婚离了,夫妻共同财产对半划分,那么他们就有至少五十万块钱(其实陈广荣估计应该有九十万,但他不想让美菊知道这么多),把这五十万拿到他熟识的一个朋友开的公司里去入股,他们以后什么都不干,每年光吃分红就够了。
远大理想鼓舞着他们的斗志,像迷魂汤一样,在新生活最初的日子里把他们灌得晕晕乎乎。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带出来的钱剩得不多了。
陈广荣有些着急了,要更长时间地对抗下去,他必须得找份工作,坐吃山空啊。可这里住的人大多都是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做的都是擦皮鞋啊蹬三轮啊一类的低档工作,陈广荣不愿意干。
美菊每天晚上都要把他们带出来的钱从头到尾地数一遍,这成了她特殊的消遣方式。开始钱还厚实点,数的时间长,数得很快乐,可一天天的,钱越来越少,数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她也有了莫名的慌张,于是再数一遍,又再数一遍。美菊还是留了点心思的,她把自己这些年当保姆挣的钱放在一边没有动,只花陈广荣的钱。还好陈广荣没有在意,他一向都是老婆打理钱财,在这方面是比较马虎的,再说他也认为应该男人拿钱出来养女人。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美菊把手上的几张钞票翻来覆去地捏弄半天,叹口气说:“我还是出去打点零工吧。”
陈广荣吓了一跳,忙说:“那怎么行?那怎么行?我把你带出来就是要你不再受苦受累的!”
美菊感激地一笑,随即又皱眉,看看手里的钱。陈广荣一把握住她的手,像入党宣誓一般庄严地说:
“明天我就去找工作,再苦再累的活儿都干。”
这句话之后第三天——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天,陈广荣终于在过了九年完全靠老婆供养的寄生虫日子之后,第一次找到了一份工作,而这时他们距离一穷二白的日子只有八十三块七角钱。
他的工作是帮巷口一对卖水果的老夫妇运货。老夫妇年纪大了,装货卸货蹬三轮都吃力,便雇了陈广荣。陈广荣就要在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简单洗漱一番后赶到老夫妇那儿,骑三轮车带着老头或老太太去水果批发市场,在老头或老太太一番挑挑选选讨价还价后帮着把水果扛到三轮车上,再把水果和老人一起拉回水果摊,一样一样地卸下鲜水果,一天的工作就算完了。这样每月可以挣两百块钱。
就这两百块,他挣得特别辛苦。也许换个农民工不会觉得辛苦,可他是陈广荣,从大富大贵的日子走过来的,每一份力都出得比别人沉重,比别人复杂。有一天早上下雨,雨倒不大,但天气凉津津的,格外催人入睡,陈广荣在床上翻了几个身都不想起来,差不多是美菊把他踢下床的。陈广荣没雨披,打着伞到了老夫妇那儿,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催着他上路。陈广荣小心地跟他们借雨披,老头特不高兴地说:“怎么自己不预备呢?”在屋里搜罗片刻,扔给陈广荣一个装水果的大塑料袋。那天陈广荣就是头上套着这个大塑料袋去拉的货。雨从塑料袋上滑下来,正好灌进他衣领里,贴着皮肉地冷,很具体地冷。那天头上套着塑料袋的陈广荣心情坏透了,他一边蹬着车一边咬牙切齿地想:明天再来我就是猪头,明天再来我就是猪头……
但是到了明天他还是当了猪头。好歹是份工作。
月底的时候,二皮来收房租,陈广荣他们才发现这个月居然忘了这一项重要支出。把钱拿出来数数,虽然挣了两百,但吃喝拉撒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美菊赖皮地将一把零钱摊在手上,送到二皮面前说:“看嘛,就剩这些了。”
二皮就有些恼了,说:“莫以为我二皮是脓包,给老子来这手!老子跟你们说,早就有人在议论,说你们两个是杀人嫌疑犯,连门都不敢出,只有我二皮讲义气收留你们,哪天惹毛了老子把你们押到公安局,也挣个几万举报费!懂不懂?下周把钱交齐!”
说完,二皮在那把零钱里挑了张面额最大的贰拾元,愤愤地出去了。
屋里的两个人面面相觑。美菊好半天才说:
“听到没有,把我们当杀人犯了!”
佳敏从放暑假的第二天就开始了漫长的搜寻工作。
李艳茹先前跟别人解释说,陈广荣到东北考察一个投资项目去了,后来时间长一点,就说他在那边和别人合伙做生意了。如果他一辈子不回来,李艳茹会永不停止地给他编派各种借口,让他在虚无中维持着一个家庭的颜面。几个月以来,她每天走在街上都会下意识地东张西望,总希望在某个时候能一眼看到那个让她气得胸口发痛的男人,但真正的搜寻行动她却不能参加,以防被人看出破绽。
只有佳敏出马。佳敏早想好了,如果在她满大街地闲逛、打听时碰到熟人,就说自己在搞一项社会调查。大学生嘛,谁会怀疑呢?
但是找一个人就像在一堆蚂蚁里找出某一只蚂蚁一样,简直就无从下手。佳敏唯一的线索就来源于陈广荣给她打过的三个电话。三次都是晚上休息时打到她大学宿舍里的。陈广荣很喜欢这个女儿,舍不得放下她,每次都会跟她说,我和你妈妈的事你莫管,我们自己解决,你也成年了,马上毕业工作了,不存在跟哪个生活的问题,我就想和你说说话……
他没打佳敏的手机,想来是害怕让她看见号码,可他没有想到佳敏宿舍里的电话就有来电显示,佳敏把号码记下来了,三次都是同一个号码。这个号码能说明什么呢?第一,从区号看,他并没有离开那座城市;第二,号码头两个数字说明,他在城市的东边,像是龙湖区一带;第三,每次电话里都有嘈杂的声音,说明是在户外的公用电话,而且三次都用同一部,陈广荣一定常在这电话附近活动。佳敏为自己的分析能力暗自得意,她最得意的是居然捕捉到一个细节:最后那次通电话,她听到电话的背景声音里有一个女人用本地方言高亢地喊:“三埠桥——三埠桥——走不走——”然后是汽车发动的声音。分明是一辆开往三埠桥的 “野面的”在拉客。
一般城市里的“野面的”行驶的路线会和公交路线重合,这样才能与公交车争抢客源。佳敏把地图拿来研究了半天,找出了三条从龙湖区经过、到达三埠桥的公交路线。在三条路线中,位于龙湖区境内的路段都被佳敏用红色油彩笔重重地描画了一遍。这就是佳敏本次暑假“社会调查”的活动范围。
事实证明,陈佳敏是个相当具有毅力与耐力的现代女性。她每天背着一个旅行背包,里面装着地图、雨伞、饮料、钱包和各种零食,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勤勤恳恳地穿梭在龙湖区一带的小街小巷里。她从不放过公交车沿线的公共电话亭,每到一处,就把公话亭里的话机摘下来,拨打自己的手机号,从手机上查看这个号码是不是陈广荣曾经打过来的那个。这个工作需要无比的耐心、细致,需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勇气,陈佳敏把这一切都装在包里挎在肩上了。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一天近中午的时候,佳敏在一个街角的小公用电话亭,找到了那部电话。为了让自己相信,她不停地用这部电话拨打自己的手机,一遍又一遍,让那一串数字清晰无误地久久显示在手机屏幕上。她挂上电话时,身子也随之靠在了话机上,浑身疲惫。
佳敏打算休息一下。目标找到了,下一步的工作就要简单一些:以这个电话亭为圆心,在周围一带搜寻。街对面正好有家小茶馆,佳敏到那儿占了个靠窗的位置,慢慢啜着一碗劣质茉莉花茶,舒展着一个星期以来的焦虑情绪。碰巧的事情发生了。佳敏无意中扭头看出去,只见那电话亭旁边的一个小巷口里走出一个人,正是端了一碗甜面酱急匆匆赶路的美菊。
陈广荣正在和二皮吵架。
还是因为房租的事情。陈广荣要求把交房租的期限往后推延一点,二皮就火了。二皮就是脾气不好,他容易上火,一上火话就不好听,他说,胖子,老子不跟你拖时间,你这把年纪了,几拖几拖就进棺材了,老子找哪个收房钱?
陈广荣气得要命,指着二皮骂娘,正闹着,美菊回来了,把那碗甜面酱往桌上一搁,毫不含糊地加入了战斗。美菊嗓门高敞,有压倒一切的阵势,二皮则在骂声中开始解开衣领、挽衣袖,用形体动作暗示他将采取的下一步骤。陈广荣见状,不顾一切地抢先把灶台上一个满是油污的锅铲据为己有,算是进行了战略武装。一场司空见惯的斗殴蓄势待发。
这时,正对着陈广荣手中的锅铲挥舞的方向,也就是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女孩。陈广荣把视线从锅铲移到她身上,就呆住了。
陈广荣有生以来第一次,以这种小市民的形象站在女儿陈佳敏面前。两个人都有些惊慌。佳敏是个懂事的女儿,她很快从惊慌中抽身出来,高高在上地问二皮:
“多少钱?”
她没说“欠”字。陈家大小姐,从来不屑于提这个字。
二皮看出一点端倪,撇撇嘴说三百五。
美菊马上更正:“三百三。”是说二皮上回已经拿了二十块钱走了。
佳敏从钱包里抽出四张一百元的钞票,用食指和中指夹着,正眼也不看地轻巧地递给二皮。二皮忙接过来,抽一下鼻子说:没零的找。
“不用找了,”佳敏傲气地说,“你出去,我们有话要说。”
二皮得意地拉拉衣服,转身走了。美菊偷偷观察佳敏的表情,知道自己在这里只有更难堪的,便低了头,把两个瓷碗摆到桌子上,沏上茶,然后不声不响地出门了。陈广荣红着脸,很客套地对佳敏说:坐吧,坐吧。
父女两个对坐着。佳敏一直不开口。她觉得说什么都没有意思,什么都不说,反而比说出来更有威慑力。陈广荣只有一句话:
“别告诉你妈我在这儿。”
自从找到陈广荣以后,陈佳敏就天天来找陈广荣了。她来找,也不说话,只闷头坐着。不管陈广荣看电视也好喝茶也好,好像都与她无关似的,她只管静坐示威,不吃不喝不说话。到时候了,她就背着包回去。第二天又来。
陈广荣感觉到女儿这一着比她妈厉害。她制造出一种无形的压力,无声的嘶叫,逼迫他投降。她是他心头最疼的人,这是带有苦肉计性质的逼迫。忽然有一天,陈广荣听到自己终于开口对佳敏说话了。其实陈广荣很久以来都酝酿着这么一次与女儿谈话的机会,话题都非常熟稔了,在想象中已经谈过好多次了。他一旦进入这个谈话的氛围,就从容不迫了。
“佳敏,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虚伪特别没责任感?”
佳敏不吭声,眼皮也不抬起来,只盯着面前的大碗茶。
“爸爸不想跟你解释什么。我只想说,我忍了二十一年,也虚伪了二十一年,不负责任了二十一年,现在才是我开始学会负责任的时候。以前不是我不想负责,不想真诚,而是你妈妈不让,她不让我好好做丈夫好好做父亲!”
“你也大了,有些事情应该让你知道了。其实,如果不是我跑出来,我一辈子也没有勇气把这话说给你听。
“你好好听着,这是我们这个家,最大的秘密了……”
他知道佳敏不会相信,或者说不愿相信。放在电视剧里,这情节一点都不新鲜,但落到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通人家里,这种事情是带着摧毁性质的丑闻。也许,每一个家庭里都会有这样那样不为人知的……丑闻吧?
要说,李艳茹很早就知道陈广荣和美菊的关系,有谁会相信呢?要说,李艳茹不但知道,甚至还默认了他俩的关系,又有谁会相信呢?
陈广荣和李艳茹是自由恋爱的。也就是说,他们曾经好过,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如果在那一阶段两个人就分手了,肯定都会把对方深爱与怀念一辈子。可惜他们不懂事地、很着急地结婚了,婚后又过了几年拮据却又甜蜜的日子。这时候,人们常说的经济大浪涌起来了,陈广荣两口子便开始了雄心壮志的创业。那真是个镀金时代,稍微肯冒一冒险的人最后都发起来了。他们倒腾了好些东一榔头西一棒的生意,终于在某一年下定决心开了一家饭店,这才算稳定下来。
他们渐渐有钱了。
人常说男人有钱就变坏。但是在陈广荣看来,在他们家正好相反。他暗暗发觉老婆李艳茹有些变化,这变化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只有特别熟悉她、亲近她的人才能感觉出来。她依然是笑眯眯的或是凶巴巴的,依然是穿着别致的西装套裙,依然每天记账查账检查厨房过问货源,但就是不对劲。这怀疑慢慢有了较清晰的方向,原来它来自于饭店的“总管”(大家都这么称呼)陆勇。
陆勇是个瘦小的男人,一点没有陈广荣魁梧、有气势,他看上去怎么也不会像个老板,最多就是个账房先生。这位陆先生在饭店里大权在握,除了陈广荣两口子,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就数他说话顶得了事。
李艳茹和陆勇的关系不一般,但陈广荣又抓不着哪条实际的证据来证明。他只能疑神疑鬼,找茬和李艳茹吵架,把心情弄得乱糟糟的。那一年,李艳茹为了家庭和睦所做的最大努力,便是不顾生意繁忙,坚持要了一个孩子,也就是现在的陈佳敏。可佳敏的出生并没改变生活的本质,陈广荣还是疑心。他不止一次地要求把陆勇辞掉,都被李艳茹挡住了,她说:现在这社会,哪去找这么能干又这么贴心的人?
陈广荣只好不吭声了。陆勇的工作真的没法挑刺儿,换个管账的人,说不定早就在女主人生孩子的节骨眼儿上趁乱卷款潜逃了,但陆勇不但没有,反而把工作做得更细致,让人更放心。
这不明不白的感觉折磨着陈广荣。女儿佳敏五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生病,李艳茹天天晚上都在女儿房间里陪孩子睡觉。有一天晚上,已经入睡的陈广荣听到女儿大声尖叫,他猛地惊醒,翻身跃起跑到女儿房间,矇眬中好像看到个黑影一闪而过,他问:“谁?”自然没人回答。冲到女儿房间,佳敏哭着说:“鬼!鬼……”李艳茹安慰她说:“哪有什么鬼?做噩梦了吧?”又跟陈广荣说:“没事,没事,她就是病还没好,脑子不清醒。”
第二天,陈广荣特意把佳敏抱到一旁,问她昨晚的事。佳敏低头说:“妈妈不让说……我看到一个鬼,和妈妈挤着睡,我一叫就不见了。”陈广荣惊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又问:“那个鬼长什么样儿?”佳敏说:“太黑看不清楚……有点像陆叔叔……”
陈广荣傻了。终于找到了证据。是个他不愿意出现、而且现在也拿不上桌面上来的证据。李艳茹会承认吗?不会,她只会说一个生病的睡眠状态下的小孩子,说的话有几分可信度?而且佳敏自己也不能肯定那个“鬼”就是陆勇。
老婆在和别人偷情,一天一天地,而他却生生地被欺负、被折磨,一分一秒地。他没有一点办法。
这才有了美菊。美菊是老早就进了陈家做保姆的,因为姿色中等,人也勤快,很得一家上下的欢心。陈广荣开始怎么也没有想过打她的主意,甚至有几次美菊主动的试探他都装着不懂——他本能地不喜欢和李艳茹一样体型的女人。但自从有“鬼”以后,陈广荣整天疑神疑鬼,终于触到了一根报复的神经。
对美菊的征服简直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非常简单,有一天晚上李艳茹和他吵了架,气冲冲地抓了几件衣物冲出门去。对外人说她是投奔一个女友去了,可落实到陈广荣脑子里便是他老婆夜会情人的场面,他气得肺都炸了!
这时,美菊披着衣服从房间里出来了,眼神里全是怯然,她小声地问:“李姐去哪里了?”陈广荣抬眼看着她。“陈哥你不睡吗?”这一句话出来,像把陈广荣五脏六腑都捏住了,他大声地、愤怒地嚷:“睡!睡!就兴她睡啊?老子也睡!”这个“睡”在后来才被理解,应该是“找人睡”的意思。因为陈广荣嚷完,就完全不像陈广荣了,他忽然变得行动敏捷作风果敢,一把拉了美菊就进了卧室。美菊连点象征性的娇羞都没铺垫下来,就实现了做陈广荣情人的梦想。
事后陈广荣曾经一度后悔,毕竟这违反了他陈广荣做人的原则。他悄悄拿钱出来给美菊,想做个了断,美菊倒是个人精,她不收钱。不收钱意味着你还欠她的。不收钱意味着她有别的想法。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淡淡地说:“我看李姐心也没在你身上,你又何苦守着她呢?”说得陈广荣又是好一阵发怔。这么犹犹豫豫的,两人真真假假地好上了。
陈广荣那时出轨出得不算彻底,只想把心头这口气狠狠出一出,出完了,就希望有谁拉他一把,那他也就纵身一跃,回头是岸了。这个拉他的人最好是李艳茹。但是李艳茹没有拉。很奇怪的,那么精明的女人,现在好像变得愚钝了,对老公视而不见了,陈广荣有一次故意让她远远看见他摸了美菊的屁股一把,可她竟然装着什么也没看见。第二天吃饭时,陈广荣又故意说,美菊这段时间太辛苦了,给她加点工资吧。李艳茹眼皮也不抬地说,那就加吧。
陈广荣死心了。对老婆死心的男人,不会轻易就把感情荒芜了,陈广荣现在要去找外遇,一时间也不会那么凑手,只有现成的一个美菊。好歹是近在眼前的。好歹是对自己巴心巴肠的。这才显出美菊的高明。
佳敏面无表情地走了。她不是那种不成熟的、动不动哭哭啼啼的小女孩,她的心思细细密密,严不透风,在得悉了家庭内幕报告以后她也一点没有冲动。她隐隐约约明白了父母为什么把她从小送到寄宿制的学校,她总是离家远远的,因为那个家,有着太多不愿让她了解的伤心内情。她一直只知道她的家庭令人羡慕:富有,和睦,风光……这是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连同她自己,也是这虚伪戏剧中的一角。
自从佳敏找到自己的藏身之处以来,陈广荣就日日夜夜提防着李艳茹打上门来大闹一通。他时常会在梦中惊醒,醒来后侧耳倾听楼下的动静。李艳茹一直没有来,佳敏消失了几天以后,倒是又上门来了。佳敏不可思议地给他们带来了一大袋生活用品,毛巾啊,餐纸啊,洗发香波啊。佳敏把这袋东西搁到桌上,面无表情地说,看你们东西备得不齐……我马上开学了。
美菊惊得像是看到了外星人,眼光直愣了。陈广荣也是一头雾水,他满怀疑虑地盯着女儿的一举一动,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直到佳敏出门了,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美菊说,八成是李艳茹要来了,你闺女是在稳住我们阵脚呢。陈广荣说,不会,佳敏是心疼她爸呢。
他觉得佳敏渐渐往自己这边靠了。
那天他送女儿出门,佳敏悄悄往他手心里塞了厚实的一卷钞票。
有了这卷钞票,陈广荣忽然恢复了对过去富贵日子的某些感觉,是热的,暖的,舒适的。他再也不愿工作了。他把钞票藏起来,每天还是出去晃一圈儿,假装去工作,月底从钞票里数出几张作为“工资”交给美菊。他宁愿穷一点,但是可以懒散点、自在点。再落魄也落不掉他大老爷的脾气。
陈广荣和美菊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了。过得有些艰苦。虽然李艳茹没有打上门来,但她的影子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美菊忍不住开始抱怨了,抱怨陈广荣是个胆小鬼,不敢回去找李艳茹离婚,只有这么一逃了之,逃又能逃几时呢?逃出来以前,虽然她是个保姆,虽然他们得偷偷摸摸的,但至少算是衣食无忧,现在呢,说自由也不自由,连吃饭都成问题了,一个大男人连个女人都养不活还敢带她私奔!哼!
美菊的头脑里一直都有个清晰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和陈广荣结婚,她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城里太太。美菊很清楚,凭自己高胖的体型与土气的相貌,能傍上陈广荣已经够运气了,只要抓牢了他,总有一天她会成为生活优越的阔太太。可是现在她很失望,对现状与未来都很担忧。陈广荣逃是逃出来了,毕竟没有脱离得干净,而且——没有钱。他们竟然成了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了!就算是这样,陈广荣也愿意这么灰溜溜地躲着,他愿意哪!
她认定自己看穿了他。
陈广荣发现美菊不如以前贤惠了,她慢慢变成一个成天骂男人没出息的那类家庭妇女。终于有一天他们爆发了大规模的争吵,美菊毫不出人意料地骂陈广荣欺骗自己,用谎言骗取了自己的青春,并一一列举他曾于哪年哪月许过什么诺言,而这些承诺现在不过是一句空话!
贫贱夫妻百事哀。何况还不是夫妻,只是一对逃难的男人女人,都觉得自己为对方付出太多,而所得甚少。他们应该是有感情吧?这么多年了,可是一遇到真真切切的风风浪浪,忽然就觉得,那点感情实在不算深厚,像装米的米缸子,一舀,很容易就见了底。
他们的争吵越来越多了,不吵的时候就什么也不说。
有一天,陈广荣提前从外面晃荡回来,正看到楼下一个角落里,瘦小的二皮和高胖的美菊竟搂在一起亲嘴。
快过春节了,李艳茹正忙着筹备店里面的各种庆祝活动,突然失踪八个月的丈夫陈广荣竟站在面前。李艳茹也有些慌乱,有一点生分地、然而是喜悦地上前说:“回来了?”
“……哎。”陈广荣垂下眼皮。
“你……受苦了。”老婆竟然体贴了一句,差点让陈广荣掉下泪来。两人在这里像初次见面的情侣,矫揉造作地温馨起来。周围的人来来往往,可他们俩像是被围进了一个小圈子,私自进行着汹涌的情感交流。
李艳茹一边派人给陈广荣倒茶,一边让他去办公室坐,忽然发现陈广荣的眼光在四处搜索。她心知肚明,找了个身边没外人的时机,几乎是耳语地对陈广荣说:“陆勇早走了,走了大半年了。”陈广荣心里一惊,算算,陆勇走的时间差不多就是李艳茹捉奸的时间。也许从那时起,李艳茹就想把这个家庭的步伐调整到正常轨道上来了。她根本不是真的要把陈广荣怎么样,就是提醒他而已。
陈广荣不知道自己应该哭还是笑。
中午,佳敏正好从学校放假回来,一开门就愣住了。她迎面撞上父母坐在一张桌子吃饭,两个人和和气气,还带点温馨的样子,佳敏瞪了他们一眼,却一点笑意都没有。
“佳敏,你爸回来了,吃饭,吃饭!”李艳茹乐滋滋地拿了空碗去厨房给女儿添饭,佳敏坐在桌旁,盯着陈广荣问:“她呢?”
陈广荣有些理亏地低声回答:“我把你给的那些钱给她了,算是……了断。”
佳敏的眼光像块抹布,轻描淡写地把她爸那张涨红的脸抹了一下,嘴角浮起一丝蔑然的笑意。一切又回来了,他们又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在同一张桌前,在同一盏灯下,各自扮着笑脸,演着没人看的戏。
陈广荣忽然对女儿的沉默感到心虚,额上有了汗。但什么意外也没发生。李艳茹把碗端过来的时候,佳敏只盯着桌上的菜,淡淡地说,吃饭,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