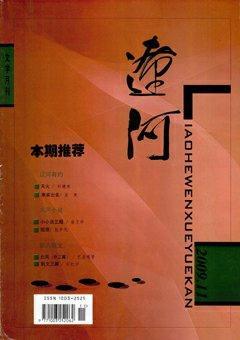流向
卜丽爽
C市的黄昏在匆忙的日落中拉长了建筑的剪影,而市府广场上的天空,却还飘着几丝烧红的云翳。每天晚上经过这里,我便停下疲惫的脚步,把满脑子的“找工作”的想法全部放下,独自一人面对着从对面金融大楼的玻璃上折射的这点余晖,想象着那颗又圆又大的太阳正慢慢地下落、下落,最后一点点地消失。
天很热,走出公汽后,阳光烤得人焦头烂额,柏油路上蒸腾的暑气好像要把人窒息,就连路边的树木也像萎靡了精神,闭了眼睛打起盹来。
我用一摞厚厚的简历尽可能挡住刺眼的阳光,没走几步远,汗已湿透了T 恤。难耐的酷热,真让人有点慌不择路。为尽快赶上约定的时间,我几乎是小跑着。突然一声急刹车,在我的意识还没有任何反应的同时,整个身体便迎着已经停下的车重重地撞了上去。一阵钻心的疼痛漫过全身,我下意识地低下头,血从小腿上流进了雪白的丝袜,一块皮被擦破了。
真的很尴尬,我觉得很多双眼睛在看我,我急急地躲到一边,好在行人很少,没有人在意。
“对不起,上医院吧!”司机的语气很急促,显然是吓了一跳。
“没关系,只是擦破点皮。”我没敢看司机,人家并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是你慌不择路造成的,人家没向你发火已经够绅士的了。
“还是上医院包扎一下。”他坚持着。
“不怪你,你走吧。”尽管这样说,其实很感激,我抬头打量一下,很面熟,终于想起他不就是经常在广场上坐着的那个人。
“真巧,是你?”他好像也认识我,更增加了一丝歉意。
“走吧。”他再没说话,随手打开车门,将我扶到车上。
其实我本不打算上车,又没有伤筋动骨,但是他的目光始终坚持着,我只好作罢。
排队、挂号、照X光、包扎,从楼上到楼下,我讨厌看病的繁琐和医生的漫不经心,几乎每次去医院,我都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不去想曾经有过的伤害。
“医生的面孔怎么都冷若冰霜?”
“看惯了死亡,就不会太在意挣扎的生命。”他好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终于说了一句。
“还要输液吗?”看到护士拿来药瓶,我坐起来,看了一下时间,糟糕,已经过了应聘时间。
“算了,我不打针。”其实我是害怕那个注射器。
“必须打,要不会感染。”他看着我,脸上很严肃。
我听从了他,反正错过了见面的时间,看来我的运气真的糟透了,明天只好再到人才中心看看。
“你忙去吧。”看到他手足无措地站在注射室外,我催促着。
“那我先走了?”他似乎有些不放心。
“真的没事,谢谢!”这个人还挺雷锋的,似乎是一种好奇心的驱使让我脱口而出问了他的姓名。他犹豫一下,像是在考虑该不该告诉我,最后低低地说出三个字:王向东。
从医院到我租的小屋,途经市府广场只有两站路,我没有坐公汽,这样走虽然伤口有点痛,但心情却比坐公汽好。走到市府广场时,已经是华灯初上了。
晚风很清爽,驱赶着中午残留的余热。我掏出一张纸巾擦了擦汗渍的脸,似乎应该补点妆,想想,还是算了吧,夜色中有谁还能留意我的容颜呢。
“喂——”,好像有人叫我。
“你的东西掉在车里了。”我回头,是那个叫王向东的人。他把一个信封递给我——那是我求职的个人资料。
“谢谢,如果丢了就麻烦了。”我指了指那个信封。
我在他面前站了足足一刻钟。我竟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足足站了一刻钟!?我轻微地咳了一声,他觉出了自己的大意。
“下午的事很抱歉。”他说。
“其实,这话应该我来说。”我说的是真心话。
“你当时是不是有急事?”他边说边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那些蓝色的烟雾被霓虹灯光照得竟有了几分扑朔迷离了。
“是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还好他没有把我当成精神病人!
“你在求职?”他接着问道。
“你怎么知道?”
“这写的。”他指指那些资料。
“恐怕错过了这次机会。反正不是你的想要也得不到。”
“我能问一下是什么工作?”
“是华赢公司。”
“你想去华赢?”他心不在焉地问。
“华赢的管理我早有耳闻,我想那种环境会很适合我。”
“据说,那个老总对人要求很严厉。”
“我只是去工作。”
我相信他是迅速地看了我一眼,虽然我没有捕捉到他的目光。而他似乎也知道华赢。
“你好像也知道华赢公司?”
“C市的人有几个不知道?”也难怪,那种规模的公司在C市已是首屈一指。我觉得刚才的话真是问得可笑。
“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我看了看时间。
他犹豫了一下,终于说“要我送你么?”其实我明白那只是礼貌地问一问罢了。
“没人敢吃我,我也曾在景阳冈打过老虎呢。”我开起玩笑。
他笑了,虽然那笑只是一瞬。但与他的冷漠的眼睛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也会笑么?
接到华赢公司的电话后,我真的有点不相信。人事部的那个人说,九点半约我见面。可是我根本没来得及去报名,甚至连一张表都没有填写,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应聘,又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出乎意料的事简直让我有些怀疑是不是搞错了。对于招聘方来说,他们像是愿者上钩的垂钓者,平静地等待熙来攘往的人流,这种事怎么可能。
九点十分,我来到华赢公司,在一位名叫兰兰的女孩儿的带领下,第一次走进了华赢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
“是蒋小姐吗?请坐。”随着声音,一束犀利的目光射过来,那种目光很坦荡,同时也不失热情,似乎没有一点老总的颐指气使和高高在上,无形中有种亲和力,给你一种自信和平等。听说他平时工作很严厉,然而,在他的举止中丝毫没有让我觉得逼人的盛气和威风。
“您好钱总,我叫蒋薇,初到公司,觉得媒体说的很客观,没有一丝虚夸的成分。”我直截了当地说,虽然稍有些恭维之嫌,却也是我的心里话。
“公司的宗旨就是诚信,人家说无商不奸,我却认为唯商务实。”他微笑的脸上始终带着自信和沉稳,显示出四十几岁年龄的那种城府和修养,平易中拉近了距离。或许人们所说的严厉是对他的一种尊重吧。
“蒋小姐是学音乐的?”
“是的,我学的是音乐学院师范系。”
“音乐是一种完美的艺术形式,只是我不太懂,但很喜欢。”他谦虚地说。
“确切地说,我对音乐也只是粗浅地知道一点,不像搞专业的学生。我们在校的时候学的东西比较杂,强调的是将来如何去教学。”
他的话怎么从不切题?我有些懵懂了。
“蒋小姐过谦了,《礼记》中说:‘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触类旁通,才能形成知识的系统,才能使教者如源头活水,也能让学生如鱼得水。”
钱总一直饶有兴趣地闲谈,有时甚至放声大笑,他坦诚的目光不时地望着我,越是这样,我倒有些局促不安了,仿佛被查明了什么心事。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并伸出手,“很抱歉,还有个会要参加。”我们握了一下手,我想问:我的事呢?但我没有开口,只是讪笑一下,“与您说话很放松。”我在口是心非。这种谈话让我始终摸不着头绪,更确切地说,好像是进入迷宫,自始至终我都在猜测,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疑团。
“蒋小姐,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明天就来公司吧,公司的试用期为一个月,具体事项人事部老王会通知你。”就在我迈步将要走出钱总办公室的时候,他说了上面的话。这个决定太突然了,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仿佛在连续和谐的和弦中,突然增加了一个小二度,猝不及防地撞击着我的神经。
“震惊!”
是的,再没有比这个词更恰当了。
“投诉我们?简直不可思议。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我的惊骇把张秘书也吓了一跳。
“早晨,工商局的刘科长刚刚打来电话,据说消费者指责我们的口服液质量有问题。”
“胡扯。又不是刚刚投放市场,而且我们是经过十二位专家的验证和数千例跟踪调查的,一直居于同类产品之首,畅销全国及东南亚,最近又在拓展欧美市场。”我有些气愤,竟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堆话。
“对各项指标的审查,当时工商局也在场。”张秘书也很气愤,不时地用手推着眼镜。
“事态有什么发展吗?”我稍冷静一下,任何凭空指责都是无稽之谈,问题是不要给我们的市场和销售带来负面影响。
“好,张秘书,你帮我给刘科长打个电话,说我二十分钟后到他那儿了解情况。如果钱总回来,你向他汇报一下。”
我知道这种事最重要的是掌握主动,不能让消费者糊里糊涂地在盛怒之下牵着我们的鼻子。遏止事态最关键的是弄清原委。这可不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呀!
同刘科长一见面,我就直接问:“什么时候接到的投诉?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一直是经得起检验的,从一投放市场,就已经有了公论。”
“当然。我们也相信。但既然消费者提出疑议,我们必须有个交代。”
“我们也在考虑,因为你们的产品很走俏,那些惯于搞旁门左道的不法分子就盯上了。这些人只要有利可图,是什么都会干的。我们也是为企业服务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查清事实。”刘科长的保证并没让我放心,我需要的是时间。如果再拖一个月,我们的损失就无法估计了。
“刘科长,你这有没有消费者用过的产品?”
“没有,这好办,我可以派人去取。”
“那好,我告诉检验科的人等你,先化验一下成分。”
从刘科长那儿回来,一进公司,兰兰就跑过来,“蒋薇姐,快去吧,钱总正等你呢。”
“你是怎么搞的,报纸都出来了,却还蒙在鼓里。”钱总“啪”地将报纸摔过来。 “这一点,是我的疏忽,我有责任。”本来是以为可以平息事态,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家报社简直是别有用心。
我手里的报纸像一个烫手的火球,烧得我想大叫,但我只能沉默。
“我们和美方谈判了一年的合作项目刚刚有了进展,那些老外是很看重企业的形象的。” 这一年里他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如果谈判成功,那将意味着公司在国际市场上从此便有了一个可以展示的舞台。
我理解钱总的忧虑,就像我理解一个满怀希望迎接新生命的母亲所经历的艰辛。这一点是一样的。
“钱总,您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
这句话好沉重,却让我说得很轻松。我的自信把自己也吓了一跳。然而我必须这样,我不能让钱总从谈判上分心。每件事的存在都有着必然和偶然,说不定在变化中已注定了转机。
可是真难,从钱总的办公室出来,我一直在构想着一些可行的方法,可是“覆水难收”哇,况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嘴除非能遥控,而谁能不让人家说话?真希望像《上海滩》中的冯敬尧一声令下,买下报馆的所有报纸。
乘公汽的人很少,车有条不紊地几乎用同一个频率在运行。今晚报已经登载,虽然没有指责我们公司的产品,只是提出消费者的疑虑,但这件事说与不说产生的结果没什么分别。
“嘟嘟”,是我的手机在响,“喂,是化验科,什么?结果出来了?怎么样?”不出所料,原来是很粗劣的做法,把我们的产品一分两份然后加水。卑鄙在私欲面前就是这样从容,它让虚假堂而皇之地走入厅堂,让人有口难辩而又必须明辩。
公汽在很大的缓冲下停了下来,这是哪儿?糟糕,这是市府广场,而我竟坐过了站。
“你好,出来走走?”一个熟悉的声音。是王向东,是他跟我说话。
“我……是的。”我怎么能说自己坐过了站?
“兰兰多次跟我提起过你,她很羡慕你。”兰兰跟他提起过我?这个兰兰,她根本不知道我的生活充满了逆流,那些支离破碎怎么也拼不出一幅美丽的图画。
“我却很羡慕兰兰,有你这么一位好哥哥。”
他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呼出来。他的呼吸像负重的喘息,在夜的背景下,好像能激起水花。那种情绪也传染了我,本来就空空落落的心更加失重了。
“今天公司被投诉的事弄清楚没有?”
“你怎么知道?”
“这种消息是不用宣传的。”
“你有什么办法吗?”
“没有,我正为这件事着急呢,媒体已经做了反应,这最棘手。”
“其实也不见得怎么样,有句话叫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既然是媒体的宣传,也可以借用一下,来个以其人之道,炒作有时不见得是坏事。”
“是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这样的话不仅可以澄清事实,还宣传了我们的产品,更让消费者知道我们的实力。这岂止是一箭双雕!”
他一语道破,竟还是心不在焉。而我被激活的思路,就如那一颗颗不灭的灯盏,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生动,好像游荡在麦迪逊大街,到处飘动着灵感的影子——我可以请电视台做个专题,介绍生产经营情况,再请一些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在宣传产品的同时,澄清当前的流言,提请消费者到指定的代理商那里去买……
就在我为投诉事件思路大开的时候,“哗”的一声,广场的喷泉喷出了十几丈的水花,猝不及防的刹那,我一下子伏在他的胸前。
那是一个温暖坚实的胸膛,心狂跳不止。这一惊也包含了对自己出乎意料的举动。
怎么了?怎么了?
这一触碰像沉沉的千年钟声,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一直进到心底最封闭的地方,它在往下坠,一直往下坠,坠得我站也站不起来。
“没关系,这种天浴不是谁都会碰上的。”他用袖子胡乱擦擦脸上的水珠,突然他指着前方说:“快看,那儿是什么?”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在迷迷离离的水雾中,广场的灯光像施了魔法的鞭子,划出一条七彩缎带,它就架设在我们的上方,那圆圆的拱形像要串起夜色中跳动的心,那是谁的心,游离于这彩桥之上,热切地渴望被引渡到桥的顶端,那上面的风景,一定是人生最绚丽、最有诗意的。
“太美了,夜晚还有彩虹。”我的惊异溢于言表。
“是很美,很独特。”他离我两步远,头斜斜地像在欣赏一幅名画,他的目光在我和彩虹之间迅速地交换着,只是几秒钟,便远远地散向了远方,像往常一样空茫而沉寂。
专题报道准时在第二天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记者招待会也开得很成功,而这一切所引起的连锁效应是,几天之内各地的提货单蜂拥而至,我的军令状终于没有让我溃败。
“蒋薇姐,你看电视了吗?给你一个特写,特上镜。”兰兰她们一群女孩子叽叽喳喳地说,而工商局刘科长的电话也打到我的办公室,“喂,是蒋小姐吗?我们对造假的团伙已经有了线索,你放心,我们会一究到底。”好累,好高兴。就像一个工匠,在不分昼夜地劳作后,终于听到了赞许。
午休的时候,大家坐在一起,谈笑中那种轻松就好像周末的一个沙龙。
就在这时,我看见兰兰,她侧着头伏在桌子上,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神采,恹恹地马上要睡去的样子。
“怎么了,兰兰?”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
“没什么。”连说话都是懒懒的。
“是不是病了?怎么这样没精神。”我摸了一下她的头,不烫。
“是我哥病了,也不去医院,昨天烧得胡言乱语。”
“他病了?严重么?”心里有种沉沉的东西,又来了,那种感觉。
“吃了药,可烧一直不退。早上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已经好了,可我还是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