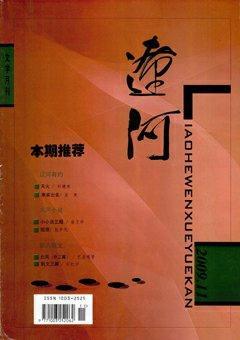赶路
彭海亮
李小军十五六岁,细高挑,大眼睛滴溜溜转,稚嫩的脸上流着汗水。他像一只小舢板,被喧嚣的人流推搡上了列车。车上人挨人,连下脚的地方都难找。“砰”的一声列车员关上门,腾出一小块地方,他麻溜把身上的旅行袋靠车门上,才站住了。他下意识地伸手到裤腰,摸到硬邦邦的一卷100元,这是母亲给缝的。放寒假了,他来千里外的姥姥家玩,顺便捎买大豆、猪肉、粮票的,带回家贴补口粮。凌晨一点大连上车,赶到长春换乘已经下午了,他眼睛还没有眨一眨呢。这会儿眼皮打架了,迷糊起来。他第一次自己来,妈妈说发电报了,姥爷在松花江车站接他。他梦见姥爷捋着白花花的胡须惊喜地说:“外孙真能,敢闯,将来有出息。”他坐上马爬犁,甩起大鞭杆子,鞭哨子“啪啪”地响,一溜烟儿地尦到了张坨子。
突然,他被人拽了一把,醒了。
“让开,到站开门!”列车员气哼哼地说。
李小军使劲挪动身子,才闪开了车门,急切地问:“叔叔,车到哪儿了?”
“九台。”
“到松花江站还有多长时间?”
“这车不走松花江站。”
李小军脸色比哭还难看,急得有些结巴了:“我……到松花江……站啊。”
“你上错车了。”
“车不是往北去吗?”
“往北两线,西线哈尔滨方向的路过松花江站,东线齐齐哈尔方向的在达家沟站分岔了。”
“啊?”
列车员看了他一眼,说:“你到丁家园下吧,翻过一座小山就是松花江站。”
窗外的雪花像一片片棉絮被风吹起,粘在车窗上滑下来,又粘上去,他的心忽上忽下地一阵阵发紧,胸口几乎喘不过气来,腿肚子也跟着酥软起来,不得不换脚站着。
到站开门,上车关门,列车员走了。上来几个胡子拉碴的人,脸上脏兮兮的,深蓝色更生布工作服油渍麻花的,呼出的旱烟儿直呛李小军嗓子眼。他本能地拉开了距离,紧锁眉头,低头不语。
到达丁家园站,雪住天晴,橘黄色小站房后的山顶托着一轮酱紫色的太阳。戴表的告诉他:4点多了。列车没有靠站台,在铁道线中间停下了。李小军从悬空的铁梯蹦下来,差一点摔个趔趄,一抬头看:一列货车横亘在铁道线上,挡住了出站的路,绕过去要走好远,就决定钻车底。他把东西放到两车的连接处,猫腰往车下钻。
“小兔崽子找死啊!”他感到棉猴被人拽住了,好大的劲儿生生把他薅了出来。
李小军身后响起一串串“咣当”声,那是车厢挂钩相撞的声音。
那人一把薅过他的包,扔在地上,拉他站到空地上,气喘吁吁地说:“幸亏我跑来的。多悬啊!”
那列货车缓缓地移动了,巨大的车轮碾着铁轨发出沉闷有力的声音。李小军捏了一把冷汗。
“小鸡巴崽子不长眼睛啊?车头都摆绿旗了,你还敢钻!不要命了?”他两手撑着光板老羊皮大衣,叉着腰,摆出一副英雄的架势骂骂咧咧地说。
李小军热泪盈眶地说:“大哥,谢谢你救我一命!”
他戴着长毛狗皮帽子,脸显得格外小,粗糙发红,唇上冒出毛茸茸的毛,很有股子见过大世面的神气儿。他把李小军的包拎到前面的狗爬犁上放稳,说:“听口音你是辽宁的。”
“大连的。”
“俺家原先长春的,跟俺爸走‘五七,落户丁家园了。俺来接俺爸,可他没回来。你去哪疙瘩?”
“到松花江站,我姥爷在那接我。”李小军戒备的心理防线被打破了。“再走20里就到家了。”
“俺捎你一段。到松花江站,十五六里山路啊,你能行?”
李小军耸耸肩,挺直了腰板,俨然像个军人的样子说:“我能行。”
出站不久,天色就像有人慢慢地拉开一张大网一样,一点点地暗下来。不远处草房上的烟囱飘起了袅袅炊烟,传来“喽喽喔嗦”驱赶鸡鸭鹅进架的声音。远山、丛林、近屯披着灰白色的铠甲,一片迷迷茫茫的。
拉爬犁的大黄狗老远朝土夯墙的院子叫,跑出来一条白地黑花的小狗,围着大黄狗又跳又扑。他说:“俺到了,今晚住俺家吧。”
“不行。那我姥爷会急出病的。”
“俺还得接下趟车,要不送你了。”
“我自己能行。”
“吃饭再走吧。”他很有劲儿地拽他,说:“俺叫向跃进,大跃进时生的。俺家就俺妈俺姐俺弟,俩屋,有地儿住。”
“谢谢!我叫李小军。我会来看你的。”话音未落,他俯身拿爬犁上的旅行袋和书包,向大哥一把抓到他肩上。
快出屯子了,向大哥撵上来,把一个烫手的黄草纸包塞到他手上说:“路上吃,火盆烤土豆,甜丝的,顶饱。”
李小军掰开土豆,热乎乎的香气扑鼻子,也不管烫不烫就往嘴里塞。
向大哥指给他看,说:“前面看到的房子就是成家窝棚屯子,出屯子往左拐二里地,有一片树林子,下沟,再翻一道岗子,就看到铁道线了。记住啊,别转向了。”
“记住了!”
“有机会到这圪垯,一定进来啊。”
李小军咽下热乎乎沙棱棱的土豆,点头说:“一定来。”
向跃进蹲下来,轻声和大黄狗说话儿,大黄狗不停地摇晃尾巴。然后他把拴在它脖子上的长绳递到李小军手上,说:“叫它带道。到了,你就拍它三下屁股,它就自己回了。”
李小军想从裤腰掏出10元钱来,怕他不收,还得骂他,就一步一回头地走了,身后不断地传来向大哥的喊声:“走不了回来呀!”
走到成家窝棚屯子,他把东西放地下,伸手到旅行袋里掏苹果。在这儿苹果是稀罕东西,打大连带给姥姥家的。几十个苹果个个冻成石头蛋子,他一啃一道牙印儿白茬儿,只好捧了一捧雪吃了。大黄狗嗅嗅旅行袋上啃过的苹果,抬头望着他,两只爪子不停地挠雪,他就挎上包出了屯子。他参加过学校组织的下乡、军训活动,但没有一次这样单独的经历,这回可以自豪地给同学讲故事了。他唱起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上来到天安门……”的歌曲,给自己打气。
天黑下来,头顶上好像扣着一口大铁锅,山坡上一处处小坟包儿,就像黑瞎子蹲在那里,张着黑洞洞的大嘴等他走进去。后来他才明白那是粪堆,不是坟堆。小时候淘气,姥爷给他讲死鬼捉小孩的故事。他害怕坟茔地冒出一个鬼来,不敢看还紧盯着,捏住水果刀的手心汗津津的。四顾远近都不见人影儿,只有绵绵起伏黑魆魆的山岭。竖耳听,没有风声,天地出奇的安静。他屏住呼吸,不敢出声,总感觉身后有人:他走快“他”也走快,他走慢“他”也走慢,他站“他”也站,影子一样尾随他。他心吊到嗓子眼了。
月亮爬上了小山,时隐时现。起风了,渐渐大起来,刮过那一片小树林子“嗖嗖”地响。远处山坳里发出“嗷嗷”的声音,是孤独饥饿的狼嚎吧?姥爷说松花江一带有狼,有年春节夜里,姥爷听到仓房有动静,就提着镰刀躲在门后,不会儿发现一只狼叼猪肉板子往外拖,姥爷一镰刀下去,砍断了狼的脖子。李小军紧张地放下肩上包,一手提拉一个,浑身上下仿佛都睁着机警的眼睛。我不孤独,我还有松花江站的姥爷等我,还有大黄狗给我带路。他在心里默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脚下“咯吱咯吱”踏雪声,“喀吧喀吧”踩断干枝声,好像盖过了风声狼嚎。透过张牙舞爪的树枝,他看到向大哥说的那道岗子就在不远处。他把包又挎上肩头,包像铁砣子一样往下坠,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肩膀勒得很痛。时髦的翻毛皮鞋底下黏着雪块跺也跺不掉,两条长腿就像木棒子似的不听使唤。
突然,他一脚迈空,滚进黑黢黢的山沟。大黄狗惊恐地叫唤起来,围着他打转儿。李小军眼睛直冒金花,瘫软地躺在沟坡上,屁股钻心地痛。他很想再多躺一会儿,可他怕再也不想起来了。他大吸一口清冷的空气,两手撑地站起来,拽起包。他庆幸自己走出了树林,掉进向大哥说的那条山沟,说明松花江站不远了。怎么听不到火车汽笛声?跌跌撞撞地下到沟底,他咬牙攀上沟坎。
看到了山岗子,坡好陡好高好长!月光下,山岗子光秃秃的,青白白的,挑衅地等着他。狗狂吠起来,山顶上移动着一片模糊的黑影。
他再次捏住水果刀。姥爷说旧社会他在汉城当了3年伙计,好不容易积攒了50块袁大头,夜里回张坨子老家,走山路被打杠子的抢走了。我棉裤里还缝着100元啊,不能叫坏人抢去了。他脑子里瞬间高速运转起来,核计对策:一旦怎样就怎样,一旦那样就那样。他把大黄狗拽到跟前。
老远就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过会儿黑影变成了四五个人到了他跟前,他侧身让开道儿,他们走过了。
李小军爬上了山顶,看到了山谷闪烁的红绿灯,看到了冒蒸汽的火车头,还听到了“呜呜”的汽笛声。松花江小站!我到了!他向山下跑去,高喊:“姥爷,我到了。”
月台上没有姥爷,他就跑进候车室:十几平方米大,一扇外窗,一扇门,一个铁桶大炉子,一条木板椅子,一个人也没有。见两个脑袋大小的售票窗口开着,他趴那儿问看到他姥爷没?回答没有。莫非姥爷回家了?还是没接到电报没来?到姥爷家还有20几里路,自己不认识道儿,得住一宿票房子了。他一屁股坐到条椅子上,肩头旅行袋和书包滑落下来,浑身上下软塌塌地像一摊子泥巴,脸上的汗水不断捻儿流。他掏出毛巾狠劲儿擦了把脸,嘴渴得冒烟儿,饿得心慌慌的。要了水,吃了牛粪卷面包,他就在条椅子上,枕包放挺了,但没忘装钱的那侧身子贴着椅子,手里抓着那条拴狗绳子,一会儿就出了鼾声。
“哐当”一声门响,一股寒风扑到李小军身上,大黄狗朝门叫一声不叫了。李小军一激灵。
一个大嗓门子喊:“小兄弟,俺来了!”。
大黄狗挣脱绳子弄醒了他,他一个鲤鱼打挺蹦到地上站,睡眼惺忪地问:“真的是向大哥?”
“嗯哪。”昏黄的灯光下,戴着长毛狗皮帽子穿着光板羊皮袄的人哈哈笑道:“没接到俺爸,俺看大黄没回来,猜你一准儿没见到你姥爷,撂在松花江站了。”
“辛苦了向大哥!”李小军心里像打碎了五味瓶子,甜酸苦辣齐从眼泪里流出来,但还是挺直腰板说:“放心我没事儿。”
“一宿还不冻干了你?”没等李小军答话,他就提起东西出了门说:“跟俺回吧,睡热炕去。”
第二天向大哥赶着狗爬犁送他到了姥姥家。第三天姥爷才接到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