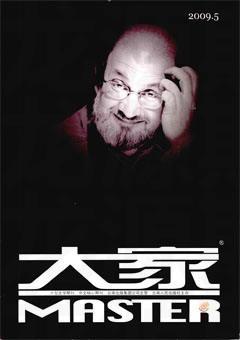行走巴基斯坦之
纪 尘
A而我放牧着村庄
199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来到一个美丽的地方,当他领略了此地的风土人情后,写出了闻名世界的《消失的地平线》。
从此,西方人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寻找“香格里拉”的旅程,一些国家,比如印度和尼泊尔,就曾先后宣布:“香格里拉就在我们国家。”至于中国,也把云南的迪庆和四川西部藏区的一些地方称为“香格里拉”。那么,真正的香格里拉究竟在哪里呢?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为之争论,因为香格里拉与其说是一个确凿的地理存在,不如说是人类用以告慰孤单灵魂的一个乌托邦。
不过,当我到达位于喜马拉雅山区西缘,喀喇昆仑腹地的罕萨山谷时,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香格里拉”。
此程我有了个同伴:来自英国的西蒙。我们是在吉尔吉特认识的。我们乘坐一辆拥挤不堪的小面包车到达了卡里玛巴德(Kafima bad),也就是罕萨的地理首都[在行政上属于阿里亚巴德(Aliabad)镇管辖]。
“真没想到你会在那里骑马。”西蒙乐呵呵地说。
他也曾在同一天看了吉尔吉特的Polo比赛,因此也就看到了那个骑马的奇怪女人以及她与当地人的舞蹈,不过当时他以为我是日本人或是韩国人,得知我来自中国后,他有些吃惊——我是他碰上的第一个孤身行走的中国人——他可是已在路上晃荡一年多了。
西蒙让我想起在拉合尔碰上的马克思:都一样的脏兮兮,头发乱蓬蓬,举止散漫无谓,嘴里动不动就冒出“Fuck”。不同的是马克思有一脸络腮胡子,西蒙没有,马克思穿的是一双硬塑凉拖,西蒙穿的则是在新疆喀什大巴扎买的解放鞋。另外,他的牛仔裤破了一个大洞,被寒风吹得发红的膝盖像个粉色补丁般露在外面。他也跟马克思一样健谈,不过马克思的谈话对象主要是我,而西蒙的谈话对象则是路上碰到的任何人。
我们住的是“老罕萨客栈”,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说现在是淡季,可给我们便宜的房价:每个标间一百五十卢比。唯一的单人间已在昨天被一个日本人住了。
我望望西蒙,虽然我们是同伴,但其实交谈不多,一是我英语不够流利,赶不上他的语速,二是也许我是位女性,而且还来自中国——西蒙对中国的印象似乎不太好。“疯狂的中国人。”这是他的原话。因为在中国时他永远都被无数人围绕,永远要不断回答同样的问题。
我知道这些。我所在小区的西方朋友也曾向我抱怨,说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问点别的而永远是“你来自哪里?你喜欢中国吗?你喜欢吃中国菜吗?你想不想找一个中国女朋友?”等等。
我曾将这种情况与巴基斯坦做过比较,在巴基斯坦,我也时常被人围观,询问,我却从没对这些人感到厌烦。也许是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实在太多,另外,巴基斯坦人不仅对外国人友好,对自己的同胞也一样。记得那年我从新疆回到南宁火车站,由于没有零钱坐公车,我问了不下五个人——没有一个愿与我兑换的。有的甚至看到我过来就远远挪开去——哪怕他们身上的零票足够跟我换两次。
最后我不得不买了份报纸——只有这样,报贩子才肯给我换零钱。我不能说我的同胞都如此漠然,但那次的遭遇让我终身难忘,并且难过。
当然,西蒙不太高兴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人们总叫他“西门”,开始他还没什么,但某天有人告诉他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个风流混蛋叫“西门庆”后,他就不高兴了。“我叫西蒙而不是西门。”虽然他每一次都强调,人们还是笑眯眯地叫他“西门”。
西蒙没说话,用手挠挠头,似乎有些尴尬:我们都想省钱,但我们都不太清楚对方的想法。
“一间还是两间呢?”老板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又问了一遍。
西蒙终于表态了:他蹲下去,双目直视前方的远山,朝后伸出了大拇指。好吧,“混账”的事我不是没有过,在西贡我不就跟一个以色列小伙在同一张床相安无事地住了一整晚?何况这间房里有两张床,且相距十万八千里。幸运的是,西蒙很快就在餐桌上结识了两个德国人——滔滔不绝的谈话使他从与我独处的尴尬里解放出来,我也因此有了完整的闲暇。我决定独自走访这个村庄。
沿着一条被人和牲畜踩踏出来的“草路”,我倾斜着身体从客栈的草坡慢慢滑下,跳过一些岩石及穿过几片荆棘后,我找到一条石子小路——这林间小路弯弯曲曲,不时在眼前消隐又永远通向前方。
至少有一小时,我完全淹没在白扬林中,虽然树叶已落尽,但繁密的树木仍如尽职的卫兵般耸立着,地上的落叶绵软厚实,一踩上去便发出清脆的碎裂声。一些其他树种那金黄或赤褐色的叶子仍挂在树梢,予以这个苍凉世界一种沉着成熟的色彩。
毫无疑问,这个村庄是美的。一名原来的总督曾说:“小小的罕萨地区所拥有的超过海拔两万英尺的山比整个阿尔卑斯山地区海拔超过一万英尺的山还要多。”的确,在卡里玛巴德,不论你从哪里看去,都能同时看到好些海拔七千米以上的山峰,比如Rakaposhi峰(7788米)、Diran(7388米)和GoldenPeak(金顶,7027米)。
由于阴天,这些白雪皑皑的壮美高峰好像云团一样相互融合。在这些伟大的山脉面前,我想人类所谓的“征服”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它们的每块石头,每棵植物,每丛灌草都清晰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并为自己存在着,它们的美与壮阔从不会因为人类的荣耀而有所增添或减损。
我继续不知疲惫地四处穿行,完全不管方向——方向什么要紧呢?这里哪儿都有美的存在,都有生命的律动。即便是流淌在巍巍群山中的冰河,即便是河对面延绵不断、荒疏孤决的悬崖,都仍有着各种生命相伴:各种荆棘灌木分布在这片粗粝又贫瘠的土地上。它们的生长环境是艰难的,但却拥有着大自然最美好的礼物——空间。正因为拥有自由,这些植物才具有如此坚韧的力量与个性。
在恬静透明的空气里,各种植物闪现出银色、深紫以及褐色,一些隐秘的低处还盛开着花。当风吹过,那些刺柏摇摆的身姿真是又刚劲又淳厚,虽然它们很多都已失去了树皮和叶子,但粗糙的根部仍紧紧地抓着下面的沙砾,枝杈上稳稳长着灰色的锋利芒针,芒针之上结着粒粒暗红的果实。
大地如此安寂,万物各安其所,以致我产生如此一种感觉:我其实是走在逆时针里,其实身处男一个古老、神秘和深远的世界。
气温开始下降,厚厚的云层遮挡住天空,只在西面留有一线开口——阳光就从那里洒向人间。山峦依次呈现出玫瑰色、灰蓝和紫——唯有“金顶”光芒万丈。我从没见过基督耶稣,但在那刻,我确信,上帝降临的迹象必是如此:一系列五彩缤纷的云彩之下是一片奇异绚烂的金色光芒,在四周萧穆又庄严的气氛中,那片红色荒原成了世界的中心、阿比的国土。
“库里玛巴德的牧民在放牧着羊群,而我在放牧着村庄。”我久久凝视着“金顶”,想起了法国那位伟大的飞行家及作家——圣·埃克苏佩里。他在天空翱翔时,总觉得自己是在放牧着一座座城市。我不是飞
行员,但此刻,我相信自己内心的幸福感与那位时常独自在漆黑里与星辰、雷电和风暴接触的大师是一样的。那是一种如此宁静又纯粹的幸福,这种幸福感甚至使我想哭泣。
原来我并不孤独。原来我一直拥有着如此忠贞而恒远的爱——种完全没有人工雕琢,宛如处子一般的爱。这爱就在四周,就在我存在之处:柔和、朦胧的雾霭,刺柏独特的香气,若隐若现的星辰,甚至光秃秃的戈壁——我爱恋着,驯养并被驯养着。
我又走了一会,天已完全黑了,气温继续下降,远处开始闪烁出点点灯火,这使我有些难过——那些局限性的微光在提醒我,应当离开了。
由于天黑而我又不熟悉路况,因此我在山坳间转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公路,虽然从公路可以看到客栈的灯光,但真要走到却至少还得一两个小时。就在我步履艰难地爬坡时,一辆汽车从身边飞过又马上停下
“需要帮忙吗?”一个温和的声音从车里传出。
当然。我这血肉之躯可比那些刺柏,石头软弱多了。
这是我第三次在巴基斯坦乘坐好心人的顺风车,当然接下去的路程,我还又坐了两次。
回到客栈,西蒙居然孤零零地在门前坐着吹风——我出门时忘了给他钥匙,而那两个德国人又走了——他就这样在门外吹了一整下午。看得出来他很冷,但精神却很好。大概卡里玛巴德是不会让任何人萎靡的。
那晚我很早就睡去了,西蒙则在餐厅不知又跟谁聊到深夜。总之,当我发现他那条破了个大洞,脏兮兮的伸在被子外的牛仔裤时,天已经亮了。
我轻手轻脚地起来,出门——我要用双唇读出这个村庄金色的早晨。
B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条冰河。
它从卡尔库仑姆山自南向北穿过,奔涌的河水一路不断与其他冰河汇集,最后成为吉尔吉特河最大的支流。这条冰河。昨天我曾远远地看到它,曾打量它身边那如天空一般安静的悬崖,也曾为堆满石头的河床伤感——在昨天的那种距离里,它看起来已快被石头淹没。
我看过许多被人类摧毁的河流。在那些土地远比这里丰饶得多的中国村庄,在那些本来鸟语花香,彩蝶飞舞的山谷,无数的岩石和大树都被标上令人耻辱的记号,那些记号预示着这些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存在了千百年的事物很快就要离乡别井,成为城市某个公园或是某个酒店门前的“风景”。短浅的目光带来短浅的利益,在那种“点石成金”的诱惑下,人们毫不犹豫地将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进山谷,将一片片山坡夷为平地,将一个个巨石、一棵棵参天大树连根拔起。
我的一位搞建筑承包的朋友说这些事物的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有的甚至高达百万。当然,这不是“进价货,它们的最初价格不过是后来价格的百分之几或十几,随着运往的地方不同,人工和各种明的暗的成本一路增加,当它们翻山越岭,终于被埋葬在城市的沥青水泥旁时,几乎每个都成了“百万富翁”。至于那些滑坡,那些一夜之间突然面目全非、混浊肮脏的溪流,还有被疯狂的挖掘机铲断了身体和头的蛇或蟾蜍,有什么要紧呢?只要能弄到钱,人们并不介意将一片沙漠留给后代。
穿过一片美好沉着的白杨林,经过一片细腻的沙地,我终于到达河边——不安消失了——河流周围即没有推土机也没有起重机,除了从山间奔涌而下的轰隆,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把手放进水里,轻轻拨弄着——我想享受一下这种与河流的亲密接触,哪怕只短短一瞬。河水凛冽刺骨,但我却有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难道我竟曾经来过?
一时里,我的记忆逆流而上,就像那种从指尖渗到胳膊,继而渗到唇齿的寒意——我终于追溯到一些东西:2005年,新疆和田的某个乡下,当我把手伸进同样冰寒刺骨的河水里时,一个牧羊的克尔克孜族少年指着前面的山告诉我说,冰河就从那里来,而那座山背面,就是另一个国家——印度。那条河的所在就跟此地一样荒凉,那个牧羊少年的笑就像刚才经过的那个拾柴少女的笑。
西蒙一直在找那种扁平的小石子打水漂——虽然人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接受不同的文化,但童年的玩乐却如此惊人的相似。每当看到石子在水面漂跃时,他都兴高采烈,他的这种快乐让人很难想象他竟然已在路上独自走了近两年——究竟是什么使一个孤独的人能始终对事物保有兴趣和热情呢?我不知西蒙将手探进河里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不知他是否也会浮现一些过往记忆或仅仅是如他所说:“想看看水有多冷。”
由于河水湍急冰寒,我们只能放弃渡河过那片悬崖的念头而继续沿河前行。
在那片平坦的沙砾地,一只山羊正专心致志地啃噬着它简陋的食物。在各种被风霜染得姹紫嫣红的植物里,我惊奇地发现竟有着苏摩草(sumo)。我曾在卡拉什山谷见过这种草本植物,当阳光照晒在它们上时,那种温暖的橙黄是多么妥帖。
当时我万万没想到这种有着如此一个美丽名称的植物原来就是那种使人松弛,记忆力衰退的“大麻”。这个邪恶的发音与在湛蓝的天空下静静生长的苏摩草是多么的不协调,由于这个发音,苏摩草不再是那位肤色黄里透红,能随意变形的因陀罗(印度神话中的雷雨之神,嗜喝苏摩酒)的神圣慰藉,也不再拥有远古时代那种使精神复苏、赋予人勇气的诗意的魔力,而是成了一个诅咒、一片污渍、一种否定。
这种视角的转变使我凝视那几株在寒风中摇摆的植物时升出一种失落——种就像失去某种绚丽的东西,就像为一颗星星的陨落而来的忧伤。
“沙子用中文怎么说?”西蒙打断了我的思绪,我的沉默大概让这个喜欢聊天的大男孩憋坏了。
我告诉了他,接着又说了几个词:天空、星星、树、河流。他则相应纠正我一些单词的发音——这个地道的英国人对我的美式发音有着些微的不满。西蒙的父母都是嬉皮士,虽然现在父亲老了,还是扎着一头麻花辫子。
“他们总叫我别做这别做那,我才不管,因为我知道他们年轻时什么都做、也许比我还疯狂呢。”说完他耸耸肩,用袖子擦了一把脸,当看到我望着他那满是油腻污垢的袖子时,他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这儿没洗衣机。”
我笑笑,西蒙撒谎时就像个正拿着一颗糖往嘴里塞的孩子,当被发现后认真地告诉别人他只不过是想闻一下槽的味道而已。在那家难得的有热水的客栈,我可是见识过这家伙是如何在等我入睡后连袜子也不脱就钻进被子里蒙头大睡的。
洗不洗澡都没关系,我们的干净与肮脏不在头发和衣裳。
我们继续相互“学习”,当我第五遍告诉他如何区别“凉快”和“两块”时,西蒙产生了羞愧:“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很疯狂,现在知道了,要学另一种语言真是不容易。”
“你应该觉得幸运,因为中国人从没有要求你们用中文跟他们对话。”
“对,中国人其实挺好的,印度人才是真的疯狂。”好家伙,一下把烫山芋丢给英文说得远比中国人好的印度人身上去了。
我又笑笑——中国是什么形象并不由我说了算,更不由一个外国人说了算。我只知道,无论中国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