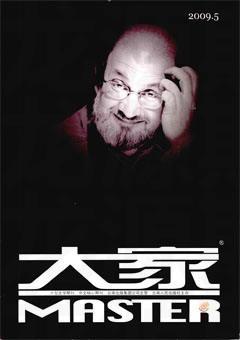续幽梦影
【作者简介】刘丽朵,女,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出版有小说集《镇与大城》(2005年),禅学读本《生死请柬》(2006年),长篇小说《谁能与共》(2009年)。小说作品收录于《小说北大》等选本,并有诗歌作品见于《诗刊》,《诗选刊》,入选《2003年最佳大学生诗歌》,《2004年中国最佳诗歌》,《2005年中国最佳诗歌》等选本。现居北京。
【文学观】这一组小说,从《春满楼》开始,到后来的《幽梦影》、《续幽梦影》、《醉扶归》,《生死恨》,其实是一些“无题”小说。“无题”是某个诗人创造的传统,非此不能表达爱,和内心的幽曲。在明代传奇《邯郸记》的末尾,黄粱生笑道:弟子一生,耽搁了个“情”字。爱是不能够明确表达的,即使写下了很多字,也只是提示爱的存在。即使在故事中经历了离乱、痛楚、死亡和伤害,也只是为了提示爱。因此它们无法被提炼,总结,只能经由暗示,一点隐约的关联,就像无题诗的题目一样。
上篇
坐上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后面,后面是个十字路口,地面上有一些瓜子壳和甘蔗皮,我看见穿黄衣服的小南在那里一边嗑瓜子一边笑。她去年出去,今年又回来了。她出去的时候,我还没有出去。唉,我一直没出去,这不是才第一次出去吗?
不过我知道是迟早得出去的。现在走已经算晚。像小粉都出去过好几年了,她比我还小好几岁。一开始她们是去了广东,后来又到北京,后来又去郑州,现在去哪里的都有。我坐上的车是去A市的。电视台在放的节目就是招工广告,和卡拉OK。那个说话的女人是东村的小雀,她说的是普通话。灯泡厂,电子厂,服装厂,空调厂,电视厂。现在我去电视厂。
车开出去不久以后,四明开始抽烟。不只是四明,不少人都开始抽烟。因为这一车是去电视厂的人,所有男女都有。车里的烟味很大,我开始吐了。我打开车窗,吐在外面。我也说过让他们不要抽烟了,可是没有用。人们都在抽烟,四明一边抽烟一边冲我笑。他看着我吐。
我看一会外面,睡一会,往往是被难受弄醒的,醒了以后就吐。肚子里曾经吃下去的东西都被吐的差不多了,车才到一个地方,让下来吃饭、尿尿。我坐在桌子那,我很饿,可是也吃不下饭。我包里有饼,我娘说,一路上吃。四明坐在对面,他在吃方便面。他吃得头上冒汗。是辣味的方便面。到处还有很多这种方便面的空金子,在地上扔着。我看着四明吃方便面,看着又吐了。“她晕车。”四明跟别人说。“喝点水吧。”有人跟我说。
又上了车走,到晚上到了电视厂。下车之后,我们被送到宿舍。八个人一问,条件还行。我们同车来的女的还不到八个人,所以有一张床空着。我们是七个人。不过,床摆得满满的,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小娜跟我住一块。小娜住我旁边的床。路上的时候,她和我说过几句话。她让我别老是开着窗。小娜是个薄嘴唇。
进到电视厂之前,我们的车在A市走。天都黑了,A市还亮着很多灯,还有霓虹灯。现在镇上也有霓虹灯,跟这个差不多,没有这个整齐。街上走着人。可是很快就没有人了。车又在路上走了很长时间,才到的电视厂。
小娜和三妮在家就认识,她们是一个村的,她们在说话。我们村没有人来,只有我。我都知道她们的名字,可是说不上话。还好很快她们都在和我说话。她们在说我。她们说我路上吐。我把铺盖铺在床上,我想睡觉了。“幼娣,你是北村的吧?”我听见有人在问我。我对她笑,我说是的。“你是叫幼娣来吧?”她又问。我说是的。“我叫清香。”我赶紧笑。
我都睡下了,有人敲门。她们去开门。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她一进来看见我说:“这么快就睡了?”“她晕车,今天老吐。”清香说。那女人再没理清香,那女人把手拍了一拍。本来小娜她们还在说话,听到拍手就不说话了。那女人说:“你们听好了,今天是第一天来,你们有的以前来过,有的第一次来。别的我不管,我不管你以前是什么样,在家的时候什么样,一进了这个厂门,你就是这个厂里的人了,要按照厂里的规矩办。你们看墙上贴的厂规,一共六十条,这六十条厂规都要遵守,要不就不要来这个厂。”说到这,女人停了一停,看着我们,接着她又说:“听清楚了吗?你们基本也都上过初中,如果有对厂规不明白的,可以问我。明天晚上咱们开一节厂规课,在上课之前,你们把厂规都看一遍,至少一遍!”接着我听见小娜在那呵呵地笑。那女人生气了,说:“王小娜你笑什么?”小娜就不笑了。那女人又说:“明年上午,参观工厂,明天下午,分配岗位,明天晚上,上厂规课!”女人说完转身就要出去了。因为她说话撇腔拉调,我有点听不懂,尤其是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到底什么意思,就一直看着她的脸,她要拉门之前好像看见我了,回头用牛样的大眼狠狠瞪了我一眼。
女人走了之后,小娜在屋里说,这个人是厂里派来管我们的,她是我们那边宋庄的人。“宋庄的?听声音不像。”清香说。“你知道啥?她现在不说咱们的话了,她跟A市人一样说A市话。”“怪不到。”有人说,“怪不到她说的跟电视台的小雀也不一样,不是普通话。”
接着小娜说,这个人让人叫她宋主任,其实她叫宋庆花,她很坏,专门跟上头说我们这些女工的坏话,让我们被扣钱。上头是一个叫小黑的男的,也是我们那边的人。这次去招工的就是他。小娜这么一说,我们都想起来了。是有一个长得黑的男的在,我们去报名的时候,都看见了。小娜又接着说,现在电视厂效益不好,她是前年来这的,去年回家了半年多,不是她自己要回,而是厂里没活,让人都回去。清香问:“那为啥又让我们过来了?”小娜说:“知不道,可能效益又好了。”
我过去很少听见“效益”这个词。
“那为啥电视厂效果不行呢?”有人关心地问。
“不是效果,是效益,效益不好就是东西都卖不出去!现在城市里的人看的都是平板电视了,像咱生产的这种木头块一样的电视没人买。”小娜说。
“那上回你回去的时候,他们给你发钱了吗?”清香问。
“发给了。”小娜点头说。
第二天下午分配工作,别人都分到了车间,我的工作是扫地。
“这工作好。”分配完了以后,清香跟我说。“不累。我们都给关到车间里头出不来,你能到处走。”
“打扫卫生,拿笤帚把子,不用培训也能行!”小井说。
那个叫李枣的、上次跟小娜一起来过厂里的。过来扳我肩膀,凑我耳朵边上说:“打扫卫生的工资跟车间工人的工资不一样,你知道不?”
我不知道。
“要不你去跟宋主任说说。”
晚上厂规培训,坐在上面给我们培训的就是宋主任。她说作为一名女工,我们都要守纪律。要把厂规背下来,明天检查。她还说,我们都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厂里给我们培训技术,让我们都掌握了技术,让我们不花钱就学到了本事,比学校还好,所以要感谢厂里。
等到培训完,我去叫宋主任说话,我说,能不能让
我也去车间,不想干打扫卫生。宋主任站住,她没等我说完,就说:“不想打扫卫生是吧?刚来城里一天就挑毛拣剌了。你不是身体不好吗?给你安排这个工作是厂里照顾你。”
我没想到宋主任会这么生气,她站在那说了我很长时间。既然这样,我也就只好干打扫卫生了。
有一段时间,她们回到宿舍都唉声叹气,说跟着师傅干活,受师傅的气。还有人羡慕我,说我干打扫卫生比她们强。确实,我虽然干的时间比她们长,可是不用受谁的气,顶多有时候宋主任站在她办公室的门口,指指画画说什么地方打扫得不干净。可就算这样,让她们跟我换,她们也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段时间我和清香好了起来。清香有时候不能准时下班,我给她买好饭。虽然也有别的人让我给她买饭,但清香不用说,我就会给她买好。
有一天清香对我说,让我干打扫卫生的工作,都是因为小娜跟宋主任说我身体不好。我问她听谁说的,她说是小并告诉她的,小娜跟宋主任说的时候,她听见了。小娜说的是,来的车上别人都没事,只有我吐个没完。而且看我长得面黄肌瘦,可能是有病。然后清香说,小娜真会背后使坏。她问我是不是要去找小娜算账,她愿意和我一起去,如果我说不过她,她可以帮忙。我说算了,我现在也不想去车间了,打扫卫生就打扫卫生吧。
但是清香越来越讨厌小娜,因为她们俩被分在一个车间,同一个师傅。清香说小娜是个马屁精,专会跟师傅说好听的,所以师傅就喜欢小娜,讨厌清香。平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一起,远远地看见小娜,清香总是要往地上吐一口。清香用眼角白眼瞥着她,口中念念有词:“马屁精,专会舔师傅腚眼。”在清香骂着小娜的时候,我看见小娜兴高采烈地过去。她每天都高高兴兴,不管是吃饭的时候还是上工的时候,不管是拍马屁的时候,还是说别人坏话的时候。她说起话来,就像一小挂鞭炮细细碎碎地放个没完。晚上别人睡觉的时候,她就在那里说梦话,从刚睡下开始,一直说到第二天早上。
小娜知道清香对她看不惯。有时候她过来的时候,清香和我正在说话,看见她过来就不说了。有时候清香和我看见她和别人说话,我们过去的时候,她也不说了。后来有一天,有一次清香哭着从车间出来了。在车房到宿舍的路上,我看见了她。她哭得很响,脸上都是眼泪和鼻涕。在我冲拖把的水龙头下,清香一边擤鼻涕一边洗脸。清香告诉我,小娜当着师傅的面,给了她一个嘴巴子。
“她能这样?”我几乎有点不能信。
“师傅还没打我呢,她凭啥打我。”清香一边用两只手甩着脸上的水,一边说。
“那是为啥呢?”
“我说她昨天一天啥也没干,师傅让我们干的活,我昨天就干完了。今天一上工,师傅说小娜的活没干完,让我帮着她干。我说我的活已经干完了,让我帮她干没门,她说她昨天被宋主任叫去,我说也就去了一头午,下午她干什么了?小娜说我不想帮她干,是想耽误交工的日子。我就骂她,她就打我。”
清香还没说完,清香的师傅就过来了。她师傅是个四十多岁的。我早就听清香说过,她师傅是A市人,在电视厂二十多年。清香的师傅过来开始劝清香。
这事过去几天,后来听说小娜被扣了钱。
我们的工钱是按月领的,但也可以不领,存在会计那里。会计也是个女人,长得干瘦,不爱说话。以前村里的女娃出去打工回来,有挣到钱的,有挣不到钱的。二叔家的小粉挣到钱了。有的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连车票都买不起一张。小粉挣了三千块钱。小粉偷偷告诉我,说她的钱全存在厂里,每个月就花不到50,到走的时候,一口气把钱拿出来。
所以我也不领钱,我跟会计说了,存在她那,到我走的时候一块给我。
别人基本都是按月领钱的,甚至还不到发钱的日子,就想着赶紧发钱。我知道小娜她们几个到了休息日去逛大街。后来到了发钱的日子,小娜说她的钱被扣去三百。小娜领完钱回来,很生气,在宿舍里摔捧掼掼。到清香进门的时候,小娜高声骂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是谁专门告状说人,嘴巴里长疔连根烂!不知道是谁狼心狗肺,一吃饭就让噎死!你害我不要紧,小心别害了你全家!”
清香说:“你说谁?你说谁?”
小娜扑了过去。我们看见小娜和清香一个人抓住另一个的领子,互相推和打,我们都赶紧把她们俩拉开。
正在打着拉着,宋主任到了。到她们俩终于被分开的时候,清香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小娜却一滴泪也没有。清香的脸上被挖烂了好几道。小娜的脖子上也受了伤。
宋主任说:“你俩都到我办公室来。其他人不准出屋。”
我们看见她们三个出去了。清香的哭声很大,我们听见她的哭声越来越远。李枣说:“这是咋搞的!”小井说:“看小娜那样儿!”
另外几个没说话的,都跟小娜好。
清香离开电视厂的时候,我正在打扫卫生。清香带着她来时候的包袱。她对我说:“妹妹,我走了。”清香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她哥哥的手机。如果我要找她,可以给她哥哥打电话,她哥哥会转告她的。我看着清香,心里头很难受,半天不知道说什么。清香说:“别哭,唉,哭啥。我是自愿离开,又不是厂里开除的。我就是不愿意受她的气。回去以后看还有什么地方招工,我还能再去。”我说:“清香姐,你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清香咬牙切齿地说:“我早晚会回来,和小娜算账。你现在一个人在这里,你又那么老实,我真不放心。”我说:“她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清香走了以后,我很少和人说话,自己天天干活,晚上回来睡觉。小娜出出进进,眼睛里像没有我这个人一样,也从来不和我说话。小娜现在成了整个宿舍的头领,没有人不听她的。以前清香跟她对着干的时候,李枣、小井和我都喜欢跟清香在一起,另外两个跟小娜在一起,她们仨每到放假,就到大街上去,买回来各种东西,也有吃的,她们三个一块吃。清香走了,清香本来是有理的,可是就连她都不能跟小娜对抗下去。后来我看见李枣和小井也和她们一块上街了。她们五个现在说笑都在一起。我越来越觉得在宿舍里像个外人,跟她们都隔得很远,就连以前一块玩的李枣和小井都不怎么说话了。
这天下午,有一批活干完了,我被叫过去打扫废料。是男工车间,在那里我看见了好长时间没见过的四明、拴马。他俩是我们村的,四明是我家邻居。他就住在我家后面,我们两家用一个墙。我们村里有句俗话:远交近攻,意思是邻居太近了没好事。所以我家和四明家一直不好。我二叔和他大爷打过架,我爹也帮着二叔打。我们两家基本上都不搭腔。不过,现在在这个地方看见四明,还是觉得心里头热乎。以前总听人家说老乡见老乡就怎么样,在这里虽然都是老乡,可四明是从小看着长大的人,跟别人不一样。更别说在宿舍里的那些老乡一点也不亲,比旁人还远。
拴马跟四明说:“那不是幼娣。”
四明说:“我看见的。”
拴马喊我,他说:“幼娣,四明和你说话。”
我走过去,看见四明和拴马两个人推推搡搡。
“没啥事。”四明说,“你在这好不?”
“还好哩。”我说。
“你咋没干车间?”
“分给我的就是这活。”
“也行。”
“你在这干啥哩?”
“俺都一样,都是装配工。”
我没太明白他们干的是什么。这会儿车间里空空荡荡的,就只有我们三个。沉默了一小会,四明说:“咱都是邻居,有啥事过来找我。”
这天晚上回到宿舍,心里面感觉很松快。拎了一桶水,在水房擦洗过了,就回房睡觉。睡到半夜,突然醒了,看见一个人站在跟前,吓得心猛地一跳,问:“谁?”那人看我醒了,三步两步走到门前,拉开门出去了。是睡前没插门吗?我赶紧起来,贴着门听了一阵,才敢把门打开,向走廊张望。我看看小娜穿着背心和短裤从厕所走出来。
这件事过去,不知道怎么弄的,每次看见小娜,我就有点害怕。小娜却跟平常一样,从不和我说话,看不出她要干什么。直到有一天,这天我正打扫着卫生,回宿舍拿东西,发现只有小娜一个人在。她坐在床边上,剪她的脚趾甲。我拿了东西刚要出来,听见后面的小娜说:“哎。”
我顿了一下,拿不准她是不是在叫我。
“王幼娣,你过来一下。”
“有事吗?”我站住了问她。
“我听人家说,你跟人说是我让你千打扫卫生的,有没有这回事?”
听到这话,我呆了一下。我是听清香说的,清香说她是听小井说的,我当时很气愤,后来也就算了,也没有去跟别人说。现在她一下子这么问我,我还真有点说不上来。
“我没有。”我只好说。
“我都听说了。怪不到你老是不搭理人,你对我有气,是吧?”
“没有气。”我说。
“那你为啥不搭理人?”
“我没有不搭理人。”
“我觉得你是不搭理人。先是不搭理我,后来看别人和我好,你就都不搭理了。不要说我没有跟宋主任说过让你打扫卫生,就算我说了,宋主任她能听吗?这个厂又不是我开的,我又不是厂长。”
我有点急了,说:“我没有说是你说的!”
“那我今天告诉你,我没说。”
我只好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了以后也没全信。我平常打扫卫生,跟你们工种不一样,所以没你们之间那么亲热,可我也没有不搭理你们。”
小娜说:“咱都是一个镇上出来的,互相之间应该照应。咱们又都住在一个宿舍里,你成天委委屈屈的,脸上跟沉冤似的难看,我们看见你,都觉得心情受了影响。你要对我有意见,你说出来,咱们谈开,有啥不行的?”
这天是我和小娜之间生平第一次交谈,小娜后来握着我的胳膊,让我和她做好朋友,她说的话听起来好像都很有道理,我也就答应下来。但是同时我又想起清香,觉得对不起清香。清香是因为小娜走的,为了清香,我似乎不应该和小娜做朋友。但是现在,小娜这么振振有词,让我一定要和她做朋友不可,我还真不大可能和她说不。
晚上大家都回到宿舍以后,小娜对我格外的亲热,这让她们觉得意外。她坐在我的床上,同我说话,还把她的苹果给我吃。我不想吃,但小娜一定让我吃。这天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心里头有点小高兴,好像会有一点好事发生。但仔细想想,日子还是一样的过。
就这么过了半年多,我有时候在厂里碰见四明,或者拴马。四明长出了小胡子,黑黑的,个子也高了。有一天他问我要不要给家里汇钱,我想了想说要。我的工资在会计那里存了半年,应该有不少了吧?我想起爹妈接到我寄给他们的钱的高兴劲儿,就恨不得赶紧跑到邮局,把钱给他们寄去。我跟四明说,如果他要去寄钱,就叫上我一起去。在此之前,我得从会计那里把钱拿出来。
一共是三千七百六十八块二。厚厚一沓。我还从来没有把这么多钱一起拿在手里过。拿到钱的时候我高兴极了。这是很多钱。比小粉挣的还多。我想我爹和我娘一定不会想到我挣了这么多钱。他们会拿着我寄给他们的汇款单。跑遍全村,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女儿有多么本事、多么孝顺。可是又害怕别人知道了以后借钱,他们一定会对人说一句:“家里年下欠的钱终于可以还上一些了。”
取钱出来以后,到宿舍,照镜子脸上是红的。连脚步都很轻。趁着没人,小心地把钱缝在床单下面,我就等着四明叫我去。
可是四明好几天都没找我。我等不及了,去找四明。我问四明什么时候去邮局寄钱。四明说:。星期天吧。”我想了想,平常四明上班,根本出不来,他的工作跟清洁工不一样,不能灵活安排时间。想到这个我笑自己太急了。
星期六晚上不用上工,所有人都在宿舍里玩。小娜坐在我的床上。她对我的亲热有点过头,有几次,她扑过来像是要咬我或者亲我的样子,我到处躲,别人看着哈哈笑。等到小娜凑近我的脸的时候,她却往我脸上轻轻“呸”了一口。有唾沫溅到我的脸上。我的脸顿时涨的通红。别人都以为她在跟我玩笑,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她是闹着玩还是真的。我只好笑着,心里却别扭得很。这天晚上小娜又在我床上玩,我催她回到自己的床上去,她不肯。我又催了几遍,她说:“行,你得给我钱。”
“给你啥钱啊?”
“没钱了,跟你借点钱。”
“我也没钱。”
“谁说你没钱?你褥子底下是啥?”
我的脸再次涨红了。我说:“你咋乱翻我东西?”
“我没乱翻,我就是坐在你床上,觉得下面硬硬的,掀起褥子一看,看见你藏了一包钱。”
听见这个,屋子里顿时静了许多。我知道她们都侧着耳朵听呢。
“那是我要给家里寄的。”
“哟,给家里寄的,我们都没钱给家里寄,就你有钱给家里寄。你真孝顺,真好,一个大孝子、大孝女。”
“我从来不上街,来城里半年多啥也没买过,你们的钱都乱花了。”我说的是实情。
“幼娣,我没和你开玩笑。我这个月的钱都花完了,这几天没钱吃饭,你先借我点钱,还有十来天咱就发钱了,发了我就还给你。”
小娜这么说,我还真有点为难。借给她吧,很不情愿,不借给她,她又赖皮,坐在我床上不肯起来。而且小娜是个让人摸不准的人,翻脸又快,没人敢惹。
“你要多少?”
“三百五百的。”
“那么多?借给你一百,还不行?”
“还有十多天发工资呢,一百不够,至少得三百,最好五百。”
“我一个月才挣五百多。”
“又不是不还给你,小气哩。”
磨了半天,一直到看见我用剪刀剪开钱包,数出三百块给她,她才满意地去了。我把剩下的钱又放进褥子下面,一晚上没有很睡踏实,第二天早上匆忙去找四明,和他一起去邮局把钱汇走。
汇走了三千二,本来打算汇给家里三千五的。虽然有点小遗憾,但心里头还是畅快的。我和四明一路说说笑笑回来。我和四明说起他大爷,四明说他大爷从小恶歪,跟前后的邻居打架。我说我二叔也不是善岔,二婶子也厉害,要不是有四明他大爷,恐怕村里就他们这
一家子大了。四明说我爹和我娘是本分人。他说着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爹也跟四明他家打过,不过那是我二叔调唆的。我二叔跟别人打起来了,我爹要不帮着我二叔,村里的人会笑话的。
我们一路说到厂门口。又往厂里走了一段,两个人要分开了。四明停下来问我说:“你是属兔吧?”
“是哩。”
“那比我三哥小两岁,比我大一岁,我是属虎的。”
“噢。”
“以前我爹和我娘都想把你说给我三哥的,因为咱们两家关系不好,就还没说。后来听说你也来电视厂,我娘还说,就不说给老三,就说给老四也行。”
我的脸顿时腾腾红,我想起四明他哥三明,我们曾经在一个班上上学,三明老留级。后来他去什么地方打工了,很早就出去了,这几年一直没有见过他,反而是四明经常见。我听见四明又说:“我来时候我爹说了,在外面除了挣钱,最好能找上个对象。现在咱村子里女娃都不多了,出去的都嫁到外头,男娃在外头没找上的,回到村里都成光棍了,三十多岁没结婚的有的是。”
我说:“噢。你还小哩。”
四明说:“不小了,这都十九了,过了年就二十了。”
我说:“十九才小哩,还不到二十。”
四明说:“你要是不嫌我小,咱们俩交朋友吧。”
开始我有点猜出了四明的意思,可不能肯定,特别是没想到他会现在就说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把头埋得低低的。
四明把我的手扯过去,说:“你不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
我想拽回我自己的手,但四明扯得很紧,我说:“有人来了。”四明这才放开。来的是一个不认识的人。我趁四明愣神的工夫,一溜烟跑回了宿舍。
这件事以后好多天我都害怕在厂里碰见四明。打扫卫生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从四明的车间里走出一个人,我就会心怦怦乱跳。每次我都觉得那是四明,等走到跟前看见不是,才能放下心来。为这个我挑一些没人的时候打扫四明车间周围的地方。可就算是这么小心,还是让我碰上了几次,算起来比以前碰见的次数还多。
有一次四明看见我,像是有话要说。我低着头扫地,他在我身边站一两分钟,又走开了。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会想起四明对我说过的那些话。其实我每天都在想着这件事,可只有在睡觉的时候,才能够更仔细地想。不知怎么的,我又想起四明小时候的事。他经常穿着他二姐的衣服,她二姐以前的衣服改小了给他穿,还是花的,好些人都笑话他。四明小的时候是个胖娃娃,他的脸上永远有泥道道。现在的四明可是瘦,个子也高。他哥三明反而长成了个胖子。就这么我从那天开始想,想着想着就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一直到睡着。在梦里,四明站在我跟前,我捏着扫把,四明说:“幼娣,你看你的衣服脏了。”我低头一看,衣服果然脏得厉害,黑得都看不清以前的颜色了。我心里想,怎么昨天晚上下工之后没好好洗洗呢?你看现在,多丢人。后来就急醒了。
就这么迷迷糊糊过了一个来星期,有时候把扫把往桶里涮,涮了半天才发现错了;有时候把袖套忘在水池上就走了,等回到宿舍才想起来回去拿。宿舍里的人和我说话,我嘴里答应着,脸上笑着,她们说的什么却一点也听不到。
星期四那天,厂里发钱了。我看见她们都从会计那回来,才知道发钱了。她们都很高兴,说很长时间没钱了,领到钱以后要干啥干啥。我问她们:“小娜呢?”她们说:“刚才还看见她哩,现在不知道她上哪了。”一直等到晚上,也没看见小娜的踪影。我因为太困就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她们都起床了,我看见小娜还没起床。我去到小娜床边叫她起床。我说:“小娜,还不起,上工要迟到了。”小娜在被窝里转了个身,过了好半天才说:“噢。”
到我们都走了以后,小娜也没起床。
我慢慢地听说小娜晚上去到网吧上网。上网我知道,我们镇上就有网吧,好几个,我弟弟有一段时间老去,后来让我爹打得不叫去了。我也不知道上网有什么好,让人上了以后就下不来。我不管这个,我得先跟小娜要回来我的三百块钱。
后来碰见小娜的时候,我就跟小娜说,她满口答应,上午说晚上就还给我,晚上说明天再还。我等得不耐烦,跟小娜说:“你有的话,就赶紧还给我吧。”小娜说:“行。”过了一会,当着所有人,小娜说:“下午你干完活,在二车间门口等我,我拿钱还给你。”我干完活以后,就去二车间门口等小娜。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的眼睛左右看着,眼珠子都快瞪得凸出来了,也没看见小娜。后来我就回去了。当天晚上,一直到睡,又没能看见小娜。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能跟小娜说。
“娜,钱你咋还不还我哩?”
“什么钱?”小娜眼睛一瞪。
“你借我那三百块钱。”
“昨天在二车间门口,我不是还给你了吗,你怎么还要?”
我气得没话说。现在我知道当时清香为什么被气走了。我说:“我昨天等你很长时间,你一直没来。”
小娜把正在吃饭的饭缸往桌子上一掉,好多汤洒出来,桌子上到处都是,小娜的眼睛都红了,她大声叫起来:“有这样的人吗?你这样还算是个人吗?刚把钱还给你,你说没还,现在我是说不清了,我是浑身嘴也说不清了!”
小娜叫着,号着,跳到床上,两只脚乱蹬,把鞋都蹬了下来。她的脚很臭,恐怕有好多天没洗。小娜发出哭一样的声音,说:。王幼娣你这个贼!骗人的钱不得好死嗅!”
我急得没办法,我想就这么算了,这三百块钱我就不要了,可是我又想起自己辛辛苦苦,一共一个月就挣五六百,每天花几块钱吃饭,什么也舍不得买,从来没上过街,这三百块钱够我过三个月的,我就心疼得没办法。而且现在也不是说不要就能算完的事了。小娜这是讹上我了。她说她还给我了而不承认,打死我都不能背这个黑锅。
宋主任进来了。
小井先上去跟她说。她说的是:“小娜跟王幼娣借了三百块钱,上个月她没钱了,这个月发了钱她还给王幼娣了,王幼娣说她没还,急得她在这里哭。”
我又急得不行,我说:“她就是没还钱!”
宋主任过去拍拍小娜,小娜扑通一下从床上跳下来,趴到地上抱住宋主任的腿,连哭带号地说:“宋主任!青天大老爷!你给做主啊!我要是还了钱说我没还,让我不得好死!”
宋主任说:“小娜你别哭,起来好好说。”
小娜就是不起来,她把她的头往宋主任腿上磕,一面磕一面号:“我要是没还钱,现世现报!太阳底下叫雷劈死,让我不得好死,走路叫车撞飞!”
宋主任直往后退,但小娜抱着她的腿不放,她往后挪,小娜就跟着她在地上爬。宋主任最后大喊一声:“王小娜你起来!有话咱好好说!哪个说你没还钱我就不和她算完!”小娜的声音才慢慢小了下去,小了下去。
我站在屋里,眼前坐着小黑。都半个多钟头了,他还没有说一句话。我已经把我的话都说完了。
小黑在抽一支烟。
我的腿很疼,站在那里有点晃。今天是星期二,别人都上工去了,我本来也应该在工上的。现在是早上
十点,我应该是刚刚打扫完了下完早班的车间,那些上中班的工人有的都到了。我又想了一下四明。但没敢多想。我抬起头看小黑的脸。
他的烟只剩下一个尾巴。他把烟掐灭,又点了一支。
“王小娜,她,她真没还我钱。真的。我没说瞎话。”
小黑还是一声不吭。
我心里面十分害怕。
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小黑猛地吐了一口烟,把烟头扔到地上踩灭。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再想想,再好好想想。”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
他从我身边过去,走向门,把门拉开走了出去。我站在屋子中间,头昏脑涨。昨天下午和宋主任说了一下午,宋主任又把我交给小黑。在这间屋子待了一晚上,门锁着,没有地方睡觉,坐在椅子上,趴着睡。半夜醒来很多次,想上厕所,出不去。被憋得哭了好几回。最后到处找,找到一个塑料袋,尿了以后,从窗户里扔下去了,感觉到小肚子很疼,到现在也还在疼。一直到早上小黑才来。一直到走,小黑就说了一句话。
我听见门从外面被锁上的声音。
我冲到门口晃门,我说:“我不要那钱了!让我走吧!”
小黑站在门口。他没走。他听我在里面晃门。晃了一会儿,喊了一会儿,听见小黑开锁的声音了。小黑把门推开一半,站在门口看着我。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用两个手捂着脸。
小黑又没说一句话,把门关上,锁好走了。我知道我是打不开这门的。
月亮透过窗户照进来时,我在屋里已经找不到塑料袋了。
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我已经不需要去厕所了。我躺在地上。
地上不凉,就是很脏。有小黑弹的烟灰。
我好像是睡着了。但钥匙打开锁的声音,还是一下子把我惊醒。
我“呼腾”一下从地上坐了起来,看着进来的小黑。他慢慢地打开灯。
屋子里一下子亮了起来。两个铁柜,两张桌子,两把椅子。这里是一个办公室。我不知道是谁的办公室。我躺在桌子和门之间。
“站起来。”小黑说。
我赶紧站起来。想开口说话,发不出声音,半天才说:“放我走吧。”
小黑把一只手伸到我肩膀上,我把他的手拨开。他又伸上去,我又拨开,小黑的手这次给了我的脸一巴掌。我冲上去打他。我什么都顾不得了。我上去抓小黑的领子,抓他的脸。小黑只用一只手抓着我的肩膀,就把我原地拧了好几圈。他又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抓到他的胸前,离他特别近,几乎都嘴对嘴了,我感到他带有很浓烟味的气喷到我脸上,又狠狠一推,把我推得撞在桌子上。
“啊!杀人了!”我大喊,但声音一点也发不出来,才喊了半句就咳嗽个没完,眼泪淌的把整个脸都蒙住了。
“别瞎叫”小黑说。“我本来来这里是要放你出去的,结果你上来就跟个疯狗一样,别是把你关疯了吧你!”
“放我出去吧求求你了。”我边哭边和他说。
外面月亮很好,跟我刚才在窗户里看见的是一个。今天晚上是满月,月亮圆得没办法,应该是到十五了。
我在走着,一直走到宿舍去。宿舍门已经锁了,我让看宿舍的张大娘给开门。她已经睡了,半天才过来给开。
“你怎么了闺女?”
我的眼睛肿,身上脏,肚里饿,脸上还有被打出来的印子。我说:“大娘,没事。”张大娘站着看了我半天,一直看着我走进门里,她说:“多可怜。”
第二天、第三天我一直发烧,小肚子一直疼。第四天好了。我这才知道为啥放我出来。放我出来是因为:小娜跑了。开始大家还以为她是像以前一样去了网吧,但小娜就算是去网吧,也总会回来,不管是12点,还是1点、2点。这天她到早上也没回,白天也没有去上工,晚上也没回来。再一看她的东西全收拾干净、拿走了,这才知道她是跑了。她跑了,没有和任何人说,谁也不知道她上哪去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小娜。
我看见四明了。四明从他的车间里出来。没错,是四明。他站在我面前时我又仔细端详了他好几眼。四明在我眼前站住。他看着我。他说:“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我觉得心里头很热。我想说:“我也是。”又没说出口。
“你还好吧,咋恁瘦?”
“好着哩。”我说。
“我一直后悔,那天跟你说了不该说的话。”
“没什么不该说的。”我说。
“你别生气,是我不好,你别往心里去。”
我低头不吭。
四明站了一会儿,但什么也没说出来。我知道他要走了。
我知道四明一转身就要走了。我看见四明转身了。我看见了四明的脚挪动了几下,有点犹豫,可还是走开了。我在他的脚刚开始挪的时候猛地抬头,我看见了四明的背影。
“四明!”
四明转过身。
“你那天说的,我都想好了,就照你说的办吧。”
四明看着我,好像很长时间都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了,看着他笑。
四明半天才咧咧嘴,我听见他说:“真?”
想让四明弄清楚一些事特别的难,比如我和他说,小娜和清香打架,宋主任说让小娜和清香两个人关小黑屋,关了一天,出来以后,小娜跟没事一样,清香却辞工了。四明就说,那清香要是有理、为啥她辞工不干?我跟他说清香斗不过小娜,四明说,那有啥斗不过的?我跟他说半天,他还是不懂。又比如我告诉他说,我很想清香,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是在家呢,还是出去招工了,四明就说,想她,为啥不去看她?我说,想归想,也就是想想,去看她的话,不知道上哪找她去。四明说:那有啥找不着的,要是我,保管一找就找着了。
四明就这样。他和你说话的时候,不管你说啥,他都说你说得不对。我就停下来不说了,看着他笑。我说:“别光抬杠,我说不过你。”四明说:“不是你说不过我,你没理。”我说:“就你有理。”四明说:“有我在,谁都不能欺负你。”
他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小黑。我一直没告诉四明这件事。要是让四明知道了,小黑把我关小黑屋,打我,我知道他会怎么做。好在事情都过去了,小娜也跑了,我的钱也拿不回来了,我的伤也都好了。小黑是电视厂的红人,连厂长都对他客气。小黑是我们乡来电视厂里混得最好的一个。在这个厂里,小黑想让谁走谁就得走,想让谁留下谁就能留下。所以我不能告诉四明,让他去找小黑打架。我看着四明笑。四明说:“你笑啥?”我说:“真好,有你在,以后谁也不能欺负我了。”四明说:“就是,谁要欺负你,我把他宰了。”
说话我们来到了树林。树林在厂外面。这里原来是庄稼地,后来给种上树。地上还有一些以前的垄子,能看出来。地上长着草。四明叫了我一声。我说:“干啥?”四明又不说话了。我跟四明说:“你家种树了吗?”四明说:“没有。”我说:“我二叔家的地里全种上了树,二叔和二婶子出去打工去了,他们孩子还小哩,跟着我家过。”四明好像没听见,他光看着我。我说:“你看啥?”就把头低下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四明把我一把搂进怀中。我使劲推四明,可是推不动。
四明把我越搂越紧,紧贴着他的胸膛。我说:“哎呀四明,你干啥。”四明说:“你不是和我交朋友了吗,交朋友就是这个样子。”我说:“你懂得才多呢。”四明说:“我还懂得多呢。”
四明说着,就开始亲我的嘴,我左躲右躲的,还是让他亲到了。如果有人能看见我的脸,一定知道我的脸红透了。我觉得脸上发烫。四明也是。他身上都是汗,把我也弄得汗津津的。我说:“快别这样了,该回去了。”
四明和我牵着手回厂,到厂门口我俩把手松开了。我俩并排走着,遇见了小井,也遇见了拴马。这下男工和女工都要知道我俩好的事了。拴马拧着脖子看着我们笑。我和四明又走了一段,在岔道分了手,我回到宿舍去。在门口就听见小井在跟她们说我的事。进去以后,她们都对我笑。她们说:“王幼娣,你上哪去了?”我说:“出去走走。”小井说:“在哪碰见四明的啊?”我没理她。有个大几岁的说,“她不是早就和四明一块上邮局吗?是不是你俩又上邮局了?”小井说:“还上邮局?上邮局寄啥?扯着手一块回来,看见人才分开的。”
我不听她们乱说,拿了个盆子到水房洗脸。又顺便把所有的衣服洗了,因为我想起以前做过的一个梦。虽然是大夏天,水房里头凉快,只是蚊子很多,咬了我不少包。我一边洗衣服,一边想起四明汗津津的身子。我想应该把四明的衣裳也一起拿过来洗。
八月份的工资拖了一个来星期才发给,说是厂里的效益越来越不好了。他们把我们招来,是为了赶一批活,有一大批电视要出口到非洲去。现在这批活要交工了,那边的资金还没有按约定打过来。我是听宿舍里的人说的,宿舍里的人是听她们的师傅说的。还有人说,这批活一干完,不管那边给钱不给钱,就算是那边给了钱,我们这些人也都得回家,因为下面没活干了。转眼我们到电视厂来已经快一年了。
我想联系联系清香。四明说得对,清香走的时候,不是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吗?我按照这个电话找她,一定能找到她。星期天,我到街上去,找话吧打长途。四明说,城里的话吧很便宜,三毛钱一分钟,有的还能更便宜。我拨通了清香的哥哥的电话,马上就有人接了。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说话的声音也有点哆嗦。我说:。你是清香的哥哥吗?我是清香的妹妹。我是和清香一块在电视厂工作的。”她哥哥说:“清香没在家。”我说:“清香上哪去了?”她哥哥说:“清香招工走了。你不是还在A市吗?清香也在那呢。”
你看我有多笨。我成天想着清香,都不知道她在A市,就在眼皮底下,我还以为她在老家呢。
“清香在A市啊?我……我想见见她!”我太高兴了,说话都结巴了。
“你打清香的手机吧。”
“我不知道号码。”
“我给你说。”
清香都有手机了,她的工作一定不错。我跟话吧老板要来笔和纸,在纸上记清香的电话。这几个数字看起来都很亲,清香好像就躲在它们后面微微地笑。我想着清香的新工作。她在电视厂学了一些技术,到别的地方肯定很容易找到工作,不像我,干了快一年了,成天扫地、拖地,手上蜕了皮也就是个清洁工,到哪都只能干清洁工。
清香的电话让我拨通了。
“清香,清香吗?我是幼娣,王幼娣!”我对着电话就嚷起来了。
“幼娣!真是你?”
开始我还有点怕清香忘了我。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知道她没忘。
“是我啊清香姐,你啥时候又回到A市了,我多想你啊!你咋不来看看我!”
“我忙得没时间回去,妹妹,你给我打电话真好。我也想你呢,我正说这两天过去看你呢。”
清香忙得没时间出来,这我信,要不清香不会不来看我。我高兴得没办法,我想四明的话真是没错,要是不找,怎么能知道这么容易就能又找到清香了呢?
我拉着清香的手走过两条街。现在清香真是变成香喷喷的了,她身上喷满了香水。她穿的也很好看。她告诉我说是在发廊工作。
知道清香在发廊给人剪头发,我想这也不错,只是我没想到清香能学会这个,干起了理发师。我们到了发廊门口了。在门口,有一个跟清香穿得差不多的大姐坐着。她看着清香和我,她问:“这是谁啊?”清香说:“我的一个妹妹。”那人就不说话了。
我们进到了发廊里面。我笑着跟清香说:“你这生意好么?来剪头的多么?怎么这一条街上全是理发店,是不是A市人理发全都上这儿来?”清香说,“不是哩,傻妹妹,你咋恁傻呢。”我不知道我啥地方傻了。坐在外面的那个女的走进来,说:“我还当是你带过来的新人哩。”清香说:“不是,就是一个妹妹,很长时间没见了。”
我们坐在理发店里,清香拿过来冰糕给我吃。这个夏天我还没吃过冰糕,清香对我真好。我在那里坐了一下午,一直没看见有什么人过来理发。我想清香她们的生意可能不太好做。我看见的几个人,不是到门口坐着向大街上看,好像在盼着能不能来一两个客人,就是哈欠连天的在屋里转来转去,穿着睡衣,好像知道一时半会来不了人似的。我压低声音跟清香说:“清香姐,这儿的老板能给你开支不?”清香说:“能。”我说,“那就好,不管他的生意咋样,只要开给咱钱就行。”
我俩又扯了一会儿,我告诉她她走了以后小娜的事。我说小娜后来迷上上电脑了,天天都出去上电脑,后来还跑了。我也告诉了她小娜害我的事。清香听了特别生气。清香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一走,小娜肯定会报复你!小娜这人忒不是玩意了!”我说:“唉,姐,你别生气,反正我以后再也不会遇见她了。”清香说:“哼,我看她就不是个好人,好吃懒做,这一跑,肯定是上街当野鸡去了。”我赶紧说:“清香姐!别这么说。小娜是不好,我到现在想起她来,还气得没办法,可咱也不能随便这么说人。”清香说:“不是我咒她,我敢肯定,这就是她的下场。”
正说着,来人剪头了。是一个老头,长得很胖。我赶紧跟清香说:“姐,你忙吧,我走,不打扰你了。”清香也没大留我。她说:“妹妹,哪天我上电视厂找你去。”
九月的工资到十月还没发。我听了四明的,找会计把以前的钱全都取了出来。四明说,要是我再不取的话,别让他们再不发给我了。我又求着四明和我去邮局把钱寄走。四明说,这次的钱就不要寄了。现在电视厂随时都有可能撵人,把这钱留着,要走的时候当个路费。
四明他们的消息比女工灵通,四明这么说,那就肯定是真的。我们宿舍里也有好些风言风语,大家都说,可能是要走了。
趁一个星期天,我和四明到城里,四明说再去找找工作,看什么地方能要我们。我说:为啥不等电视厂关门以后再出来找?四明说,工作这事,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万一好几个月都找不到,我们还能在A市待好几个月?不要花钱吗?就现在出来找,也不一定到时候就能找到的。我觉得四明说的很有道理。
“最好是我能找到保安的活,你当保姆,咱们在一个小区。”
我知道镇上有好几个年轻人都是在外面当保安,我们村里的梨花、满月也都是当保姆,我听四明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