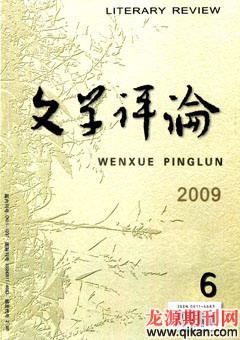论王国维“隔”与“不隔”说的四种结构形态及周边问题
彭玉平
内容提要:在王国维生前改定的三种版本的《人间词话》中,“隔与不隔”之说一直稳居其中,其地位仅次于境界说。考察三种版本有关条目的文字增删,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其实包含着不隔、隔之不隔、不隔之隔、隔四种结构形态,大体分别对应意与境浑、意余于境,境多于意、意与境分四种意境形态。不隔而深被王国维悬以为审美理想,文学的常态是隔之不隔与不隔之隔两种中间形态。王国维致力的是如何从狩猎古典的隔转化为融合隔与不隔,并结合高尚之人格和天赋之才能,创造出文学的经典。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对于纠正当时的摹拟因袭之风和程式化创作倾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王国维《人间词话》自1908年末开始在上海《国粹学报》发表,直至1926年俞平伯将其标点并序后由北京朴社出版单行本。期间近18年中,基本上是沉寂的。随着王国维晚年国学大师的名分渐盛,其早年学术才逐渐抖落尘埃,为世人所关注。回顾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人间词话》研究,虽然视点各有不同,领域互有差异,但“隔与不隔”与“境界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可以说共同构成了学术史的三大热点。尤其是“隔与不隔”之说与“境界说”等若即若离,其本身即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王国维对词话文本屡有删改,其理论也在删改中不断趋于完善,而长期以来对隔与不隔说的理解多限于《国粹学报》发表本,自然也是一种局限。追溯手稿本中的原始话语,再对勘最后发表之《盛京时报*中的定本,也许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王国维隔与不隔说的理论形态。
一、三种文本中的“隔与不隔”之说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手稿本、《国粹学报》的发表本(简称学报本)和《盛京时报》的发表本(简称时报本)三种。手稿本当撰写于1908年夏秋间,学报本发表于1908年末至1909年初间,时报本发表于1915年1月。这三种版本的《人间词话》,就篇幅上来说,是不断压缩的,从手稿本的125则到学报本的64则,再到时报本的3l则,王国维不仅大致以“对半”的篇幅压缩着《人间词话》,同时对词话的内涵,也在不断做着调整。特别是在时报本中,连为后来学界广泛关注,讨论过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等重要条目,都被王国维悉数删除,但“隔与不隔”一则不仅一直稳居其中,而且其重要性也在不断的整合中被不断强化着。如学报本第39则云: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如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
这一则在手稿本是第76则,在时报本中是第24则,三本文字基本相同。
而学报本第40、41则云: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阑干十二独凭春,睛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可以直观,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楼凝望久,叹芳革、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深浅厚薄之别。(第40则)“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第41则)这两则在手稿本中分居第77则和第80则,学报本将其调整为前后相连的二则,语意当然也就更为集中了。但在时报本中,这原本以两则出现的条目则合并为一则:问“隔”与“不隔”之别。曰:“生年不满百(下略)……”“服食求神仙(下略)……”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下略)……”“天似穹庐(下略)……”写景如此,方为不隔。词亦如之。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云:“阑干十二独凭春(下略)……”语语皆在目前,便是不隔;至换头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使用故事,便不如前半精彩。然欧词前既实写,故至此不能不拓开。若通体如此,则成笑柄。南宋人词则不免通体皆是“谢家池上”矣。(第26则)时报本台前二本两则而成一则。次序变化较大,时报本将手稿本第80则与学报本第41则置前,而接以手稿本第77则和学报本第40则,融合而成一则,隔与不隔的问题论述得更为集中与自然,由写情到写景,由诗歌到词作,由作品举例到归纳理论,学理充足。时报本删掉论白石《翠楼吟》部分的文字,盖此前于白石多下苛刻之论,至此略加缓和之意,而将矛头泛指南宋人词。对于不隔的态度,时报本也有转变,由简单地否定,而变为根据作品需要来下判断,其论欧阳修《少年游》后半及其与前半的关系,即可见一斑。时报本自“使用故事”至结尾为新写成文字,王国维词学中的理性成分,随着修订的进行,也在不断加强着。同时将浮泛的以诗人或诗句来论隔与不隔的例子删除,重视在更广阔的语境中来讨论隔与不隔之说。而这是在王国维将有关专论境界类型的条目删除的同时,精心地润色隔与不隔这一条,其高度重视的心态当然是可以想见的。所以就具体论及隔与不隔说而言,手稿本尚显散漫,学报本则初步汇合,时报本则整合成说。其理论固随其不断调整而渐趋精密也。
隔与不隔是对举的一对概念,则诠释何谓“不隔”,“隔”之义自然也就清晰了。什么叫不隔昵?王国维除了举例之外,只有“语语皆在目前,便是不隔”一句算是解释。但这解释又实在模糊得很。在手稿本第75、76、77、80等则中,王国维大体以时代、诗人、单句、数句、半阙、整篇等多种方式来表述其不隔例证,朝代如北宋词不隔,南宋词隔,诗人如陶渊明、苏轼之诗不隔,韦应物、柳宗元之诗“稍隔”单句如“池塘生春草”等不隔,“数峰情苦,商略黄昏雨”等隔;数句如姜夔之“二十四桥仍在”数句等隔,姜夔“此地”数句不隔;半阕如欧阳修《少年游》上阕不隔,整篇如姜夔《暗香》《疏影》隔,《敕勒歌》不隔(仅少开头两句),等等。则隔与不隔的评判基础是呈流动形态的,是在朝代、诗人和作品之间变化着的,而在作品中更有全篇与部分的不同。所以隔与不隔说更多地类似一种批评理念,而且因为其评说对象多变,所以其理念也带有模糊色彩。
当然这种动态而略带模糊性的理念在三种版本的《人间词话》中也是渐趋稳定的。在学报本中,不隔的诗人增加了谢灵运,稍隔的诗人增加了颜延之,其他除了偶有文字润色,基本不变。而在时报本中的变化就更大,以人或单句的隔与不隔之例被删除了,而从篇的角度来分析隔与不隔之间的保留了下来,其理论形态则更为稳定了。王国维在时报本中分析欧阳修《少年游》一词,先言上阕的不隔,
再言及下阕换头数句时,没有用“隔”或“稍隔”一类的概念,而是用了“不如前半精彩”这样模糊的话语,这意味着王国维对于“隔”的具体形态更加谨慎了,更注重从整篇的角度来考量其隔与不隔的合理性了。
对于“隔”字的使用谨慎了,当然也意味着“不隔”的内涵也当有所调整。如果为王国维从整篇角度来论证其“不隔”之例添一证的话,则不妨可以看看王国维托名樊志厚所写的《人间词乙稿序》:“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在《人间词话》手稿本中,基本把这一节的意思保留了下来。按照手稿本的意思,此数阕词以“开词家未有之境”为自得,而《人间词乙稿序》则誉之为“意境两浑”的典范之作。由此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所谓整篇之不隔,尚需以创造性为前提。其次“意深”也是王国维颇为自赏的。所谓深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来探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一般隋感的流淌。如“百尺朱楼”一首,乃写一个有悲悯情怀的人俯看无力改变悲悯境遇的芸芸众生,试图彰显人类的普遍性的悲剧命运,确实非限于一家一人之堂庑而论;“天末同云”一阕则可以视为从“失行孤雁”的角度来为一个时代(清末)所写的挽歌,“昨夜梦中”似乎隐约要表现的是一种天才无法摆脱的痛苦。这三首词所表现的主题确实较为深远,而且都偏于悲情。这与王国维的审美倾向是有关系的。王国维的“物我两忘”乃是强调对现实情景的超越性而言的。所以既然“意境两浑”等同于“不隔”,则所谓不隔当然也就包含不为目前情景所限的意思了。
朱光潜可能是最早对于隔与不隔的问题进行重点分析的学者。因为只关注到学报本中的相关文字,所以对于王国维在时报本中对于“隔”的理解和宽容自然无法体会。朱光潜一方面肯定王国维的隔与不隔之说“是前人从未道破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王先生论隔与不隔的分别,说隔‘如雾里看花,不隔为‘语语都在目前,也嫌不很妥当。因为诗原来有‘显和‘隐的分别,王先生的话,偏重‘显了。‘显与‘隐的功用不同,我们不能要一切诗都‘显。说赅括一点,写景的诗要显,言情的诗却要‘隐。”后来学者颇有对于朱光潜用隐与显来概括隔与不隔持不同意见者,但朱光潜用隐显来分析其实是预设了前提的,那就是从情趣和意象的关系来区别,则在由意象而呈现情趣上,也确实存在着隐与显的不同。朱光潜的感觉未尝没有道理。但问题是解读隔与不隔是否仅由意象与情趣的关系一端就能得到圆满的结论,这才是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
不过朱光潜的思路还是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响应,譬如在1941年出版的《斯文》卷一第21、22合期上,有两篇《评<人间词话>》的同题文章,作者分别是唐圭璋和吴征铸,其评述隔与不隔即大体持隐与显两者的关系而论。稍后饶宗颐虽然也不脱隐显的语境,但他依据词的特性在于“以隐胜,不以显胜”,“以曲为妙,以复见长”,所以王国维之所谓隔,在饶宗颐看来,正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饶宗颐说:“予谓‘美人如花隔云端,不特不损其美,反益彰其美,故‘隔字不足为词之病。”更直言如姜夔“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波心荡,冷月无声”之句,“言外别有许多意思,读者不徒体味其凄苦之词境,尤当默会其所以构此凄苦之境之词心。此其妙处,正在于隔。”就对词的体性和对姜夔词句的分析来看,饶宗颐所说,确有道理。但饶宗颐的裁断不免对王国维的整体语境有所忽略,因为对于词体的隔——隐、曲、复等特征,王国维并非漠然视之,其以“深美闳约”、“要眇宜修”为词之体性,即意味着王国维必然会重视词体隐、曲、复的特性。不过在王国维看来,这种特性应该是与“不隔”状态的言情写景交融在一起,通过结构的调整配合而整体呈现出来。
孤立地来看待隔与不隔,自然难以成就学理的圆满。钱钟书说:“有人说‘不隔说只能解释显的、一望而知的文艺,不能解释隐的、钩深致远的文艺,这便是误会了‘不隔。”确实,仅仅用隐与显来解释隔与不隔,不仅流于表面,而且容易误导王国维的理论宗旨。
但是,只从隔与不隔之两端来展开分析,恐怕仍是不能完全契合王国维本意的。
二、隔与不隔的四种结构形态
在手稿本和学报本中,王国维还用过一个模糊的概念:稍隔。这是介于隔与不隔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在手稿本和学报本中,被称为“稍隔”的诗人有颜延之、韦应物、柳宗元、黄庭坚四人。这四人为何被列为“稍隔”?王国维没有解释。倒是手稿本第18则言韦应物的“流萤渡高阁”不及冯延巳《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在《人间词乙稿序》中,冯延巳是与李白、李煜并称为“意境两浑”的诗人之一,按照上面的分析,即是“不隔”的典型,则这里言韦应物此句“不能过也”,也即是“稍隔”的意思了。而黄庭坚的“稍隔”,则在《人间词话》更难觅旁证,参诸他人评论,或赵翼《瓯北诗话》所说略近于此:“山谷则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过于用力,略失自然之趣。在手稿本第85则中,王国维批评史达祖《喜迁莺》之“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句,张炎《高阳台》之“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句说:“此等语亦算警句耶?乃值如许笔力!”亦是此意。
关于“稍隔”的内涵,能够藉以参证的也许是手稿本和学报本中论姜夔《翠楼吟》的一节文字。王国维先是分析了欧阳修《少年游》咏舂草一阕,上阕不隔,而下阕“谢家池上”两句隔。接着分析姜夔《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数句不隔,而“酒祓清愁”两句则隔。这些对于隔与不隔的划分,似乎十分明确,但实际上王国维接下的一句话才是关键所在:“然南宋人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深浅厚薄之别。”则纵然都是不隔,姜夔之不隔与欧阳修之不隔也是不同的;或者直接说,姜夔之不隔其实也仍然包含着隔的成分的,是不隔之隔。因此在王国维的语境中,北宋词虽以不隔为主,但也包含着隔的内容。而南宋词的不隔本身就是在北宋等面下之的不隔,同以“不隔”为名,其实是隐含着高下的。所以王国维的隔与不隔之说绝非简单地区别隔与不隔两种形态,其中颇有介乎其间的模糊形态的。“稍隔”与“不隔”中等而下之部分的内容,其实构成了王国维隔与不隔说的第三种状态了。
在时报本中,“稍隔”的概念也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隐含“稍隔”之意的具体分析。手稿本和学报本都没有提及“稍隔”的单句、数句或整篇,而只是就诗人的基本特征而言的,但其介于隔与不隔之间的状态自无问题。时报本不言“稍隔”,而只是在分析作品时将“稍隔”的感觉表述出来,也许与王国维认识到“稍隔”的说法也同样有“雾里看花”的特点有关。王国维的这一转变明显表现在对于隔的态度的转变上。如时报本论欧阳修一节云:“如欧阳公
《少年游》咏春草云……语语皆在目前,便是不隔,至换头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使用故事,便不如前半精彩。然欧词前既实写,故至此不能不拓开。若通体如此,则成笑柄。”这一节其实是对学报本第40则的改写。注意到这段改写,我们可以将前两本中的不隔、稍隔、隔的三分法进而细分为不隔、不隔之隔、隔之不隔、隔四种,不隔当然是审美理想,纯粹的隔是反面典型,王国维在这四种形态中,其实更为关注中间的不隔之隔和隔之不隔两种状态。
隔与不隔说的四种结构特征是王国维在时报本中才将其最终完成的。在学报本中,对于姜夔《翠楼吟》的结构还是不隔与隔的二分法,而在时报本对欧阳修《少年游》的分析中,王国维既指出从“阑干十二独凭春”到“行色苦愁人”一节的不隔,而对于换头“谢家池上”三句,王国维没有用“隔”来评价,而是说“使用故事,便不如前半精彩”来评价。按理说,“使用故事”便是隔了,手稿本和学报本便明确使用“隔”来评论这几句,时报中的这一转换,意味着王国维对“使用故事”在特定语境中的认同,这既不是“不隔”,也不是“隔”,而是在。不隔”之中的“隔”,所以虽然“不如前半精彩”,依然能得到王国维的部分认同。而且王国维还为自己的这一“不隔之隔”作了解释,王国维反对的是“通体如此”,即整首作品的“隔”。王国维从结构角度考虑到欧阳修在实写后“不能不拓开”,这“不能不”三字,其实是对“使用故事”的一种肯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王国维对于隔与不隔的评定是从整篇结构来考虑的,若是结构上的延伸或拓展,需要将意思隐藏或模糊,则这种“隔”是允许的。王国维反对的其实是通体如此的“使用故事”所造成的“隔”的体验。
王国维对辛弃疾词的评价,倒是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他对隔之不隔的认同。辛弃疾被王国维誉为“堪与北宋人颉颃者”之“惟一”之人。为何如此眷顾辛弃疾?这个问题其实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今以“隔之不隔”解之,或许有助于接近王国维的思想底蕴。手稿本第11、56两则都提到稼轩《贺新郎·茂嘉十二弟》一首,如果按照王国维反对用典、使事的理论,辛弃疾的这首词正蹈此弊。唐圭璋即说:“王氏盛称稼轩《贺新郎·送茂嘉十二弟》词,以为语语有境界。然是篇罗列荆轲、苏武、庄姜、陈皇后、昭君故事,依王氏见解,正隔之至者,何以又独称之?”唐圭璋注意到王国维之说在现象上的矛盾,堪称锐眼。不过因为王国维只是在话语上揭出“隔”与“不隔”两种基本形态,而对介于其中的两种交叉形态只是有描述有分析,而未提炼出明确的理论的话语,在此隔与不隔的两极背景下来考量王国维的这一节话,确实是存在着悖反的现象的。但如果我们能从学理角度将王国维隔与不隔说细分为四种基本形态,则王国维对稼轩此词的垂青,也就可以得到学理上的支撑了。王国维先后以“俊伟幽咽”、“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来评价此词,前者是言其符合词体“要眇宜修”的文体特点,而后者对其结构及其用典的化人为己、自具境界称赏不已。在运用典故“隔”的形式下,依然表现出情感的不隔状态。隔与不隔的两极现象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倒是介乎其中的隔之不隔与不隔之隔更显常态,所以理论可以悬格甚高,而批评则要落实到实际的层面,因之王国维在理论话语上明确提出隔与不隔,而在实际批评中则更为关注隔之不隔与不隔之隔两种形态。
之所以在王国维显在的隔与不隔说之外,寻绎提炼出潜在的隔之不隔与不隔之隔两种中间形态来作重要分析,与王国维惯常的概念对举的思维方式的启迪直接相关。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基本上就是通过概念对举的方式来建立理论和进行批评的,如造境与写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理想与写实、主观与客观、大境与小境、动与静、出与入、轻视外物与重视外物,等等。这主要是从立说鲜明的角度来说的,其实在对每一对概念的解释中,都对介乎其中的中间形态予以了足够的关注。换言之,两极往往是王国维制定的标点,而其论说的范围是游乎两极之间的。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王国维即在优美与宏壮的对举中,加入了“古雅”的概念,其理念与此也是一致的。时报本第3则:“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这一则能够在手稿本、学报本、时报本中都得以保留下来,王国维的重视之意当然是不可否定的。极端形态的造境与写境其实是不常见的,常见的反而是介于其中的合乎自然的造境和邻于理想的写境。只是能将这种介乎不隔与隔之间的不隔之隔与隔之不隔表达合理,就非一般诗人所能及,所以王国维提出了“大诗人”的概念。王国维将这些概念对举出来,确实没有简单地褒此贬彼,而是在一种互动关系中来确立自己的审美理想。所以隔与不隔当然也不能将其简单化处理。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虽然没有把境界以一种合成词的方式来分解其意蕴,但在此前王国维使用更频繁的意境概念中,王国维已然将之分为数种类型,其理念可以与其隔与不隔的类型分析对勘。如《人间词乙稿序》云:“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王国维虽然在字面上将意境具体形态分为三种:意与境浑、意余于境、境多于意,实际上只是就“足以言文学”的角度来说,若意与境分,则已不成其为文学了,故王国维未予论列。则综而论之,王国维的意境说其实也是有四种形态的,这与其隔与不隔之说之间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如果“意与境浑”略等于“不隔“的话,则“意与境分”相当于“隔”了,而介乎其中的“意余于境”和“境多余意”就相当于“隔之不隔”和“不隔之隔”了。王国维既然明确说明意、境二者可以偏重而不能偏废,则其对不隔之隔和隔之不隔的理论认同自然也无可怀疑的。如此说来,环绕在王国维心中的境界说,其实是一个系统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各有侧重,但汇流成河,彼此都在一个理念下互相依存着。
隔与不隔说的四种形态虽然此前未能为解读《人间词话》的学者明确划分,但在相关评述中,也有部分学者曾感悟及此,只是未能用清晰的理论话语表出而已。如钱钟书首先认为“不隔”其实是一种“透明洞彻的状态”,要靠作者特殊的艺术本领才能达到。他说:“比喻、暗示、象征,甚而至于典故,都不妨用,只要有必须这种转弯方法来写道‘不隔的事物。”窃以为钱钟书所谓“转弯方法”颇能得王国维之用心,因为王国维虽然一面明确反对用典使事,使用替代字,另外一方面对于在“不隔”的写景前提下,从考虑结构需要而采用“隔”的写法表达了认可,所以由不隔可以“转弯”到隔,由隔也可以“转弯”到不隔。钱钟书的“转弯方法”在吴征铸的笔下便是强调隔与不隔
的“配搭得宜”。钱钟书所重在如何达成“不隔”的艺术效果,而吴征铸所重在“谋篇之道”上,是从整篇作品来考量的。他说:“……故知一人一词,不隔语与隔语相杂者不得已也。……自然与人工,隔与不隔,在一篇中配搭得宜,实有相得益彰之妙。盖人情恶重复而喜变化,故文事务参差而起波澜。”很有意味的是,吴征铸上述所论乃是就王国维之不足而言的,而在我看来,此本是王国维题中应有之义,在时报本的相关论述中,这种题中之义表述得就更清晰了。但在诸家纠缠于隔与不隔两极而对王国维妄加评议之时,不能不佩服吴征铸的别具慧眼。
三、从虚实关系到不隔而深的审美理想
王国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不隔之隔,与其对词的艺术韵味的追求密切相关。“语语都在目前”的实景描写,固然能给人以真实而深切的影像,但其背后的韵味才是王国维努力追求的。由此,隔与不隔之说与王国维的出入说也可以发生关联。手稿本第117则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人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人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人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这一则以往多孤立解读其内涵,盖与此则理论本身内涵较为自足有一定关系。但其实此则在王国维词学体系中,尤其是与隔与不隔之说有着重要的关联。从此则结尾来看,原是针对周邦彦和姜夔二人而发的,因为王国维直言姜夔以下之词人,于出、人二事均未梦见,暂将姜夔撇开不论。“美成能人而不能出”到底是何意?试对看数则词话,便可略窥一二。如《人间词话》手稿本第8则云:“美成词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手稿本第9则云:“词最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王国维评价周邦彦“能人”,按其语境,当是指“言情体物,穷极工巧”这一方面,即在写景咏物方面能做到体察人微,揭示出景和物的神韵所在。而所谓“不能出”,则是太过胶执于景物,不能由实到虚,升华景物的内涵,从而缺乏“深远之致”。王国维数条评论都提到周邦彦词的创意之才的缺乏,也是因此而起,所以出入说的本质正在于虚实关系的合理运用。
因为王国维偏尚不隔,而其所举不隔之例,往往属于自然显豁的境界,遂令人对王国维词学是否有对深度意蕴的追求不免产生怀疑。其实缺乏深度的不隔并不是王国维所追求的,通过不隔的语言表象而能让读者感受到超越语言表象的深意,才是王国维所大力提倡的。手稿本第7则云:“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可见“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是艺术评价的基本前提。在手稿本和学报本中,王国维虽然都将欧阳修《少年游》上阕和姜夔《翠楼吟》换头数句认为不隔,但按照王国维的意思,南宋之不隔相比北宋之不隔,仍是有差距,这差距就在“深浅厚薄”上。北宋词素来是王国维悬以为理想的阶段,则按此语境,只有不隔而深厚才是其审美的最高标准。所以讨论不隔,便无法回避“深”的问题。
王国维这种由实到虚、虚实并重的评判态度,也足以说明他绝非仅仅停留在意象的鲜明灵动上,而是以不隔为基础,追求通过适度的隔来造成词的深远之致。在手稿本第4则、学报本第11则中,王国维反复强调要用“深美闳约”四字来移评冯延巳,而在《人间词话》中,冯延己—直是王国维引以为典范的人物,则“深美闳约”的审美旨趣也当然是王国维所努力追求的。写实的词句虽然容易达到不隔的境界但泛泛的写实并不意味着高境的产生,在明晰的写景中能让读者生发出言外之意,这才是王国维偏尚的深度所在。手稿本第5则、学报本第13则说李璟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两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换言之,由眼前的景致而生发出更深更高的人生联想,这样的写景才有深度。因此王国维对于冯延巳、王安石等冷落此二句,反而对“细雨梦回”两句独致青眼不能认同。因为“细雨”两旬的联想空间毕竟限制在鸡塞与玉笙的范围内。而“菡萏两句流露出来的“豪华落尽”之意,与屈原《离骚》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个人命运的严重失落之间,确有可供联想的空间。而屈原之命运困顿在中国古典文人中不啻有范型的意义,相形之下,“菡萏”两句与“细雨”两句之阐释空间,确有“深浅厚薄”之不同的。
言外之意当然有待于读者的阅读体验。作为作者来说,用直观的语言表述出令读者感到陌生而有意味的景象,才是首当其冲的。王国维之所以在原则上反对用替代字、典故等。除了这些有碍于直观之外一因为替代字、典故已自具一定的历史意蕴,也与这种典故、替代字其最初产生的情景与作者当下所要表达的情景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距离或偏差有关。所以不仅所有的比喻都是蹩脚的,而且所有的典故也都是有缺陷的,其由历史意蕴对当下意蕴的侵占或吞兹,所造成的局面不免是当下意蕴的流失和残缺不全。而一旦当下意蕴与历史意蕴大体重合,则文学创作的原创意味便被削弱了,而失去原创价值的文学,同样是没有意义的。这—层意思,王国维已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先期表达过:。……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王国维在这里提到的“特别之境遇”其实正是梅尧臣所谓“难写之景”,而“特别之眼”只是写出言外“不尽之意”的前提所在。这两层“特别”又都是建立在诗人“深邃之感情”的基础之上的。“出”与。人”的主体虽然是同一人,但实际上已是两个不同的审美主体了,而“出”之主体才能造就文学的“言外之意”。所以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不是简单地追求一种语语都在目前的自然直观之景象,而是以深厚的情感底蕴、景物的特殊性和观察体会的特殊性作为背景的。对言外深意的追求,对悲情的强调,对特殊景物的关注,对诗人之眼的要求,对自然真切的语言的偏好,彼此结合,才构成王国维“不隔而深”的审美理想。
四、隔与不隔的语言特征与经典观念
王国维对隔与不隔具体内涵的描述,一直如云中鳞爪,略显端倪而已。在这些有限的端倪中,语言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手稿本第77则和学报本第40则都有。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一句,手稿本最初的文字更是“语语可以直观”。手稿本第75则、学报本第38则评论姜夔的《暗香》、《疏影》为“无片语道着”,等等。这些关于隔与不隔的评论,都以语言为直接的表象,所以考察隔与不隔之说的内涵,语言一项乃无法回避。
先从隔的语言表象说起。在《人间词话》中,替代字、用事、典故一直是王国维反对的创作手段,因为它们负载了固有的意义。再加使用,意味着诗人原意的屈就和部分的流失。而不完整的表达带来的是文学意义上的不完整。譬如“谢家池
上,江淹浦畔”,此在原作者而言,固是触景生情、自然而成之好句,然姜夔移用到自己的作品里,就是“借现成的‘古雅来替换独特的创造”。因为姜夔既难有谢灵运一般的心情。也难遇谢灵运当时所遇之景,却要借用其成语,则这种成语确实会带来词人原意的流失。独特性和创造性一直是王国维孜孜以求的,所以“原则上”王国维反对使用典故及替代字等这些有可能影响到独特性和创造性的文字表达方式。
之所以强调“原则上”,是因为在既往词史中确有一段以用事用典呈才使气的历史,如南宋词的典雅化往往带有程式化的倾向,替代字不仅使用频繁,而且从理论上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但替代字其实也是一种历史经验,当一个作者将自己原本冲口而出的情感要寻找合适的替代字来表达的时候,其实正包含着将自己的情感规范到历史的情感当中的意识。为此王国维不能不以一种强烈的态度来反对事典之风。手稿本第8则批评周邦彦《解语花》以“桂华”二字代“月”,等等。认为词人多用替代字,“非意不足,则语不妙”。手稿本第42则云:“人能于诗词中……不使隶事之句,不用装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替代字实际上是作者无法“语妙”“意足”后的一种补救而已,是借他语来补己语,借他意来补己意,自然是等而下之的事了。
替代字、用事、典故都是从阅历中得来,王国维因为强调词体的言情之真和语言之真,故对词人的阅历也深致疑问。学报本第16则所云之“赤子之心”其实就是没有被经验和历史语境所熏陶过的直觉率真之心。王国维曾接受过西方文艺思想中的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之分,其实也类似于凭借历史经验之诗人与纯然自然流淌之诗人的分别。学报本第17则云:“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学报本第18则亦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这两则从理论上来说,其实是从不同角度来强调主观性情之真对于抒情文学的重要性。但阅世浅当然可以让词人摆脱历史典故的束缚,而直陈性情之率真。王国维极力称赏李煜,正于李煜词的语言多生活化、感性语,但却包孕着生活的真实,又因为真实而能让读者产生审美上的共鸣。所以强调词体语言的直观和如在目前,在王国维的观念中,正是词体体性的规定所致。
这让我想起了日本学者竹内好,并对他的敏悟欣赏不已。竹内好曾经引用1910年出版之永井荷风的长篇小说《冷笑》中的一节来表现他理解中的对“隔”的理解:……他们(指汉学家)一直恪守着几千年以前的,那个时代的诗人依该国(即中国)语言和发音的自然规律而创造的形式,不图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反而把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感想视作卑拙,把一字一旬极力转化运用古人的用语看作是正确的写诗的方法、技巧之生命。那些人兴趣之所在是故意压抑着个人独特的感情,考虑如何把它纳入一定的模式中去,从而捉摸如何使这样写出来的诗,显得很自然,如脱口而出的窍门。
……他们赏花也好,赏月也好,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自然之美,直接引起他们的感动,而通过回忆或回味古人歌咏花月的名句唤起他们的兴趣。……古人的诗句是他们的生命。对于过去无上的崇拜,承认传说的绝对权威,使他们安坐在不受任何时代影响的、坚固不摧的城堡里。永井荷风批评的虽然是日本的汉学家,但这种思维模式和创作模式其实正传承自中国。在中国被引为“传统”的模式里,永井荷风恰恰看出了其中所蕴含的自我和自然的消失,将原本活泼泼的生命体验用历史的经验和框架来过滤来规范,从而形成了一种积淀着历史意蕴的所谓文学。竹内好把永井荷风这一节话语作为对王国维“隔”的注释,也令我们这些至今生活在传统思维或创作模式的现代人为之震撼。
反对典故和用事只是王国维为了强调“不隔”而提出的基本要求,事实上,典故问题并不是一味反对或简单排斥就能解决的。王国维对欧阳修《少年游》和姜夔《翠楼吟》的分析,已可见出其内心对事典的“妥协”原则了,这种“妥协”当然是王国维从悬格甚高的审美理想回归到常见的创作状态而不能不作出的理论调整。竹内好说:“没有对于‘隔的怀念,岂有对于‘不隔之执着?王国维没有说过一丁点儿‘隔不好、‘不隔好这种小家子气的话。……我想。他是把‘隔之‘不隔与‘不隔之‘隔区别了开来。绝不是以卑陋的尺度去蹂躏古典的狩猎者。”我以为“没有对于‘隔的怀念,岂有对于‘不隔之执着”—句是顿悟见性之论。不过竹内好毕竟言之简单了,如何“怀念”,如何“执着”?竹内好未加说明。“古典的狩猎者”完全可以呈现出古板和灵动两种形态,则因为留恋于事典而在表象上流露出“隔”的气象的,也可以融人到“不隔”的境界中,而成为一种创作的常态的。“自有名句”是不隔自创而成,所以令人瞩目·自成格调往往与隔相关,因为文字背后的历史意蕴,也可以使作品的审美韵味得以延展。语言的创造性与典故的合理使用其实可以从对立而走向统一的。
隔与不隔的问题在王国维的语境中,也与诗人的人格有关。在文学领域,王国维一直高举着两面旗帜:一面是高尚伟大之人格,一面是高尚伟大之文学。所谓“高尚伟大之人格”,其基本内核则在于对名利的疏离,以“游戏”的心态来从事创作。所以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一再强调:“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在强调高尚伟大之人格之外,王国维还不断强化着一种天才意识与经典观念。在《人间词话》中有一系列与“创造”相关的概念或词语,如“创调之才”、“创意之才”、“与晋代兴”、“开拓之功”,“换意”,“开前人未有之境”,等等。这些概念都从不同角度强化着王国维对于创造的重视,以及创造这一内涵在王国维词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王国维语境中经常出现“豪杰之士”、“大诗人”、“大文学家”等概念,这是一种对超越一般文学之士之上的文学群体——天才的一种独特称呼。王国维说:“势力之欲,人之所生而即具者……故非旷世之豪杰,鲜有不为一时之势力所诱惑者矣。”所谓豪杰应是专指不受“势力之欲”诱惑之人物,他们因为超越人间种种之“关系”,所以不仅在烛照物情上高人一筹,而且能有对自我内心之观照旁及于众人之情,故其境界自然高远。王国维说:“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隋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所以对名利等势力之欲的超越及其自身情感和表现在文学中的情感带有人类普遍意义,这样的人才是王国维心目中的“大诗人”,也只有这样的大诗人才能造就文学上的经典。
六、余论:隔与不隔说提出的现实背景
在20世纪初,王国维曾经一度是思想新锐的代表。在王国维生前,吴文棋即曾撰《文学革命的先行者——王静安先生》来称赞其对此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启蒙意义。细读《人间词话》,我们很容易就发现,在文本中时时出没着一个被批评的群体:近人。在王国维的时代,以晚清四大家为代表的词坛,宗尚南宋吴文英、王沂孙等人词风,王国维在《人间词乙稿序》中就称其不过是“伪文学”而已。如手稿本第23则说“近人”偏嗜南宋词是“弃周鼎而宝康瓠”,手稿本第69则认为谭献和朱祖谋等对于“自然神妙”的审美旨趣“尚未梦见”。学人之词往往以学问为本,历史语境成为其创作的常态,这在提倡“不隔”的审美理念的王国维心目中,无疑是悖反的。
“近人词风”是个什么概念?窃以为吴征铸所说,最切事实:“有清一代词风,盖谓南宋所笼罩也。卒之学姜、张者,流于浮滑;学梦窗者,流于晦涩。晚近风气,注重声律,反以意境为次要。往往堆垛故实,装点字面,几于铜墙铁壁,密不通风。静安先生目击其弊,于是倡境界为主之说以廓清之,此乃对症发药之论也。”境界说堪称正面揭旗,而隔与不隔说,则可视为对境界说的形态分析,以此来切人对近人词风的分析,不仅针砭时弊,而且有导引填词创作方向的用意在内。王国维是纯文学的积极鼓吹者,纯文学的提倡正是因为目睹锵锻之文学之途已开的现实而言的。王国维不是“肉食者”,无力以国策的方式来改变这种令他担忧的文学现实,所以只能致力于文学观念的清理,试图以境界说来一醒世人耳目。只是1908年之前的王国维还是处于“人微言轻”的地步,而认识到王国维文学观念的价值则差不多要等到王国维去世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