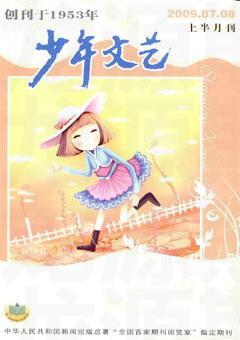发财梦
王晓俭
我永远记得童年时候的一件事,虽然已经那么遥远。那么微不足道了。
那时候,我和姐都还在上小学。暑假,正是收粮的季节。油菜籽、小麦、稻谷、玉米,都以金黄的姿态展现在眼前。在粮站上班的爸妈每年到这时节便早出晚归,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家就住在粮站的家属大院里,隔着一条水泥路,是粮库门口一大块空地,每天一大早,这里就挤满了前来卖粮的,热闹极了。
有一天,我和姐正做暑假作业,窗外传来热闹的声音使我们心里痒极了,我们便溜出去看。妈和几个一起开票的同事把桌椅都摆到外面来了,几台磅秤一字儿排开。妈他们一边称粮一边把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随后开票,给农民付钱。那些农民用舌头舔一下大拇指,喜笑颜开地点着辛苦一年换来的钱,收起空粮袋走了。随后,便会有粮站的工人背上鼓鼓的粮袋送进仓库。
太阳挂在天上,那么高,那么亮,仿佛能熔化一切。我被晒得口干舌燥,对姐说:“我要喝水!”姐没回答我的话,却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些来卖粮的人。
天真热,我们站在旁边看着都浑身冒油,而且头顶上还有大树遮阳哪!粮站里的职工都有粮站提供的凉开水消暑,而那些来卖粮的农民呢,大老远赶过来,真不是滋味儿吧?瞧他们的白背心,泥呀汗的,都变成灰的了。
“你看见了吗?”姐捅捅我的胳膊。
我眼睛一眨巴:“卖茶给他们?”
“嘿!”姐咧嘴直笑,“你倒是挺灵的。”
我和姐都知道有钱的好处,也一直梦想发一笔大财,这样,好吃的东西可以买个够,好玩的东西可以买个够。但父母除了给我们买学习用品的钱,其他一分钱也不给。
卖茶也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爸爸一有工休,便用自行车带着我们姐妹俩去乡下奶奶家,我坐前面的横杠上,姐坐后面的车架上,一路上,总看见路边柳树阴下有几个茶摊。卖茶的都是些老头老太太,也有几个小孩子,估计是帮大人看着的。扯一块帆布遮阳,摆一张歪歪扭扭的桌子,上面放着几个玻璃杯,有白开水、茶叶茶,还有红红绿绿的水果茶、糖茶,价钱也1分、2分到5分不等,有的茶摊还摆着切开的香瓜,上面盖着白纱布防灰尘和蚊蝇。卖茶的人呢,坐在竹椅上优哉游哉,好不自在。爸爸有时骑累了,会就近在一个茶摊上买茶喝,一般都是1分一杯的白开水。其实我们都非常想尝尝那种水果茶,但不敢吱声。也奇怪了,普普通通的白开水喝在嘴里,都比家里的解渴一千倍!我和姐在那时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摊子,挣很多的钱。比如说,茶摊。
说干就干,姐在家烧水,我去院子里摘佩兰叶子、霍香叶子,还有抽出嫩尖尖的竹叶芽儿,用来泡茶。把一只铅桶洗干净了,烧开的水灌进去,直烧了三壶水总算将铅桶灌满了。我和姐一左一右拎起铅桶。还各自拿了方凳,两人的肩膀都耸起好高,泼泼拉拉来到粮库的场地前。
场地上人山人海。我们将方凳摆好,放上几个玻璃杯,倒上茶,摆开架势开卖。没人注意我们。姐推推我:“你先喊。”
我忸忸怩怩地笑:“你先喊嘛。”
“没用!”姐朝我一瞪眼,转过头就叫唤起来:“快来看哪。清清凉凉的茶叶茶哪,2分钱一杯,包你解渴哪——”像卖冰棍卖茶叶蛋的贩子那样叫,叫得悠扬抒情,充满旋律。这一喊,真有人转过头来了。一个排在队伍里等收粮的农民将粮袋放在原地占位,自个儿踱过来,左一看,右一看,饶有兴致的样子。我被看得不好意思,低着头就知道傻笑,姐一边推我,一边老相地问他:“看,这么热的天,你还排在后面,有得等哪,还不买一杯茶?”那人笑眯眯地不做声,依然看着我们,然后慢悠悠从腰上解开一个袋子,再从袋子里拿出一个水壶,仰头喝了一大口,这才说:“是呀,这么热的天,当然得随身准备点茶哕!”边上一些人都哈哈大笑起来,随后像合谋好了似的,一个接一个拿出自己带来的各种装水的容器,咕嘟咕嘟喝起来。有的还摘下头上的草帽给自己扇风。
我一看傻了眼,凑到姐耳边悄悄说:“他们都带了水,我们还怎么卖啊?”姐这回也给弄了个干瞪眼,她气呼呼地“哼,哼”了半天,才吐出这么一句话:“卖那么多粮还舍不得喝2分钱一杯的茶,小气巴拉的。”
“哎,哎,小姑娘,粮食粮食哪里来,农民伯伯种出来。这可是你们课堂上学的哦,这些钱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粮换来的,不作兴浪费的。”人群里有人说话。
再没人理我们,他们忙着上磅、开票、取钱。我们的小茶摊冷冷清清。太阳把水泥地晒得滚烫滚烫,汗水成串儿地从额上滚下来,汗出多了,喉咙里便渴得要着火,嘴皮子像绷上了一个布套套。我们只好不停地喝自己的茶。姐都懒得吆喝了。
我和姐就这样足足坐了有一个钟头。依然没人光顾我们的茶摊。
“晒死啦!我们还是回去吧!”我嘟囔着。
姐斥责我:“不行!起码卖掉一杯茶再走,不然白忙活了。”
歪嘴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歪嘴是粮站的背粮工人。他没有家,一个人住在粮库边上的一间小屋里,平时看仓库,收粮时背粮。叫他“歪嘴”,是因为他的嘴巴不知为何歪在一边。半边脸像给抽掉了筋似的皱成一团,据说是头颈神经坏了。假如你在他前方跟他说话,他就向后方拧下巴颏。不熟悉他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很倔、很不友好的老头。别看歪嘴年纪不轻了。走路还微瘸,力气却很大,一大麻袋的粮他不歇一口气就背进了粮库。我们都不怕他。有几回我们看见歪嘴背着两袋面粉,防尘帽下的嘴巴、眉毛、胡子糊得一片白,我们围着他哈哈大笑:“歪嘴,大白脸!歪嘴,大白脸!”歪嘴不恼,弯着腰,从面粉袋下面转过脸来看着我们呵呵笑,一张脸挤得更皱了。有时歪嘴跟我们开玩笑:“给我做孙女好不好?”我们朝他翻白眼:“谁要做你孙女,你连儿子都没有哪来的孙女。”这句话每每都让老人蔫了,背着粮的脊梁也塌下去。这是歪嘴最心虚之处。成年后的我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对老人经常讲这句话。成年后,我才意识到,孩子多么残酷,多么懂得利用他人的痛楚。
歪嘴笑呵呵递过来一张暗紫色的五毛纸钞,说:“姑娘们,别愣着啊,给我喝杯茶。”我有点回不过神来,还是姐反应快,高兴地端起茶。我不顾姐朝我眨眼睛使眼色,问他:“那边不是有给你们搬粮工人备着的凉水缸么?”
“嘿,我喜欢喝你们姐妹俩的茶呀!”歪嘴一口气喝完一杯茶,说。
“可是,我们没带零钱,找不开。”
“没关系,过会儿嘴干了,再到你们这来喝茶。五毛钱,归你们了。”
我迅速用仅有的算术水平在心里速算了一遍,五毛钱,可以买25根棒冰,也可以买50根搅糖稀,可以买无数的画片,我开心极了,和姐交换一下眼色:我们发财了!
姐虔诚地将茶杯再一次灌满,等待歪嘴来消费他余下的四毛八分钱。
可是,直到卖粮的人寥寥无几了,歪嘴还没来。我看着手里的五毛钱,问:“他该不会是忘了吧?要不要去找他?”
姐想了想说:“歪嘴说五毛钱归我们了,来不来喝是另一回事,钱先放身上。”我觉得姐的分析很有道理,便心安理得地收拾东西回家了。
第二天,我们没去卖茶。人虽小,也会算账。为歪嘴一个人烧茶?还要在太阳下烤?没
门。第二天我和姐的主要话题便是怎么去花这五毛钱。讨论了半天,最后我们决定先用两分钱买两根搅糖稀,一人一根,找回的四毛八分钱一人一半,各自花。这时我们才明白自己干出什么样的事来了。这和偷窃有什么两样?
为此,我们第一次对歪嘴有了畏惧感。一次放学,远远就看见歪嘴从对面走来,他那两道浓得出奇的眉毛往下一压,向我们张开双臂,一副来势汹汹的样子。我和姐吓得尖叫。分别从歪嘴的两侧一溜而过,我却被歪嘴拦腰抱住,姐只得转回身来救我,她抓住歪嘴的衣服又拉又扯。歪嘴紧紧抱住我,那张沟壑纵横的脸此时显得如此恐怖:“小、r头,做不做我孙女,啊?”我叠声尖叫:“我做,我做,快放了我。”趁他松手的当儿,我鱼一样滑脱下来,牵住姐的手撒开腿,仰着脸飞跑。惊魂未定的姐又得意起来,回头朝歪嘴做了个鬼脸:“做你个大头鬼孙女!”
我们到底还是有些不祥的感觉,歪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给他喝茶而存心报复我们?但想想又不对,他可以向爸妈告状呀,或者直接问我们要回钱。最后的结论是,歪嘴早把这事给忘记了。成年后的我才想明白,歪嘴是不忍心看我们在大太阳下空守茶摊,失望而归。才故意来买我们茶的。然而,当时年幼无知的我们见着歪嘴照样仓皇逃走。那剩下的四毛八分钱成了烫手的山芋,成了我们的心病,花又不是,扔又不是。
我永远记得那天一大早,我和姐还在床上,就听爸妈在院子里和别人说话:“什么什么?歪嘴中风去世了?”然后是进屋拿东西,接着又是出去的声音。
我心里一紧:“姐,你听见什么了吗?”
姐有点不敢相信地看看我:“不会吧?”
我们磨磨蹭蹭地起床、刷牙、洗脸,其实内心百感交集,耳朵一直在竖着听外面的动静。终于,我们忍不住了。透过窗子朝外张望。那儿,曾经热闹非凡的那块空地,有人在默默地忙碌着。这告诉我们,歪嘴的离开是事实。
歪嘴没有一个亲人,一切后事都是粮站的领导和职_T为他办的。其实也没什么好办的,他的小屋里很简单,一床一桌一椅和简单的灶具,那些都是粮站的,唯一的私人财产是他塞在床底下的一叠钱,粮站用这些钱为歪嘴办了丧事。
“姐,我忽然觉得歪嘴挺可怜的。”我说。
姐呆呆地站在窗口,没说话。我走近去,仔细看了看她的眼睛。“姐,你哭了吗……是不是……歪嘴……因为那五毛钱,才……你别哭呀,都怪我……”我说着,忽然一咧嘴,也抽抽搭搭地哭出了声音。
“你说,如果我们答应做他的孙女,让他高兴高兴,还有,坚持卖茶,不,送茶给他喝,也许……”姐擦了擦眼泪。
“嗯……”我点点头,头一次体会到那种失落、沉重、沮丧的心情。
我和姐也去参加了歪嘴的追悼会,姐悄悄拿出我俩的四毛八分钱,看看我,将它塞进准备和歪嘴一起火化的被褥包裹中。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又一次流出来了。
也许,童年就是在那一刻结束的。
阅读点睛
小姐妹对歪嘴态度变化的过程是“瞧不起——伤害——讨厌——畏惧——愧疚——崇敬”,作者剥笋般地剥出了老头红亮滚烫的一颗爱心。情节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
作品成功地运用了反衬手法。以歪嘴的形丑反衬心美,以儿童的幼稚反衬歪嘴的真诚的爱心,以小姐妹的卑微反衬歪嘴的伟大,强烈的反差引人思考。
五毛钱是老人存入人类爱心宝库的一颗明珠,是老人赠给孩子的爱心启蒙读本。歪嘴老人走了,他所产生的强大的、历时久远的心理磁场使小姐妹的心灵的指针偏转了——童年结束了。
(李经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