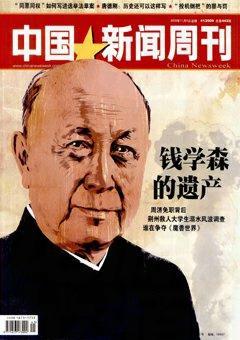我们时代的精神根源在哪里
秋 风
每一次社会的良性变化,包括利他的、利公的道德行为的增多,都以刚健质朴之气的恢复为前提。比如,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良性变化,都始于士人群体——当然最初肯定是其中少数人——的道德自觉
为救两名落水少年,武汉长江大学十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营救,两名少年获救,而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三名大学生不幸被江水吞没。随后,各种消息也证明,冬泳者与渔夫也曾经积极救助学生。
他们是这个时代罕见的道德英雄。这些普通人,平时可能是非常平凡的,甚至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当看到同类陷入死亡危险的时候,孟子所命名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驱动着他们置自己的危险于不顾。在这一刻,“善端”激发出了令人敬佩的道德行为。在这些平凡的英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刚健质朴之气。
这个故事证明了孟子的命题:人性本善。但孟子及后来的儒家哲学也接着指出,人的这种“善端”很容易被外物所遮蔽。此时,人就会变得自私,面对生命的选择,就会优柔、算计,精于计算而怯于行动。总之,刚健质朴之气就会逐渐流失,大多数人会变得萎靡、猥琐、自私。
很多因素都会导致刚健质朴之气的流失。最直接的因素是物质主义哲学,这一点无须多说。令人感到伤感的是,每一种文明,随着时间推移,似乎都有趋向衰败、腐烂的趋势。这个时候,生活在文明之边缘的人群,相对来说更为刚健质朴。中国人历史上,比较成功的王朝似乎都由边缘人群进入文明中心区建立的,比如刘邦由楚地而入主中原,李唐宗室有突厥血统,他们为已经腐烂、萎靡的南朝文明注入了生气。
生产、生活的特殊形态也会导致刚健质朴气质的流失。这方面,亚当•斯密有精彩论述。斯密虽然赞美商业社会带来繁荣与自由,但也指出,高度发达的商业会给民众精神带来不良影响。首先,分工过于细致后,每个人只做一种简单的工作,对除此之外的世界一概不知,人们的见识将变得短浅、狭隘。于是人们会看到这样一种奇异情景:“在城市居民的知识不及乡村人”——这种知识,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应付风险的能力,生活的常识。
斯密也指出,这种商业分工也会让人丧失尚武精神。商业、经济学教导人们做每件事情时进行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金钱也会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价值,而从金钱到物质主义享受只有一步之遥,于是,人们的“心思不断用在享乐方面,因此变得懦怯,没有须眉气概”。也就是说,人们普遍缺乏刚健之气,
反过来说,每一次社会的良性变化,包括利他的、利公的道德行为的增多,都以刚健质朴之气的恢复为前提。最近我研究古代中国历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良性变化,都始于士人群体——当然最初肯定是其中少数人——的道德自觉。比如,宋代士大夫的自觉,就一举扭转了五代十分败坏的社会风气。清末士人有一些生气,也与曾国藩的道德自觉有关。梁任公晚年曾经这样评论曾国藩、胡林翼等一般儒家士人在清代、乃至中国文化历史上的意义:
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坏极了,一面严格地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恶势力跑,而同时也以这一点与朋友们相互勉励,天天琢磨保持自己的理想⋯⋯他们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渐次声应气求,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
曾国藩们是从练兵开始的。当西方人入侵中国之时,八旗、绿营军队已经完全腐烂。本来对汉人保持戒心的清廷,不得不允许汉人编练新军。曾国藩深知刚健质朴的精神对军队的决定性作用,他定下挑选士兵的条件:不收绿营兵,不要集镇码头上的油滑之人,不要衙门当差的滑吏,最好是山村朴实的农民。他理想的是士兵是忠恳、质朴、健壮的。至于军官,曾国藩要求他们具有书生的“血诚”,心志高远,不沾染浮华的风气。总之,他把刚健质朴之气带回军队,也带回社会。晚清所有的现代化的社会变革,精神根源都在这里。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属于什么状况?在长江边上,我们看到了刚健质朴。但就在这几天,第七届全国(广州)性文化节在广州火车站附近隆重而热烈地进行着。在这里,日本AV女优、内衣秀、性用具店观者火爆,而性文化展区却大受冷落,因此我们不得不质疑:到底性文化节有多少文化?难道,这就是文化?——它真是透着萎靡的气息。
可见,刚健质朴与萎靡交织于这个时代,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这两种精神的较量。★
(作者为本刊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