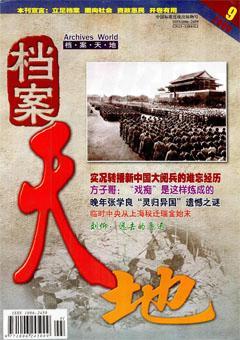远去的鲁迅
刘 仰
鲁迅以及他身处的时代已经越来越远了。近日,一件悄悄发生的事情,又再次拉开了现代人与鲁迅的距离。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减少了。据说《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再列入课文,只有《拿来主义》、《祝福》、《纪念刘和珍君》三篇被保留。教材编撰者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很多,各种各样的议论也很多。反对这一决定的理由大致可以用一句话表示:鲁迅过时了吗?
我觉得,鲁迅是否过时,是个理论问题,把这样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放在未成年人面前,意义不大。中学生多学点广泛的知识,等到他们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让他们自己判断鲁迅是否过时,这种状态比较好。因此,对于中学教材减少鲁迅作品,我表示同意。事实上,鲁迅生前就说过,说他的思想比较黑暗,不主张年轻人多学他,还建议把自己的作品从学生课本里撤掉。但是,鲁迅的这个意见并没有被接受。对于鲁迅的整体评价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鲁迅是被神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鲁迅的神性,把鲁迅当成一个“人”,我觉得可以让人们了解更加真实的鲁迅。
对于中学教材来说,关于鲁迅的理论评价,不应该是第一位的。语文教材应该把文学性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这大概是新版中学教材减少鲁迅作品的原因之一。鲁迅的作品从文学上说,有些方面的确不太成熟。鲁迅身处白话文运动蓬勃推广的时候,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健将之一,鲁迅的作品在那个时期风靡一时。但是,由于处在文言文和白话文相互转换的特殊时代,鲁迅的很多作品文白夹杂、诘屈聱牙。现在中学课本里留下的三篇作品,在这个问题上,算比较好的。即便如此,鲁迅的文字还是有问题。
鲁迅经常翻译外国作品,外国文学的文体和语法,因而也大量出现在他的白话文中,用今天的话说,鲁迅的文字很多都属于翻译体,与中文自身的语言规律相去甚远,因此,鲁迅的某些文字并非真正好的中文。仅以现在中学课文里保留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就可以举几个例子。文章开头第一句是:“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逗号表示该句子还没有完。如果我是中学老师,学生写出这样的句子,我一定会让他改掉。比方说,改成这样:“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二十五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她们召开了追悼会。那一天,……”而鲁迅原文中,“那一天”加了一个巨长的前缀修饰定语,显然是西方语言的习惯,而不是中文的习惯,读起来叫人接不上气来。
《纪念刘和珍君》的第二段,也是地道的中文:“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第一个短句“这是我知道的”,是西方文体常用的倒装句,中文很少用,后面一句“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艰难”是怎样的艰难?是谁的艰难?这属于上下文交代不清:第二,这是一个不太顺的倒装加倒装句,完全是翻译体写法。如果是我,大概会改为这样:“……,她依然预定了全年的《莽原》。”
“翻译体”对于中文的伤害,现在已越来越多,尤其在一些学术文章里,堆砌罗列的前缀,叠床架屋的修饰,臃肿累赘的超长句子,读起来,需要游泳运动员的肺活量。读完还没懂,还要做一些语法分析,才能理解作者在说什么。这种现象虽然不能完全归之于鲁迅,但是,鲁迅的文字确实为这个现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从好的中文的角度,白话文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文字作品。鲁迅的文字作为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确实已经与当代有了较大的距离,
《纪念刘和珍君》是鲁迅作品中传播比较广泛的一篇文章,其中,“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经常被人引用。这句话就属于诘屈聱牙,短短的句子,就有几个可以不要的零部件,删去毫无影响,反而更精练。此外,这个短句的含义,属于鲁迅自己所说的“黑暗”,按照文中上下文的意思,向来都用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结果中国人比这“最坏的恶意”还要坏,那就是坏到无以复加了,大概已经超过魔鬼的水平。鲁迅的年代,他所身处的环境,使他有这样的念头和断语,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永远这样看待中国人,那就很不合适。把这种念头教给年轻的孩子,就更不合适。理由很简单,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是工作单位还是家庭,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永远把别人看成最坏的坏人,永远认为别人都是最坏的动机,这个人一定不受欢迎,而且令人讨厌,
如今,中学教科书中减少鲁迅的作品,我认为是件好事。不用担心,少了几篇鲁迅的文章,中华民族就没有了脊梁。中国的孩子们要了解鲁迅,还有很多可以选择的途径。而且,让孩子们长大以后,更加成熟一点,再了解鲁迅,也许更合适。我想,这应该也是鲁迅自己的心愿。当鲁迅说“救救孩子”的时候,他一定不希望天真的孩子,从小就把心灵变得无比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