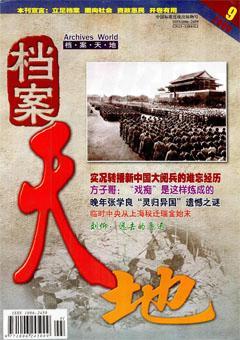“戏痴”是这样炼成的
方子哥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方官德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兼演员。母亲吴艺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员。从影之前。方子哥曾经当过东北兵团战士、油漆工、搬运工、汽车司机;1981年,方子哥调到文化部《中外电影》当编辑。两年后又在文化部外联局工作了两年:1985年终于如愿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当了演员,
方子哥步入影坛后曾经在《小扬征税记》、《虾仔擒盗记》、《死去活来》、《无人喝彩》、《混在北京》等影片中饰演角色。其中,他在《无人喝彩》中饰演的“大款”钱康,一招一式动作都极为到位,于浓郁的喜剧韵味中道尽生活的尴尬与无奈,为当今银幕增添了一个极为难得的而又极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获第十四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另外,方子哥在影片《混在北京》中饰演了一个从外地来到北京的风流诗人,因表演出色,获1996年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方子哥擅长喜剧表演,他在许多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滑稽、憨厚、迂腐、严肃都充满了喜剧味道,他是一个可塑性和角色感较强的演员。
(接上期)
调到剧团以后第一个角色应该是个男主角,片名叫《温柔的眼镜》。在那个之前演过一个风光片,是个关于海南岛的“天涯海角行”,一个风光片,就是把海南岛走遍了、吃遍了、玩遍了,走一个地,介绍一个地。当时我演一个东北的伐木工人,到海南岛去旅游结婚。后来紧接着就拍了陈佩斯的《父与子》,演陈佩斯的邻居,完了那以后被调到了北影。当时考北影的时候,因为跟陈强合作过,他对我有印象。另外就是说还有演过电影的资历,他们看过这些资料,觉得我还行。
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演员的家庭,所以我每演一个角色都是受好评的,包括第一个电视剧演的一个单本剧,一个小喜剧,还得到了一个表扬奖,后来几个戏基本上都得了奖。我在演《混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是得了一个百花奖,当时,傅彪还没名气呢,他还专门跟着别人来剧组见着我,跟我说:五哥,您以后有什么戏您带着我,咱俩长得有点像。我也没感觉,咱俩长得像,咱俩可以演哥俩。后来我跟他还有一个约会,就是专门找一个人给我们写一个剧本,我们演哥俩的那种。但是后来也没弄成,他去组织剧本,剧本还没组织好就走了。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小姑娘见到我,说:特喜欢你的表演,但是有时候就把你跟傅彪混了。
傅彪很可惜,他属于很聪明的人,而且入门了,就是得法了。我总觉得演员,好些人虽然从电影学院、中戏学了多少年,还是不得法,没明白什么叫演戏。实际上表演也就一个窗户纸,有可能两天一捅就破了,也可能这辈子也捅不破。我原来给他们举过例子,比如说这个人你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做完了以后,现在我告你,我这支了一个摄像机,有好多观众去后边看你,你把你刚才做的那个再做一遍,很多人就做不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思想复杂,实际上这些事情能不能做?都能做。但是你有了这种思想负担以后,你再去做就有一个意识要往下演了。实际上你要是把这种意识给去掉了,你不再想我是演给别人看的,我演得对不对、像不像、好看不好看等等之类的东西,你没有这种思想意识了,我就在做我刚才做过的事情,你就是最好的演员。我很理想的,就是说最好的演员境界是什么?就是像纪录片一样,这就是最好的演员。所以演员你怎么把他做好啊?就是你要想办法让自己去掉那些私心杂念,去掉那种有一种意识,就是我要演的意识。我不是在演,我是在生活。我认真做好我要做的事情,你就是最好的演员,而且任何人都行,包括瞎子、瘸子什么的都可以。为什么?生活里有这些人,你认为长成任何的样子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人,所以就可以变成戏中的人。难度在于哪?在于我要演一个跟我自己不一样的,这是难事。但是你如果完全把自己又融入到另一种人的性格、特点、职业、爱好、习惯等等之类的,你不就完全变成了那个人,认认真真在做那个人的事,你就是最好的演员,我觉得一丁点都不难。
演自己吧,我觉得还好一点,如果去演别人,那就是功夫。你要观察,要想,要去体验,要去寻找。另外一个人肯定跟你不一样,所以你要寻找另外一个人,你要找到原形,那个人是怎么样做的,你找到他的心理根据,找到他的生活习惯、动作习惯、性格的习惯、或者他的思维的习惯。你按照那种去做,你把自己融入到那个人,就能做到了。实际,我这个理论可能和他们学院派的不一样。
至于说我演过的角色。我觉得每一个角色演的都挺好。为什么呢,就是基本上每一个角色我都是很用心,哪怕再小的角色我都会很用心的去做的,而且我尽量做的就是区别于我自己。因为,平常我这个人不爱说话,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这可能也和文革中那种政治上得谨慎小心哪、不能出事啊,跟这段挺长时间的经历有关系。我为什么喜欢演戏呢?是属于我换了个角色后,不是我自己,在合理的释放、合理的发泄,而且就是合法的发泄。所以我爱演戏,在那个境况下我可以自由,虽然现在都放宽了,开放了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习惯那种内心的保护。
血液里的艺术传承
我这个人永远是低调的,绝不是那种到处去那惹祸的。你让我敞开了去折腾,不太可能,除非剧本里写的是这样的。但是换句话说,我能不能做成那样?能做到,所以任何人都是这种情况。只要在某种条件下,任何事情,它实际上都能做到的。而且比如说你演好人也好,演坏人也好,区别它的不在于你长的什么样,什么气质,不在乎这个,而在于你做得事情的行为,你违法了,你就是坏人,你做这个事害人了、违背良心了,你就是一个坏人。所以,区别一个人的好坏,不在于他长的什么样,是不是歪鼻子斜眼,而在于他的行为。当然啦,这里而也可能有很复杂的东西,没这么简单,他做这个事,虽然违背他自己的良心或者他就是要做这个坏事,但是他也一定有自己的心理依据,这种心理依据你要把他给阐述的非常明白,他这个坏人才能够成立。这种中国特有的表演方法,坏人就是歪鼻子斜眼,不正眼看人。但有的时候,也可能有些人做坏事就是挂像。因为他有心理依据,所以你要做个表现得很坏的样子,也一定要有心理依据。他看人贼眉鼠眼的,为什么?他得看人是不是发现他了,一定要有心理依据,把他自己认为是正确地去做出来这种行为。
那么多年蹉跎的这些岁月,现在回想起来,也给我留下一些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实际上就是我父辈他们对艺术的这种追求,因为我从小在人艺的那个院子里长大的,老人们常说戏比天大,对于戏的特别玩命的这种追求啊,把它捧为最神圣的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从小受熏陶。而且我父亲这个人是个特别善交际的人,特别招人儿,特别有人缘儿的人。所以很多人经常到我家里聚会,我父亲做饭也好吃,他们讨论各种各样的事,聊
艺术、聊表演什么的。所以虽然我没有上过什么中戏电影学院,但是我上场就能演戏,可能就跟小时候受过的这种熏陶有关系。比如说董行信,他教过我朗诵,我那时候就背着这么大的录音机到他们家去,让他念,念完了以后回来一遍一遍的,重复他的。从小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没有直接让人家来教导我们,而是我们从小泡在排练厅里面玩,他们演出我们就从后面跑到台下去看戏。那时候各种电影,内部电影,不许外人看的,我们都是从首都剧场的天桥,爬啊爬啊,爬着过去,爬到幕后去看,特别危险。反正从小是受这个熏陶。所以要说影响最大的,实际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于戏的追求,对我们影响最大。
我父亲也当过导演,他们排戏的时候,我们都到后面去看,按理说不许小孩进来的,我们偷偷跑到后面,就坐在那看。那个时候,导演前面都放一个按的铃,叮一下,鸦雀无声。什么声音都不能有,特别肃穆,完了就开始拍戏。导演的脾气也特大,上去恨不得踹演员一脚,就是那种权威性特别大,大家都把他作为特别神圣的那种形象,排练场那种气氛,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殿堂。不像现在这帮孩子追求的全是名利方面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演戏,不是追求名利,我追求的是演戏的过程,可以说我不是给观众演的,我是给我自己演的,就跟那个票友似的,我过这个瘾。但是,观众有反馈,对你的赞扬,对你的评价,这是让你非常舒服的事。这也是这么多年潜移默化当中,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我现在这种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全家只有我还没退休,还是北影的在职人员。我的状态就是在演戏,没有别的,别的我也不愿意干,也觉得只有演戏对我是最踏实了。
我的名利观
通过这么多年,我看得也比较明白了。名和利这种东西是没有头的,尤其是演员这行不可能永远辉煌的。按一般规律,这些明星们都是七、八年就下来了,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心理准备能够去承受,我有让大家欢呼的时候,也有大家把你遗忘的时候,总是有高潮有低潮,所以不能总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当你被人冷落的时候,你必须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所以你看明白这个,就无所谓了。
另外我是从小生活在明星堆里的,都是巨星,从小生活在他们的堆里,所以没有觉得,而且就是一定得看明白这些。
我是等于从最苦的时候过来的,所以忆苦思甜,我不用回忆,我觉得苦随时在脑子里边,这么一对比,多幸福啊。而且不光是我个人,现在咱们的国家,包括北京建设的这么好,人民的生活这么幸福。我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谁又能想到大家都能开上汽车?现在我们家三辆车,仨人一人一辆车。当年我给别人当司机的时候,开的是工厂里国家的车,你能想象得到我们每个人现在能开汽车吗?所以拿现在的生活跟那时候一比,你不能不知足,真的,人要是不知足,什么时候就没有头了。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看清楚自己有多重。你不是英雄,你也不是多牛的。反正对于我来说,你说还有什么别的能耐,我没那能耐,或者去做生意啊赚钱,我就满足于我这种演戏就行了,而且我的梦想就是在我老的还能稍微动一点的时候,还有戏演。这就是我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