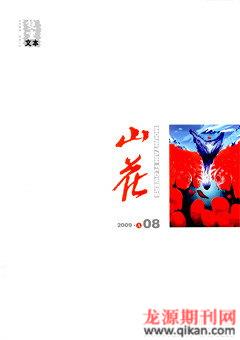天数使然,可遇而不可求
韩少功
很少有作品具备巴别尔《骑兵军》这样多的当代商业卖点:作者的惨死,犹太人的悲情,哥萨克的浪漫与野性,红色的怀旧与恐怖,艺术上的独特风格,甚至还有西方教派之间不宜明言的恩怨情仇……但巴别尔本人与商业无关,从未想过要成为畅销书作家。
一般的畅销书作家是用手写作,高级的畅销书作家是用脑写作,但巴别尔是用心写作,用心中喷涌出来的鲜血随意涂抹,直到自己全身冰凉,倒在斯大林主义下的刑场。在倒在刑场之前,他的心血在稿纸上其实已经流尽。肉体之死只是心灵之死的迟到性追认。
他处在一个历史的压力集聚中心,一个现代文明失调期的深深痛点,在激发白炽闪电的两极之间把自己一撕两半:他既是犹太诗人,是富有、文弱、城邦、欧罗巴的一方;又是红军骑兵,是贫困、暴力、旷野、斯拉夫的一方。因此他眼中永远是视野重叠:既同情犹太人的苦难,也欣赏哥萨克的勇敢;既痛惜旧秩序虚弱中的优雅,也依恋新世界残酷中的豪放。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散焦与目盲了。各种公共理性的视觉坐标对于他无效,眼前只剩下一个个生命血淋淋地消失。换句话说,他集诸多悖论于一身——这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痛苦,也是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幸运。
第一流的作家都会在黑暗中触摸到生活的悖论。老托尔斯泰在贵族与贫民之间徘徊再三,维克多,雨果在保皇与革命之间犹疑不定,苏东坡、曹雪芹在人世与出世之间上下求索……但巴别尔的悖论也许是最极端化的,是无时不刻用刀刃和枪刺来逼问的,一瞬间就决定生死存亡。这使他根本顾不上文学,比方顾不上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情境交融,虚实相济、乃至学贯今古识通东西那一套文人工夫,甚至顾不上文体的基本规定——他只能脱口而出,管它是文学还是新闻,管它是散文还是小说。如果读者把这本书当作一堆零乱素材,大概也没有错到哪里去。
大道无形,无文亦远,他已经不需要形式,或者说是没有形式的形式浑然天成——这也许是文学史上罕见特例。因为他血管里已经奔腾着世纪阵痛时期的高峰感受,随便洒出一两滴都能夺人魂魄。他不是一个作家,只是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灵魂速记员和灵魂报告人,技巧与方法即使顾得上,也显得有些多余。这种作品的出现是天数,可遇而不可求,就像中国当代诗人多多说过的:这样的作品出一部就会少一部,而不是出一部就会多一部。
巴别尔在法文与英文中成长,浸淫于欧洲现代文明,但不幸遭遇了欧洲两大边缘性族群:其一是犹太人,给欧洲注入过正教与商业,最终却在集中营和浪落旅途成为欧洲的弃儿;其二是涵盖苏俄和东欧不少地区的斯拉夫人,为欧洲提供过大量奴隶和物产,却一直被欧洲视为东方异类——其“斯拉夫”(奴隶)的贱称,无时不在警示这种冷冷的距离。因此,巴别尔最好的读者当然是欧洲人,特别是欧洲近地的居民,其种族和宗教的经验是其必要阅读准备。在很长一段历史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成了标准的欧洲故事。其实这并非现代西方的全部。特别是身处边缘位置的犹太人与斯拉夫人,因为缺乏强权体制的掩体,在文明的谱系中身份暧昧,更容易落入辉煌故事后面的阴影,落入宴会厅咫尺之外的屠宰场。巴别尔不过是这个屠宰场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而已。多年以后的中国读者,也许需要一点历史知识,才可以看出《骑兵军》不是一次对苏维埃革命的简单疑惑——这是西方主流媒体最乐意的卖点;更重要的是,这本书速记了文明之间的挤压真相,展示出自然的物竞天择和历史的删繁就简——这些“现代性”的残酷代价往往被西方主流媒体闪灼其辞。
当然,这种代价一度出现在德涅斯特河流域,将来也可能会出现在另外一片大陆。二十世纪是东方以西方为师的世纪,然而长期以来,很多中国人看西方多是看西方的核心地区,比如西欧与北美,而且只是看它们的某一阶段和某一层面,比如看《红与黑》和《简爱》里的中产阶级,看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笔下的冒险侠士。如果我们也看看西方的“郊区”,甚至看看西方的“农村”,比如看看东欧、北非、中东以及拉美,看看欧洲的犹太人、斯拉夫人、摩尔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非裔黑人以及印地安人等,才会明白西方不仅仅是巴黎和纽约,不仅仅是优雅爱恋或成功奋斗。只有在这样一个更丰富和更真实的西方世界里,一次与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与恐怖主义才是可以理解的,血淋淋的《骑兵军》才不值得过于惊讶。
读过巴别尔以后,后人能抱怨谁和谴责谁吗?历史是否本来可以有另外的选择?一个来自西方的“郊区”故事,展示了压迫之前的被压迫,凌辱之前的被凌辱,虐杀之前的被虐杀,提供了一个无能之美和有为之恶之间的难解方程,即人文主义者永远的痛。也许,这是西方也是人类历史中常见的宿命性局限,是后人们不管在什么时候也无法得意洋洋的原因。眼下,“现代性”正从西方爆炸性地扩展全球,众多发展中国家的GDP竞赛和文明“农转非”的热情高潮不退。但这个时代有航天飞机、高速公路、电子游戏以及快餐店,也有巴别尔这样一些令人心情沉重的作家。这样很好一对于正在全心身投入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尤其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