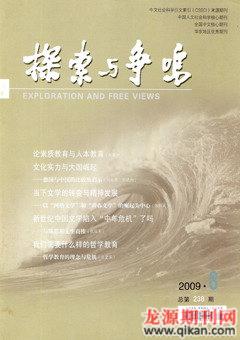古典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社会契约论的演变
付翠莲
内容摘要近代社会契约论于16世纪兴起后,在长达两个多世纪里一直主导着西方的政治潮流。通过集中探讨社会契约论在16世纪以来的勃兴、18世纪遭遇到的批判及其后在当代重构的历史,可以剖析其对西方的政治发展所起的重要理论支撑作用。
关键词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论自由主义政治发展
契约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古希腊智者最早用契约观-念来解释政治生活。伊壁鸠鲁借用“原子”理论的张力,以形而上的方法宣布了人的自由的本质、国家起源的契约性质。斯多葛派的古典自然法学说为近代社会契约论提供了论证基础,而古罗马的自然法观念经由西塞罗的诊解才得以流行。但真正把契约理论用于解释主权国家,并进行系统的政治论证是从近代开始的。
理论预设:关于自然状态与国家起源
作为西方国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流派,社会契约论是用来解释国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理论,它认为国家起源于人们之间的某种契约,立约宗旨在于人们能够获得保护自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所需要的和平环境与稳定秩序。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之一,社会契约论在近代兴盛的原因,在于它适应了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实践和现实需要。16世纪以后,随着封建体制的没落和基督教的式微,政治问题由于宗教论争的隐退而世俗化,政治哲学逐渐从神学中独立。此外,近代主权国家兴起,由政教二元体制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逐渐成为时代的政治主题。如何避免君主专制和社会混乱,如何建设一个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如何合理地安排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理论难题。新的政治秩序要求获得合法性论证,而神学的论证显然已经不能承担这一任务了,经过改造和融合起来的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论应运而生,特别是契约思想中所包含的平等、自由、功利和理性等原则符合了新兴资产阶级对理想社会与国家的要求,为近代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政治论证。于是,社会契约论就为近代政治思想家所用,用来解释政治社会和国家的起源,论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及功能,并成为引领社会政治发展的主导思潮。
近代社会契约论者的国家观和自然状态联系在一起。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二者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关系。自然状态是社会契约论者为论证政治社会的正当性而设置的逻辑起点。按照洛克的版本,在人类进入政治社会前存在一种自由的自然状态,人们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应遵守自然法;而理性,就是自然法。同时,自然状态又是一个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切权利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每个人都有权执行自然法,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但在洛克看来,自然状态尽管美好却不完备,是一种自由但却是无政府的状态。因为它缺乏明确的、众所周知的法律;缺乏支持正确裁决的权力支撑;还缺乏公共权威来仲裁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但人天性偏私,无法保证公正合理,人们的自然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因此人们不得不交出一部分权利,缔结社会契约,建立国家(政府),从自然状态走向政治社会,托庇于国家的保护。
康德把自然状态的缺陷归因于它的无法律性,由于这种无法律性,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缺乏可靠的保障。人们并不能自觉自愿地、一贯地克制自己的过于膨胀的利益需求,而总是受到自我保存欲望的支配和服务于自我保存欲望的短视、狭隘的理性计算能力的鼓动,而尽可能扩大自己的占有。古典自然法学派思想家们从自然状态的种种不便中得出,人类要过上和平、安定和幸福的生活必须进入政治社会,诉诸政治权力来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其途径就是每个加入社会的个体向整个社会(也即政府)让渡其部分或全部自然权利,使这些权利由个人权利转化为国家权力,通过国家权力来确保公民权利的实现,政府和国家也就产生了。
理论检视:卢梭社会契约论的使命
自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相隔逾一世纪。卢梭已视稳定的社会模式为理所当然,他的社会契约不是用来解释社会稳定之道,而是说明社会如何可臻正义。社会契约变成重塑一切社会与政治建制的媒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勾勒了人类从“自然状态”到蕴涵着“道德的自由”的“社会状态”的应然途径。在卢梭看来,最初的人类并没有善恶观念,也不存在道德和义务关系,在生活中起作用的只是这样两个先于理性而存在的原理:“一个原理使我们热烈地关切我们的幸福和我们自己的保存;另一个原理使我们在看到任何有感觉的生物、主要是我们的同类遭受灭亡或痛苦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天然的憎恶。”他认为,政治社会所建立的、由人们之间的集合而组成的社会秩序,“决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而只有“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他认为,个人自由既是“社会契约”赖以缔结的前提,又是人类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所应坚持的一以贯之的价值。“一个人抛弃了自由,便贬低了自己的存在,抛弃了生命,便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因为任何物质财富都不能抵偿这两种东西,所以无论以任何代价抛弃生命和自由,都是既违反自然同时也违反理性的。”这是卢梭所理解的社会契约的使命。
卢梭的社会契约建立在人们一致同意的基础之上。人们表达同意的方式和载体是社会契约。他认为,把个人意志和政治共同体本身的意志统一起来,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不再区分自身的存在和公共的存在。统一的方式和途径是自然状态中自由和平等的人通过签定公约,把“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人们通过缔结社会契约,把所有结合的个人意志结合和升华为共同体的最高的普遍意志——公意。卢梭以“公意”所蕴涵的“公正”作为每个个人在“社会状态”中的价值主体地位的保证,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卢梭指出:“公意必须从全体出发,才能对全体都适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或国家的“公意”可以确立在个人的独立性之外,“社会条约以保全缔约者为目的”,“‘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他的“公意”思想蕴含着政府只是人民权利的受托者,是为公民服务的机关,如果政府职能不能合理地发挥,出现专权、特权、渎职、压迫人民等现象,则公民有权联合起来,执行公意,恢复自由,行使主权,推翻现政府,重建一个能够真正为人们服务的政府机构。这也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透底之论。
质言之,社会契约论立足于个人同意的基础上建构的政治理论,把公民的个体优先性摆在第一位,把保障公民
权利视为公共生活的第一需要,把个人自由视为最基本的社会价值。契约的订立者是自然状态中独立、平等的“自然人”,契约是每个人与其他所有人分别订立的,参与立约是每个人代表自己也只能代表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表达,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自律决定。
“自激进宗教改革的时代,以至18世纪下半叶,社会契约的理念主导政治思想。”它以“自然法”或“理性”的名义为政治肯定了赋有普遍、永恒意味的“公正”或“正义”价值,为现实政治指示了一种应然指向,而那应然又深深植根于政治所以为政治之本然的内涵中。社会契约论者把政治社会的合法性问题放置当下,给人们在逻辑上提供在政治社会之外理性选择和评判公共权力的空间和基点,认为公共权力只有维护和实现每个人自然而然珍视的东西,从而得到人们的理性同意时才是合理的“权利”,其时人们自主承诺的对它的服从才可成为政治义务。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理论思维铸就了契约论丰富的哲学蕴涵,并成为西方影响至深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论证方式之一。
理论挑战:社会契约论所遭遇的批判
18世纪中后期,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实证主义、保守主义思潮兴起,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理性的推理,更需要的是经验的证明,更加注重的是由事实和经验来说明问题而不是通过抽象的推理,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的基础。思想家们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学说的理论困境为靶子,开始对社会契约论质疑,痛斥社会契约论忽视人们的感情、共同体传统,而导致人们对理性的过高估计。这预示着社会契约论陷入了政治哲学危机的前夜。
保守主义的鼻祖柏克认为,政治是实践科学,在理论上空谈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没有意义。虽然他承认在设想的自然状态下,人们有明晰的、抽象的自然权利。但人类是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文明状态实际上是人类的本质。在公共社会,人的激情和欲望必须受到自身之外的某种力量的节制,必须受到不依个人的自愿为转移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的节制。抽象的自然权利没有价值,人们真正的权利是文明状态中的自由权利,是与传统、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权利。柏克认为,如果谈论社会契约,那它也不是彼此孤立的个体为了自保在自然状态下达成的,而是作为团体的人民源于自身的道德纽带而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性质的社会契约论不仅在理论上是庸俗的,在实践中也是危险的。每个人在完全独立和孤立的情况下,不可能达成组建国家这个道德存在的契约,社会契约论的思维方式不能真正理解国家的本质,社会契约论把充满家庭依恋、道德情愫、宗教圣洁的国家和社会简化为偶然的、算计的利益交换与合作关系。每个人不可能重新选择自己出生就置身其中的社会的原初约定,因为,这样的约定是由独立于每个人的意愿的先在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决定的,我们必须对此承担责任,“社会性的公共关系才是我们负有的国家责任的决定者。”
大卫·休谟深刻意识到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思想不可克服的理论困境,从情感、习俗和传统等方面对社会契约论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挑战性的批判。休谟摒弃了以理性法则规范政治现象的传统立场,主张立足于人们利益需要和社会传统习俗来解释政治生活。他认为,如果是情感而非理性对人的行为起关键的作用,契约就变得纯属虚构和妄想,而所谓自然法则在人类中的作用更是枉然。针对契约论者所谓政府的产生来自于同意的说法,休谟认为这是个不合乎历史事实的假定,因为“几乎所有现存的政府,或所有在历史上留有一些记录的政府开始总是通过篡夺或征伐建立起来的,或者二者同时并用,它们并不自称是经过公平的同意或人民的自愿服从”。人类事务的发展决不会容许出现这种同意,实际上,“始建的政府是由暴力建立的,民众服从它乃是出于无奈;继续的政府亦由武力支撑,人民之所以默忍不是出于选择,而是遵守义务”。因此,社会契约本身难于让人信服,也无法证明政府的起源,无法得出人们政治服从的合法性。休谟认定人类政治社会的出现,绝不是基于某种抽象的理论,而是基于以下三大基本的现实因素:必要性、自然趋向和习俗。休谟的这种革命性观点完全摧毁了启蒙时期的契约理论的理性传统,给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以致命的打击。休谟政治哲学的出现,形成了对启蒙时期传统契约理论的全面挑战,预示着古典自然法学说的衰落。
杰里米·边沁对“虚构契约”的批判具有建构性的意义。边沁认为社会契约论纯属“虚构”,他坚持的功利主义取消了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基础,并把其论点建立在社会效用之上,认为国家起源于人们的服从习惯,而不是虚构的社会契约的结果。约翰·密尔对契约论的批判也是从自然状态的虚构性出发的。他认为人类的最初生活状态就是社会状态,自然状态从来都是不存在的。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出发,密尔从根本上否定了契约论思想家们提出的那些“不证自明”的原则和基础,认为国家和政府也并不产生于社会契约,因为在人性中情感的力量是远远大于义务和责任的力量的,对公共权力的服从和忠顺并不仰赖于人们对自己许诺的义务感,而取决于人们的好恶,取决于人们的功利欲求,能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公共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此外,罗素尽管也承认“社会契约说当作一个法律拟制,给政治找根据,也有几分道理”,但他以另一种苛责的口吻说:“社会契约按这里所要求的意义讲,总是一种架空悬想的东西。”黑格尔也认为,“(社会)契约乃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为其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为有力彻底。马克思主义认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有缺陷的,他们的出发点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不是历史的、社会的人;他们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空想的。
在柏克、休谟、边沁、黑格尔、马克思等政治思想家的批判中,社会契约论沉寂了一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对古典契约理论进行了修正、继承与发展,将其提升为一种“新契约论”。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是一种能够设计出正义程序的价值工具,是在一个假想的“原初状态”、“无知之幕”下的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去找到正义的理想。罗尔斯的正义论,使社会契约论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出现,又一次担负起新的政治使命——在自由的基础上来解决平等问题。在罗尔斯的影响下,许多新的“社会契约论”的变体产生,如诺齐克的“无意图的契约论”、哈贝马斯的有意图的“政治契约论”等。
编辑沐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