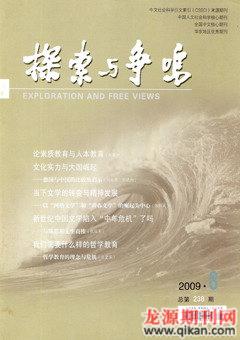新世纪中国文学陷入“中年危机”了吗
张丽军
内容摘要陈思和先生认为,“新世纪文学”显现出一种作家主体精神力量丧失、不再被理想和激情所支配的“中年危机”。笔者在认同其思考具有重要价值的同时,认为新世纪中国文学陷入的不是“中年危机”,而是新世纪青年作家的“成长危机”。比照五四作家和新世纪作家,就会发现新世纪青年作家陷入了文化断裂困境、代际冲突和现实维度缺失的多重“成长危机”中,
关键词20世纪文学青春主题新世纪文学“80后”作家成长危机
陈思和先生在《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5期发表《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一文,选取了“少年”、“青年”关键词,来阐述20世纪中国文学从五四到新时期所具有的“青春主题”、“青春叙事”特征。在对比20世纪初和2l世纪初这两个“新世纪”文学特点及其精神之后,他认为“新世纪文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显现出作家主体精神力量丧失、不再被理想的激情所支配,取而代之的是“中年危机”。
毫无疑问,陈思和先生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30年,我们没有解决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更新换代问题,“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显然是严重滞后了”,以至于许多学者和批评家“都在喟叹当代文学萎缩的趋势似乎不可阻挡”。陈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思的。笔者在认同陈先生文章建构价值的同时,也有一些不敢苟同之处,在此不顾浅陋一一陈言,以求抛砖引玉。
断裂式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断裂
陈思和先生从非常文学化、生命化的视角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这固无不可。五四时期,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就从新陈代谢的生命化视角来引证文学革命的内在天然合理性。但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生命状态的考察和认定,我认为仅仅以20世纪100年的时间长度来度量与言说是不够的,也是不确切的。因为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的时间跨度中,这100年不是一个自然孕育、常态发展的过程,而是处于一种断裂式发展状态之中;更重要的是,这100年中国文学内在的精神血脉和思想内核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处于不断地否定、裂变与更新过程中。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思和先生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来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正是从中国现代化历程来看,20世纪中国呈现的不是一种持续型现代性,而是一种断裂型现代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不仅仅是持续的,断裂也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纵观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断裂式的。具体到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经历了两次裂变:
第一次裂变是1940年代。富有青春理想主义色彩的五四新文学启蒙思潮尽管已经受到“革命文学”的冲击,但还是在巴金、老舍、曹禺、丁玲、沈从文等的文学经典作品中显现出五四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的精神血脉;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20世纪中国文学就渐渐发生了由知识分子启蒙民众转变为工农大众改造知识分子、从思想启蒙转变为阶级革命的叙述主题裂变。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这一文学转变得以彻底完成。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些重要作家处于“失语”状态,除了新的时代氛围、新的时代主题的因素之外,文学断裂是一个更为内在的原因。显然,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开启了,一段新的青春叙事开始了。但是,此青春迥异于彼青春,有着不同于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新青春主题:阶级、革命、集体、奉献等等。
第二次裂变在1980年代。“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意味着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又一次断裂式转型。以“伤痕文学”、“朦胧诗”肇始的新时期文学,结束了从1940年代开始的阶级性文学叙事主题。这一时期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五四新文学思想启蒙和文化反思的精神血脉。以张承志《北方的河》为代表的青春写作呈现了一种雄浑壮美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从1990年代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到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又呈现新的“先锋文学”形式探索、人文主义精神探寻和多向度的文学创作尝试。新世纪中国文学迈入了一个持续发展时期,出生于不同年代的作家共同拥有一个拥挤的新世纪文坛。
因此,在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状态时,我们不能忽略文学内部的断裂状态。五四时期的青春文学和建国后的青春文学,以及新时期青春文学在思想主题、叙述方式和艺术形态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才会出现陈思和先生提出的“一方面青春主题包含一种强大的生命活力,一种批判社会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也呈现出话语中的幼稚、粗暴和简单的对抗性”的两面性特征。这一结论忽略了20世纪青春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内在差异性,并把这种差异性人为地扭结在一起。对五四新文学巨匠而言,他们的青春叙述固然有着激进特征和批判精神,但决不是“幼稚、粗暴和简单的对抗性”,相反倒是充满了深刻的思索和义无反顾的理性自觉。
被遮蔽的新世纪青春文学
陈思和先生所提出的“中年写作”及“中年危机”是很有警示性的。但是,这种“中年危机”究竟呈现的是一代人的自然生理性危机,还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中年危机”呢?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辨析的问题。
陈思和先生不断谈到“中年一代作家”、“新一代的中年”等词汇,意在指“史铁生、余华、莫言、林白、阎连科、韩少功、刘震云、方方等等”一代作家,从年龄来看已经达到或是“也几乎是接近中年了”。他们的写作具有一种“中年写作”的叙述心理、立场、风格:社会责任的沉重感,对人生、命运、工作性质这类问题以及秋天般的写作心情,轰隆隆青春热情的消失以及个人独立寒秋的风霜感和成熟感等。而发生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诗人和作家的年龄在其创作风格的转变中还是会发生深刻的影响”。但这种分析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因为从作家个体的年龄,并不能引证出20世纪文学的年龄。“就像人的生命总是会进入中年时期一样,文学的中年期也总是会到来,只是我们这一代的作家碰巧遭遇了这个时机”。何以证明这一代作家的“中年写作”就“碰巧遭遇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中年期”呢?仅从一代作家的“中年写作”来引申论证文学进入了“中年期”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从文学史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无不具有300多年以上的自然生命周期。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来看,20世纪中国历经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文革”等阻断现代化进程事件,直至改革开放,中国才迎来了一个持续的发展阶段,乡土中国正在发生急剧的社会变革。梁启超和李大钊所召唤的“少年中国”和“青春之中国”在今天才得以成为现实。从这个意义而言,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中国文学的“青春阶段”才真正开始。新时期文学不过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优美的序曲而已。
对于“中年写作”,陈思和先生的立场是游移的、矛
盾的。陈先生一方面认为中年作家们“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叙事风格和民间立场,他们建立了独特的创作风格的审美领域”,“几乎是10年一个境界在不断地提高”;另一方面,他认为“文学不是依靠个别作家而是依靠一代代作家的生命连接起来延续繁衍的”,并提出了“中年危机”症候。毫无疑问,一些作家的确陷入了“中年危机”之中。但是,“不是事实上的青年文学的萎缩,而是在我们既成的整个文学话语体系下误以为他们萎缩了”,“今天主流的作家和主流的批评家都已经是中年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显然是严重滞后了”。正是因为这种滞后,才导致对新世纪青春文学的遮蔽,误以为现代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年期”。事实上,新世纪中国“青春文学”已经蓬勃兴起,只不过被一些“中年批评家”所忽略而已。令人遗憾的是,陈先生似乎也有意无意忽视了新世纪“青春文学”的成长,在文中几乎没有提及。
新世纪中国文学,不是进入了“中年期”,而是进入了一段青春文学无比繁盛的时期。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李傻傻、蒋峰、小饭、春树等众多“80后”作家已经登上文坛,显示了强大阵容和创作实绩。在销售业绩上,韩寒的《三重门》自2000年出版至今,已经销售了130万册,创下了当代文学受众数量的新高峰。以“80后”写手为主体的青春文学类作品,约占文学图书市场份额的10%;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加起来,也约占文学图书市场的10%。在广受批评家诟病的文学性维度上,“80后”作家已经在叙述模式、语言表现力、审美想象力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文学水准。
“80后”作家“成长危机”
从陈思和先生关注与思考新世纪文学的思路出发,我认为,新世纪文学存在的危机不是“中年危机”,而是新世纪青年作家的“成长危机”。对于新世纪以来的中年作家而言,“中年危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危机,是可以重获新的转机与生机的。令人欣慰的是一部分作家已经从“中年危机”的困境中走出来,如贾平凹的《高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20世纪文学从未有过的“自觉认同城市的进城农民形象”,莫言的姓《疲劳》、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苏童的《河岸》和格非的《人面桃花》等都体现了作家的自我超越与突破。因此,新世纪中国文学真正的危机是来自青春文学作家的“成长危机”。
新世纪青春文学作家的“成长危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危机来自成长的文化困境。对比20世纪初文学作家和21世纪初作家,我们会明显感到这种文化的困境。20世纪初期的作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既拥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又经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与五四前辈相比,新世纪青春文学作家在文化方面的修养,简直是天壤之别。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文化沙漠”语境危机,以及新世纪青年作家对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冷漠与疏离。对于新世纪青年作家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斩断了传统文化的语言之根,“文革”期间的文化断裂又把五四文化新传统打倒,他们处于沙漠化的文化土壤之中。否定传统文化、蔑视五四新文化,已经是众多新世纪青年作家的文化通病。
第二个危机来自被遮蔽的代际冲突。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言,“过去是10年一轮改朝换代,新人辈出,文学之流如长江之水,滚滚后浪推前浪,而今天……1990年的文学再也没有流派,也没有思潮,变成了个人话语的众声喧哗多元共存。”无论是创造社批判文学研究会,还是左翼作家把鲁迅、茅盾等人当作敌人,除了文学理念的差异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文坛话语权和文学资源的争夺,即源于代际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在“后革命”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和谐、持续、继承等保守性思维取代了以往革命时代的断裂、否定、斗争等激进性思维,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持续连为一体,进入了一个超稳定的文坛格局和不同代际作家共存的结构。面对这样一个超稳定文坛格局,新世纪青年作家,无论怎样左冲右突,但都无法实现突围。既然无法改变这一超稳定结构,新世纪青年作家只能另起炉灶,玩起了另外一套游戏,“1980年代出生的所谓‘80后作家,完全在传统的规范以外求生存,他们寄存于现代媒体,接受媒体的包装和塑造,成为网络上出色的写手”。陈思和先生作为亲历者,真切地描述了这一时期文坛内部的代际冲突,并不无忧虑地指出新世纪青年作家的另类生存与成长危机,他发出“这对于我们自五四发轫以来的文学传统和文学主流而言,到底是一个令人兴奋,还是感到沮丧的局面”的疑问,无疑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第三个危机来自生活现实维度的缺失。较之五四作家留学经历和新时期作家上山下乡的生活,新世纪青年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想象是较为贫乏的。较为富裕的城市生活、独生子女背景、单一的校园生活等无不制约了新世纪青年作家成长的丰富性。因而,我们看到新世纪青春文学缺乏深厚的现实生活维度,如王蒙先生所提出的,张悦然的青春文学没有“昨天”,缺少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这一批评是中肯的,也是深刻的。没有历史和现实维度的文学是无根的文学,是缺乏穿越时空的富有生命力的文学。就目前的新世纪青春文学而言,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下的大众生活变迁及其心灵颤动的文学书写还是极为少见,更多呈现出一种青春世界的、属于个体的爱与忧伤的景象。因此,如何把新世纪个体的独特体验和时代的、历史的、乡土的乃至是民族的集体经验传达出来,如何重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对于新世纪青年作家来说是一个极为迫切而重要的难题。
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追问的,“我们的高校中文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博士、硕士,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不把眼光放到与他们同代的人身上?”对新世纪青年作家而言,新世纪文学批评界同样存在着一个代际冲突问题,加之文学期刊的市场化背景和文学批评经典化的学术考量,新世纪青年学者本身也面临一个自我突围的问题,自然无暇顾及被主流文坛所忽略的新世纪青年文学了。
新世纪青年作家在面临“成长危机”与文化困境的同时,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20世纪以来所寻求的民族复兴和“青春中国”,在新世纪有获得实现的巨大可能性。古老的乡土中国正处于巨大的现代社会转型时期,这为21世纪的伟大文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众多“80后”中国青年所表现出来的负责任、有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他们的成见。因此,对于21世纪中国文学,我们同样有理由期待伟大作家和伟大文学的诞生。事实上,新世纪青年作家和批评家,正如王安忆所言,“我们早就存在了!”
编辑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