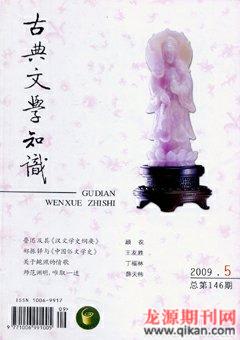也说花木兰为什么姓花
杨 玲
花木兰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自美国迪士尼公司将其搬上银幕后,更是走出国门,跨越国界,成为“世界名人”。但是花木兰为什么姓花至今仍是一个谜。众所周知,花木兰的故事最早来自北朝时的乐府民歌《木兰诗》。诗中开篇即言“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木兰”仅仅是诗中主人公的“名”,还是“姓名”,不得而知。总之,《木兰诗》中没有“花木兰”的提法。关于木兰的姓,历史上有魏、朱、花、木四说。木姓自然是来自于《木兰诗》。魏姓之说起源于元代。清代焦循《剧说》卷五有:
考《商丘志》,有孝烈将军祠,在城东南营郭镇北,一名木兰祠。元人侯有造作《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云:“将军魏氏,本处子,名木兰,亳之谯人也。世传:可汗募兵,孝烈痛父耄羸,弟妹皆稚呆,慨然代行。服甲胄、鞬橐,操戈跃马,驰神攻苦,钝锉戎阵,胆气不少衰,人莫窥非男也。历年一纪,交锋十有八战,策勋十二转。天子喜其功勇,授以尚书。隆宠不赴,恳奏省亲。拥兵还谯,造父室,释戎服,复闺妆,举皆惊骇,咸谓自有生民以来,盖未见也。以异事闻于朝,召复赴阙。欲纳宫中,将军曰:‘臣无媲君礼制。以死誓拒之。势力加迫,遂自尽,所以追赠有‘孝烈之谥┮病!…”按此考辨精确,而所传木兰之烈,则未尝适人者;传奇虽多谬悠,然古忠孝节烈之迹,则宜以信传之。因文长有“王郎成亲”之科白,而详之于此……
在侯有造之后,明天启年间宰相朱国祯《涌幢小品》、清刘澍年《三十二兰诗钞》均认为木兰姓魏,亳地人。一些地方志,如《亳县志》、《保定府志》、清雍正《完县志》亦有同样记载。
朱姓之说见于明代焦竑《焦氏笔乘》卷三:“木兰,朱氏女子,代父从征。今黄州黄陂县北七十里,即隋木兰县。有木兰山、将军冢、忠烈庙,足以补《乐府题解》之缺。”另明代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清代《康熙黄陂县志》亦有相似记载。唐代诗人杜牧《题木兰庙》也是他于会昌年间任黄州刺史时,为位于现湖北黄冈西木兰山上的木兰庙所作。但是,朱姓与木姓、魏姓一样,最终都没有得到大众认可。
现今广为流传的花姓来自明代著名作家徐渭(1521~1593)创作的杂剧《四声猿•雌木兰》。《雌木兰》中,旦角开场即自我介绍:“妾身姓花名木兰。”徐渭为什么不直接采用《木兰诗》中“木兰”这一称呼或当时已存在的魏、朱二姓,而要让木兰姓花?其中是否有他的独特用心?这是一个值得探寻的问题。
有人认为“花”有迷惑人、不真实之意。《雌木兰》中木兰母亲姓贾,贾者,假也,不真实,与木兰的花姓正互为注释,徐渭是要借此说明剧中人物乃凭空虚构,并非确有其人。这一解释失于牵强,也有悖作者的创作意图。徐渭在诗作《西北三首》(一)中说:“西北谁家妇?雄才似木兰。一朝驰大道,几日隘长安。红失裙藏镫,尘生袜打鞍。当垆无不可,转战谅非难。”(《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边词廿六首》(十三)又有:“汉军争看绣裆,十万弯弧一女郎。唤起木兰亲与较,看他用箭是谁长?”从中看出,徐渭喜爱、欣赏木兰这个人物,既如此,他又怎肯无端地否定她的真实性?不仅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徐渭是把木兰当作自己的化身来塑造的。作为文人,徐渭虽然没有战场上浴血奋战、英勇搏杀的经历,但是他曾间接参与了明代抗倭活动。袁宏道《徐文长传》说:“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谭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徐渭在胡梅林门下做幕客时常常参与胡的军事策划,并屡有奇计。遗憾的是他没有木兰那般幸运,使战争成为人生转折的契机,扬名立世,成就未来。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徐渭要借与自己一样有战争经历,而且不同于众的木兰表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他笔下的木兰自负、骄傲,获得赫赫战功如探囊取物,处处折射出徐渭自己恃才傲物、不流于世俗的性格行为特点。而当我们仔细体味《四声猿》时,又会发现《雌木兰》一剧与徐渭关系最为密切,蕴涵着他诸多良苦用心。譬如他给木兰的妹妹取名木难也是有喻意的。木难是宝珠名。“火齐木难”比喻珍奇难得之物,多用来指书画诗文。三国魏的曹植《美女篇》有:“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美女篇》写了一个美丽高洁的女子因为欣慕高义而难以寻求到知音,故而“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这是曹植自叹文才斐然,却无人赏识,壮志满怀,然抱负难施。徐渭书画诗文俱佳,文才武略均备,却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正如稀世罕见的木难宝珠不遇明主,鱼眼珠玑混为一谈。由此看来,《雌木兰》中,木兰寄予着徐渭的理想和抱负,木难则映射徐渭的现实人生。通过改变木兰的姓,着意暗示剧中主角是虚构的,既无关《雌木兰》主旨,也不能给作品增色,反而有损作者的寄托,岂非画蛇添足之举?才华超群如徐渭者,怎会有如此愚笨之表现?至于木兰母亲之姓“贾”,与其说指木兰故事是不真实的,不如说与木兰的女扮男装相关。木兰是以父亲的名义从军的,她是“假”花弧。但是贾姓如用在木兰身上,与作者创作意图不符,且有损人物形象,故徐渭将其安在花母身上,借以提示木兰易装的特殊身份。那么,徐渭让木兰姓花的原因究竟何在?破解了这一创作之谜,我们才不辜负作者的苦心孤诣,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雌木兰》。
中国文人对兰的喜爱源于《楚辞》。《楚辞》中兰出现四十余次,木兰作为兰之一种明确出现三次:“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梼木兰以矫蕙兮,凿申椒以为粮”(《惜诵》)。另外,“揽木根以结茝兮”(《离骚》)一句中,“木”亦指木兰。木兰另有一名辛夷,辛夷在《楚辞》中出现五次,如《九章•涉江》:“露申辛夷死林薄兮。”由此看出,木兰这一植物在《楚辞》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离骚》中,兰、蕙是香花香草的代表,既象征着屈原高洁的品性,也寄予着他的人才理想。正是屈原赋予兰的这些深刻意蕴,使其与菊、梅、竹并称为花中四君子,受到国人喜爱。兰与《楚辞》仿佛一对孪生兄弟,形影相随,不可分割。《楚辞》的代表作《离骚》以其浪漫主义文风和执著坚贞的精神内涵对中国古代文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使得兰频繁出现在文人笔下。徐渭也是深受楚辞影响的古代作家之一。他亲自抄录过楚辞,其文中有一篇《题楷书楚词后》,此处的“楚词”即“楚辞”。《柳浪堤楚颂亭二首为溧阳史氏题》(二)是徐渭读屈原《九章•橘颂》而作,诗中说:“屈子颂匪今,轼也志空寓,千载伊谁子,后皇锡嘉树。曾剡刺崇檐,青黄揉广阼,永与兹亭留,不迁乃其素。”借诗赞赏橘树所象征的独立不迁的人格品性。屈原作品中,徐渭最喜爱的还是《离骚》。他在《梅赋》中说:“亦有游心道德之儒,含思风雅之伯,读《易》说《诗》于其下,咏《骚》作记当其处,飞觥爵于弥留,顾徘徊而不去。”《赠光禄少卿沈公传》一文又有:“余读《离骚》,及阅青霞君塞下所著《鸣剑小言集•筹边赋》,扼腕流涕而叹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愤,等死耳,而酷不酷异焉。”沈练是明代嘉靖帝时的御史大夫,嫉恶如仇,刚直不阿,因弹劾奸臣严嵩被谋害。徐渭对沈练深怀敬意,故以忠贞的屈原比之,可见他对屈原的敬佩之情。受屈原和楚辞影响,兰成为他钟情的花卉也就是情理中事。徐渭有两首题名为“兰”的诗歌。其一说:“懒从九畹看兰花,只取隃糜弄影斜。闻道金陵马姬手,补将燕子污袈裟。”“九畹”句显然出自《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只是此处徐渭是反屈原之意而用之。其二云:“兰亭旧种越王兰,碧浪红香天下传。近日野香成秉束,一篮不值五文钱。”用的正是《离骚》的比喻象征手法,使兰与野香相对,用野香的繁茂,衬托兰所象征的贤才之落魄。在《牡丹赋》中,徐渭借他人之口说:“是以古之达人修士,佩兰采菊,茹芝挈芳,始既无有乎秾艳,终亦不见其寒凉,恬淡容与,与天久长。”“佩兰采菊,茹芝挈芳”让我们不由得想起屈原,想起《离骚》中“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等诗句。由此可见,徐渭熟稔楚辞,楚辞给予徐渭精神、创作两方面的滋养。这是徐渭让木兰姓花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