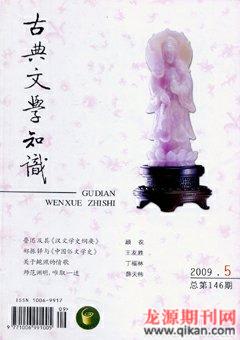中国古典小说回目对朝鲜汉文小说的影响
李小龙
朝鲜古典小说的产生与发展都接受了中国小说的强大影响,如大家都公认金时习(1435-1493)仿《剪灯新话》而作的《金鳌新话》为朝鲜小说的开山之作。即便再向前追溯,新罗时期(660-936)的《双女坟记》,实即朝鲜著名文士崔致远在唐朝为官时期的作品,它不应仅仅被指出模仿了唐传奇,事实上,它本身也当被置于唐代传奇之中。那么,在中朝两国如此密切的小说关系史上,中国小说传统的回目体制是否也曾经有过一番异国旅行呢?
据目前可考之作品,郑泰齐的《天君演义》应是最早具有类于回目之标目的朝鲜汉文小说,朝鲜文学史家赵润济也承认“朝鲜小说采用章回体,这篇小说大概是嚆矢”。郑泰齐的时代颇早,甚至早于“标志着汉文长篇小说成熟”的金万重。这篇作品属于韩国当时流行的寓言类小说,延续了林悌(1549-1587)《愁城志》中“人的心性的拟人化处理”,是“天君小说”的代表作。它已开始受到中国历史演义的影响,比如,它虽把人的心性称为“天君”来进行寓言式写作,但同时又把天君描写为一个帝王,写他如何即位、如何执政、如何御敌、如何平难……总之,正如书名所显示的,它已从“天君小说”之《天君本纪》、《天君实录》中衍化而出,一似《三国志演义》从《三国志》脱来一样,变成了“演义”。不仅如此,赵润济曾引了郑泰齐自序(序署“菊堂”,大多认为即郑氏)中的两段,颇有可论:
尝见史家诸书衍义,其主言遣辞皆是浮夸。实虚而修之,有无而张之,分其事而别其题,未结于前尾,而更起于下回,盖欲利于引用,而务于悦人也。
近来小说杂记行于世者固多,而以其中表著者言之,来自中国者《剪灯新话》、《艳异篇》,出于我东者《钟离胡卢》、《御眠盾》等书。非鬼神怪诞之说,则皆男女期会之事,其不及诸史远矣。
这“不及诸史远矣”中的“诸史”自非史学著作,而是历史演义,因前已明言“史家诸书衍义”,又言其为“近来小说杂记”。所以,他是有意识地抛开当时在朝鲜很有影响的《剪灯新话》而转向新的演义文体的,主要模仿对象很可能就是在朝鲜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中国小说《三国志演义》。而且,虽然目前现存于韩国的《三国志演义》版本几乎全为毛宗岗评本,但仍可肯定所效者当为明代早期版本:如嘉靖本或建文本。这倒不仅因为毛宗岗本成书大致在康熙四年(1665),此时距郑泰齐去世也只有四年的时间,而是从《天君演义》的标目体制中可以看到早期《三国志演义》标目清晰的影子:全书分为三十一“则”,没有回目序数,单目,七言。其目从“天君即位分封官”到“天君平难论功罪”,与嘉靖本标目如出一辙,微异之处在于标目文字尚不纯熟——但此亦不足为病,在当时的中国,《三国志演义》影响下的其他历史演义小说,也有许多标目文字面目简陋。
从郑氏序中,亦可知他对章回体制仿效的自觉:他先论述了“史家诸书衍义”的特点(“浮夸”等词或只是描述,并无贬意),认为这种体裁有“利于引用,而务于悦人”的功效,便也使用了“分其事而别其题,未结于前尾,而更起于下回”的体制形态。因为汉文小说资料的存佚不同,我们只能从现存作品中指认郑氏此作为最早的章回体。但通过分析,可以隐约感觉到,也许这种指认恰恰暗合了历史的真实,因为他是直接学习“衍义”、“诸史”,开始“分其事而别其题”的,而作品体制形态的原始与粗糙也体现出这一点。假设此书是作者生命中途所作,其时大致为中国的明末,回目体制也刚刚成熟半个世纪左右,应该说,郑泰齐能做到这一步,称得上反应迅速了。
接下来便是金万重的两部著名作品《九云梦》与《谢氏南征记》。金万重很重视韩文写作,故此二书皆先以韩文写成,后经其孙金春泽(1670-1717)译为汉文,才广为人知(也有韩国学者认为此二书先以汉文写定)。据韦旭升云,译本对原本进行了一些改动,如《谢氏南征记》,“每章的标题,原文颇简单,粗分六章,标题各为《成婚》、《妖妾》、《奸恶之门客》、《家祸》、《南征一》、《南征二》、《家运恢复》”,“金春泽则把它细分为十二章,仿照中国章回体小说,分别标出每章的基本内容,如‘宽耳君子信谗言,奸婢妖人戕爱子”。在金氏创作或改译的时代,朝鲜汉文小说的回目已较郑泰齐之作有了发展,起码开始了双回目的历程。不过,金万重的这两部作品情况还稍有不同。《九云梦》共十六“则”,标目为双对形式,且一半为七言,一半为八言,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回目长度。但这样成熟的回目,却竟然尚无回目序数——其辅助要素还不齐全。《谢氏南征记》的回目从四言到六言均有,在长度上较为原始,但每回前却有“第一、第二”的序数,虽然尚非典型的“第×回”字样。
赵圣期的《彰善感义录》大约与金万重的两部作品同时问世,补上了“第×回”字样,回目亦均齐为五言对句。当然,五言在中国传统回目中出现的比例很低。而另一部别名中亦有“彰善”二字的作品《玉麟梦》则已发展为五十三回的长篇(这在朝鲜汉文小说中是很长的作品了),回目也统一为七言对句。此后的《九云记》、《玉楼梦》与《汉唐遗事》,不但篇幅增大,在回目长度上也均向八言倾斜,甚至出现了九言、十言目;直到二十世纪初的《包阎罗演义》,回目终于成为纯粹的八言目。
这些作品的回目不仅在形式上模仿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回目,内容上也多有借鉴。《汉唐遗事》的回目颇与《三国志演义》相似,如第二十回上句云“三江口丞相用兵”、第二十七回上句云“避贼势迁都长安”,再如“青主大起七军”、“徐福百骑劫吴硕营”、“降吴兴三分归一统”等,都是直接从《三国志演义》中搬来者——甚至还可推测其来自毛评本:如最后一例,只有毛本作“降孙皓三分归一统”。不过,此书每回均极短,如第五十二回“降吴兴三分归一统”,全文如下:
降吴兴,三分归一,正如晋炎统天下也。
单说青主斩了朱成,尽降其众,大赦天下,改元建中,建国号大唐。仍合三分为一统,自此天下太平。正是:天开新日月,地列旧江山。
未知如何,下文分解。
全回只有七十三个字,再除去“单说”、“正是”等套语就更少了,由此亦可看出草率之迹。但这么单薄的内容仍要凑出一联八言偶目,亦可知其回目创作之定型化。
《九云记》的情况要复杂些。如第一回云“西王母瑶池宴蟠桃 释性真石桥戏明珠”,下句来自《九云梦》老尊本第一回“老尊师南岳讲妙法 小沙弥石桥逢仙女”之下句,二书本有渊源,故可不论。然据赵冬梅的研究,其上句来自《女仙外史》第一回“西王母瑶池开宴 天狼星月殿求姻”的上句,第二回“咸宁县性真投胎 众邻居潘瞽说命”实亦来自《女仙外史》第二回之“蒲台县嫦娥降世 林宦家后羿投胎”。此外,崔溶澈将其与《红楼梦》进行了详细对比,指出:“《九云记》的回目,如果和《红楼梦》回目比较,在文字上有相似的地方,约有三四回,如第二十九回‘乐游园赏秋咏菊花和《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相似,第三十一回‘白凌波雅宜牙牌令和《红楼梦》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相似,第三十四回‘庾太君开宴群芳院和《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也很类似。”可知它也当仿效了《红┞ッ巍贰*┆
《九云记》的回目形制与典型的中国古典小说仍有不同之处。据崔溶澈介绍,此书抄本“只有卷首有题目,同一卷的各回直接连写……总纲收录回目,但只表卷数不表回数”,全书共九卷,据崔溶澈大文所附书影可知,卷一有“一回 西王母瑶池宴蟠桃 释性真石桥戏明珠”的标题,不但回目序数前无“第”字,以下三回也均连写而无回目,直到下一卷的开始一回即第五回方出现回目。总纲(即目录)亦只标卷数而不标回数,类似于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等早期章回小说的标目体制。然而,这些特点在中国大陆整理出版的两种《九云记》中都被传统回目体制的惯性思维自动整合了:不但目录中有了“第×回”的序数,正文每回前也添加了回目,回目序数前亦补充了“第”字,但前言、后记中却无相关说明。其实,《九云记》的这种特点在朝鲜也并不罕见,如《六美堂记》,回目虽为标准的双对七言,却没有回目序数;《玉仙梦》取“卷”而弃“回”:都可看出朝鲜汉文小说体制的相对自由。
在这种接受中,朝鲜汉文小说的回目也有自己的多方取资与新变,如水山《广寒楼记》(朝鲜家喻户晓的《春香传》的汉文异本)的回目便是一例:它每回先有一个二言单句的标目,然后再有一个正常的七言或八言的双句偶目(《广寒楼记》有很多版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二者回目不尽相同,体制则一)。这种形式与中国话本小说中的“贪欣误”式标目(笔者另有文专论)及丁耀亢《续金瓶梅》类似。而从韩国所藏完山李氏《中国小说绘模本》的小序中可知,属于“贪欣误”式的作品《五色石》至迟已于英祖三十八年(1762)传入朝鲜,《续金瓶梅》现在韩国亦有两种刊本存世,可能皆为务本堂本,或亦于十八世纪中期传入者。
不过,这只是就形制而言,如从内容上着眼,《广寒楼记》回目则应是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回目与明清传奇出目叠加影响的结果。《广寒楼记》的写作与评点都受金圣叹批《西厢记》影响甚深,这在其评语与正文中大量沿袭金批文字可见。其一级回目分别为“探春、寻春、凝情、惜别、拷艳、保信、践约、续缘”,金批《西厢记》折目分别为“惊艳、借厢、酬韵、闹斋、寺警、请宴、赖婚、琴心、前候、闹简、赖简、后候、酬简、拷艳、哭宴、惊梦”:二者不单单是用语类似,后者甚至将前者在舞台上最脍炙人口的“拷艳”一出出目原封不动地照搬了。
关于此还有一特殊的例证,即法乳《西厢记》的《东厢记》,它被称为是“最早的韩国戏曲作品之一”。此剧先为汶阳散人(姓名未考)据李德懋(1741-1792)文言小说《金申夫妇传》改编而成,后来白斗镛(18世纪末)又再次编定,于1798年出版。从其题目即可见模仿《西厢记》的本意,在体制上,它也仿效了元杂剧:全剧四折,且有“正目”,而标目形态亦如《广寒楼记》一样呈现出混杂的面貌,因为它在四句正目后又缀了一个二字的标目,极类明清传奇的出目:
正目:穷措大南洞窃叹——才贤 老处女北阙彻闻——德慧
诸尚书西城主婚——眷泽 好夫妇东向感恩——福缘
可见这种复合型的标目已不独小说为然了。
不仅如此,朝鲜汉文小说在接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回目体制后,还接受了插图与图题的体制,并亦呈现出与回目的关联。如被誉为“汉文小说的巅峰之作”的《玉楼梦》,其德兴书林本中所附插图为典型的明代通俗小说插图,图中写刻出图题,如图十一为“望仙台卢均迎道士”,图十二为“文昌玩月白玉楼”,分别为第二十九回与第一回回目的上句。
总体来说,朝鲜汉文小说的回目在体制上大致与中国古典小说回目无异,虽然遣词造句还稍嫌生硬,但个别作品对仗之工整与概述之贴切已能较某些中国的粗劣之作为胜了,如《九云记》第十二回“秦宫娥掩泣随黄门 杨学士陈情叩青锁(按,当为‘琐)”、第二十五回“西园新第两公主出阁 东楼寿席二佳姬入门”,不但叙事得当,且有意识地使用“黄”、“青”、“西”、“东”等字词组成工致之对仗。再如《玉楼梦》,以“青楼”对“红娘”、“白云洞”对“紫辰殿”,也见组织之力,“玉笛酬唱雌雄律 瑶琴断续山水弦”之类也的确精巧,可见其回目制作已颇为成熟。
其实,朝鲜汉文小说中的短篇小说也有了类似的标目,《韩国汉文小说全集》中《东国拾遗》部分的几种野谈作品均有单句叙事标目,如“轿中纳鬟诳贼师”、“老翁禳星话天数”等,颇类我国的《绿窗新话》。由此可以知道,正如回目在中国已不止为章回小说之专利,同时亦进入了话本小说一样,在朝鲜也影响到了短篇汉文小说的标目体制。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