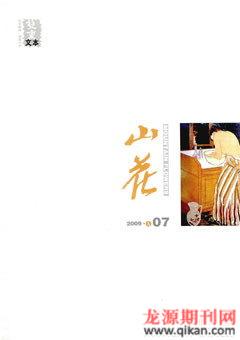聊聊经典
阿 成
坦率地说,对于文学作品之经典的界定,其实是很个人化的。我曾经说过,每一个阅读者都有自己的权力,就是对于某篇作品的评判权。现在看,这个权力评论家掌握得比较好,运用得也比较充分。此外就是教中文的老师,他们运用得也可以。但是普通的、非专业的读者在这方面运用的就不是那么自觉,甚至忘掉了自己的权力,常常不由自地主跟着人云亦云。说起来,经典文学作品之评判通常是在大众之中产生的,这是经典之花的土壤,如果是无土栽培出来的经典之花,这类经典作品就比较可疑,比较脆弱了。当然,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现在我们回到阅读的源头,闲着没事,随便打开一本杂志看一篇小说,这种行为通常没什么目的,就是阅读。就是没事,就是消遣。但是一读,放不下了,被震撼了、感动了,不能从中自拔了——要说经典小说,这应当算是基本条件之一。
总的说来,世界文坛还是普通作品多。如果全都是经典小说,那普通的小说就显得犹为可贵了。经典就是对普通而言的。要说经典之产生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也未必,不过,我到是想,可不可以把作者非凡的天才和思索的深邃加在里面?不知这样说对不对。自然这是一家之言了。听说,琐碎之呓语、新小布尔乔亚、香软肥俗,连同顺嘴故事在经典界也有交椅坐了。蹙眉一想,也对,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大家都在文坛上混,不仅仅要慷慨激昂,撒豆成兵,私底下也很泪水的。总之,倘若把小说写到经典这个层面上,那就是了不起,那就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成功。
如果,一个人写了一百篇小说,其中有十篇成功,在我个人看,这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了;如果写了一百篇,有九十九篇成功,只有一篇小说失败了,或者有点争议,间或悄悄地、羞羞答答地泊来几句微词,您就是一个有趣儿的作家。如果写一篇成功一篇,您哪是写小说呀,您是在生产神话。有了这样的神人,其他人还跟着瞎忙活啥呀,有他一个人就足够了。当然,较短时间内这事儿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之于经典的产生,说句大白话,首先要有自己诚实的人生感受,并难以忘怀,哪怕它极其的微小,但始终震撼着你和读者的心灵,像第一缕春风下的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那种全新的感受。这当然不是什么方法论,但多多少少还是带有一点宿命的味道。我认识几位写小说的人,他们私下很怀疑自己的能力,但却毫不怀疑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帮助他们,助他们一臂之力。这是一个很有趣儿的现象,超凡而真实。这样看来,写小说似乎又有点玄了,不过,回过头来我们看那些传世之作,像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鲁迅先生的《故乡》、《孔乙己》,像那些世界级的小说大师写的短篇小说,写的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小事情。但只要打开这篇作品看您就会被感动,被震撼,打开一千次,感动一千次。那么,是不是具有这样品质的小说就是经典小说呢?相信会有不同的意见。
我最近阅读少,主要是觉得当下的阅读变累了。特别是读那种絮絮叨叨的小说,讲那种很长又很拙劣的玩故事的小说。无力地放下书,我就傻傻地想,哪怕其中有一两句经典之语,一小段儿拨动心弦的细节。或者啥事儿没有也行,但叙述生动,神采飞扬也好哇。是的,文本之中尚有经典之语点缀其中的小说肯定有,但不太好碰,就像不放农药的蔬菜,能没有吗?指定有,哪怕卖贵点儿也行啊,但不容易买到。所以我很茫然,在阅读的途中常有一种迷路感。说到这儿,我想说一句走题的话——我常说走题的话(有的老派同志受不了我这个):就是能不能把那种不放农药的好小说,集子也好,书也好,定价高一些,按质论价地卖。比如放农药的小说一本卖36块钱,不放农药的好小说可以提高到100块钱一本。我们老百姓买了之后,读了之后,觉得物有所值呀。总之,好的小说和散文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故事和经历,那还远远不够,而是超凡的智慧和艺术才能,让买家动容而喟叹。
回到正题。说起来,我这一生也不敢奢求出经典,不是认为绝不可能,而是没想过。这就像和嫦娥约会,约她到哈尔滨的露西亚酒吧坐坐,白色的餐布上:一盘地道的哈尔滨红肠,一盘纯绿色的、自腌的、加了小茴香的酸黄瓜(两菜是不少点?),两杯地道的俄式红茶,我哈下腰跟牛皮的嫦娥说,这个地方,包括后面那个巴洛克建筑风格的黄楼,原来是我读小学的学校哩——这可能吗?我辈唯一之目标,极其的单纯,就是有一部分人喜欢我的小说就可以了。
简言之,经典之作品,在我看,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首先要人家能读下去,并侥有兴趣地读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