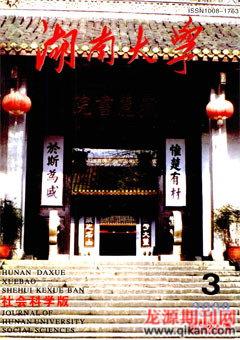从认识到认同
[摘要]运用萨特的“自欺”理论,分析了中国文人对死亡从认识走向认同,从“自欺”走向直面的过程,同时批驳了关于古典文人死亡意识的两种错误观点,进而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现代死亡意识的建立对于新文学的意义。
[关键词]认识;认同;死亡意识;自欺;个性思潮;科学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3—0106—04
一
“五四”新文学,无论小说、诗歌还是散文,涉及死亡之多前所未有,其中蕴涵着的死亡意识之丰富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些现象说明,“五四”文人相对于传统文人,他们的死亡意识发生了某种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到底是什么呢?它是怎样发生的?这些问题必须回答。已有一些文章谈到过相关问题,但是或者零零碎碎,管中窥豹,或者偏执一说,顾此失彼,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本文试图运用萨特的“自欺”理论,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个比较全面而辨证的解释。
在逻辑学里,关于演绎推理有一个著名的三段论:人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仅从逻辑认识层面上看,我们都会为它的正确性所折服,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推论,因为它选择的论证起点再完美不过了。试问古往今来,除传说中的彭祖之外,还有真正不死的例外吗?不过,苏格拉底在做这个推论时,他仅仅只是在进行一场理性思维活动,一点都不会因这个推理的结论而引起情感的波动吗?也许会,也许不会。我想不会的可能性也存在,因为苏格拉底是一个狂热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但他首先毕竟是一个有死的人,所以会的可能性同样存在。如果将推理中苏格拉底的名字换上你我的名字,我们恐怕对其结论多少也会有所触动,敏感一点的,甚至会感伤莫名,对其推理的严密性倒是不会那么在意了。苏格拉底是会死的。我也是人,我也是会死的。读者很可能因此不禁对生命的短暂性黯然神伤。
作为一个逻辑学上的著名论断,人的“有死性”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普通的理性认识。但是对于鲜活的生命个体来说,死亡的意识是那样让人灵魂震惊、精神发怵。对于死亡,人们总是要通过种种方式进行排斥、规避、淡化或消解。理性上的认识是人类走出原始群居生活时代就已基本完成了的,但情感上的认同却要晓得多。从中国文学史来看,情感上的普遍认同,恐怕只有到“五四”时期才开始。那么在此之前的漫长的时期里,中国文人的死亡意识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借用萨特的说法,我们认为它基本上处于一种自欺状态。这里所谓的自欺,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生命意识,后文会有详细的剖析。对于中国古典文人的死亡意识,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偏颇认识。一种认为,在“五四”之前,中国文人对于死亡的必然性与终极性没有深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否定死亡的存在,而只是强调生命意识。抱这种观点的人于是得出结论,中国文学因此缺乏生命悲剧意识。另一种观点则否定了现代文人关于死亡的意识相对前人有任何超越。执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远在曹操的诗歌中或者王羲之的散文里,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死亡意识和对生命的悲剧情感,唐宋文学和明清文学就更是如此了。“五四”文人和“五四”以后的文人在这一点上丝毫不比前人高明,他们只是重复了古典文学中一个古老的主题。事实上以上两种观点都不尽然。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上回避了死亡,不愿直面人生的终极结局,这从某个角度来看是正确的。在浩瀚的古典文学作品中,有多少篇章是以死亡为主题的?真是少之又少。但是,古典文学作家们真的像不少观点认为的那样,被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的观念和道家的齐生死思想淹没了,死亡完全沉人到他们的潜意识里去了吗?他们当真就没有死亡的感伤吗?曹操说:“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滕蛇乘雾,终为土灰”(《步出夏门行》)。“莫不有终期”不就等于苏格拉底的“人是会死的”这样一种死亡意识吗?张若虚则委婉地表达了这种感伤:“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浩月永恒,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江月年年总是如此美丽,仿佛在等待一个能欣赏她的人。是描绘月亮的高手李白吗?抑或是富有才情的张若虚自己?但是李白也不得不与月亮永别,张若虚也在理性中认识到自己不可能与明月流水长相伴,他只是无数赏月、颂月者中的一个短暂过客。还有更多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杜甫的一些诗歌,近人王国维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古人不可能像今人一样敢于直面死亡的残酷,但他们对于死亡的必然性和终极性的认识也是很清楚的,并非如一些今人想象的那样毫无知识,一味盲目乐观,丝毫没有生命的悲剧观念。
既然认识到了死亡,为什么中国古典文人会在总体上回避死亡问题,淡化生命的悲剧意识呢?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心理学问题。人类在遇到无法直面、不能接受的事实时,常常会做出一种心理反应,以求平衡和自我保护,那就是自欺。譬如在比赛中一个很有实力的人吃了败仗,他或者会将原因归结为诸多偶然因素,或者会认为对方舞弊。这时候,他不是在说谎,而是在自欺。萨特下面这段话,对我们理解这种心理很有帮助:“说谎的本质在于:说谎者完全了解他所掩盖的真情……这只要一种不透明性从原则上向别人掩盖他的意图就够了。只需他人能够把谎言看作真情就够了……对实行自欺的人而言,关键恰恰在于掩盖一个令人不快的真情或把令人愉快的错误表述为真情。因此自欺外表看来有说谎的结构。不过,根本不同的是,在自欺中,我正是对我自己掩盖真情。于是,这里不存在欺骗者和被欺骗者的二元性。相反,自欺本质上包含一个意识的单一性。”这样说来,如果一定要说这个强大的失败者在说谎,那他就是在对自己说谎。但他不了解自己失败的原因,他只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在逻辑推理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是偶然原因或对方作弊,我怎么可能失败呢?因为对于这个人来说,失败太难接受了,所以他会做出自欺的反应。而对于人类来说,有比失败更难接受的事实,那就是死亡。人类面对死亡的必然性,并不那么容易就能客观地处理,自然地面对。而且自然的死亡态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的死不只是因为他年事已高,往往还有具体的原因,比如癌症、心肌梗塞、肺炎——这些灾难像飞机失事一样,既令人害怕又来得突然。所以自然死亡是不存在的:降临在人身上的一切不幸都不可能是自然的,因为正是有人的存在,才有世界的存在。人人都会死,但对每个人来说,死却都是飞来之祸、无妄之灾,即便他是平静地死去。正是因为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自然面对,人们才提倡追求这样一种超越的境界。人必有一死的残酷现实使弱小而又意识敏锐的人类无法面对,他们往往靠自欺才能维持生存的热情。于是有了各种宗教和神话,让人们可以把死亡的恐惧交给神来负担;也有了各种哲学,使人们形而上地看待死亡,多少淡化了形而下的对于肉体消亡的恐惧;而在中国,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在家族的传宗接代活动
中,幻想自己的生命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了下去。也就是说,人们在各种宗教、哲学,或者集体观念中获得一种永生的假象。有些是肉体不死的许诺,有些是精神永垂不朽的激励。总之,人们通过这些方式,实现自欺。
生命意识处于自欺状态中的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信徒们不仅不害怕死亡,相反却追求死亡,渴望早日升入天堂。当时的文学作品,热衷于表现的就是这种狂人的情感。…而中国古人则不同,他们选择的是逃避或转移死亡意识。曾经在生死问题上那么明智的曹操,在临死前却吩咐他的婢妾们居铜雀台,“善待之,于堂上安六尺床,施穗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全三国文》卷三曹操《遗令》)。作过《兰亭序》那样哀伤感怀之作的王羲之,在《兰亭诗》里说:“陶化非吾国,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白泰。”《兰亭序》里的感伤,在此已被一种随其自然的安详心态取消了。中国古典诗词特别钟情于写“老”,以消淡死亡的意识。“老”是死的一种预兆,但还不是死。只写老不写死,既没有否定无可否定的事实,又可避免直面那不敢直面的现实。而写老,也不直接写。往往通过“悲晚”、“悲秋”、“忆昔”一类主题来委婉表达。李商隐的《登乐游原》非常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感怀年老一直被认为是这首诗的主题。但是人们忽略了“近黄昏”的感慨只是“意不适”的转移。之所以“意不适”,只能解释为诗人内心深处潜在的某种意识在作祟。被莫名的痛苦折磨的诗人外出登高散心,而在这种心境下,即使看到了无限美好的夕阳,发出的也只会是“近黄昏”的悲叹。外在景象是诗人内心的象征,从诗句前后的联系来看,“近黄昏”的“夕阳”暗示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很可能就是死亡的意识。但是诗人只写黄昏,只写夕阳,他不会,也不能表达自己内在的真实的意识。再如孟郊的《秋怀》:“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纹,肠中转愁盘。疑怀无所凭,虚听多无端。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弹。”把一个病入膏肓、幻听重重的老者的临终哀呻,消淡为悲秋的吟咏;而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后两句用艰难旅途的记忆转移了前面生命短暂、虚无的描写。而更间接的则是写老屋、旧墙、废寺、落花,以寄托对青春岁月、辉煌过去的思念。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这样的诗词比比皆是,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就这样,中国文学几乎将死亡主题驱逐出去了。中国文人就是通过以上种种方式实现了自欺,阻止死亡进入意识层面,从而逃避死亡恐惧的。
二
但是,自欺不可能完全将死亡意识压抑到潜意识之中,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意识。根据萨特的理论,潜意识与自欺是两码事,潜意识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他说:“自欺连同它的所有矛盾存在着,它充满着意识……它用潜意识压抑力来施诡计并力图逃避潜意识压抑力。……唯有这潜意识压抑力能够理解精神分析者的问题或启示,或多或少接近了用它来压抑的实在意象,这是因为唯有它知道它所压抑的东西。……潜意识压抑力为了发挥它的识别的主动性,就应该认识它所压抑的东西。如果我们确实放弃了所有把这种压抑力表述为盲目力量的冲突的隐喻,力量就恰恰要承认潜意识压抑力应该选择,而且为了选择要再次出现。”……总之,潜意识压抑力没有对识别可压抑的刺激的意识,它如何能识别它们呢?人们能设想对自我无知的知吗?既然人们不能将死亡意识完全推到潜意识中去,它们就总是会时不时地涌现出来。所以尽管中国文人不谈死亡,中国文学几乎没有死亡主题,但并不等于说中国文人就真正相信不死观念,中国传统文学里就没有死亡意识。在一定情境的刺激下,中国文人总是会对生命的终极性和毁灭性发出哀叹,不过很快又会将这种悲剧意识转移、淡化。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前后很不一致,前面深沉厚重的生命悲叹被后面缠绵悱恻的男女情思所替代,而且二者之间过渡得如此之好,仿佛前面部分只是后面部分的铺垫。不过仔细分析,似乎恋妇思念良人或者良人思念故乡,都不需要反复发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生命哀唱。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恋归与思乡之情的抒发,在很大程度上为的是转移死亡的悲恸。中国文人的思乡之情、恋妇之情、仕途感受和历史情怀等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它们总是要与生死情感的抒发融汇在一起。名句“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到底是感怀历史,还是感慨生命?无法分得清楚。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发出的是功名未就的叹息,还是对时间一去不返的惋惜?值得推敲。如果是前者,则有些不好解释。事实上苏东坡当时已很有成就了,为什么他还会如此悲恸?千古的读者为什么竟会不去计较其中的漏洞,而只是与苏学士共沾儒巾?除了眷恋功名的共同心理之外,难道就没有对生命将逝的共同悲伤?我想,千古读者认同的,主要还是苏东坡的这种生命感伤情怀。
如上所述,自欺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也就是说,自欺所依赖的手段——潜意识压抑力实际上总能意识到它压抑了什么。中国文人明显意识到了被压抑了的死亡的存在。但是这种意识要冲破压力,进入显意识层面,成为文学艺术一个重要的表现对象,则只有在消除了形成这种压抑力的诸多因素之后,才能实现。在中国,压抑死亡意识的主要是以家族观念和功名思想为中心的集体意识。说家族观念是集体意识好理解,说功名思想是集体意识则不那么容易让人信服,因为功与名也可以是个人的。问题的关键是,家族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几乎成为左右一切的力量。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社会伦理,无不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组织的。在这种体制下,功只能是为国立的功,名只能是为家族出的名。家族观念淡化了个人意识,个人于是相信自己的生命在死后可以在子孙或同族晚辈身上得以延续;而追求功名者则相信生命在肉体消逝后可以精神的方式永存。只有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个人主义思想,才能扫荡这些观念。因为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人是一切的始点和终点,是一切价值评判的标准,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个人生命的结束就意味着世界的毁灭。苏格拉底的三段论推理,对于现代人来说就成了另外一种推理:“我是会死的,这太可怕了,我死了整个世界就毁灭了”。这种推理不再仅仅是理性的、逻辑的,它也包涵了非科学的、非理性的、非逻辑的成份。但你能说它是错误的吗?它饱含着人文的情感色彩。因此更贴近人的心灵现实。你能不为其感动吗?在你的生命过程中,会时时那么理性,从不去进行这样震撼心灵、情理难分的推断吗?可见,在很多时候,认识不等同于认同,认识与认同是差别明显的二种意识活动。改变“五四”文人的生命观念的,正是对死亡的认同意识的确立。丘景尼在《无限性自由的径路》里写道:“人们的意识发展到相当的
程度的时候,每觉到心中有说不出的压迫,对于这种压迫。我们想从人生的事实上去说明她的由来,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这种烦恼的本身,就是人们求自由和想打破有限的存在去得到无限性的投影;”说穿了,这就是死亡意识的苏醒在个人主义者心灵上产生的反应,或者说是人们的生死意识从自欺走向自觉的自然症状。可见,只有种种封建的集体意识崩溃之后,也就是说只有树立了个人生命意识,死亡才有可能冲破潜意识压抑力,进入意识层面,人们才会完全由自欺走向自觉。因为此时,他们再也不能想象自己的生命可以在子孙后代的身上得到延续,或者在光荣的功名里永垂不朽。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各自承担死亡的终极性结局。这样,人们的自欺意识就有了被摧毁的基础。
但是除上述因索之外,还另有压抑死亡意识的力量存在。那就是神幻意识。尽管中国人相较于西方人来说较少对于超越的上帝神力的信仰,但是他们更多对于神秘力量的敬畏。在他们的观念里,这种力量无处不在,神秘虚幻,难以捉摸。人的生命也被这种力量所控制。“阎王叫你三更死,不会留你到天明”、“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这些观念让人顺应天命,自然对待生死,它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死亡的痛苦,压抑了人们对于死亡毁灭性的意识。而从西方引进的生命科学将人描述为高级动物,认为人和其他低级动物一样,有一个有生有死的肉体,一样在死后就完全毁灭。可以说,科学主义还原了人的动物性,当然,它也毁灭了人的神性。尽管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主义思想存在种种弊端,它对人文主义构成了多种潜在的威胁,但在”五四”时期,它无情地击毁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的生死之梦,让他们回到现实中来,清醒地面对现实。
三
个性思潮和科学主义的进入,使“五四”新文学作家们获得了崭新的生命体验和死亡意识,他们直面了生命的欢欣和痛苦。而这种欢欣和痛苦不可以用功名观念、神秘意识,也不能用宗教观念或传种接代观念进行蒙蔽或实现转移。“五四”文学的死亡主题因此较此前任何时期文学都要丰富。作家们恸呼生命短暂、人生虚无,同时也在死亡的阴影里发现了生命的美丽和神奇。郭沫若的第一首诗《死的诱惑》,毫不隐晦地表达了死亡的幽灵对自己的巨大吸引力;朱湘的第一首诗直截了当地名之日《死》,纯粹描写临终一刹那的情景;王独清诗歌的第一页就是这样的哀叹:“唉,我愿到野地/去掘一个深坑,/预备我休息/不愿再偷生。”(《失望的哀歌》)。“五四”诗歌以“死”字命名的情况也不少:除朱湘的《死》之外,闻一多和郭沫若也仅以一个赤裸裸的“死”名诗;此外,徐志摩、姚蓬子等亦以“死”字名诗,只不过在“死”字之前加上了不同的修饰语而已;更多的诗人以与“死”字有关的字眼名诗,如《毁灭》、《末日》、《永不回来》、《落花》、《葬我》、《过去的生命》《昨日的园子》,等等。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这种情况就更清楚。事实上,“五四”文人很少有不涉及死亡主题的,如郭沫若、梁遇春、朱湘、徐志摩、李金发、徐玉诺、于赓虞、汪静之、闻一多、鲁迅、郁达夫、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邵洵美等都对这一人生终极现象进行过正面或侧面、直接或间接的描写;即使只偶尔涉及这一命题的,如冯至、朱大楠、姚蓬子、何植三、郑振铎、陈南士等人,也有非常出色、耐人寻味的作品。可以说,关注死亡,是“五四”文人一个重要的创作倾向。以上材料显而易见地表明,死亡已不再是“五四”诗歌中躲躲闪闪的主题了。
对于死亡的必然性与毁灭性的认同,为“五四”文学开创了一片广阔的表现领域。“五四”文人在其中开掘、拓展、创作了丰富的以死亡意识或生命意识为主题的作品。相对于古典文学来说,这恐怕是“五四”新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诗人既知死亡的毁灭性,又必须单独面对死亡,其痛苦就常常强烈到无法忘怀的地步,感伤之情往往无由而至,又绵绵延延,没有绝期,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无可奈何的脆弱的情感。这又是心灵被死亡的恐惧控制而不得自由的表征,比如他们的一些诗歌一任恐惧的情绪流泻,毫无节制。朱湘的《死》。极力渲染临终时刻的阴森、恐怖:灯光时暗时明,最后化成一丝幽烟消失了,而灵床旁的人面色惨淡。同样是朱湘的诗,《有一座坟墓》写荒山野岭一座杂草丛生、只有黑暗与怪鸟相伴的坟墓,恐怖得连月亮都只敢躲在“黑云之后偷窥”。坟墓、枯骨、蛇骸、死城、破塔、落花、古寺、残阳等等是“五四”文学中泛滥成灾的意象,尤其是在象征派诗人如李金发、王独清等人的诗里,几乎每隔几行就要出现一次。文人们的这种情结,是对死亡的摧毁力的恐惧的表现。而且,由于过于认同,使现代文人沉醉于死亡的偏至之中不能自拔。当我们读到徐志摩的《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时,还可以感觉到诗人对此岸世界的批判激情,但当我们读到徐玉诺的《墓地之花》中“我”的呼唤“为什么不宣告了同伴,大家都来到墓的世界”时,那种在死神面前的陶醉、沉沦态度,真难让人相信作者还会对现实世界有一点热情。尽管作为文学作品,有些诗歌喜欢故意夸张情感,如郭沫若的“我心爱的死!我到底要几时才能见你”,就不能信以为真。但是对于灰色情绪的执迷,在“五四”文学里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这是不是又形成了对主体自由的约束?这种现象恐怕是对死亡的认同必然会带来的一个后果。冰心似乎看到了这一点,她的《春水之一三一》写道:“青年人!/觉悟后的悲哀/只深深的将自己葬了。/原也是微小的人类呵!”
[参考文献]
[1]段德智.死亡哲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2]萨特.存在与虚无[J].北京:三联书店,1987.81.
[3]丘景尼.无限性自由的径路[N].晨报副刊,1925-01-07.
[4]庄子.庄子·大宗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肖百容.死亡:自我的出场——“五四”新诗死亡意识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9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