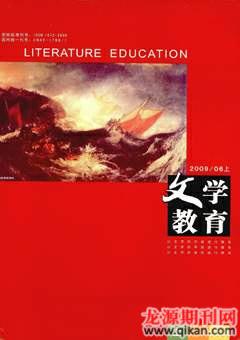今夜无人入眠
斯继东
1.李白
李白发现那只未接电话,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事了。
“蹊跷!”李白对着手机嘀咕了一声。老婆正在客厅里给女儿把尿,就问了:“什么?”“噢,没什么。”李白敷衍了一句。有些事还是别让女人知道的好。这是李白结婚七年总结出来的经验。“爸爸,是什么啊?”三岁的女儿跟着问了一句。“爸爸的手机上有一只未接电话,你拉你的尿吧。”李白说,李白对女儿从不敷衍。号码是马拉家的。李白对数字木讷,能立马反应过来的号码没几只。让李白觉得蹊跷的不是号码,是来电时间:凌晨2点18分。昨夜看完演出喝完酒,到底几点回的家,李白已记不确切,但不会超过凌晨1点,这个酒再多也不会错。
李白的单元房不大,两室两厅一厨一卫,不到九十平米。因为缺个书房,装修时李白就把饭厅合并到了客厅,反正家里从不开伙,可伸缩的西餐桌收紧了靠在客厅空着的那堵墙边,也碍不了什么事。为了给走廊腾地方,餐椅的屁股都被藏到了餐桌底下,只露着几张靠背,却成了天然的衣架子。每天回家,李白的第一件事情是脱衣服。等到衣裤在椅背上一一找到位置后,李白才会晃荡着一身赘肉挪进卫生间如厕冲凉。然后当然是上网,直到凌晨。如果应了饭局牌局或者卡拉OK局回来,则是如厕冲凉后直接睡觉。但不管有局无局,进卧室之前,李白铁定会有个动作:从椅背的裤袋里掏出手机,闹上钟,再带到卧室里。
如果不出差错,这只电话应该是已接电话,但显然昨晚进房间前李白遗漏了那个动作。这个遗漏显得不可饶恕——虽然李白还是准时醒了过来。是的,它很小,小得无足轻重。但最小也是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依然不可饶恕。
嘀咕着“蹊跷”时,李白就站在餐桌前面,他刚刚从房间出来,身上只穿了一条裤衩。一模一样的裤衩,但已不是昨天那条。除了裤衩,还有这张戏票为证,它安静地躺在餐桌上,已经过期;还有李白嘴里的酒嗝为证。
在去单位的路上,李白给马拉打了个电话。他没回拨那个未接电话,而是打了马拉的手机。
凭直觉,李白认为那只未接电话不是马拉打的。马拉不可能这么迟给他打电话。不是马拉,那么就是马拉老婆。马拉老婆打这个电话只有一种可能,马拉那个时候还没回家。在把其他人送回家的至少一个多小时里,马拉干嘛去了?马拉老婆不知道,李白也不知道。李白只知道,一个多小时能干成很多事,特别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现在,第二天的早上8点,马拉在哪里呢?他回家了吗?作为一个目击证人,在没有弄清来龙去脉之前,冒昧地把电话打到他家里,主动接受一位女警官的诘问,肯定是不明智的。
能不能打通手机李白并没把握,因为马拉昨晚喝酒时就宣称他的手机没电了。
但手机通了。看来他已回家——如果当晚他没说谎的话。
“喂!”是马拉的声音。嗓门沙哑,有些迷糊。
“昨晚给我打过电话?”李白问得小心翼翼。
“没事了——再说吧。”马拉说。声音一如往常的平静。连一丝起码的涟漪也没有,但李白却感觉到了底下汹涌的暗流。李白把手机放回裤兜,开始想像手机另一端的场景:客厅里还亮着昨夜的灯,曙光被窗帘严严实实地阻隔于外面,马拉高大的身体深陷于沙发——看上去一点都不高大。他的老婆就坐在对面,穿着睡衣。没人吭声,空气凝重得能绞出水来。
在办公大楼的电梯里,李白碰见了一位女同事。她看了看李白的眼睛,很关切地问了一句:“昨夜没睡好?”李白去洗手间照了照,眼白里果然有不少的血丝。我睡得不好吗?昨晚我可能是睡得最好的一个。李白想。这样想时,他去开水间打来开水,倒掉烟缸里的烟蒂,擦干净办公桌和茶几,然后坐下来打开了电脑。新的一天开始了,看上去跟昨天没有两样,但确确实实是新的一天。
文书送来了文件夹。又是厚厚一叠,即使从头至尾看一遍,也得花去李白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刚参加工作时,李白看得很仔细,字斟句酌,一个标点都不漏。后来,李白开始一行一行地看,再后来,就发展到一目十行。李白在这个岗位上已经整整干了十年。现在,李白一般只看标题。一上午的活半个小时完成。这就是效率。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单位的工作从没因此出过什么纰漏。
马拉还陷在沙发中吗?他老婆只穿了睡衣冷不冷啊?他们一定忘记开空调了。该发个短信提醒他一下吗?当然不行。作为朋友,李白自然希望马拉夫妻和睦家庭幸福。有次跟老婆聊起,李白曾经断言过,四家子中马拉那家子是最牢固的。都说七年之痒,已经过了那个坎,要出事早就出了。可是作为男人,说实话,李白骨子里是挺希望马拉干成点什么坏事的。我们都干不成,那么就让马拉去干吧。像马拉这样有才华的人这辈子不留下一点什么风流韵事,简直天理不容。另外,马拉要么别干,要干就得跟赵四小姐那个档次的人干,否则我们也跟着掉价。
当然,具体到昨晚上,这么个时间段,孤男寡女,不干好事能干什么坏事?
李白就想到了另外两位目击证人:黄皮和毕大师。先打黄皮。关机。再打毕大师。居然也关机。李白很扫兴。于是又开始在电脑前发怔。
真的是他吗?是的,是帕瓦罗蒂。他的全球告别巡演之中国行明明只安排了上海和北京两站,但在无数个演出公司一层接一层的不可告人的交易的操纵下,他的助手、经记人兼保镖,长得富有明星气质的罗伯特·琥珀居然真的把他连哄带骗地弄到了这个在中国版图上找不到地儿的小城市。谁都没想到帕瓦罗蒂会有这么胖这么馋这么懒。在他下塌的贝斯特大酒店,为了能让他顺利通过,酒店的工人不得不把通向总统套房的门凿宽了三尺。应他的要求,酒店还专门在他的房间里配备了一套五星级饭店专用的肉类切片机。帕瓦罗蒂对经理解释说,他每次出门都带着意大利家乡小镇特选的肉,有了这家伙他就能随时为自己准备一顿美餐。演出当晚,主办方专门为他在人民大剧院的后台安装了一部国内最先进的液压升降机,这样他就可以直接从豪华汽车到达舞台,他甚至还提出从后台到前台的步行距离最多不能超过二十步。老帕的确是老了,由于年龄和体重的原因,舞台上的帕瓦罗蒂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他自始至终都坐在钢琴后面没站起来,每唱完一首就得停下来,歇歇气,喝上两口农夫山泉。据专业人士说,“开场的那几首,老帕偷懒了!”还有人说,“他在《今夜无人入眠》最后的高音C上降了半个音”。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李白)终于亲眼目睹了老帕的风采,当“高音C之王”的最后一个高音在天际消失后,李白相信,所谓的天籁之音已在这个世界上绝迹。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少数几个幸运儿之一,他见证了珍稀动物的灭绝。
演出结束了,老帕乘着他的豪华轿车走了,带走了这个城市所有的鲜花和掌声。他们被孤独地掷在人民大剧院门口涌动的人海里。一般情况,“他们”指的是四个人:李白,马拉,黄皮,毕大师。四个男人就好像是马拉那辆又破又脏的“7086”的四个轮子。但这次,很显然,“他们”得指五个人,四加一,另外那人是赵四小姐。“赵小姐姓赵,是赵钱孙李的那个赵”。反正张楚就是这么唱的。“7086”就停在剧院不远处的狗不理包子店门口。他们都不想回家。那个高音C把他们弄得很沮丧。跟它比起来,李白的后后现代诗是狗屎,马拉的先锋小说是狗屎,黄皮的“驴行天下”论坛总盟主是狗屎,毕大师的“江南根雕毕”是狗屎,赵姑娘的“草桥县第一女高音”应该也是狗屎。还有那个今晚要回的窝,明天要亲密接触的生活,都是他娘的狗屎。今夜无人入眠。今夜当然不应该这样草草收场。有人提议去府山的星子峰亭喝茶,但马上被否决了:这种天气上山,喝西北风还差不多。最后决定去根据地酒吧喝酒。李白、黄皮和毕大师都没车,他们习惯坐马拉的“7086”。赵四小姐本来开了一辆车来,他们让她挤挤得了,她也就上了马拉的副驾驶座。
根据地门口有个白胡子的外国老头在迎接,都意外。赵四小姐说,你们不知道吗?今晚是平安夜。是吗?老帕可真会选时间。“欢迎光临,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欢迎光临!”柜身里外的服务生都戴上了尖尖的圣诞帽。快乐就像禽流感,身处这暖洋洋的童话王国,哪怕白痴,哪怕外星人也会被感染。四个男人一块鬼混了这么多年,还从没在一起过过平安夜呢。加上还有一个女人。加上这个女人又漂亮。加上她的漂亮又是建立在高雅艺术的基础上。
啤酒上来了,烟点着了,天开聊了,于是他们就跟着傻乎乎地快乐起来。赵四小姐开始不肯喝酒,但终于还是喝了。赵四小姐开始不肯抽烟,但最后还是抽了。其实她能把满杯啤酒干得不留泡沫。其实她的烟圈吐得比毕大师都漂亮。这个城市太小了,小得连隐私也像厕所一样是公共的。其实他们对她都有足够的了解,之所以一次次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缺少的仅仅是一个认识的机会。这个机会就像干啤酒前必需的那个启瓶器。酒精和尼古丁能让软掉的鸡巴变硬,也能让僵硬的舌头变得无比柔软。那个“高音C”早已被那辆狗日的豪华轿车接走。泡沫在暗暗地扛着他们,男人们一个个又重新变得牛逼轰隆。
啤酒在一打一打地上来,烟缸在一次次地撤换,客人在一批批地离去。又破又脏的“7086”载着“他们”在高速公路上飞驶。李白,黄皮,毕大师都是其中的一个轮子。加速。加速。他们只有一个念头。
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李白的身体又回到了乱糟糟的酒吧。自己说过什么话,他已经一句都记不起来了。他只记得自己、黄皮、毕大师,一直在说话,高潮迭起,妙趣横生,声音夹杂在背景音乐中,像钓鱼线上的浮子一样浮浮沉沉。但问题是,他们把另一个轮子给忽略了。马拉根本就没说过什么话。他几次拿手机看时间,后来干脆把手机掷到桌上:操!没电了。11点多的时候,他像是找到了一个难得的空隙:“怎么样?喝光手上的酒——”但他的话刚出口,就被黄皮拦腰截断了:“早着呢!今夜无人入眠!”长夜漫漫,长得仿佛没有彼岸。我们都像黄皮一样讨厌那个该死的被窝。于是继续喝酒、抽烟、巧舌如簧。这之后还有过一次机会:音乐停下来,钟声敲了十二下,服务生上来说圣诞快乐,并送上了礼物。但毕大师没给第四个轮子机会,他又抢着拾起了被打断的话题。最后,如果赵四小姐不先站起来,这辆又破又脏的“7086”不知道会奔驰到什么时候。
漫长的聚会终于结束,马拉提前把车靠到了人行道边,于是商量谁先谁后。毕大师像是有点心事,他说,你们开路吧,我走回家。他的家就在根据地对面不远。于是剩下几个人上了车,赵四小姐还是坐了副驾驶座。李白照例是第一站。按路线第二个应该是赵四小姐,因为她的车还在剧院门口。黄皮是最后一个。车子启动后,赵四小姐说,这么晚了,你们谁总得送我一下吧?自然,这话除了毕大师,他们都听见了。赵四小姐在城郊的一所中学教音乐,好像在跟家里那位闹离婚(也有人说早已经离了),反正就一个人搬出来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后来李白就下了车,他只知道,那个时候“7086”里还有马拉、黄皮和赵四小姐三个人。
2.毕大师
毕大师横穿过马路回家。从空调间出来,闷头闷脑一阵冷风,胃里的酒就泛了上来。喝了多少百威?不知道。在看演出之前,他还赶了场婚宴,攒了半斤高度烧的底。酒从胃里泛上来,他压了几次,到底还是压不住,于是撑在路边的墙上开始呕吐。吐的时候,毕大师想,胃真是了不起,居然可以装这么多的东西。吃啊喝啊的时候,人们并不记得有个胃,但现在当胃开始反抗时,人们终于想起了它。胃就像女人。
毕大师继续沿着人行道走,大街上很安静,半天才有一辆小车甲虫样驰过。人行道踩上去轻飘飘的,像铺了一块块带条纹的橡皮。再转个弯,家就到了。但毕大师回不去,他已经有半年多没回家了。自从有了那个女人之后,不,应该是自从老婆知道他有了那个女人之后,他就再没回过家。那个女人欢迎他上床,但是却不允许他过夜。女人在床上很撩人,但床上是床上。干完活后,不管多迟,女人都会撵他出门。“你把婚离掉再说吧。”女人说。现在她好像只会说一句话了。以前可不是。以前她的话很多。女人在绣衣坊开了家时装店。毕大师在她门口等人,没事就转悠进了店里。“你长得像一个人。”女人说,嘴里磕着瓜子。“像谁?”毕大师不看衣服了,开始看她的脸。“说了也白说,反正你又不是他。”声音跟瓜子一样脆,跟人说话并没有影响她磕瓜子的速度,瓜子从嘴里进进出出,她的牙齿忽隐忽现的,很白。“你认识他?”毕大师问。“不认识,电视上见过。”女人说话有一搭没一搭的,也没拿正眼瞧人。后来,毕大师的手机响了,他等的人正在橱窗外给他打电话。毕大师从架子上挑出件衣服,付清钱,就扭头出了门。女人从里面追出来:“嘿,你的衣服。”毕大师朝她笑笑,掷了一句话,“那个人送给你的。”后来他们就上了床。她知道他是有妇之夫,这在上床前似乎不是个原则问题,但现在忽然是了。
毕大师吃不准该不该去找她,就去摸兜里的手机。他想看看时间。但手机不见了。
丢哪了?脑子里雾腾腾的。在酒吧聊天时好像接过一个电话,记不清是谁的,但手机八成在酒吧。毕大师离开那摊巨大的呕吐物,开始往回走。吐完后,脑子清醒多了。这半年多来,毕大师几乎碰不得酒杯,一碰就醉。醉了之后就落东西。挎包啊钥匙啊手机啊外套啊,什么都落。就差头上那脑袋了。当然,还有脑袋上的那顶帽子。全城的人都认识毕大师那顶帽子。帽子在脑袋就在。艺术家嘛。别人都这么说。只有毕大师自己知道,这事其实跟艺术不沾边。他戴帽子只是为了遮盖脑瓜上的头发。头发每天都在掉,已经稀拉得不成样子。每次面对镜子,毕大师就会恐慌。他觉得自己正在一天天地老去。这跟年龄无关,但跟创造力有关。“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的疲惫。”这句话李白经常在念叨,好像是他崇拜的哪位诗人的诗句。李白当然只是无病呻吟,但毕大师觉得用在自己身上却是那么的确切。曾经(像李白一样年青时),毕大师对自己的才华是那么的骄傲和自信。但是现在,他的骄傲和自信躲在帽子底下,已经所剩无几,并且每天还在流失。他已经再也离不开那顶帽子了。那顶帽子是什么,是他曾经视为狗屎的所谓的荣誉,全国美协会员,省民间文艺家理事,国家一级画师,民间工艺大师,等等。
在坐过的椅子上,毕大师找到了手机。有两条新短信。一条是在外地寄宿制学校读高中的儿子发来的。“老爸,圣诞快乐!”另一条是女人发来的。“别过来了,我睡了。”看得出来,儿子很高兴。这么晚了,他还在外面跟女同学鬼混吗?也看得出来,女人不高兴。生活中充满了矛盾。女人跟儿子就是一对矛盾。儿子暑假回来摔断了腿,他必须去医院看护。但他之前已答应女人,当夜陪她去省城进货。他狠狠心掷下儿子去了省城。女人要求他离婚,想想儿子,到底还是下不了手,于是只好有上顿没下顿地拖。
女人跟帕瓦罗蒂也是一对矛盾。女人想跟他过平安夜,虽然没说,但他知道。他当然不想让女人不高兴,但是他更不想错过老帕。平安夜明年还有,但老帕就要告别艺术舞台了,就算不告别就算他再唱一百年一千年,他也决不会第二次来这个狗屎样的小城。说实话,在认识马拉之前,毕大师根本就不知道帕瓦罗蒂。当然更不知道什么歌剧、咏叹调、连续9个高音C和《今夜无人入眠》。但问题是他后来认识了马拉,更为严重的是,他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坐马拉的“7086”。刚开始那段时间,搭马拉的车是他最怕的事情之一。当马拉把车钥匙插进去后,一个吊嗓子的男人立马就会钻出来,直奔你的耳朵。吊嗓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男人的嗓子一直吊着,上去,上去,再上去,千辛万苦地,终于等到他下来了,下来了,这下总该着地了吧?可是颤一颤,他又上去了,上去上去再上去。毕大师根本就没听到他在唱些什么,他只看到一根喉管被人从嘴里吐出来,一截一截又一截,长得无穷无尽,长得无休无止。就在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的时候,马拉会靠近他的耳根跟他唠叨说:这是意大利的谁谁谁,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与谁谁谁和谁谁谁齐名,擅长演唱谁谁谁和谁谁谁的歌剧,某某某几项歌唱大奖得主,某某某主题歌的演唱者,复活了欧洲的传统古典歌剧,作为意大利美声唱法的一座高峰,至今还无人能逾越,等等等等。马拉唠叨起来时,毕大师真想一拳头把那个喇叭砸碎,他真想立马往车窗外跳,他对自己说,够了够了,这是最后一次。但问题是,毕大师一直没买成只属于自己的可以由他决定听不听帕瓦罗蒂的小车。于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搭乘马拉那辆又破又脏的“7086”去野营,去爬山,去骑马,去唱歌,去参加各种莫名其妙的酒会晚会宴会和文艺沙龙,然后一次又一次地听凭那个该死的帕瓦罗蒂来践踏他的神经。但人是一种最犯贱的动物。后来,慢慢地,毕大师中了毒。先是耳朵被收卖,接着心脏也里通外国。上了“7086”如果听不到帕瓦罗蒂,毕大师就会骨头发痒,身体发软,像做爱时隔了只安全套,再怎么捣腾也进不了状态。再后来,在“7086”上听听已经不杀瘾,毕大师跑遍草桥县大大小小的音像店找来了所有跟帕瓦罗蒂有关的带子。
现在,帕瓦罗蒂居然来了,毕大师怎么可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别说一个女人,就是一卡车女人拦他也没用。
老帕要来演出的消息,本地媒体提来半个月就开始炒了。各种小道消息层出不穷。据说帕瓦罗蒂这次全球范围的巡回演出除了“告别艺术舞台”的意义之外,还有一个现实原因。5年前帕瓦罗蒂和前妻阿杜瓦正式离婚,为此他付出了高额的分手费,之后帕瓦罗蒂一直存在着经济压力,举办这次全球巡演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刚刚两岁半的女儿。读这则花边新闻时,毕大师就想起了一句话:女人都差不多,男人都一样。这话是以前写先锋小说后来改写畅销小说的女作家皮皮在一个访谈中说的。八十年代时毕大师曾经看过她的一个短篇叫《全世界都八岁》,于是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这句话应该跟一个叫马原的男人有关。据马拉说,马原也是个作家,跟皮皮一块在西藏呆过,名气比皮皮大得多了。其实,有名气没名气,男人都一样。帕大师就没比毕大师好到哪儿去。在跟前妻离婚之前,老帕一定也像老毕一样举步维艰过。但最终老帕做出了抉择(这是他比老毕伟大的地方)。可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居然到这种鬼地方来演出,想想都让男人心酸。如果老毕做出抉择,那么他要承受的,除了经济上的压力,还有良心的谴责。草桥县的人都知道,在结识领带老板刘玄德的宝贝女儿刘美丽之前,毕大师只是一个整天在街头游荡的小混混,除了裤裆里那根鸡巴和一肚子自以为是的才华,毕大师一文不名。“我欠着那女人,没有她我早就死了。”这句话毕大师已经跟其他三个轮子说了很多遍,醉了就说。
演出的票子,黄牛们很早就开始炒了,票价一直像垃圾股一样在涨。但是毕大师做了决定,再怎么高也得掏腰包去买一张。算是一个可怜的男人支持一下另一个可怜的男人吧。让人没料想到的是,马拉居然弄到了票。“老是让你们听带子,这回让你们见见老帕。”马拉说话的神情比发表就职演说时的县长还牛比。那段时间,毕大师、黄皮还有李白天天都争着请马拉下馆子、泡歌厅、洗桑拿,谁都生怕马拉一不高兴反悔。演出当天的早晨,毕大师还在被窝里,收到了马拉的短信:“晚上七点半,剧院门口等。别迟到。关掉手机。”于是,事情越加变得郑重其事起来。
那晚毕大师破天荒提早十分钟到了剧院门口,在出租车上他真的关掉了手机。可马拉在门口已经等急了:“怎么这么迟,别人早到了。”剧院的灯光已经暗下,四个轮子顺利在座位上会合,但是轮子中间夹了个女人。开始毕大师以为那女人是黄皮老婆。黄皮老婆叫倪萍,草桥县著名的钢琴师,开了家琴行,业余带着帮孩子。她当然配听老帕。按照国际惯例,演出一半中场休息。灯一亮,毕大师才发觉,那女人不是倪老师。毕大师认识赵四小姐。草桥县那么小,都算是文艺界有头有脸的人,难免不时凑在一块。但李白、黄皮与赵四小姐显然不熟,马拉在忙着介绍。赵四小姐来看老帕,当然也配。但是马拉把她和他们捣腾到一块来,毕大师还是有点纳闷。女人是女人,朋友是朋友。水乳不相容。这是毕大师的原则。
家回不了,女人那又去不成,毕大师就只好回他那冷飕飕的根雕毕工作室了。工作室刚刚新搬到草桥县艺术村里面,离酒吧有三四站路。街上的出租车已经很少,毕大师就沿着官河路慢腾腾地走,边走边回头瞅过往的车。
毕大师结果是走回去的,他一直没有拦到的士。在中国银行门口的石狮子底下,他倒是看见了一个乞丐。像只狗一样缩着,似睡非睡。不知道为什么,毕大师经过乞丐时,仔细地看了半天,好像在看一块刚买来的树根。
回到工作室,毕大师泡了包方便面,又从破纸箱里找出那床棉被。木沙发很硌腰板,棉被已经有点霉味。毕大师就想到了那个乞丐。他好歹还像只狗,可我连只狗都不如。这样一想毕大师就有点酸。但毕大师很快就睡着了,还做起了梦。他梦见自己在太阳底下晒棉被,棉被被支在那把藤椅上,怪兽一样贪婪地吸纳着冬日暖阳。他又梦见一帮工人七手八脚地在工作室给他安装空调。空调,空调,他想这狗日的空调已经想了一个冬天。
但是后来,振铃声把毕大师的美梦给搅黄了。手机不知放了哪,半天才摸到。铃声一直在响,就是老帕的那首《今夜无人入眠》。毕大师没看号码就接了,他以为是那女人。
谁知不是。
“你睡了?”对方说。
“早睡了!”毕大师没听出是谁。
“你们喝酒了?”对方又问。
“喝了。”毕大师还是没听出声音。
“马拉喝得多吗?”
“马拉?”毕大师听出来了,是李警官。
“他到现在还没回家!”李警官说。
毕大师从床上蹦了起来,他的酒醒了一半。棉被完了,空调也完了。“马拉喝多了吗?”在酒吧时,他只顾着自己喝,根本就没留意马拉。糟了,马拉还开了“7086”。
“你打他手机了吗?”
“一直关机。我刚才还打了李白,无人接听。你几点回的家?”
“我离开酒吧应该是12点多吧。”
“你们晚上不是看演出吗?”
“对啊,去看老帕。”
“看完演出后去喝酒了?”
“喝了!”
“去哪喝了?”
“根据地!”
“哪几个人去了?”
“就我,马拉,李白,黄皮。对了,还有一个女的!”
“女的?谁?”李警官的平静露了馅。
天,女人——赵四小姐。毕大师的酒终于彻底醒了。该死的马拉,干嘛偏偏要追求水乳交融呢?但问题是,他已经说漏了嘴。马拉怎么可能喝醉酒呢?凭他的酒量,凭他的性格。这么多年真是白混了!李警官是刑侦大队的业务骨干,据说草桥县那桩著名的“2830”连环杀人案就是她破的。警察就是警察。通话一开始,她就掌握了主动权,先用酒误导你,然后顺藤摸瓜。
“我不认识她。看演出时她正好坐我们旁边,有可能不是跟我们一块去的吧?”毕大师开始补嘴。
“喝酒她也去了吧?”馅又包了皮。
“去是去了,不过,好像是李白邀请她的。”毕大师开始撒谎。
“他喝了这么多酒,还开车。是他送你们回家的吧?”李警官可真沉得住气。
“我没坐他的车,我是从酒吧走回来的,我的家不是离根据地近吗?他们怎么回的家我也不清楚。”毕大师觉得这一句不能算撒谎。
“你睡吧,我再等等看。”李警官就挂了电话。
毕大师看了看时间,凌晨2点35分。看来事儿闹大了,怎么办呢?一个轮子打滑,就得靠其他三个轮子补救。赶紧跟黄皮通个气吧。按常理,应该是他最后下的车,只有他信息最全面。但是电话占线,李警官已经先了一步。再试着拨马拉手机,是一个电脑小姐的声音: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黄皮
凌晨3点差5分的时候,黄皮开始起来穿衣服。他的嘴里嘟囔着。穿一件就嘟囔一句:我真倒霉。因为习惯裸睡,所以冬天他穿起衣服比谁都复杂。
“为什么是我?”黄皮说,他找到了内裤。
“他们凭什么可以呼呼大睡?”黄皮说,他穿好了保暖内衣。
“人家老公丢了,为什么要我去找?”黄皮说,他开始拉牛仔裤的拉链。
“活该!”倪老师说。倪老师半躺在床上看书。黄皮从酒吧回家时,她就这样坐着。黄皮从卫生间冲了澡出来,她也这样坐着。黄皮躺下睡觉时,她还这样坐着。她连个姿势都没换,那本书在她弓起的膝盖上一页都没翻动。“还没睡?”进门时黄皮问她,她没回答。“太迟了,睡吧。”冲完澡黄皮跟她说,她也没回答。黄皮就倒头自己睡了。半夜三更黄皮被电话吵醒。翻个身起来,发现倪老师还菩萨一样坐着,连电话都没接。黄皮火大了,但终于还是忍了。黄皮不想吵架,这么多年过来他已经吵够了。电话通了很长时间,是李警官打来的,说是马拉失踪了。黄皮是最后一个下的车,下车时“7086”上只有马拉。但赵四小姐的车跟在后面。马拉说他再送一下赵四。那时应该是凌晨1点差一刻。李警官打来电话时,黄皮看过时间,是2点35分。马拉送赵四得送2个小时?以前黄皮只知道马拉与赵四很熟,他曾在马拉的办公室见过赵四两次,另外还凑巧撞见过马拉跟赵四单独在咖啡馆。也就朋友吧。老夫老妻一屋子关那么多年,香炉对着蜡烛台,审美疲劳了,跟另外的异性接触接触,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黄皮就有不少这样的异性朋友:一个在殡仪馆上班的高复班同学,一个大学刚刚毕业对黄皮崇拜得要命的超级嫩驴,一个QQ名为“百分百处女”的加拿大籍网友,一个在健身房认识的骨感得需要增肥的单身少妇。平时发发短信,能见的偶尔找个机会见见,不能见的网上打打情骂骂俏。说是普遍朋友吧,似乎要暧昧得多,说是情人吧,当然没到那个份上。不是挺好吗?寡淡了,想放纵一下,可以跨出去一步两步;觉得过了,踩地雷了,又随时能收回脚。当然,这一切都是瞒着倪老师的。也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只是觉得没这个必要。但是接了李警官的电话之后,黄皮就有了另外的想法。所以,他开始在电话里给马拉补漏洞。他说他回家也就半个小时,他说去看演出再喝酒也就四个男人,他还说马拉会不会把车停在路边休息,因为马拉真的喝了不少的酒。挂了电话后,他马上打了马拉手机。关机。于是他就开始穿衣服。他得找到马拉。撒了谎就得把谎给圆上,这事没谁逼他,但是也没谁会替他去做。这期间,倪老师依然没吭声。黄皮给牛仔裤拉拉链时,她终于憋不住,于是骂了句活该。
“别人老公丢了你会去找,自己老婆丢了你还不一定会去找呢。”倪老师说。
倪老师一开腔,黄皮就松了口气。他不怕别的,就怕老婆一声不吭。最多一次,倪老师三天三夜没吭声,黄皮都快被她逼疯了。黄皮当然清楚老婆这次怄气是为了什么。倪老师知道老帕来草桥,倪老师也知道他们几个去看了老帕。黄皮当然想带老婆一块去。但是该死的马拉只给他一张票。黄皮不心痛那几个钱,可如果去给老婆再买一张,马拉的脸面就会过不去。黄皮很想跟老婆说明白这道理,但老婆不提这事,他无从启口啊。老婆现在说话了,本是个解释的机会。但黄皮现在没时间了,他必须先找到马拉。
“你先睡吧,回头跟你说这事。”黄皮就出了门。
在去车棚拉自行车时,黄皮的手机响了。是毕大师打来的。黄皮马上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忘了还有另外两只轮子,该死!果然,毕大师已经提前把他给出卖了。当他自作聪明地在电话跟李警官撒那些谎时,李警官一定在冷笑。“你怎么这么笨啊,你应该立马给我打电话啊。”黄皮真是火大了。“我是放下电话就给你打啊,可还是她抢先了一步,谁叫她是个警察啊?”毕大师在电话里很委屈地申辩。“好了好了,我去找人,你睡你的大觉吧。”黄皮啪的关了手机。黄皮拉了自行车呆在车棚门口。事情已经被越搅越混。还有再去找马拉的必要吗?开始是怕马拉有事,所以他才撒谎。而现在,马拉即使没事,也已经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在李警官眼里,我们都是一丘之貉。那么,就这样回去睡觉,让马拉去自作自受?万一的万一,马拉真没干坏事,只是酒喝多了车子出了事怎么办呢?
我一定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人。这样嘟囔着,黄皮终于还是拉着自行车出了门。
让黄皮没想到的是,不知什么时候,天上已经飘起了雪。看来,连老天爷也被好心人黄皮给感动了,于是给了他一份意料不到的礼物。黄皮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有看到雪了。“你们这帮蠢猪都睡吧。明天起来雪就会融化。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今年的圣诞节曾经下过一场雪。”于是黄皮就高兴起来。
但是黄皮高兴得太早了。先是从家里出发,沿着医院路,过东桥,再顺着307省道,找到赵四的学校。没人,也没车,只有满天飞舞的雪花。再从赵四学校出发,顺着环城路,过西桥,穿长春路,找到马拉家门口。没人,也没车,只有满天飞舞的雪花。雪越下越大,黄皮越来越冷,出门时他忘了戴帽子和手套,手僵了,脚木了,耳朵冻没了,落到他的项颈里的雪开始融化,并慢慢向下蠕动。现在,他早已看烦了雪,他只想把这份礼物连本带利送还给老天爷。一路上黄皮都在不停地打电话。先是给马拉打,一直关机。后来就想到了给赵四打。赵四的手机没关,音乐一直响着(居然也是那首《今夜无人入眠》,老帕来草桥的消息传开后,把手机铃声换成这首男高音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一直无人接听。不会真出什么事吧?第三趟,黄皮是从马拉家出发,沿江滨路,过剡湖桥,经医院路,找到人民医院。看了所有的急诊病房,问了所有的医生护士,都说没这号人。
赵四小姐为什么不接电话呢?如果她在睡觉,那么就是死人也被吵醒了,哪个死人受得了帕瓦罗蒂的嗓门?那么是因为她不熟悉我的号码。不会吧?她以前不是偶尔给我发短信吗?节日问候啊,稀奇古怪的成人笑话啊。
那么是因为她与马拉在一块?他们还在鬼混?在她宿舍的床上?在他或她的车上?或者在雪地上?对,一定是在雪地上。赵四说,我很冷。马拉说,我会让你热起来的。于是他们开始在雪地上忙乎。怎么做呢?躺着?坐着?或者站着?应该是站着吧,至少马拉是站着的。而赵四就挂在他的身上。脸对着脸,双手圈住马拉的脖子(马拉的脖子是足够粗壮的),叉开修长的双腿。只要找到支点,即使马拉站着,她也照样能骑到他的身上。对,赵四穿了条裙子。这个时候,裙子比裤子可方便多了。赵四说,我的手机响了。马拉说,别理它。马拉微微曲了曲腿,大腿就贴着了赵四的屁股。赵四说,我的手机又响了。马拉说,一机不能两用。马拉又向下蹲了蹲,支点的活动余地更大了。赵四说,我的手机又响了。马拉说,管它呢,别忘了我的手机还在通话中。马拉的马步功夫很好。这点黄皮知道。
黄皮开始给赵四发短信。我是黄皮。发送。知道马拉在哪吗?发送。他老婆正找他。发送。我跟她说。发送。四个男人看演出。发送。喝酒。发送。说他。发送。酒喝多了。发送。可能。发送。在车上休息。发送。
他们不冷了,他们早已做得汗水淋淋。黄皮却摔了一跤。人摔了个狗吃屎,自行车的链条也掉了。从雪地上爬起来时,黄皮的手机响了。很意外,是赵四!老帕没影响他们,但是,气喘吁吁的短信把他们给吵醒了。也许按照国际惯例,他们正好中场休息。
“不会吧,他把我送到就走了。你都找了?学校也来过了?你找的是前门吧?我学校有两个门,他是从后门走的。”赵四小姐说,听不出气喘吁吁的迹象。
于是黄皮开始跑第四趟,从医院出发,重新沿医院路,过东桥,顺307省道,一路找到赵四的学校。路上,黄皮还给马拉家打了个电话,求证马拉是否在他找的时间段回了家。因为完全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赵四撒了谎,他们一直在一块,只是没功夫接电话,后来事完了,马拉走了,于是赵四才得空回话。雪已经积了起来,自行车在黄皮背后留下两条很不规则的麻花小瓣,但在黄皮面前,马路像一张白纸,什么车辙,连一个浅浅的野猫的脚印都没有。
就在黄皮快要彻底绝望的时候,感谢上帝,他看到了一辆小车。那车子就停在学校的后门口,只露了个屁股。黄皮抖擞精神,脚底加加劲,把自行车踩了过去。
但是非常遗憾,那不是马拉的“7086”。黄皮只是个药剂师,不是魔术师,他没办法把一辆白色的现代跑车调包成马拉那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
4.马拉
我很想跟赵四上床。从认识她的第一天起就想。
你们不想听从前的事,你们最关心的是那个晚上,那我就直接说那晚上的事吧。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说清。我真的一点都没把握。
黄皮下车后,赵四的车子就超了上来。超过去时,赵四拉下车窗跟我说过一句:跟着我的车。于是我就跟着她的车。她把车子开得很慢,我跟在后面,一直保持着50米左右的距离。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几点了,我想看看时间,但是我的手机没电了,喝酒那会就没了,这个你们知道。我车上的表也坏了,这个你们也知道。于是沿医院路,过东桥,再顺着307省道跑,一路上没碰见一个人也没碰见一辆车。狗娘养的夜晚安静得就好像只剩下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后来就到了赵四的学校。赵四的学校有两个门。正门就在307省道边上,早已经关了。我们走的是后门,走后门得转个弯再走200米路。路的一边就是学校的围墙,另一边是一条灌溉渠。路是水泥路,不宽,碰到车技差的,两车交会有一定难度。后门的铁栅门像是坏了,黑嘴洞开。赵四跨着门停下车,把头从车窗探出来:“你回吧,没事了。”我说:“不急,送佛送上天”。反正外面也倒不了车。我对自己说。就没点别的蠢蠢欲动的念头?不瞒你们,有。我就跟着赵四的车进去了。进去是一个操场,赵四的宿舍在操场另一边。
赵四把车子停进一个自行车棚,走过来了。
“你回吧。”她说。
“不急!”我说。
“你不会想把我陪上楼吧?”她说,声音有点夸张。
“你需要我就陪啊。”我说。
“你要真陪我上去,那我可就不让你下来了。”赵四说。
发动机没熄火,借着车灯的光能隐约看见赵四的脸。我得说实话,赵四说那话时很迷人。当她以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时,总是很迷人。我们平时发短信,她回复很快。有次我夸她:你打字的速度真快,服你了。回复立马就过来了:我也有慢的时候,你会更服。那短信的确让我想入非非了。她在车灯下说那句话效果更理想。你们面前我就不说假话了。
“你要这么说,我可真陪你上去了。”我说。这是真心话。我挺想跟她上楼,然后上床。
但没等她回答,我的嘴立马又补了一句:“不早了,你上去吧!”
我的嘴有时并不听我使唤。相比之下,它似乎更听别人的,比如我老婆。它知道什么时候该踩刹车,这一点很像我的脚。我的嘴不想给她回答的机会。于是,之前的话变成了很有分寸的戏谑。
她挥挥手进了楼。楼梯的灯亮了。一会儿,三楼的一个窗口亮了,再一会儿,楼梯灯熄了。
就这样,我蠢蠢欲动的念头熄了,你们等待的好戏也收场了。我不得不像往常一样,掷掉烟蒂,拉上车窗,松开手刹,踩下油门,方向盘死命一打,让“7086”在操场划出一条漂亮而又伤心的圆弧,离开了学校。
我知道你们很失望。其实我比你们更失望。
我刚才说了,我很想跟赵四上床,从认识她的第一天起就想。但问题是,我从没跟她上过床。我连她的一头发丝都没碰过。以前没有。那个晚上也没有。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疑问。你们的疑问就是我老婆的疑问。这么多年来,上帝给过我很多次机会。每次都是这样,我把边鼓敲得很响,但是该把那层纸捅破时,我的手指头就软了。我怕什么呢?我当然怕老婆,但这不是主要原因。如果让你们跟一个警察在一张床上睡二十多年,你们也会在侦破中学会反侦破。我觉得我就是《手机》里那个费老。“左思右想,右思左想,最后改在茶室坐而论道。”像费老一样,我也怕“麻烦”。我不就请她看了场演出吗?结果呢?
不过,我想跟你们说的,不是这些。从赵四学校回家,我不可能开上三四个小时的车。我回家后看过时间,凌晨4点差10分。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发生在后面那几个小时的事。但我必须先说前面这些。只有相信了前面这些,你们才有可能相信后面的事不是我编的。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说清。我真的一点都没把握。如果连我自己都没信心,那么我又怎么能期望你们相信它呢?
那个晚上,你们(包括我老婆)认为我跟一个女人在一块。
事实上,我一直跟一个男人在一块。
我还是继续从头说吧。
就在我刚刚打了转向灯准备转出校门时,一辆车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它开了锃亮的远灯,简直是在朝我撞过来。我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对方到底也踩了刹车。我以为撞上了,但是没有。双辆车像公牛一样对头对脑地顶在一块,估计中间最多也就插一只打火机。
那个人下了车,没关车门,一步一步朝我走来。
你们一定猜到他是谁了。兄弟们,你们跟我想到了一块。
当时,我的脑子有点蒙。跟一个女人上没上过床这种事,你说三言两语能说清吗,尤其是跟她的丈夫?
我下意识地跟着下了车。但我把车门关上了。你们知道,我有这习惯。
在我的车屁股后面,我们迎面遭遇了。借着车灯的光,能感觉他的个头比我小,像是理了个平头。但我来不及看清他的脸。因为对方的拳头已经过来了。
我的右下颌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
很爽。真的很爽。
他没跟我废话,这挺好。
他的拳头告诉我,他受过专业训练。他的拳头还告诉我,他是个左撇子。这也很好。
容不得我多想,他的右腿已经朝我跨下踢了过来。对那个晚上来说,这是最最重要的一脚。如果我没有躲开那一脚,那么可能现在我就没机会坐在这里跟你们喝酒了。是的,我侧身躲过并撩到了他的脚,顺势一掀,他重重地摔到了地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漂亮的鲤鱼打挺,他的拳头又影子一样跟了过来。
雪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下的。你们看见那晚的雪了吗?太美了。当然,作为当事人我那会没心思欣赏雪景。
是的,那个晚上我太想跟人干一架了,是谁不重要,棋逢对手当然更好。要知道,我还从没跟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左撇子交过手呢。我的斗志被激了出来,但我的手早已生疏。你们看见过我书桌墙上挂的那对拳击手套吗?它已经结满了灰尘。幸亏我们还在驴行野营,夏天骑骑马,冬天裸裸泳什么的。深挖洞,广积粮。果然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他的攻势很猛,有点急于求成。我基本取守势,防守加反击,因为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雪越下越大。夜静得出奇。我们就像两只斗得难解难分的斗鸡。他的长处是身体比我灵活,腿功好,拳脚配合密切。估计除了拳击他还学过散打。我的优势是气长,内力还行,块头又比他大。所以,除了开始时猝不及防外,后来我就没再吃什么大亏。虽然我身上的落点比他多得多,但后来他落到我身上的拳脚已经越来越不让我觉得爽了。
我们的嘴都闭得紧紧的,自始至终都没说过一句话。这一点挺好理解。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对他来说,事实就摆在那里,已经用不着问了;对我来说,什么都没干过,又有什么好解释的呢?对。后来我跟我老婆就是这么解释的。
他忽然停了下来,回身朝后车厢走。我有点慌,他去拿什么呢?刀啊棍的?我想到了自己座位底下的那把军刀——那刀你们不是看见过吗?是我上次作家节从龙泉买回来的。我该去拿出来吗?我说了,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有名无实地死在一个所谓的情敌手上。其实,即使我想拿也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拿出来了。
他没拿刀也没拿棍。他翻出了一瓶矿泉水。
他开始拧开盖子朝嘴里倒水,头上雾气腾腾的,像刚揭开的蒸笼。我的口更渴了。
他看看我,再次回身朝后车厢走。
他朝我走过来,把另一瓶矿泉水递给了我。
是农夫山泉,小瓶装的,就是帕瓦罗蒂在演唱会上喝的那款。
我有点羞愧,为自己想到刀啊棍啊什么的。接过那瓶矿泉水时,我真想说声谢谢。我当然没说。我很清楚,谁先开口谁就会落个下风。但我的确很意外也很感动。如果换个场合相见,我想我跟他一定会成为朋友,甚至兄弟,就像我跟你们一样。因为我们有一样的口味,比如小瓶装的农夫山泉。你们知道的,如果我的后车厢里有水,那么一定是农夫山泉,因为我喜欢他们那句有点甜的广告词,而且还是小瓶装的。谈到口味,你们一定会说,也不仅仅是矿泉水啊,还有赵四呢。他喜欢赵四,这跟离没离婚没有关系;我也喜欢赵四,这跟上没上床也没关系。对,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但这一点我没跟我老婆说。
接下去的事我也没跟我老婆说,但我必须跟你们说,否则我会死不瞑目的。
他喝光矿泉水,把空瓶掷到雪地上,我也跟着掷掉了空瓶。
他拍了拍衣服和头发上的雪,这个动作是多余的。我也跟着拍了拍身上头上的雪,我的动作当然也是多余的。
几点了?我的手机早已没电。
雪还在继续下。寒气像蛇一样笔直地从脚底朝上钻,我的斗志由冰化成了水,下颌也开始隐隐作疼,我已精疲力竭。我想他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重新开始吗?继续打下去吗?
我不知道。当时我挺想抽根烟,或许他也挺想。于是我就去车里拿香烟。你们都知道我把香烟放在哪个位置。拿烟时我顺手把音乐开关拧高了,这次我也没关车门。
帕瓦罗蒂的嗓门破窗而出。荒唐,又是那首该死的《今夜无人入眠》。
但是,且慢。
我突然被镇住了——当老帕熟悉的嗓门传入耳朵。我想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个。醍醐灌顶。也许就那感觉。听了这么多年的帕瓦罗蒂,可那一刻,我成了个白痴,就觉得自己是第一次听到帕瓦罗蒂。以前所有的感觉和记忆都被抹去,我听到了根本不可能是从喉咙里出来的声音。可那不是喉咙里出来的声音又是什么?不知道,反正我他妈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搞不懂这是为什么。对,可能跟那晚的雪有关。也许,还跟那一架有关。说真的,那一架来得太及时了。我挺感激那个理平头的先出左拳的小个子男人,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搞清他是不是赵四的丈夫。
他是谁的丈夫真那么重要吗?
对,那晚的结局就这么平淡。打完架后,我们在一起抽了根烟,之后,就各自掉头回家了。
(选自《收获》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