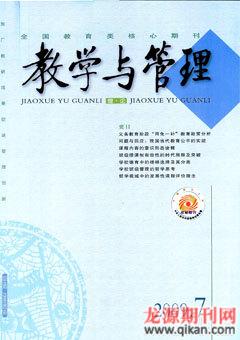课程内容的意识形态诠释
徐 卫 范会敏
课程内容是系统的知识和经验的体系,这是比较公认的观点。现实中很少有人会把课程内容与意识形态联系到一起,因为在人们已成定势的思维方式下,课程内容所承载的知识往往是中立的、没有偏见的,出自其中的东西往往被视作真理的化身,很少有人去怀疑它。但课程内容并不是通常所描述的那样,实际上它是主流阶级的权力、意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体现和象征,是一种官方知识,是一种法定文化。没有一个国家的课程内容能够脱离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渗透,没有一个国家的课程内容不或明或暗地反映某种意识形态。因此,只有把课程与课程内容放回到更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之中,才能揭示出课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内在机制。
一、意识形态界定及特性
意识形态在哲学词根上最早是培根创造的,而最先使用“意识形态”这一词的则是法国思想家特瑞西,原意是“观念的科学”。真正对意识形态有系统研究的是德国思想家曼海姆,之后又形成了三个流派,但对意识形态的描述仍纷繁复杂,有文化学视角的,也有哲学视阈的。综合各家所言,意识形态多涉及观念或价值体系以及相应的行动。在我国比较流行的是把意识形态与政治伦理联系在一起,看成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受到社会文化影响的有关世界和社会的观念体系,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哲学、道德、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思想观点,是指导人们实践、行动的思想准绳或纲领。它具有如下特性。
1综合性和实践性
之所以说意识形态具有综合性,是因为在观念分析学派看来,意识形态不仅在形成上是一个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度结构、主体的主动意识等相互作用的多样态过程,而且从其内容上看,也表明意识形态是一个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总是与一定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不存在超越现实生活的形而上学式的意识形态,它总是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联系,充分体现权利集团的意志和利益,并借助一定载体,体现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阿尔都赛甚至将其与物质实践相提并论,把实践界定为将一定的物质资料加工成产品的过程,这样,实践就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实践,还包括理论实践、政治实践、科学实践、意识形态实践等等。
2认知性和冲突性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也具有认知特性,简单地说,任何认知活动都是在某个理论框架内进行的,其过程渗透着各种主观因素,其中包括认知主体的世界观、理论观点、文化修养、个人经历等。这一点当代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感觉渗透理论”或“理论负荷论”有较为具体的阐述。正是由于主观因素的介入才使得认知活动具有能动性。同时,由于意识形态是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观念或价值体系,因此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便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虽然有一致或相似之处,但更多地是具有对立性和冲突性。
3虚伪性和无意识性
“虚伪性”是一切意识形态所固有的普遍特性。霍克海默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无不斥责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公开的谎言”、“大众的欺骗”和“集体性迷惑的工具”,把虚假性和欺骗性看成是意识形态的本质性特征。从本质上看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分裂与异化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主要功能是美化现实生活,替现实辩护。人们对他们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是不能选择的,很多时候是理所当然地接受并去适应,且往往把主流意识形态所界定的真理观接受为真实的真理。把那些道德原则视为不可违逆的。
二、课程内容的双重本质
1课程内容的知识本质
从严格意义上讲,所有的课程都离不开知识,所以课程内容内在地就表现为一种知识体系。通常,被纳入学校课程中的文化,俨然如真理的化身,备受信奉。但一经分析就不难发现:所有“知识”都不是中立的,而是带有社会偏见的。知识的构建总是为社会中某些人的特定利益服务的。在一个国家,并非所有社会集团拥有的知识都能进入课程,只有统治阶级的知识才能成为课程内容,也就是说,课程内容反映了社会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学校如何选择、组织各种种类的文化和符号资源与阶层化的社会需求的、规范的、概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辩证关系。”所以,课程内容本身就具体地体现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控制的重心。意识形态不仅控制着社会所认可的知识的范型,而且控制着知识的具体内容。任何一种知识,无论其社会价值和本体价值有多大,要想成为课程内容,必须符合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满足其社会控制的目的,否则很难或根本不可能进入学校课程。
2课程内容的社会本质
在人们已定势的思维方式与理念中,出自教育的东西常常被视作真理而不容置疑,课程所传递的文化也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公平与正义的同义语,人们很少去怀疑它,也不相信教育及课程所传递的文化会有什么意识形态偏见或不公正及不平等的因素、特征、机制与作用。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种效果或效应,即通过教育或学校课程所传递的文化最容易使人们接受,因而成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利分配、知识分配、角色分配的最有利手段。它也最容易使人对政治盲目服从,丧失独立的意识与观念及怀疑、批判、反抗的精神,所以学校的实质是社会对年轻一代实施控制的主要工具。统治阶级总是力图通过控制学校课程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从微观领域来说,社会控制的主要方面在于课程内容的控制。因此,课程内容就其社会本质而言,是社会控制的中介。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确为什么在特定社会的知识总体中,某些部分能成为课程内容,而另外部分却不能成为课程内容。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定这样的现实:有的内容是“中性的”,超时代、超阶级的,看不出特定的意识形态的特征,如数理学科,甚至是语文这样的学科,也有这类内容。关于这种现象可以作这样的解释:首先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具有越来越多的“共性”,这也是“全球化进程”的反映。其次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教材中的有些内容虽不一定“充分”或根本不反映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们肯定与这种意识形态不相抵触,否则不可能进入课程。从本质上看,课程内容还是社会对其未来成员加以控制的中介。
三、意识形态与课程内容的关系
1意识形态决定课程内容的选择标准
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称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决定着课程内容的选择标准。一般而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作为社会规范的、合法的。全体成员必须遵从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因而,它往往是引导课程专家思想法定的、唯一的意识形态,他们决定哪些人能进行课程编制、进行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的选择标准要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服务,正如阿普尔所说:“学校知识体系——接纳或排斥某些内容,通常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目的,因而正式的学校知识体系能成为一种社会和经济控制的形式,因为它们
保存和分配了被知觉为‘合法的知识——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所必须具有的知识,并且作为课程内容选择的首要标准在课程规定中得到反映。”因此,不同的社会制度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也会不同。也就是说,学校经常基于某些特定的标准,选择、采纳或排斥某些教材或知识内容。在古代社会,等级制鲜明,由于受教育者在身份上具有高低贵贱之分,课程内容则伴随着所承载的课程目标及功能的差异而被赋予了“获得性”的价值差异,原本同为人类认识成果的知识在被择为课程内容后便具有了“规定性”的“尊卑”、“显微”之异。因此,在古代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的思想中,关于学校课程内容选择的原则观念无不呈现出等级制的特点。
诚然,我们也不否认,有些课程标准往往看起来不是仅仅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出发的,似乎它是依据社会发展需要来定的。例如塔巴根据学校的社会功能、社会需要、知识和学科的性质,提出了六项课程选择的原则,其中位列一、二的是:内容的有效性和重要性,与社会现实的一致性。我们并不否认课程内容选择原则有的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也不否认有些原则客观上也反映了“社会现实”或“社会需要”,但一经分析便不难洞察其中蕴涵的意识形态性。可作参考的“社会现实”一般是统治阶级认可的“主流社会现实”,即社会现实的主流方面,而基于这一“主流社会现实”之上的“社会需要”则是统治阶级认可的“社会需要”。即使是依据“社会现实”或“社会需要”来对课程内容进行筛选,这些“现实”或“需要”也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的特征,反映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需求”。
2意识形态对课程内容的过滤与渗透
从历史发展来看,尤其是在等级制社会中,课程往往直接“取材”于社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学校课程的目标、内容具有决定作用。如从19世纪在英国出现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仍未完全消失的双轨制教育传统中,课程的社会意识决定性便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贵族阶层所接受的英才教育、绅士教育很少关心课程的实用性,而古典语言如拉丁语、希腊语及古典人文学科却如同“尊贵”与“风度”的象征而倍受崇奉。
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最初的课程(当时主要是教材)内容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有所改编,有所排斥,而且多排斥了有关生产经验的知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社会学者看来,从现象上看,很早就进入课程的知识符合统治阶级或优势集团的价值取向,因而备受其青睐而获选,那些迟迟未进入课程的知识(有关生产经验的知识)则不符合他们的价值取向。这一“筛选”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控制。意识形态对课程内容的过滤首先具有欺骗性,它掩盖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实际情况,而使每一个阶层的孩子都能接受现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合法化的解释;其次它以剥夺或选择提供不同“文化资本”给不同社会阶层学生的方式重建社会现存阶层结构;最后,通过不同的学校知识带去不同的个人气质和身份意识。
课程内容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是其所主导的知识的缩影。课程内容是传统阶级意识形态进行阶级关系再生产的载体,同时也是经济与文化上的权力群体与希望课程知识更能反映自身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普通阶级之间冲突的结果,而且课程知识往往和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相联系,透过课程内容可以瞥见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在阶级、种族、性别和宗教等方面的做法和主张。由于社会的变迁,教科书中所呈现的知识发生了变化,展示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反而视之,从教科书内容的价值取向的变化也可以透视社会变迁的一二,同时也可揭示教科书内容的“惰性”和教育的“滞后性”,更可反映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在教科书内容中的影射。
3“文化霸权”与课程内容
意大利学者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通常以两种方式实现其对整个社会的主宰和支配,其一是强制,即指军队镇压、警察拘禁、法律制裁等;其二是认识与道德方面的引导,即让被统治者同意、相信、服从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法律制度等,而且这两种方式都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前者一般被视为国家的镇压机器,而后者被葛兰西称之为“文化霸权”。课程作为“文化霸权”主要是指课程的法理化、教化机制,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控制进入课程领域的文化因素与范畴,其二是控制个体对社会文化的态度。其实质是一种原则性的限定,使课程不仅仅是一种权力控制、意识形态控制的手段,而且本身就是作为一种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象征而存在的。事实上,学校课程对文化的传递,从指导思想的确定到内容的选择与组织,都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属性,是一种政治性行为。人类知识的产生、形成,不仅与利益相连,而且受已有社会结构的制约,课程对知识选择的过程就是“文化霸权”的确立过程,也是对某种利益及社会结构的选择过程。课程内容与其说是社会文化的反映,不如说是对社会文化的政治解读与过滤;与其说是人类历史积累的精华与结果,不如说是特定社会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意识形态重构的产物。课程发展的历史表明,课程从来都是统治阶级权利、意志、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体现或象征,从来不曾有什么“公共文化”所构造出的“公共课程”。而任何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经济文化无不体现出专断、强制的本质属性,即霸权性特征。课程史揭示,课程内容并不是知识的“镜式”反映,课程对于知识发展状态的响应取决于统治阶层的意旨,取决于权力,这一点,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形态都是相似的。福科认为,“任何教育制度都是维护或修改话语占有以及话语知识和权力的政治方式,教育用它掌握中的知识和权力,无非是在形成具有思想原则的群体,无非是在散布和占有话语。”纵观教育实践史,尽管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政体和不同的权力运行方式,但国家对于教育知识的控制则主要有支配权力和隐蔽权力两种形式。
参考文献
[1]吴永军,课程社会学,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M·w·Apple,Ideology and Curriculum,NewYork,1990
[3]郝德永,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4]郝明君,靳玉乐,课程结构的意识形态诠释,当代教育科学,2005(18)
[5]吴康宁,“课程内容”的社会学释义,教育评论,2000(5)
[6]李静,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释,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3)
[7]李刚,教科书的意识形态分析,淮阴工学院学报,2004(4)
(责任编辑付一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