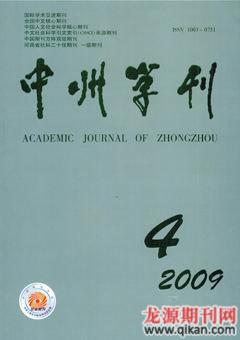木斋词体起源及发生研究之反思
欧明俊
摘 要:论词体起源与发生,首先需界定清楚并合理使用“词体”、“起源”、“发生”几个重要概念,这是论证的“前提”。木斋先生明确论断:词是配合法曲而非燕乐的歌词,词体发生于盛唐宫廷而非民间,李白词是词体发生的标志,皆是对近百年词学界盛行的主流观点的“颠覆”。这些观点新颖深刻;但要令人信服,仍需进一步充分论证。词体起源与发生研究,众说纷纭,不少问题皆应认真反思。
关键词:词体;发生;李白;木斋;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4—0203—04
木斋先生最近有系列论著,就词的起源与发生问题提出新见,如《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等。其中新见迭出,多“颠覆”性的观点,新人耳目。笔者拜读后,有一些疑问,也有一些想法,极不成熟,这里提出来,就教于木斋先生和学界方家。
一、词体起源及发生与音乐的关系
论词体起源与发生,首先需界定清楚什么是“词”或“词体”?什么是“起源”和“发生”?这几个重要概念是论证的“前提”。“词体”是指音乐的歌词,还是诗体的律词?这是有区别的。词体初始阶段,乐因辞生,辞随乐行,乐、辞共生一体,不分先后。词体的雏形是歌词,是调无定格,句无定式,字无定数,韵无定声;成熟的词体是律词,是调有定格,句有定式,字有定数,韵有定声。如带着“前理解”,心目中先存有“律词”概念,这概念本身即是词体演变的结果,是词体“衍生态”概念,而不是“原生态”概念。不应以“衍生态”词体观念解释词体起源及发生。
“起源”与“发生”,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起源”包括渊源和胚胎,只是“祖宗”、“父母”,不是自身;“发生”是指词体的产生过程,强调一种长时性、动态性,而“产生”只是一时的、静态的。历代论者论词的起源及发生,所用概念甚多,如渊源、肇始、兴起、发轫、鼻祖、胚胎、孕育、滥觞、萌芽、权舆、雏形、诞生、形成、成立等,内涵不同。词体演进可比喻为河流,如长江,最远源头是沱沱河,在东流过程中,又汇集了众多山涧之水,便形成长江。汇入长江的这些小河流,皆是长江之源。长江源头是一源,又是多源;论词的起源,亦应作如是观。词体起源是一源,又是多源。多源,不是平均,有主次之分,有主源和非主源。有远源,有近源;有直接渊源,有间接渊源。有内源,有外源;内源即作为音乐与文学自身之源,外源即外部文化环境。有音乐之源,有文学之源,还有文化之源。有民间之源,有宫廷之源,有文人之源。应做全方位的考察,不应只强调某一方面而否定其他方面。
论者站在音乐立场,词就是流行音乐的歌词,词体起源及发生,就是所配音乐的起源及发生;站在文学立场,词就是新体格律诗,就是律词,律词的起源及发生,就是词体的起源及发生。律词是“衍生态”的文学之体,是成熟的词体,不是曲子词的起源和发生。不应将“起源”当做“发生”,亦不应将“发生”当做“起源”,历代不少论者多混为一谈。
词体是“类”概念,抽象概念,总括此类文体。词体是由众多具体的词调构成,词调才是“实体”的词;应从词调入手论词的起源及发生,即哪一或哪些词调是最早产生的?那就是词的起源及发生。
木斋先生明确论断,词体发生的音乐原因,“是盛唐之后经过法曲变革而形成的新曲子”;“影响词体发生的音乐因素并非燕乐,而是隋代初唐燕乐的对立物法曲兴盛的结果”①;词是配合“新清乐”的歌词。由此推论,词体发生于盛唐宫廷。这是对通行的“词是配合隋唐以来兴起的燕乐的歌词”观点的“颠覆”。窃以为这一观点要令人信服,还需先论证词与燕乐确实没有关系,或说明法曲与燕乐究竟是何关系?通行观念,词是配合隋唐以来吸收胡乐新成分的时代音乐燕乐的歌词。“燕乐”概念有广狭之分。隋唐时,广义燕乐实际上也包括清乐。在使用燕乐概念时,宜用狭义概念,即与清乐等相对应的概念。我们要思考的是,词体起源,究竟是一源还是多源?词究竟是配合燕乐的歌词,还是配合清乐或法曲的歌词?燕乐和清乐或法曲有没有可能都是词所配合的音乐?
论词体起源及发生,首先应讨论词的“母体”。衍生态的律词,是从音乐蜕变而来,还是从乐府诗、近体诗蜕变而来?如从音乐蜕变而来,又是何种音乐?曲调又是如何转化为词调的?转化机制是什么?
论词体发生只谈音乐是不够的,还必须谈文学因素。木斋先生认为:“就词体的文学建构因素言,是糅合偏取乐府诗的杂言以成长短句,熔铸近体诗的格律而为词律。”②词体发生与乐府诗、近体诗究竟是何关系?历代论者多认为曲子词是从古乐府演变而来;又有论者认为词与近体诗之间是“母子”关系。张炎《词源》卷上云:“粤自隋、唐以来,声诗渐为长短句。”③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如太白之《清平调》,即以被之乐府。太白《忆秦娥》、《菩萨蛮》,皆绝句之变格,为小令之权舆。”④汤显祖《花间集》序云:“古诗之于乐府,律诗之于词,分镳并辔,非有后先。有谓诗降而词,以词为诗之余者,殆非通论。”⑤也就是说,词体发生及演进,与近体诗发生及演进是共时并行的,这又如何理解?
二、李白词与词体起源及发生的关系
木斋先生强调,真正能作为词体产生标志的,应该是李白天宝初年的宫廷应制词。李白宫廷应制词“确为百代词曲之祖”,李白是词体发生的奠基人。研究李白词与词体起源及发生的关系,首先要弄清两个问题:一为真伪问题,一为是否词体问题,应对历代李白词真伪讨论充分“体认”,认真梳理。这两个问题是进一步论证的“前提”。前提如有问题,建立在它上面的结论便是不可靠的。
讨论李白词真伪问題,当时人的记载最重要。木斋先生据以立论的《清平乐》、《菩萨蛮》、《忆秦娥》,李白自己没有说明,其家人和友人也没有记述,李白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无人提及。如真是李白所作,为何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尊前集》中最早收录《菩萨蛮》,真伪难辨。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的记载,本身的真伪就值得怀疑,后人以其为证据,结论亦不可靠。《忆秦娥》一词,崔令钦与李白交往密切,《教坊记》中却没有记载;现存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中也没有收录。北宋李之仪作有《忆秦娥》,调下自注云“用太白韵”,这只能证明当时已有此《忆秦娥》词,已传为李白所作,但不能确证为李白所作。南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选录李白《菩萨蛮》和《忆秦娥》,并认为此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后人多以黄昇观点为推论“前提”;黄昇的依据何在?亦值得怀疑。
我们看“肯定论”者的论证是否无懈可击。有论者由《菩萨蛮》词调产生年代入手,论定该词是李白所作。他们详尽考证,论证崔令钦《教坊记》中已有《菩萨蛮》词调,说明盛唐时已有此词调,以证明李白创作此词。这一推论无法说服读者,《教坊记》中所载曲调,多后人添加;所记《菩萨蛮》曲调,本来即值得怀疑,即使当时已有此调,并不能证明李白就创作此词;《教坊记》中有此调,并不能证明盛唐文人创作此调;即使盛唐文人都创作此调,也不能证明李白创作此调。退一步说,即使《教坊记》中其他词调皆是李白所作,也不能证明李白创作《菩萨蛮》,何况《教坊记》中此调也未必就是词调。
有论者从李白才情和词作风格入手,认为只有具李白那样的才情才能创作出佳词。黄昇云:“按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⑥黄昇以有无“清逸气韵”作为判定李白《清平乐》四首真伪的标准,完全是主观臆断。李白作品是有“清逸气韵”,但有“清逸气韵”的并不一定就是李白作品,“清逸气韵”并不是李白的“专利”。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二引杨绘《本事曲》说《菩萨蛮》:“其词非白不能及此,信其自白始也。”⑦认为只有李白才能写出如此好的词,《菩萨蛮》是李白创制的,依据何在?即使李白创作此词,也不能证明是他创制了词调。木斋先生认为,以风格而言,《菩萨蛮》、《忆秦娥》也断无晚唐五代人所作之可能,别的不说,只“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阔大气势,便是晚唐五代人所难以企及的。此词眼光阔大,正是盛唐之音的词体表现,而这种眼光境界、技艺手法,非太白难以企及也。木斋先生将此二词解读为典型的李白风格,认为只有李白这样的个性才能写出,他人无能写出,论证似欠充分。其实,此二词并非李白的典型风格;即使是,也不能证明为李白所作。“时代风格”不是绝对一致的。盛唐有似晚唐者,晚唐亦有似盛唐者。具体作品风格的个体差异性甚大,同一时代作者的作品,风格不同;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风格也不同。作品风格的形成,有创作背景、具体情境、作者个性等复杂因素。对同一对象,同一作品风格的理解,也因人而异。“时代风格”只能作为判断真伪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标准。因此,以“风格”论真伪,是靠不住的。
即使肯定此二词为李白所作,还应论证盛唐李白之前词体发生情况。既然李白创作出如此成熟的词作,就说明在他之前,词体已有一段发展过程,逐渐成熟。敦煌曲子词中,有隋及初唐词作,皆在李白之前;又有唐明皇御制曲子《献忠心》。高国藩认为,词体成熟于盛唐开元十三年以前实行的府兵制时期。⑧那么,此后李白的词作只是更成熟,而不是词体“发生”。如何看待李白以前和同时的词人词作在词体发生中的作用呢?李白的作用是不是有些“放大”了?
李白词真伪问题,牵涉到词史的真伪。词体发生的时间界定、词史的原生态与衍生态、词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词史的写法,对研究词史意义极大。《菩萨蛮》、《忆秦娥》二词,是盛唐李白作品,还是晚唐、五代或宋代作品,皆会“改写”词史。说是李白所作,不是说绝对没有可能性,而是可能性确实不大。即使肯定是李白作品,在史的坐标中,由现存词史资料看,此二词超前成熟,也是“异数”,是词史的“非逻辑”发展。学界过重“逻辑性”,对其史的评价也是不到位的。如肯定为李白所作,盛唐时已有成熟的词作,词史是一种写法。还有许多可能性,比如也是盛唐的作品,但不是李白所作,那么对词史做出重大贡献的就不是李白,而是他人,由此连带的对此词艺术高下的评价也大不相同。如是盛唐以前的作品,此二词的词史意义就更大了。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是晚唐温庭筠所作,此二词置于温庭筠现存六十余首词中,只是其中比较优秀的,《花间集》中也不乏此类作品,此二词的词史意义即很一般;如是温庭筠以后五代人所作,此二词价值又会降低;如是宋人所作,那么其词史意义就极为有限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此二词真伪、时代、艺术评价等问题完全解决清楚之前,词史发展的逻辑线条依然是模糊的。李白词的真伪,李白的词史地位,古今所论,或信或疑,或褒或贬,都只是“可能”,不是铁的事实。因材料所限,李白词真伪讨论可能是永远没有结论的。如不能以“铁证”证其“真”,最好“存疑”。以“可疑的”词人词作写出的自然是“可疑的”词史。词体起源及发生史只是由一些历史“碎片”拼接而成,而不是完整的历史。历史也往往如此,这是我们面对历史时的无奈。
木斋先生认为,李白宫廷乐府诗,多以宫怨思君为题材,以宫廷女性为主人公,风格柔媚婉约,这些要素成为以《清平乐》五首为代表的宫廷应制词的题材、视角和风格,同时,也就奠定了唐五代曲词的题材、视角和风格。这一论断合乎逻辑,但要令读者完全信服,还需先论证李白之前诗歌或歌诗史上从没有这类题材、视角和风格,证明确是李白“首创”;还要充分论证李白宫廷乐府诗与宫廷应制词以及唐五代曲词存在明确的时间先后顺序,构成逻辑发展关系。那么,“唐五代曲词”就不是泛称,而是特指盛唐李白以后的曲词。史实果是如此,又如何解释盛唐以前以《玉台新咏》为代表的宫体诗?南朝宫体诗与唐五代词相似处甚多。如果说《玉台新咏》奠定了唐五代曲词的题材、视角和风格,且材料真实可靠,是不是更有道理?
李白的宫廷乐府诗、宫廷歌诗、宫廷应制词、抒发个人情怀之词,其间究竟存在多大关系?这种“关系”是不是本身客观存在的?是不是李白清楚意识到的自觉行为?这些问题仍需要
进一步论证。
三、“宫廷词”与“民间词”、“伶工词”、“文人词”的关系
木斋先生认为,词发生于盛唐天宝初年宫廷中,而不是民间;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以后才发生的;所谓民间词,可能主要是由宫廷流散到民间的宫廷乐工的作品,应该称之为“伶工词”可能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又是对近百年盛行的“词起源于民间”说的“颠覆”,值得讨论。认为词体发生于宫廷,以前也有学者论及,只是没有如此明确。
首先要界定清楚“宫廷词”和“民间词”的概念。木斋先生认为,“应制词”是狭义的宫廷词;广义的宫廷词,是指以宫廷为中心或是在宫廷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曲词,并强调敦煌词中绝大部分都是宫廷词,而非民间词。作者使用的广义宫廷词概念,把不少文人词甚至民间词也包括进来,模糊了“宫廷词”与“文人词”、“民间词”的区别。实际上,“应制词”只是宫廷词的一部分,它是宫廷词概念下的子概念,宫廷词中“非应制词”也有许多。敦煌词中是有部分宫廷词,但这“宫廷词”是“广义的”。将表忠心的或歌功颂德的皆视为宫廷词,扩大了宫廷词的外延,实际上已包含了部分“文人词”和“民间词”,这样反而造成了概念上的模糊。“宫廷词”概念,如界定为宫廷中创制的以宫中生活为内容的词作,似更合理。
木斋先生论证,中唐德宗朝始遣散宫中乐工、伶人,流向民间,顺宗、宪宗朝又一次大规模遣散宫廷乐工,民间词始兴。不论是词乐还是曲词,都应该是由宫廷而向民间,而不是相反。此观点如成立,必须首先说明中唐以前民间词状态。有无民间词?如果有,情况如何?宫廷词又从何而来?是宫廷内部产生的,还是从前代宫廷承传下来的?李伯敬认为,词起源于六朝宫廷和文人乐府。⑨有无道理?宫廷词是接受胡乐改造已有本土音乐而成的,还是由民间采集加工而来的?笼统看,词本来即是配合宴享之乐的歌词,因此,可说词发生于宫廷。问题是,还需先证明盛唐宫廷词制作与民间词没有任何关系。由敦煌曲子词及现存史料看,中唐以前民间词的创作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有成绩的,又如何看待?只有证明中唐以前确实不存在民间词,词体发生于宫廷而非民间的观点才能真正成立。事實可能是,宫廷乐工、伶人流向民间后,提升了民间词的品位,推动了民间词的创作,扩大了民间词的传播。但这只能说明是宫廷词对民间词的影响,是词体“发生”以后的事,并不能说明词体不是“发生”于民间。
“民间词”有不同内涵,使用时需注意:1.相对于宫廷而言,宫廷以外的,都是“民间词”。2.相对于士大夫文人词而言,没有身份、功名的词人的词即为“民间词”。3.相对于具名文人,“民间词”指无名氏词;无名氏词人,只是姓名无传,有的是真的“无名”,有的则是姓名散佚,才情可能比具名文人更高。“民间词”概念与“文人词”概念存在交叉,“民间词”中的优秀作者,本来就是优秀的“文人”。
“乐工”与“民间”究竟是何关系?木斋先生认为,如没有宫廷中乐工流散到民间,便没有“民间词”。也就是说,“民间词”只是宫廷词的延续,实际上就是“伶工词”。这种观点是否妥当?
《旧唐书》卷三十《音乐志》云:“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⑩“里巷”即指民间,而绝非宫廷;而“里巷之曲”发生于李白天宝作词之前,这如何解释?
词体发生阶段,必定是众人即“英雄”和“人民”共同创造。宫廷中君主臣僚、乐工伶人和士大夫文人贡献尤大,因为只有宫廷、政府才能组织统一规范的音乐歌词制作;“方言”的民间词,传播有限。宫廷自上而下,影响民间;民间亦自下而上,影响宫廷。宫廷与民间及文人之间,是互动影响,绝不是单向影响,只是影响程度上有差异,不应将其对立起来。
木斋先生认为,唐五代曲子词可称“宫廷之词”,其本质特性可概括为“宫廷文化”。这一论断,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合理的,但不能绝对化。因为宫廷文化在任何时代都是“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宫廷文化”,势必“遮蔽”了民间词和宫廷以外的文人词对词体发生的贡献。
注释
①木斋:《宋词体演变史》,中华书局,2008年,第7页。
②木斋:《略论词产生于盛唐宫廷》,《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
③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55页。
④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500页。
⑤汤显祖评:《花间集》卷首,明万历四十八年刊朱墨本。
⑥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四部丛刊景明本。
⑦高承:《事物纪原》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
⑧高国藩:《敦煌民间诗词中的府兵制与词的起源问题》,《许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86年第1期。
⑨李伯敬:《“词起源于民间”说质疑》,《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
⑩刘昫:《旧唐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86年。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