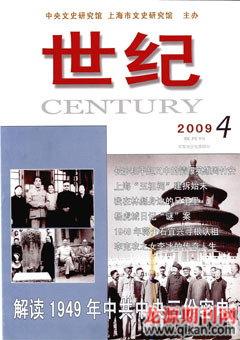走笔散记陈虞老
蔡 平
一、开场白
陈虞老者,上海新闻界前辈陈虞孙也,从1953年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起就任副馆长。今年是他乘鹤西去的15年。他在1938年入党迄到亡故时,已是近6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解放前他曾任国民党《浙江日报》总编,1941年又在上海《文汇报》任副总主笔;同年在杭州因暴露身份,逃亡上海重新入党,并任地下上海市委文委负责人。我们初识,是在1951年,当时他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他做起报告来很生动而且没有稿子。我记得很深刻的是,他在大会上批判《新闻日报》一位副总编、经济学家娄立斋时说:在解放前,你写过不少经济评论,笔头很健,倚马可待。而现在,你写的既少,且无生气,何以故?你可以以此为主题反省、检查之。这位经济学家听了心境舒畅,他做了深刻的检查后,以沐浴、理发自我祝贺。喜曰:这场浴洗得好!
二、唐振常为虞老立传
在我写这篇散记前,介绍陈虞老的文章不少,其中名记者、历史学家、电影《球场风波》的作者唐振常的大作可说把虞老写活了。读其文,虞老的声容立见之,立闻之,乃至可以闻到他的一呼一吸,精彩处不禁拍案叫绝,可称作虞老的外传也。而我这篇散记不过是续其尾,当作拾遗补缺吧。
我这篇散记,着重刻画虞老在奉贤新闻出版社“五七”干校的言行录。此时虞老已被揪出戴上“叛徒”、“走资派”的帽子,正过着被侮辱、被损害的日子。用他自己的风趣话:“我是过着华盖运也。”然而,他的风格、个性依旧,昂然不屈,话带讽刺幽默不变。他的书法极好,还忙着为革命群众写批判报、大字报。出工时,时见这位老人背着锄头踏着碎步去田头出工,这形象迄今不忘。
三、癞蛤蟆为虞老解闷
按照最高指示:“老弱病残除外”,陈虞老是可以不参加“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然而还是来到干校。也许出于“好心吧”,老人孤独的被留下看守茅屋宿舍。因为是茅屋,癞蛤蟆就会常常堂而皇之的在地上爬行。凄凉的老人也就以它为伴,两眼直盯着它爬行的动态,几乎忘乎所以了。就在这片刻间被休工回宿舍的革命群众发现了,就要他交代,何以对癞蛤蟆如此“多情”?老人答曰:无他,无聊也。
一位极左的人物,也是虞老一手提拔的人批他说:“不对,你是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翻天,想翻案!……”于是这场现场批斗会,搞的声势浩大。这个左派人物也就得其所哉,得到工宣队的表扬:有水平、立场稳!
这场闹剧终于不了了之。批斗后,虞老黯然地回到宿舍对面的半隔离的小茅屋中时,见到我一个人独坐在那儿,他就气呼呼地说:“虎落平阳被犬欺也。”我低声地慰藉:何必这样气愤呢?谁错、谁对,明眼的人是会理解的。无限上纲就是极左派人物的专长嘛!虞老接着说:“这我明白,此人人党时,我曾同他谈过一次话:‘现在是和平期间与战时不同。战时,无论在战场,还是在白区,那是要经过出生入死的考验的。而今,对一个党员的考验,只能依赖党性觉悟了……。”
“现在此人不是露出自觉的党性了吗?——政治投机”。他凄然笑日:“是呀,是呀!我是自得其咎。严格地说,我应向党负罪,还值得反思的是,我喜爱奉承嘛!”
此人已故,我就不想点其名了。“四人帮”粉碎后有人揭发他在“文革”中的种种劣迹时,听说他大哭一场。
四、父子相见戚然无声
陈虞老有七个子女。唯一的男孩是幼子,前六个都是千金。显见虞老的“传种接代”的传统意识还是很浓的。有句笑话,他自嘲地说:“非生一个男孩,决不罢休。”果不其然,幼儿终于出世了。
在虞老潜心默教的影响下,孩子显得很出色,中学毕业后就考进了“哈工大”。大约就在他毕业那一年,匆匆回上海探亲,时已知其父被打倒了,所以又匆匆地来到干校探视父亲了。而干校当局者并没有让他们父子单独会见,而是在众目睽睽的茅屋大宿舍里。在这样的场面下,父子除了称呼外,只能默默无言了,只能用父子双目的关注来替代了。父亲的冤屈,儿子的探望都只能在沉默中,在目光中去理解了。这真是无声胜有声呀。
好在儿子一回家,他的慈母当然会与之解释:其父所遭受的打击,叛徒呀!走资派呀!……
“四人帮”粉碎后,虞老很快就被解放、平反。在此时,虞老还在锦江饭店举宴向亲朋好友相互致意,并兴意盎然地把宠儿向宾客一一介绍:“他已在中共福建省委工作了。”几年后,我因公出差到福州,虞老这位宠儿还到我所住的招待所看望我。
五、林彪九·一三事件的传达
1971年10月间,我们“牛鬼”与革命群众一起在上海度假后,就在徐家汇集合乘大卡车返干校。第一件新鲜事是:上海空四军派来的军宣队不见了。第二天,革命群众就集中大礼堂听取工宣队头头的紧急传达。我们“牛鬼”是“靠边站”。但还是听到了从礼堂中发出“打倒林彪”的口号声。其实,回上海时的我们已听到小道消息:林彪出事了,乘机叛逃并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了。听到了口号声,这小道消息也成现实了。我们这些“另类人物”是分批传达的,虞老和我是最后一批。传达后,还要我们谈感受。记得虞老以语录答日:“假的就是假的。”
这几天,陈虞老吸烟吸得很厉害,一支又一支地抽,并自言自语地说:“天报应,天报应!”其心情似乎很沉重:为党担忧也。我曾劝他,少抽点。他幽默地说:生产牌嘛!八分钱一包。抽与不抽,随心所愿。不想抽,就可以不抽。弃之不足惜,解闷也。我也向他幽默一下:“回上海,你一定抽高级烟吧?”
“不行,不行。现在只拿生活补贴,只能抽‘大前门。”
六、令人反感的违心之论
解放后,不断的运动,人际关系很紧张,到了“文革”期间更紧张了:一怕株连,二怕横祸从天而降。好友成为陌生人。索性被打成了“牛鬼”,相互之间倒有真言粗语。
虞老在“文革”前,总是领导运动的领导人。要认识他的本心。就更难。在运动中,他或是板着脸,或是弹眼落睛训斥人,甚至发出令人难堪的违心之言。记得1957年“反右”期间,举行了一次揭发批判座谈会。《新闻日报》一位陈姓党员同志在交待“白蕉素”一案时说,他推行治疗肺病的“白蕉素”是取得中央同意的——指国务院“九办”。这时陈虞老就插言:是哪个中央:菲律宾?美帝中央?这就言过其实了。然而我评说是违心之论,倒不是“奉承”他,而是经过观察的:一是亲身体会;二是据他自己的文章。
先说亲身体会吧。“反右”一结束,虞老就从上海市文化局代局长调任《文汇报》总编。在他的倡议下,《文汇报》和文化局合编一张副刊《戏剧周刊》。当时我处在右派边缘还没有作出结论,在半靠边的情况下,他却点名由我代表报社,与文化局何慢共同负责编辑。有一次发生了一场风波:何交给我一份文化局艺术处长撰写的评论稿,并要求下期刊出,而我看了稿,则认为要修改。他随即去了虞老的办公室告了我一状。虞老听了,火冒三丈说,此人还在翘尾巴。随后就要文艺组负责人转告:要我立刻去他办公室。我也就拿着原稿奉命而去。虞老看完稿,不但没有指责我,而是苦笑一声:“你回去吧。看稿这一关还是要守牢。”他这种对事不对人的工作风格,怎能不使我敬佩。其二,在“四人帮”粉碎后,他写过一篇大文,对“反右”期间的报纸,作了深刻的评述:蛮不讲理,声势吓人。(大意)此文受到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的支持,要他继续写。这说明他对“反右”是有异议的。前面的违心之说,也就有所依据了。
七、老年痴呆乘鹤西去
“四人帮”粉碎了,虞老也随之“解放”了,很快就被任命为新建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编辑部总编。这是一项全新的学术工作。好在他是老马识途,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他很忙碌,不时要上北京总社联系工作。“大百科”总编是姜椿芳,他们是老战友。虽忙,只要他在上海,我还是不时造访,他非常信任我。我在彻底平反后,就担任《辞海》新版的国内外的新闻条目编辑。主编是陈虞老。他把有关印章交给我。两手一拱说:“代劳了。”有一次在闲谈中,他告诉我:从长沙来的蒋燕(原上海市中苏友协副总干事)来看我了。我告诉他:她是来上海主办《华国锋主席生平画展》的。有一次我陪着老学长汪培去看望他。因为此公在市文化局工作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二十多年来吃尽苦头。他对汪颇同情。可惜,“反右”时他已不任市文化局代局长了,看到了汪培,他很高兴。汪培改正后,担任黄浦区文化馆的负责工作。这次专访,汪培是特地邀请他出席区文化馆主办的戏曲会演。
自其夫人离世后,他很悲伤。我去慰问他时,他口口声声对我说:我是面临家难、国难呀!不久就病倒了:患了老年痴呆症,躺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我和汪培一起去探望时,问他:认识我吗?他有时呆笑;有时清醒地用家乡话说:认识1
1994-年1月8日,陈虞老两腿一伸默默地走了。是笑着走,哭着走还是梦幻地走,谁知道?没有遗言,没有嘱咐。他一生爱听评弹,而且曾率领上海评弹团去香港演出。但愿老人伴着弦声去向马克思报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