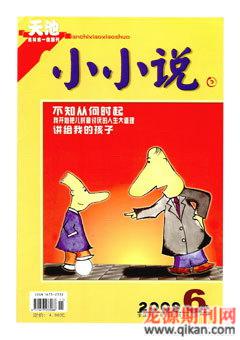煎饼飘香
韦如辉
鸡叫三遍,娘起床摊煎饼。娘要赶在五更之前,摊几张像样的煎饼。
娘摊的煎饼相当有名。公社来干部的时候,队长就把娘喊了去。娘只有一个任务,摊煎饼。娘摊好煎饼,队长给娘记十个工分。在那时,一个男劳力一天的满分才十分。娘摊一次煎饼,能挣十个工分,娘感到十分满足。公社有个麻脸的书记就喜欢吃娘摊的煎饼。麻脸书记酒足饭饱后,回味着娘摊的煎饼味儿,跟队长说,这娘们,手就是巧,她摊的煎饼比红烧肉还好吃哩。所以,麻脸书记每来队里一次,我娘就能挣到十个工分。
娘很少给我们摊煎饼吃,记忆中好像只有一次。爹腰伤的那次。爹一个人翻大车,车很重,车没动,爹的腰却动了。当然,逞强这话是娘擦着眼泪说的。娘嗔怪爹,实际上是心疼爹。爹的腰就是家的腰,就是全家的柱子啊。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爹急死了,爹算了一笔账,在床上三个月,工分就像流水一样从身边哗哗地流走了。就是那一次,娘摊了煎饼。娘摊煎饼给爹吃,娘想让爹快一点儿好起来,娘一次用完了全家半年的计划油。娘摊煎饼的香味儿,弥漫了整个村庄。村里的孩子们聚集在我家的院子里,大人们开骂了还不愿离去。
那回是我第一次吃娘摊的煎饼。爹含着泪往嘴里塞着煎饼,趁娘转身的工夫,把一大块煎饼塞到我手里,低声对我说,到外边吃去。我跑到外边,煎饼的香味也飘到了外边,大黄狗也随我跑到外边。我万般无奈给了大黄狗一砖头。大黄狗夹着尾巴狼狈逃窜,我才狼吞虎咽地吃上那块煎饼。
娘小时候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丫环,娘从小就练习摊煎饼,娘摊煎饼的技术练得炉火纯青。随着时世的变迁,大户人家没有了,娘摊煎饼的手艺一直还保留着。
厨房里已升火,丝丝缕缕的青烟透过不太封闭的窗户透进屋里。爹翻了一个身,咳嗽了几声。
自从娘起床,我一直就没睡。我敢断定爹也没睡。爹翻身的动作拿拿捏捏,似乎怕惊动我的梦。
厨房里开始飘出煎饼的味道。那味道很浓重,把早先进入房间的青烟味儿赶得无影无踪。远处,响起几声狗叫。可能煎饼的味道也飘出院子了吧。在那个初冬的凌晨,霜花已落满干枯的树枝,村边的小路,也该一层层白了。
爹悄悄起床了,点上一支又粗又大的纸卷旱烟吸了一口,差点儿呛得他喘不过气来。爹赶紧用岔开的五指捂住自己的嘴,好让那一声咳嗽慢慢消失。爹有慢性哮喘病,医生让他戒烟,他不听,仿佛烟是他的最爱。
爹把昨天从集上买回来的鞋、内衣和手套装进一个尼龙袋子里。爹很利索地做完这些活儿,厨房里娘已把早晨的活做完了。
隐隐约约地听见爹说娘,哭什么!没出息,儿大还能由爷!
第二天,我带着娘给我摊的煎饼,背着爹递到我肩膀上的尼龙袋,去往新疆的方向。娘在村口哭,爹不让娘送。爹对娘吼,再送,打断你的腿。只有我家的大黄狗,不顾爹的反对,把我送到伸往天边的乡路上。
我把娘给我摊的煎饼撕了一块给了大黄狗。趁大黄狗吃煎饼的时候,我上了一辆从远方驶来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