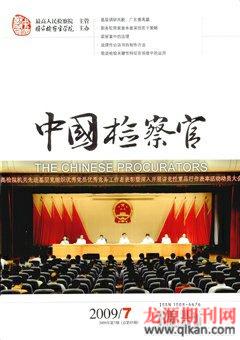梁丽给谁出了个难题
熊 智
参加完《中国检察官》杂志社举办的“梁丽案”研讨后,我陷入一种深深的思索始终没能释怀。也许,梁丽案真的给法界出了道难题。
既然,更多的认识基于本案件所触及到某种社会公德及公共秩序而判定梁丽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继而需要用刑罚处罚的形式予以警示后世。我想,这也许符合法哲学的某些功能性价值判断,特别是当人人都会恐惧“黄金门”行为可能被复制而泛滥成灾,最终必然影响到公共价值的时候,法律的社会功能、预防与矫正价值似乎应当前倾。但是,或许人人都懈怠于对遗弃物的积极作为,甚至漠视,进而导致社会有效资源被刻意置之狼藉的处境时,我们是否还应当思考法律本身能做些什么?抑或法律既有规范能调和些什么?是否可以思考法外评价的某些功能,避免让法律万能化。我们在重塑或维护一种价值观的时候,遴选或确认善恶是我们必须经历的内心刺痛,处理本案也不例外。那么,我们作为法律人以哪一种精神作为价值判断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如果我们确实看到距离法律核心价值的天国还存在空间,而又不能因为等待怠慢了民意或公德所需要法律的现实功效,我愿意选择梁丽之行为的确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倾向去强调法律的另一种价值,即警示与教育价值。所以,科以其较之盗窃罪更轻的侵占罪,甚至,如与会专家提出作微罪不诉或免予刑罚处罚的惩戒,也不失为一种法律智慧的特别体现。然而,我所担忧的是,公权力介入到当前的程序时期,这样的法律智慧真能解决本案件所存在的司法技术问题吗?
梁丽一案到底如何定罪呢?以当下涉嫌构成盗窃罪为据,兼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似乎于理于社会都有个交代,还能为后世例为戒碑。
但是,盗窃行为作为一种结果性犯罪,窃取高达300万元人民的特别巨大公私财物,并构成既遂事实,在刑法上已经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情形,就算是科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也不为过。那么,我们凭借什么对其法外开恩呢!难道仅仅就凭“宽严相济”的四字罚则再加上一个惯常的自由裁量?显然,这样做是有问题的,至少现行刑法规定没有给出这样的参照依据。这样一来,岂不是以牺牲现行法治原则为前提去换取区区一个个案的平息结果?如果真是这样,法的精神无疑再一次遭受践踏,其对法律的破坏程度比起判处梁丽无期徒刑更可怕。
那么,若判定梁丽构成侵占罪,拟请检察机关启动微罪不诉或由法院作出有罪不罚的裁判,也许也能达到息事宁人之功效。
可是,侵占罪在现行刑法里被确立为亲告罪。也就是说,公权力中的侦查与公诉均不宜出现在这个罪名里。从刑事法理论上讲,一般侵占罪是到不了检察机关这个程序的,那就不存在微罪不诉的问题。那么,是否可以寻求法院有罪不罚的司法救济呢?显然,也不可能。作为刑事自诉一方是否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是无法把控的,总不至于为了达到惩罚梁丽之目的,去鼓动所谓的受害人上法院起诉她吧。刑法既然将该罪名确立为亲告罪范畴,目的就是给当事人足够的自由分配诉权的权利,这样的设置,既符合当下和谐精要又符合司法经济的原理。
也许,前述二罪都走不下去了,最后就只有“放人”!简单两个字,却是很难做到的。这样的决定需要司法机关莫大的勇气和胸怀。再说,前后落差的骤然出现,对已经实施的公权力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冲击。人放了,或许民心得到安抚了,但公权力却因草率遭到贬损。
在这样的进退两难之下,使我们突然又寄希望于要是事态还在当初该有多好!要是在当初,我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和智慧来把握本案件各方的前途。
然而,问题也许就出在当初。我们一直有个大大的疑团,作为设置在一个特定环境下的机场公安派出所,在有严密又完善的监控设施之下,第一时间为何不鼓励那个“拾金而昧”的梁丽交还财物呢?为什么要放任其自由控制、处置涉案财物长达一天呢?甚至于后来还欲擒故纵地一直追踪到其下班,继而前后十几分钟之差入室责令“盗窃嫌疑人”交还物品。从深圳机场完善的科学的监控设施来看,这个“盗窃嫌疑人”从一开始都能被监控并被跟踪。我们不解的是,侦查机关把案件引导至今天的情形到底有什么社会价值?还是有更大的司法价值呢?
不管怎样,公安机关既然这样去行使赋予他手中的公共职权,一定是有他的价值追求的。但是,我们想知道这个价值到底体现为什么样的价值,是以最快、最便捷、最安全的方式保护受害人财产为价值前提呢?还是这本身就一种侦查常态?抑或,“盗窃嫌疑人”已是瓮中之鳖,逐之捉之也有一种成就和快感!
沉思本身就是一种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