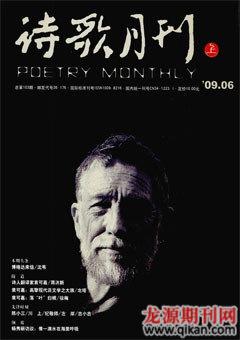袁可嘉:高擎现代派文学之大旗
北 塔
200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参加完卞之琳先生追悼会之后,袁可嘉先生应邀来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那时他已八十高龄,明显老迈,但仍保持着某种莫名的兴奋。在文学馆举足轻重的20世纪文学成就展中,“九叶诗派”占着偌大的版面,袁先生既细看诗友的展品,也看着自己的照片、书影与诗作,感到十分欣慰。随后在与时任馆长舒乙先生会晤时,袁先生先就“卞之琳文库”的建成表达了谢意,说到自己,他谦逊坦言:以个人的文学创作成就,恐怕没有资格建文库,但问能否以“九叶诗派”集体名义建。舒乙当即拍板:“当然,没问题。”这就是文学馆中惟一一个多人文库的由来。后来开库时,由我负责协调,举办了“九叶诗派”学术研讨会。袁先生远在纽约,没能与会,我代他朗诵了他早年的诗作《沉钟》。袁先生始终关心着“九叶”文库的建设。最近,他还从纽约托人带来了《关于新诗与晦涩,新诗的传统》和《茵纳斯弗利岛》等著译手稿12件,捐赠给文学馆。不过,“九叶”文库的设立更多地在于其象征意义。
在文学馆的展览中,“九叶”派与“七月”派虽然篇幅相当、地位均等,但由于受到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九叶”诗派曾长期受到边缘化。如果说“七月”派是现实主义,那么“九叶”派更多表现为现代主义。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被二元对立的时代语境里,“九叶”虽然内蕴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显著的现实主义因素,但还是被划定为现实主义的对立面,长期被孤立、压抑、打击。在我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所使用的指定教材中,“九叶”是缺席的。而如今能为这一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建立文库,尽管是迟到的荣誉,依然显示出时代在进步。
袁可嘉不仅在新诗领域卓有成就,在改革开放初期,更是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热心开拓者。以往大学里,在僵化的教育观念指导下,课堂上老师只能讲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却不能讲当下的实验,不能讲现代主义。所以,当年袁先生主编的皇皇巨著《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不只是一个窗口,而且展现了窗口外的一个世界。在这套书出版之前,我对外国现代派的了解仅限一鳞半爪,阅读这套书时,我有过屠门而大嚼的快感,后来,我又读了袁先生的其他许多论述欧美现代派的文章,我才对西方现代派有了较系统的了解。这对我以后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积极影响。
袁先生思维的开放和敏感是一以贯之的。他不仅写作现代诗,而且重视研究诗论。如果说唐?是是“九叶”评论家,那么,袁先生就是“九叶”理论家。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始终注视世界诗歌潮流,为20世纪40年代关心现代主义的中国诗人,及时输送西方现代主义的新观念、新手法,推动了中国新诗创作的创新。纵观袁先生一生的文字生涯,除了在他不被允许研究、翻译现代主义文学的非正常年代,他几乎一辈子是个现代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