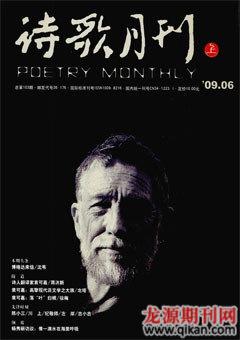新疆:我的天方夜谭
沈 苇/朱又可
朱又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1988年进疆的。
沈苇:是1988年秋天。先是在天池脚下的小城阜康生活了两年,然后到乌鲁木齐,当了10年记者,接着从事专业创作。2000年后,我不用上班了。按我女儿小时候的说法,是“下岗”了。这一晃,就20年了。
朱又可:诗歌写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沈苇:严格来说是到新疆后才真正开始的。大学4年,写了大量失败的小说,到了大四,突然觉得自己缺乏讲故事的天赋,更喜欢抒情性和概括性的表达,对诗歌产生了兴趣,也越来越痴迷。在阜康的两年,写诗是每天最重要的事,在单身宿舍写。去乡村采访也写。那时,写诗是排遣孤独的最好办法了。
我的诗歌起步较晚。80年代校园诗歌几乎没有参与进去。我是90年代开始成长起来的一位诗歌写作者。朱又可:新疆20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沈苇:这20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新疆20年,就没有现在的我。我经常想,如果我不在新疆,又会出现在哪里?此刻正在做什么?想了多次,想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新疆和中亚对我有养育之恩,这是无疑的。我吃新疆的烤肉、抓饭,读《福乐智慧》、《突厥语大词典》,听十二木卡姆,看天山南北好风光……这种养育是身与心的养育,是异常珍贵的异域的教诲。可以说,我的人生是在新疆大地上一点点醒过来的。
有朋友说我的新疆20年是一个“从湖人到胡人”过程。因为我的家乡在太湖南岸的湖州。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我现在是少了三点水的“湖人”,也大概是多了三点水的“胡人”了。
20年过后,我才感到自己与这块土地建立起了一种新的亲缘关系。毫无疑问,隔阂与差异依旧存在,但在异乡建设故乡已不只是一个梦想。我付出了20年时光,也付出了20年的行动。
朱又可:你的诗歌和散文中都写到过“两个故乡”……
沈苇:事实上,我在内心从未真正离开过故乡。20年来,我每年至少要回一趟老家,回到大运河边的小村庄。虽然比不上在新疆待的时间多,但我感到自己更加清晰地看见了童年、记忆和失去了的光阴——我是以离开的方式在亲近故乡。
多年前,我称浙江和新疆、江南和西域是“两个故乡”,现在我感到它们是同一个地方,或者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我的意思是,空间不应构成诗人的囚笼和樊篱。文化的差异性、地域的大跨度往往会给一个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新的造就。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并不少见。
朱又可:你曾说“新疆是以天山为书脊打开的一册经典”。我以为是很精准的。那么请描述一下你心目中的新疆。
沈苇:即使一册煌煌巨著也无法将新疆写尽道完,更何况我简单的勾勒。地理的雄奇和风情的浓郁是她的直接显现,在她有时要虚晃一枪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文明的新疆”。
在一般人心目中,新疆或许代表了地理上的远、景象的荒凉和文明的缺失。然而在我眼中,新疆是丰盛的、华美的、绚烂的。壮丽的风景,神奇的地貌,四大文明的融会,多民族的共居,以及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音等等,都是它可见的基本特征。有人只看到了沙漠戈壁,看到她荒凉的一面,却看不到她骨子里的灿烂。
朱又可:新疆文化还具有一种开放性。
沈苇:对!新疆的文化传统从来不是保守的、封闭的。除却地理和政治上与中原汉地的依存关系,新疆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一种“向西开放”的胸襟和姿态,它能吸纳和融入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这使我们通常所说的中亚传统变得十分宽泛和广博。在新疆的现在时和过去时中,你常能感受到浓郁的印度味道,阿拉伯味道,波斯味道,乃至希腊味道。在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我甚至听到了维吾尔纳格拉鼓似的音乐和节奏。就拿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木卡姆来说,它是新疆维吾尔族与许多中亚西亚国家的人民所共有的音乐遗产。
朱又可:对新疆的表述中有这样两个说法:历史学家说,新疆是地球上唯一的四大文明融会区,地理学家则认为,凡是地球上具有的地貌新疆都具备。
沈苇:所以我称新疆多元文化的共存是一个“启示录式的背景”。它有点像拉美,像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它的文化是混血的、融合的,一点也不土气,反而是洋气十足的。当然更是大气的。如果把新疆比作一本书,南疆和北疆展开了它的页码,沙漠、戈壁、绿洲、群山均是华彩的篇章和段落。
还有一点,我对新疆消失的部分——也就是斯坦因所说的“沙埋文明”——似乎更感兴趣,因为它能点燃一个人的探究之心和历史想象。对时间的敏感、对消失的挽留,已是我近几年诗歌最重要的主题。
简单地说,新疆就是我的天方夜谭、我的一千零一夜。我一直梦想着能写出一本像《一千零一夜》那样的书。朱又可:我注意到,这几年你除了诗歌而外,还写了大量人文地理方面的文字,像《新疆盛宴》、《新疆词典》,还有研究波斯和突厥民族古典诗歌形式“柔巴依”的专著《柔巴依:塔楼上的晨光》。
沈苇:我感觉到只用诗歌来表达新疆已经不够了,需要拓展一下表达的范围和领域、形式和方法。至少这是我十分真切的想法。因为我想多角度地去理解新疆,想描写一个“立体的新疆”。有的作家会一生写一个村庄或一个小镇,锲而不舍,而且写得很好。但我想把新疆当作一个整体来写,它是巨大的、启示录式的,是我心灵的圣寺,同时充满了世俗的鲜活的细节。
我刚完成写丝绸之路植物的书,最近又在写与喀什噶尔有关的一本书。这么多年,我几乎走遍了全疆。走过的路以万里为单位,喝过的酒以吨来计算,看过的美景也只能以“盛宴”来描述了。现在,喀什噶尔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希望我的文字不要辜负了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或许人文地理方面的写作还会持续几年,但它只是我的“阶段性写作”,只有诗歌写作才是身心交融并贯穿如一的。
朱又可:洪子诚先生说《新疆盛宴》是一部“旅游圣经”。还有一位评论家说这本书带动了近年来新疆的“人文地理写作热”。
沈苇:这样说有些过誉,现在看来它只是一本“基础读物”。我用半年的时间跑遍了新疆,所以这本书是用手和脚一起写出来的。《新疆盛宴》的写作使我对多年来的新疆体验、知识积累和纷繁的背景性的东西,作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如果它增添了一点所谓的“新疆热”,倒是我乐意看到的。
人文地理是相对于自然地理而言的,在新疆早已有之。像《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就涉及了新疆的人文地理。尤其是上个世纪初,斯文·赫定写新疆的书,凯瑟琳·玛嘎特尼的《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等,在我看来都是有关新疆人文地理的经典之作。还有三个法国修女写吐鲁番、哈密的《戈壁沙漠》,也是十分精彩的。近年来,新疆出现了许多从事人文地理写作的作家,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毕竟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新疆、了解新疆、热爱新疆。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人文地理写作不是对地域资源的贩卖。作为一种“非虚构文学”,它需要作家具备综合的
写作能力、独到的发现与扎实的亲历。它需要开阔的视野、多学科的知识,需要保罗·康纳顿所说的“身体实践”。
朱又可人文地理是一种地域性写作,与地域资源的利用是密不可分的。你是如何来理解地域性的?它对一个诗人来说很重要吗?
沈苇:诗人们容易受到地域性的困扰,尤其在新疆这么一个地域色彩很浓的地方,地域性有时变成一个“迷人的陷阱”。
对地域性的过分仰仗,会把一个诗人变成地域主义的“寄生虫”,一个自大又自卑的“寄生虫”。当一个诗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地域的“优势”就是他个人“优势”的时候,他就会为这种“优势”而沾沾自喜,就满足于贩卖地域资源,包括那些迷人的地域符号,成为彻头彻尾的地域性的二道贩子,诗歌越写越像地方土特产……我们要坚决反对做文学上的“二道贩子”。
朱又可:但离开了地域性是不行的,譬如说“西部诗”、“西部文学”……
沈苇:我对“西部文学”的提法一直持保留意见。它的提出,蒙上了太多社会学的急功近利色彩,而不是文学本体意义上的准确定位。在中国,既然有“西部文学”,为什么没有“东部文学”呢?也没听说过有“南部文学”或“北部文学”。常识告诉我们:文学不是由地域划分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时代的“当代文学”都在经历无情的死亡,都在经受时间苛刻的淘洗。“西部文学”这一概念之所以存在,或许是评论界的某种偷懒行为,是为了谈论的方便。从我们自身来说,因为刻意强调了地域性,反而将自己边缘化了。
朱又可:或许“新疆文学”这个概念更好些。
沈苇:文学从来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文学,而人是一面面镜子,折射他置身的时代。譬如说我吧,我是作为一个体验着的人在新疆生活的,而不是一个抽象的“西部诗人”。我只想写出几首好诗,而不是所谓的“西部诗”。“西部诗”和“西部诗人”的概念,说穿了就是把具体的人抽象化了,把具体的事物抽象化了,也把活生生的诗歌和文学抽象化了。
朱又可: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这就是说,地域性对每个人个性的形成和塑造是至关重要的。
沈苇:地域性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力量,源头般的力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被打上了地域的印记。有的人一辈子都带着这种“地方习气”的印记,而又有的人,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抹去这一耻辱的“该隐的印记”。
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的确,不同的地域包含了不同的地理、习俗、人文、历史等等,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魅力。别尔嘉耶夫曾谈到空间对俄罗斯灵魂的影响和统治。他说,一望无际的空间在俄罗斯命运中具有巨大的意义。一方面,俄罗斯灵魂被俄罗斯无边的冰雪压跨了,被淹没和溶解在这种一望无际里。使俄罗斯人的灵魂和创造难于定型,另一方面,俄罗斯无垠的空间也保护了俄罗斯人,给了他们母性般的安全感。他指出:“从进一步的观点来看,这些空间本身就是俄罗斯命运的内在的、精神的事实。这是俄罗斯灵魂的地理学。”
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然而不仅仅是。在我看来,空间中不同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是同一事物的多个侧面。
我注意到,从来没有人从时间的角度去考察过地域性。似乎地域性只是时间之外的某种东西,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另类空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诗经时代不是一种地域?盛唐时期不正是一种地域?而且你也不能武断地说,诗经时代和盛唐时期已经消失了,与此时此刻没有了任何关联。这样一问,地域性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同时也变得有趣了。
朱又可:按照你的看法,地域性更像是一种时空的同在和混融?
沈苇:对。只有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角度去理解地域性,我们才能接近自己置身的地域,否则会失去了此在的立足点。
朱又可:以上我们其实谈的是诗歌与地域的问题,接下来让我们谈谈诗歌与人的问题。涉及到诗歌与人的话题,我们很容易往大的方面去思考,变成了诸如诗与读者、诗与人民、诗与社会、诗与时代等关系的谈论。我想,仅从社会层面和传播意义的角度去谈论诗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能不能将这个话题往小里谈一谈?能不能往一首诗生成的时刻那种诗与人的关系的角度去想一想?能不能将这个话题放在具体的诗与具体的人?
沈苇: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诗歌现象,我们被现象困扰,错把现象史当作了诗歌史。孰不知,诗人不是由现象来支撑、归类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更需要从大回到小,回到具体的诗与具体的人,从博尔赫斯所说的“人群幻觉”回到希门内斯的“广大的少数人”。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一首诗的诞生是一个重要而神圣的时刻,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它。当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时,他绝对是一个本质的人,一个焕然一新的人,同时是一个忘却了时间与焦虑、得到了诗歌庇护与救赎的人。这样的瞬间,丰盈高过了贫乏。这个瞬间会持续,会穿越漫长的贫乏,与另一个丰盈的瞬间相遇。正是这种诗与人相遇的瞬间、诗与人的奇遇记,使我们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并精神振作、一跃而起。
朱又可:我想,诗歌的诞生与小说、散文的诞生肯定是有所不同的。
沈苇:诗歌写作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需要耐心,需要等待,当然也需要持久的技艺的训练。当一首好诗诞生时,诗人是吃惊的,这首呱呱坠地的诗对诗人也是吃惊的。如果非要拿诗歌写作与小说写作进行一番比较,我只想说,诗歌写作中有更多的奇遇,更多的意外,而小说写作,更像是一场预谋。二三流小说家藐视诗歌,而一流小说家敬重诗歌,这是一个事实。一首诗诞生了,诗人为他漫长的一千零一夜找到了一缕曙光。每一首诗都是迎向曙光的一扇窗户。
朱又可:我们常常谈到诗歌的出路问题,诗人们在谈,文学界也在谈。
沈苇: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伪话题。诗人们在写作,这本身就是出路;诗人与诗在一起,这已经是出路。再说,有了出路又能怎样?出路之后的路又在哪里?诗人们不是在寻找出路,因为诗已经在路上,当然是在一条困难重重的路上。
一个诗人过了四十岁、五十岁还在写作,并且越写越好,诗歌写作在他已是一种个人修为,同时有了更大承担。在今天,我们不要夸大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力,文学已经很边缘,诗歌更是边缘中的边缘。然而,正是这种边缘化了的“审美的孤独”,保证了诗歌的纯正性和毫不妥协性。诗歌永远走在各种文学的最前面,它是文学中的“探险队”。
朱又可:你是否认为诗歌是坚持的产物?
沈苇:90年代中国诗歌界引用最多的是里尔克的一句话:“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挺住就是坚持。但诗歌不是坚持的产物。挺住也不一定会挺出一个诗人来。说“一个诗人在坚持写诗”,是不近情理的,甚至有点荒唐,就像说一个健康人在坚持吃饭、坚持睡觉一样。
朱又可:不谈坚持,就说持续吧。你的诗歌写作是持续的还是爆发的?
沈苇:总体是持续的,缓慢成长的,当然也有爆发的时候。就在几个月前,还留下了一个月写50多首诗的记录。然而这仅是一个意外。近几年我的诗歌产量大约是每年四五十首,比以前要少。产量已不是我的追求。我更愿意让自己缓慢些,有时还需要停顿和静止。我更信赖那些持续成长、不断精进的诗人。青春期写作是呼啸着的冲刺,而到了中年写作,则是轰隆隆的推进一不,是一种无言的推进!
朱又可:在我看来,写作和阅读一样,可以使人摆脱时间的困扰和时光流逝的焦虑。那么诗歌写作呢?
沈苇:诗歌是一种人生,有时掘地三尺,有时离地万里。如此来说,诗歌就是一种自由的人生,一种既有根又有翅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