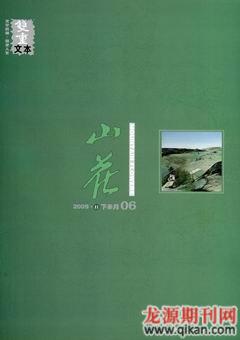从《文选》“情”类赋看萧统的文学批评标准
虽然是放在赋的最后一类“癸”,萧统将《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洛神赋》选入《文选》,并为之单列一类,命名为“情”,这是萧统对于文学史的一大贡献。对此,李善有很恰当的理解:“易日:‘利贞者,性情也。性者,本质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别名,事于最末,故居于癸。”按李善的理解,萧统把“情”定位为“事于最末”,这一点也许值得商榷,但他把所谓“情”视为“色之别名”,即把这几篇赋的共同题材视为性爱,这点认识是很到位的。至此,写性爱题材的文学作品既不是作为“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的对象被抛弃,也不是作为圣人“经夫妇、厚人伦、美教化”(《毛诗序》)的教材而出现,而是第一次以其本来面目——作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审美对象而进入了文学史。不过,对后人来说,这段历史就止于曹植,曹植之后,就无法延续了。因为,《洛神赋》之后,萧统再也不选此类赋作。不仅不选,还对与这一系列赋作题材相同的陶渊明之《闲情赋》大加挞伐,在《陶渊明集序》中称“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杨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萧统为什么把《闲情赋》看成是陶渊明作品中的瑕疵呢?《闲情赋》与《文选》“情”类四赋的区别何在呢?为何不仅不能选入《文选》,就是《陶渊明集》也“无是可也”呢?我认为关键不在于陶渊明写了什么和是否可以这样写,而是在于萧统为什么认为陶渊明不该写这些和不该这样写。对比《闲情赋》与“情”类四赋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不同点,笔者发现,萧统之所以强烈否定《闲情赋》,原因在于《闲情赋》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符合萧统所继承的儒家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
萧统“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交接的也是著名儒者。在与这些儒者的交接中,萧统的人格思想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在这些儒者中,刘孝绰和王筠是与萧统关系最为密切的,萧统曾“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日:‘所谓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王筠称他“宽绰居心,温恭成性,循时孝友,率由严敬。”在这些儒者中,至少刘孝绰和王筠的文学思想与萧统是互相呼应的、互相影响的。刘孝绰在《昭明太子集序》主张“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浮,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在两个极端之间求其中和,这是典型的儒家中和之美美学观的表现。王筠在《昭明太子哀册文》中认为“吟咏性灵,岂惟薄技,属词婉约,缘情绮靡。”所谓婉约,就是“典而不野”、“丽而不浮”,对儒家中庸思想的继承也是很明显的。萧统的文艺思想,因此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对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与刘孝绰如出一辙的要求:“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主张在艺术表现的方式上有一定的尺度需要遵循,表现出对儒家“中和之美”美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在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儒家诗教传统对萧统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在《陶渊明集序》中,他说“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兢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可见,他编选《陶渊明集》的目的,在于有助于政治教化。而在《文选序》中他也表示:“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他认为文学应该是“随时变改”的,既可以借之了解时代变化,也可以用之教化天下。总之,在思想上要求有助于政治教化,在艺术上追求中和之美,这就是萧统的文学主张。
《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四赋均以性爱为表现题材,共同地遵守了“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规范,共同追求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毛诗序》)这样的社会教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萧统的文学批评标准的。
《高唐赋》在“珍怪奇伟”的自然的背景下,铺排了一个由祭祀、车服、音乐和田猎组成的、隆重的、声势浩大的群舞。在这个豪华的背景上,出现在前台的是“简舆玄服”的楚怀王,与背景形成极大的反差,那种追求心仪的女性的虔诚不言而喻。本来,追求的结果应该是极乐的欢会,但是,“风起雨止,千里而逝”,一笔带过,欢会的女主角根本没有出现就消失了。文本转而描绘由这两性的欢会带来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盖发蒙,往自会。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九窍通郁,精神察滞,延年益寿千万岁。”把纯属个人的性爱活动转化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既可以借此思虑天下大事,广开圣贤之路,还可以弥补君王政治措施之不足。个人情感至此完全被社会情感所遮蔽,个人情欲的实现顿时转化为完成社会教化的手段。与神女交合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性爱欲望的满足,而是为治理天下这样更为宏伟的目标。虽然联系牵强,起码要用原始人的神话思维才能进行解释,但是,作者就是这样归纳的,而这正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笔法。
《高唐赋》于男主角楚怀王并未作细致的刻划,其笔触停留在神化的外部行为描写,而内在的企盼、追求和欢愉被悬置。与之相反,《闲情赋》虽仍未敢表现其男女相会的欢悦,却将内在的追求和企盼作了尽情的展示,甚至到了离经叛道的程度。陶渊明也明白这种情感的不合法度,表示写作此赋的目的就是要“闲情”,即防闲欲望之流露,以期“有助于讽谏”。而这一点原本是符合儒家传统的道德取向的。黑格尔论欧洲宗教艺术时曾说,这是把苦痛和对于苦痛的意识和感觉当作真正的目的,在苦痛中愈意识到所舍弃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它们的喜爱,愈长久不息地观看自己的舍弃,便愈发感觉到把这种考验强加给自己身上的心灵的丰富。“闲情”的审美价值就在于戴着镣铐的舞蹈——在礼教的面纱下,微露个人情感的冰山之…角,欲盖弥彰,这才让人心旌摇荡:在陶醉于情欲的强烈的同时,震憾于克制情欲的意志之强大;在情欲的喧嚣中突现意志的主旋律,体现出一种理性的光芒。阅读这样的作品,既可使凡俗的读者因情欲的渲泻而迷醉,也可以让高雅的卫道者为理性战胜情欲而折服。但是,虽然在作文前有如此理性的初衷,艺术行为与人类的欲望却并不能够截然分开。在行文之中,在实现创作意图的时候,有些东西偏离了正道,使得陶渊明忍不住直陈自己愿意时时刻刻与自己所爱的美女有肉体的亲近,为此愿意成为她的衣领、腰带、发油、青黛、簟席、鞋子、影子、烛光、扇子、鸣琴,并为愿望的不能实现而自悲自叹、自怜自愧。缠绵悱恻,神魂颠倒,近乎迷狂。此一情状是前所未有的——既是陶渊明自己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也是陶渊明之前的别人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对于当时的文坛,可以说有_一种振聋发聩的影响,对以《毛诗序》所主张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规范为
代表的儒家文艺传统,客观上构成了鲜明的反讽,故成为“白璧微瑕”,让萧统认为“无是可也。”
到《神女赋》中,那个令楚怀王痴迷的女主角方才正式出场,而且还是那样的奇怪地矛盾着:“搴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倦倦。怀贞亮之絮清兮,卒与我兮相难。陈嘉辞而云对兮,吐芬芳其若兰。精交接以往来兮,心凯康以乐欢。神独亨而未结兮,魂茕茕以无端。含然诺其不分兮,喟扬音而哀叹。瓶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既对男主人公既招引又拒绝,既是爱欲的发出者,又是礼教的坚持者,奇怪地游走在爱欲和礼教之间。男主人公非常被动,既被招引。又被峻拒。因招引而“私心独悦,乐之无量”;因峻拒而“徊肠伤气,颠倒失据”。全篇落笔在男主角若即若离的欲望对象和追求欲望实现的神魂颠倒的情态上,其关注和表现的并非如《闲情赋》之“十愿”那样就是欲望本身。男主角内心狂热的情感用“情独私怀,谁者可语”一笔带过,情爱活动止于“精交接以往来”,结果是“神独亨而未结”、“次情未接,将辞而去”。虽然在这篇赋作中作者未将自己所写的性爱活动归结为“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之类的政治教化的手段,但是,明显看得出所写也在“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范围里面,并未越雷池一步。
《登徒子好色赋》是对《高唐赋》和《神女赋》的思想总结,集中体现了萧统之设置“情类赋”的良苦用心。“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如此美丽的邻女,却不是主人公宋玉的欲望对象,而是作为道德检验物存在。“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作为文本中的主人公,宋玉经受住了考验。而作为文本的作者,宋玉认为这样表现都还不够,还应该如章华大夫那样,在“目欲其颜”的同时,能“心顾其义”,在“扬诗”挑逗的同时,又“守礼”不前,只是“以微辞相感动,精神相依凭”。总之,美色不是用来喜好和追求的,而是用来启蒙自己和考验自己的。与之相反,《闲情赋》中的美女。却不是道德的试金石,她就是一欲望对象,没有宋玉笔下“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神秘,也没有曹植篇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诡幻,完全消退了比兴寄托的象征,再没有社会政治意义这样的面纱,美丽的身体就是作者表现的目的。主人公对女性美丽的身体是如此的着迷,以至要用“十愿”的方式来加以表达,恣意尽兴,直击欲望本身。对女性身体的迷恋,用儒家传统眼光来看,是一种危险的需要约束的情感。“凡淫乱者,未有不至於杀身败国而亡其家者。”它让男性丧失了自我,处于迷狂状态,以至于杀身败国亡家。不能说陶渊明不认同这一点,但是,在文本之中,他似乎更为情欲所左右,只能寄希望于“憩遥情于八遐”,或者用自然的险阻来对它进行阻遏,或者在无性的自然中对它加以淡化。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在性爱主题的表现上,《洛神赋》可谓集《高唐赋》和《神女赋》之大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求爱的表现方式上看,跟《高唐赋》和《神女赋》一样,《洛神赋》也有一个隆重的、声势浩大的求爱群舞。《高唐赋》中男人用来吸引异性的是祭祀、车服、音乐等身外之物和突现男性刚猛气质的田猎活动;《神女赋》中女神用来吸引异性的是美丽的身体。跟《高唐赋》凡间男子向女神求爱不同,《洛神赋》继承了《神女赋》女神追求凡间男子的模式。在众女神“体迅飞凫,飘忽若神”的柔曼群舞的背景上,处于领舞位置的洛神宓妃美仑美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不过,《洛神赋》中的女神跟《神女赋》中的女神比起来,其行为举止和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她对凡问男子的追求是坚持到底的。她不仅以自己的美貌和迷人的举止吸引了男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追求,还积极应和:“抗琼(王弟)以和余兮,指潜渊而为期”。面对男主人公的犹豫,她彷徨、哀歌、舞蹈,还“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可以说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虽然最后是愿望未能实现,落得个“泪流襟之浪浪”,也还始终“长寄心于君王”。关于“陈交接之大纲”,顾绍炯先生将之理解为“诉说交接的礼数纲常”。对此,我不能赞同。从上下文关系看,洛神在这里不可能“诉说交接的礼数纲常”。上文写她的求爱遭到了男主人公的怀疑和拒绝,下文写她“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怎么可能在这里跟男主人公诉说什么“交接的礼数纲常”呢?她应该是再次重申愿意交接的旨意吧。可惜这回男主人公已经吸取了在历史上多次被招引后又被峻拒的经验,不会轻易上当。当然,他同时也就错过了可能的艳遇,一旦幡然醒悟,只能“冀灵体之复形”。但是,昨日不可重现,只落得“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曙。”综上所述,就男主人公而言,《洛神赋》所写的仍然是一次“欢情未接”的、没有超越“发乎情,止乎礼义”范围的精神恋爱。
《洛神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一句。可以说,正是这一句,使得该赋继承《登徒子好色赋》“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之精髓,作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标本,当之无愧地被选入了《文选》。虽然实际上男主人公在此是要用礼法来控制自己面对美女不再冲动,并不是控制自己不冲动以遵循礼法,但是,他毕竟明确意识到“礼”的存在,并愿意用它来遏制自己的情欲。与之相似,《闲情赋》的写作初衷也是要遏制自己的情欲,“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但赋作本身却极为张扬这种本想遏制的情欲。在《高唐赋》和《洛神赋》用舞蹈来表现的对异性的追求,于它改成了男主人公的大段内心独白的,用语言而非舞蹈,而语言是“一切思想和事实的外衣”,它是那样的直白,不需要注释,也不需要想象。这就更加切近爱欲的本质:直露而非中庸。故钱钟书评之为“流宕之词,穷态极妍,澹泊之宗,形绌气短,诤谏故摇惑;以此检逸归正,如朽索之驭六马,弥年疾疚而销以一丸也。”
当然,对于写作《闲情赋》的陶渊明来说,女性仍然是男性悟道或养生的媒介、娱玩的对象,还未能上升到关注其思想情感的境界,当然更不能把女性当成平等的灵魂来相互欣赏。写作的关注点仍然是从女性身上可以领悟的道理,或者女性可供男性娱玩的形体、容貌、情感。其隐含的读者是那些以女性为娱乐玩赏对象的男性读者。这种对女性的赏玩是作为男性的一种本能。不过,男性到魏晋,尤其是晋宋之交,由于主体意识的张扬,已经学会了关注自己的容貌、风度、情感:“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在此基础上,男性对女性的赏玩、渴慕之情也成了欣赏对象。《闲情赋》这样的作品,其隐含的读者正是那些如陶渊明一样以个人情感为欣赏对象的文士,尽管还需要躲在悟道、讽谏的遮羞布后面。从玩味女性,到玩味这种对女性的玩味,这是性爱审美意识的一个进步。从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看,伴随着这一进步,男性为女色所迷的程度是更加深重了,完全不符合儒家的文学批评标准,故萧统曰“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自然不会将之选进《文选》。
作者简介:
刘代霞(1965-),贵州金沙人,毕节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在职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及民族文化。
——论王闿运对宋玉《高唐赋》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