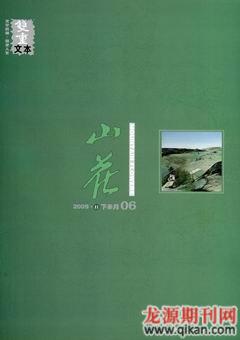第七日
尔 雅
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及至得了水汽,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
——《圣经,约伯记14》
妈妈
我妈离开的时候,告诉我说,一定要等着她回来。因为她说,不管她走到哪里,她一定会回来的。我妈一边这样说,一边流泪,她的泪水哗啦哗啦地落下来,一直落到我的脸上。那时候我好像还有一点发烧,对于她反复讲的这些话很没有耐心。再说,她哭泣的样子那么难看。因此我希望她能够赶快离开。我大声对她说,知道啦,知道啦。
然后我妈离开了。她一直在哭。直到我看不见她的身影,听不见她的哭声。
我想,我妈当然能回来。我当然要等她回来。为什么不呢?
我在等我妈回来。就这样,好几年过去了。
多多婶婶
每次见到多多婶婶,她总是说,快了,快了。她是说,她快要死了。她说话的声音一次比一次小,到后来,如果不是我听惯了这句话,就只是看见她的嘴巴在动;就以为是那些苍蝇在说话,因为她的脸上有很多苍蝇在飞。但是她肯定在说,快了,快了。她自从躺在土炕上,就没有说过别的话。她蜷缩在那里,越来越小,跟一只死去的猫一样。她身上和嘴巴里的臭气却越来越浓了。实际上我还没有走到她跟前,离她有一百步远的时候,她的臭气就传过来了。它们粘到我的身体上面,怎么也摆脱不掉。多多婶婶刚开始躺在那里不能动的时候,我心里还觉得难过;到后来我就慢慢地不那么难过。因为多多婶婶变得越来越难看了。她根本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了。我猜她自己肯定也很难过。她活着那样难受,还不如死掉。我希望多多婶婶能快一点死掉,这样她就会好过一些。再说,这种气味实在是令人难熬。
恐怕多多叔叔也是这样想的。他总是不说话。他看着多多婶婶越来越小的样子,一点表情都没有。他比多多婶婶还像个死人。有时候多多婶婶问他,你说,我怎么还不死呢?多多叔叔这时候就会说,你不会死的,离死还远呢。但是他这么说的时候,脸上的神情非常模糊,很没有底气,显然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自己所说的。他可以忍受多多婶婶身体上的臭味,但是忍受不了她这样难捱的样子。多多叔叔坐在炕头的日子,和多多婶婶躺在那里的日子一样久。她要是不死,多多叔叔就得一直坐在那里看着她;她要是死了,多多叔叔就可以干别的事情了。因为大宝去了新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得知道大宝是不是活着;二宝整天躺在泥土里睡觉,就算给他一点吃的,他也不知道吃。多多婶婶要是还不死,二宝就差不多要死掉了。大宝和二宝是多多叔叔的儿子,也是多多婶婶的儿子。
唉,可怜的多多叔叔。
原先的时候,多多婶婶一直是肥肥胖胖的。有些时候多多婶婶蹲在茅坑里拉屎。镇上有几个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就会说,多多婶婶拉屎了,我们去看她的屁股吧。于是我跟着他们爬到多多婶婶院子后面的墙头上去。多多婶婶的屁股正对着我们。我们就趴在那里看她的屁股。又雪白又肥大。看得我们之中的两三个人直想尿裤子。那时候二宝也趴在墙头,和我们一起看。忽然有人放出一个屁,多多婶婶听见了。她站起来,穿好裤子,对着我们大声喊叫起来:狗日的,日你祖宗!我们从墙上溜下去跑了。二宝没有跑,他认为他妈只是骂我们,不会骂他。结果多多婶婶追上来,只剩下二宝。她就把二宝拎起来,然后扔出去,二宝就跟一团屎那样粘到墙上去了。但是下一次多多婶婶见到我,并没有骂我。她把我看她屁股的事情已经忘记了。她还给我一个萝卜。她说,可怜的娃娃,真是个虫子。那是因为我就叫虫子。我总是在尘土里滚过来,滚过去,于是他们就叫我虫子。
然后多多婶婶就成了这样了。她一天天地变小。她脸上飞来飞去的苍蝇比茅坑里还要多。她说,她要死了。起初这么说的时候她还会流眼泪,后来就没有了,她凹进去的眼睛就像个死人的眼睛,像墙壁一样干涸。
虫子
从多多婶婶那里出来之后,我就到古堡里去了。我经常会在古堡停留很久,有时候我还会住在那里。我看见蛇从草丛里滑过去,尘土里留下一道弯曲的痕迹;看见蚂蚁在地上跑来跑去,还看见蝴蝶在零星的花瓣上面飞。那里其实和街道一样寂静,但尘土里的气味是干净的。古堡墙壁下的土是红色的,那是因为古堡里死过很多人。100年或者20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镇子里的祖先和一群飞檐走壁的土匪决斗,结果很多人死了。血像河水一样流过来。死去的人们在夜晚的时候,会在古堡里唱歌、说话和哭泣。我们镇上的很多人都听见过。因此他们都不愿到这里来,因为活着的人不能够和死去的人说话。如果那样活着的人会死去,而死去的人就会活过来。我会怎么样呢?我希望和什么人说话,即使是死去的人。街道是那么安静,活着的人也像是死去的。但是我在古堡里停留了那么久,却没有看见死去的人,也没有听到他们说话。
古堡里有一个女人。不知道被谁丢弃,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这里。但我觉得她很像芳芳。因此我就叫她芳芳。她没有衣服,又脏又小。但她眼睛清澈,脸面干净。她躺在那里,就像是一直在沉睡。十天前我看见芳芳。我以为第九天的时候她就会只剩下残破的骨头,就像我遇见的很多这样被丢弃的人。因为有狗,有猫,有老鹰,还有蚂蚁和苍蝇。它们会密密麻麻围上来,直到芳芳只剩下骨头。可是第九天的时候我去看芳芳,发现她还是和十天前一模一样。之后的几天,她还是这样。一直到今天,她还是这样。她的气味也和尘土一样。因此我认为她没有死。她为什么还没有腐烂,还没有被它们吃掉?因为她没有死。我坐在她身边,希望她会突然睁开眼睛,突然对我说一些话。我看着她,觉得芳芳要是没有穿衣服,就这样躺在这里,那么她一定就是这样的。
我们镇子上的芳芳是和我说话最多的女人。她总是偷她家里的馍馍给我吃。她每次给我一小块。因为要是拿一大块,她妈就会发现,然后她就会被打死。她妈总是说,你为什么不死?你要是死了,我就省心多了。有时候我在地上睡着,她也就学我的样子睡着。我有时候踢她的屁股,叫她滚开,就跟她妈踢她一样,但是不久她又回来了。她不怕我踢她,她跟尘土一样结实。我走到哪里,她跟我到哪里。我走到古堡里,她也跟我到古堡里。我在古堡里挖了一个坑,然后舒舒服服躺进去。我说,这就是房子。
芳芳说,这不像房子,这是埋死人的坟地。
我想一想,觉得她说得对。我就搬来一些枝条和蒿草,把它们罩到坑上面。
我说,现在就是房子了。
芳芳说,还是不像,你得有个女人才像。
我想一想,觉得她说得对。可是,上哪里去找个女人呢?
芳芳说,我就是女人,我可以给你当女人。
她的话把我逗笑了。而且她说话的时候,看起来还很认真。我躺在坑里哈哈哈地笑起来。因为我一直没有把她当女人看。就算她是个女人,我认为还是要找一个别的女人来给我当女人。
好吧,我说,就算你是我的女人,现在你去做饭,我很饿了。
芳芳立刻屁颠屁颠地去找吃的了。过了一会,她回来了。她的小腿和胳膊上烂兮兮的,被枝条草叶什么的划了许多血印。她手里举着一把东西,里面有野草的根,一根细萝卜,几颗野果。虽然不算什么好东西,我还是高高兴兴地把它们吃掉了。我想等我们长大以后,我要是找不到别的女人,就让芳芳当我的女人吧。有时候我和她面对面站在那里,把裤子脱掉,我拿着我的鸡鸡,她把屁股迎上来。我在她那里蹭来蹭去。因为男人和女人就得这样。
一个月前,芳芳失踪了。她妈在街道上走来走去,一面哭着叫她的名字。但我知道她是假装的。说不定就是她把芳芳推到井里面或者扔到什么地方去了。因为她哥哥回来了。她哥哥一回来,她好像积攒了很多力气,打芳芳的次数比从前更多了。芳芳的身上和脸上跟墙皮一样斑驳。然后芳芳就再也偷不到吃的东西给我了。
我在很多地方寻找芳芳。我想她一定还在什么地方。一直到十天前我看见古堡里的那个女人。那天我告诉芳芳她妈说,我看见芳芳了。然后我带着她来到古堡里。她看了看,说这个不是。说完她就走了。她脸上一点悲伤的痕迹都没有。她一定是已经把芳芳忘记了。因此就算真的是芳芳,她也会说,她不是。
可是我觉得古堡里的这个女人就是芳芳。十天过去了,她还是好好的,跟刚开始我看见的那样。她没有腐烂,也没有腐烂的气味。她不肯这样是因为她还有话要说。人要是还有话没有说完,那他就不会腐烂,他的尸体也不会被吃掉。
正午的街道
我太饿了。我上哪里去找一点吃的呢?我走在镇子的土路上。街道上空空荡荡。这时候是中午,镇上的人们都蜷缩在自己家里,沉沉睡去。有些人睡着之后,也许就不再醒过来。空气里充满腐烂和发霉的气味。我走在街道上,看见我脚下的尘土飞起来,听见我的脚踩在地面上的声音。太阳罩在头顶,越来越重,脚下的地面开始摇晃起来,就像是喝醉酒的人那样。我会不会被它抛到空中?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也许哪一天我正在地上走,忽然就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了。有些人在走路的时候,就会突然死掉。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披头散发,摇摇摆摆地走过来,舌头从嘴巴里伸出来,呼哧呼哧地喘气,跟一条奔跑了很久的狗一样。可是他看上去很高兴,因为他说他走了三天的路,总算走到我们镇里来了。他开始说话的时候,镇上只有我一个人;等到他说完话,我们镇上的一些人突然就出现了,就像是从地里突然长出来的一样。我们镇上的人就是这样,你经常以为这个镇子的人都已经死光了,实际上不是,如果有外乡人出现在街上,或者一条蛇从街道上爬过去,他们就会突然从地里面长出来。那时候镇上的人站在街道上,安安静静地,都在看这个伸出舌头的外乡人。他说总算走到镇上来,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镇子里藏了黄金和麦子做的面饼吗?
这个人也停住了。他看着我们,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他的嘴唇像是两片破烂的树皮,因此他舔嘴唇的时候,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他说,我走了三天的路,总算是走到镇上了。忽然,他倒在地上,四肢朝天,就像是被一颗子弹击中那样。我们有那么一会看不见他在什么地方,因为他被地上升起来的尘土包围了。过了一会,我们看见他还跟刚才那样躺在地上。又过了一会,他还是那样躺着。有个人走过去,踢了他一脚。他还是没有动静。这个人又踢了他一脚。
他说,死了。
另一个人说,嗯,死了。
然后我们镇子上的人突然都冲了上去。他们就像是很多条狗见到一块骨头那样。他们在尘土里挤来挤去,有些人摔倒了,又爬起来;有些人还在骂娘。过了一会,他们散开了。那个人躺在街道上,赤身裸体,肮脏不堪,看上去已经死了很久。我们镇上的人那天居然还从他的身上找到了一块饼子,两角钱,一只碗,三根筷子。
当然了,这样的人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甚至我们镇上的人也会这样。那是有一次,我们看见李有福的爷爷在街道上走,他一边走一边说,他还能活10年。因为算命的说过他还能活10年。那时候他手里拿着一个土豆在吃。但是忽然他开始咳嗽起来,他一边咳嗽一边拍着自己的胸口,因为吃下去的土豆卡住了嗓子;他拍了很多下,土豆还是卡在嗓子里。然后我们看见他抽搐着,缓慢地倒到地上去了。过了一会,他就死了。李有福这时候走过来,先把他爷爷手里没有吃完的土豆拿好,然后摸了摸他爷爷的脉搏。他对我们说,看来算命的没说对。
算命的确实没有说对。因为大家都以为李有福的爷爷不会这么容易就死了。因为李有福会偷东西。谁也没看见李有福偷东西,也没人能抓得住,但是大家都知道李有福是贼。他家里就他和他爷爷,他偷来的东西根本吃不完。可是他爷爷就这么死了。李有福说,他爷爷死了也无所谓,但是活着总比死了好一些。他爷爷要是活着,还至少有个人和他说话。他是贼,除了他爷爷,镇子里所有的人都在仇恨他。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被镇子里的人打死,然后把他扔在街道上。
那天街上来了两个女人。一个很老的,一个年轻的。她们喘着气,看上去快要死了。年老的女人坐在地上,对着空荡荡的街道说,这是我的娃,哪个好心人留下她吧。
她说,我只要五斤粮食。
这时镇上的人出现了。他们看着她们。
她说,你们看看,这是我的娃,胳膊、腿、屁股都是好的,做饭、缝衣、生娃,样样都会。
他们看着那个年轻的女人。她看着镇上的人,跟个傻子一样。
有人问,她会说话吗?
会呀,老女人说,会说话,我的娃,你说两句叫他们听听,说两句。
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还是没有说话。
前面那个人说,是个哑巴,说不定还是个傻子。
于是镇上的人笑起来。有人说,要是哑巴,就不值五斤粮食,三斤差不多。
我的娃真不是哑巴,老女人说,她要是哑巴,我就白送给你们。
就算她不是哑巴,有个人说,那也不值五斤粮食。
我们没有那么多,另一个人说,三斤粮食也没有。
多多的女人快死了,她可以给多多当女人,有人说,多多或许有三斤粮食。
多多也没有,另一个人说,多多最多有一斤。
天啦,天啦,老女人说。她摆出要哭的样子,可是她的眼睛里没有眼泪。
这时李有福过来了。镇上的人们让到两边,就像是混浊的河水被划开。李有福走到年轻的女人身边,从上到下打量她;接着他伸出一只手,抓住她的脸,看她的眼睛、嘴巴和牙齿,就跟检查一个牲口那样。然后李有福做出考虑的样子。
李有福看着老女人说,我最多给你三个土豆。
天啦,天啦,她说。
就是三个土豆,李有福说,要行,我这就把她带走,我给你三个土豆。
她说,五个吧,五个。
就三个,李有福说,我只有三个土豆,我爷爷要是不死,你白送给我也不要。
于是,镇上的人叫她土豆。她是李有福三个土豆换来的女人。镇上的人没有见过土豆说话。也许土豆真是一个哑巴。但是土豆看起来干净多了。当她有时候在镇子的街道上走过去,镇上的男人就评论说,要是那
的香味。就那么很短的一会工夫,就吃完了。我觉得好过多了。
虫子,我有个东西先放你这里。
嗯。
我不能让土豆知道。所以就先放你这里。
嗯。
你不能看,也不能告诉别人。
嗯。
我过几天就来取。先放在你这里,就放两三天,也说不定我明天就来取。我一会要到远处去一趟,我去去就来,很快就回来了。
嗯。
你要是不说出去,他们谁也不知道东西在这里。你要是说出去,你知道我怎么收拾你?
嗯。
我就把你随随便便弄死了,弄死了扔到沟里去,让野狗和狼把你吃掉,吃得干干净净,一根骨头都剩不下。
在听我说话吗?你是不是想着我不敢这么干?是不是?我随随便便就能这么干。弄死你就跟弄死一只老鼠那么容易。
日你妈的,说话呀。
嗯。
我来取东西的时候,要是东西是全的,我就再给你一个土豆,比刚才给你的还要大。
嗯。
我把它埋起来。你就在屋子里不要动,我自己把它埋好。你就当院子里什么都没有埋,要是有人问,你也这么说。
嗯。
然后我听见李有福走到院子里。找到锄头之后,钻进草丛。他窸窸窣窣地,跟一条蛇那样动来动去。后来他选好一个地方,把蒿草连根拔起来,一下一下地挖起来。他挖了很长时间。后来我睡着了。
天亮的时候,我来到院子里。院子里什么都没有。我在蒿草里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哪个地方是李有福挖过的。就跟他根本没有挖过、没有藏过东西一样。
多多叔叔
天亮的时候,我听见多多叔叔在哭。他的声音干枯、荒凉、绝望。接着多多婶婶身体上的臭味漫过来,就跟黏稠的空气一样。我知道,多多婶婶死了。她在炕上躺了一年多,身体早就腐烂了,然后她被自己身体里的臭味风干,终于死去。她那么难过,早就该死掉了。
多多叔叔坐在自家的院子里号啕大哭。他脸上的鼻涕比眼泪还要多。那些鼻涕在空气中晃来晃去。多多婶婶也躺在院子里,看上去像是一节干枯的木头。她身下的褥子肮脏无比,散发出一股一股的恶臭;褥子上有一些蛆虫在爬动,它们又肥又嫩。太阳升起来了,多多婶婶好像是睡着了一样。实际上她已经死了,只有那些蛆虫还活着。
多多叔叔说,她说要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我就把她抱到院子里,谁知道她就死了。
多多叔叔说,天啦,天啦,你真就这么死了。
多多叔叔说,你真这么死了,剩下我该怎么办啊?
多多叔叔这么说话的时候,两只手在地上刨来刨去,坚硬的地面被他刨出一个坑,他的两个指甲被蹭掉了,满手都是血。还从来没有见过多多叔叔这样。我一直以为多多叔叔也在盼着多多婶婶死去。没想到他会这么伤心。他满脸鼻涕和眼泪,又沾满了灰尘,手上鲜血淋漓,比多多婶婶还要难看。
这时候镇子上的几个人来到院子里。他们站在那里,看看多多婶婶,又看着多多叔叔哭了一会。然后有人说,多多,别哭了,赶快把她埋了吧。
另一个人说,嗯,埋了,这味道太臭了,放在这里会传染的。
前面那个人说,这样你也会死,我们也都会死。
他们一起说,嗯,赶快埋吧。
前面那个人说,死了挺好的,早就该死了。
他们说,对呀,早就该死了。
但是多多叔叔还是在哭。他哭到后来,就没有眼泪了。声音也越来越嘶哑。再到后来,就只是看见他的嘴巴在动,摆出哭的样子,但是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
这时我忽然想起,我要去古堡看看芳芳。昨天下了大雨,不知道她会怎样。我就从多多叔叔的院子里出来,来到镇上。
疯子
我忽然看见了疯子。疯子怎么会出现呢?他已经消失了很久,镇子上的人都以为他死了。但是千真万确,我看见的就是疯子。他正从远处走过来。他走路的姿势慢慢悠悠,轻飘飘地,很像是一种奇怪的舞蹈。风带来他身体上的臭味,强烈、刺鼻,令人心惊肉跳。那不是镇子里飘荡的那股腐烂和衰落、死亡的气味,而是一种浓烈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新鲜的恶臭。只凭着这种气味,我就能认出他是疯子。他只穿着一件肥大、破烂的棉袄。腿和脚油光闪亮,就跟刷上黑漆的两截木头那样。鸡巴裸露着,在双腿之间难看地晃荡,很像是一只快要死去的鸟。他一边走,一边唱着什么歌,看起来高兴极了。
我害怕疯子,因为有一次他忽然把我举到空中,然后快速地旋转起来,他越转越快,最后我就像一片树叶那样飘飞。那时候我看见地面离我越来越远,我轻盈、弱小、孤单,在等待我从高高的空中坠落下来的时刻,然后就像一朵花那样绽开在地面上。但我等了很久,却没有落下来,因为我在飘飞的过程中悬挂在镇子里的一棵大树上了。我在那里挂了很久,疯子和镇上的人们都在大笑。最后到天色将晚的时候,疯子离去,这时候多多婶婶走过来,她让多多叔叔爬到树上,把我弄下来。从此我害怕疯子。我又仇恨疯子,我想等我长大的时候,我也要把他抛起来,然后看着他从高高的空中掉下来,就像一团屎一样进散在地上。
他总是带来不安和混乱。那时候,每当疯子出现在街上,镇子里的人就会立刻惊慌地逃窜躲闪,就像是躲避一场突然到来的瘟疫。他总是知道镇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包括那些最隐秘的,然后他会大声地说出来。这使得镇上的人们羞愧和慌张,因为他说的是真的。他知道已经发生的,而且还知道将要发生的。他说,某个人要死了。结果那个人不久就真的死了。他说某个人会从树上掉下来,结果那个人就真的从树上掉下来了。他说某天有一场大洪水,结果到了那一天,真的有一场大洪水,淹没了镇子旁边的一个村庄。他预知未来和生死的能力是如此准确、神奇,使得镇上的人们在惊恐之中还包含了对他的畏惧和敬意。人们说,也许疯子是被一个鬼魂附了体,所以开口说话的其实不是疯子,而是那个看不见的鬼魂。因为镇上的人们有一次亲眼看着疯子从古堡的城墙上面落下来,就跟一只巨大的、难看的乌鸦那样,然后掉到坚硬的路面上,所有的人都以为疯子被摔死了,因为古堡的城墙离地面至少有三丈那么高。结果,过了一会之后,疯子站了起来,开始对着镇子上的人们发出大笑。
更糟糕的事情是,疯子总是追逐镇子里出现的每一个女人。在他开始奔跑的时候,他双腿之间那个难看、肮脏的鸡巴就会突然变得肿大和坚硬。女人们狼狈逃窜,一个女人因为过于害怕而尿湿了裤子,另一个女人则因为慌张,裤子突然从腰间滑落,整个镇子里的人们都看见了她裸露出来的大腿和屁股。人们希望生活是安静、讲究秩序和有条理的,但是疯子却令他们感觉到羞愧和放荡。
没有人能够制止他,因为当他发怒的时候,他能够把镇子口的一块大石头举起来;而那块石头,需要镇子里四个最壮实的男人一起用力,才可以抬起来。那时候镇子里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感觉到饥饿,人们也正在思考为什么可以吃的食物越来越少。当疯子很多次出现在镇子里,并且一次比一次疯狂的时候,他们忽然意识到,那些令人不安、荒唐的事情,也许就是疯子带来的。要是没有这个古怪的疯子,也许他们会好过得多。他们说,必须要让疯子从镇子里消失。要是别的什么人,当然是
毫不费力的事情,镇上的男人们联合起来,随便就可以把他扔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或者把他丢进山林里,让那些野狼把他吃掉:而疯子则麻烦得多,驱除疯子的时候,同时还要驱走附在他身体上的那个令人恐惧的鬼魂。谁也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直到有一天,疯子在街道上撕开一个女人的衣服,然后像一条狗一样把她的胸口咬得血肉模糊,镇上的几个男人们冲上去,把疯子掀翻在地,用木棒和拳头把他打昏过去。疯子很久之后醒过来。他看着镇子里的人们,忽然说,你们一个一个都会死的!
这句话比疯子撕咬女人的样子更令人恐怖。镇子里的人那时候明白,他们需要立刻把疯子赶出去,否则,他所说的话就会变成现实。他们马上去请教镇上的李阴阳。此前,因为疯子所说的预言比李阴阳更准确,已经没有人再去向他占卜了。李阴阳其实也正在琢磨如何才可以让疯子消失。他说,既然疯子是鬼魂附体,那么就得按照驱鬼的方式把他赶走。
那天夜里,镇上的男人们联合起来,再一次把疯子打昏,装到一个麻袋里;李阴阳手持火把和咒符,嘴里念着驱鬼的咒语,一路走在前面。他们翻过两座山头,最后走到山脚下一个一丈深的水塘边。他们把麻袋扔进了水塘,然后看着它缓慢地沉入水底。
疯子消失了。镇上的人们也都确信,他已经死了。镇子上出现了短期的安宁。事实上饥饿的感觉并没有消失,而且,正像疯子所说的那样,开始有人死去。有一股奇怪的气味在镇子里弥漫。那是死亡的气味。所有的人正在慢慢地腐烂和死去。我也是这样。我没有一点力气。我脚下的土地在摇晃。越来越强烈。对于我来说,镇子上有没有疯子,无关紧要。疯子出现,不会更糟,没有疯子,也不会更好。我看见疯子,他从远处走过来,精神抖擞,还是那样的不顾羞耻。我忽然觉得,疯子的生活,其实比我还要好过。因为他是疯子,而我,除了不断寻找食物,还要花去时间,等着我妈回来。我感觉我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就算疯子带来更可怕的预言,又能怎么样呢?难道比现在更糟糕?没有了。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
我看见疯子走过来。镇上的人们也都看见了。他们惊慌地躲闪,四处奔跑,就好像死亡在追逐着他们一样。我没有奔跑,也没有害怕。事实上我已经没有奔跑和害怕的力气了。
疯子
他走到我跟前,看着我。他的眼睛通红。多多婶婶有一次说,眼睛里有血的人是吃过人的。疯子当然是吃过的。他什么都吃,有一次我看见疯子手里拿着一节黑乎乎的东西在吃。那是一节狗屎,也可能是人的屎。他放进嘴里咀嚼,满嘴都是屎的碎末,一面吃一面笑,就像是吃得很香。那时候镇上的很多人都看见了。然后李有福忍受不了他吃屎的样子,开始呕吐起来。另一次他手里抓着一条蛇在吃,那条蛇其实还没有死,当他咀嚼的时候,蛇的身体还在扭动。他吃什么都是被允许的,因为他是疯子,他还被鬼魂附了体,不会有什么报应。
那股强烈的臭气漫过来,让我喘不过气来。疯子这时看了我一会,然后在我旁边坐下来。他脱下棉袄,开始晒太阳。看上去很舒服。他的身体全部裸露出来,又黑又脏。上面沾满了草叶、尘土、鼻涕、屎尿的碎片,还有一些虱子在爬。
过了一会,他把棉袄翻过来,开始寻找上面的虱子。他抓住一个,就放到嘴里咀嚼;又抓住一个,放到嘴里。我听见虱子被他咬破的声音。嘎嘣,嘎嘣。他忽然向我伸出手来,手里是一个虱子。他说,虫子,你吃不吃?你吃一个。
我说,不吃。
好吃,他说,吃一个。
我站起来,走到离他远一点的地方。然后我坐下来。
他好像有点生气。接着他就自己把它吃掉了。
他说,你妈回不来了。
我心里猛地有点痛。我看着他。我说,我妈能回来。
他说,我前几天看见你妈了。就那个镇子,没死一个人的那个镇子。她在那里走来走去的。脸色不好看,不停地咳嗽,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她看见我就问我:虫子怎么样了?我就说:我也好久没有看见虫子了。她说:你说虫子不会饿死吧?我说:饿死没饿死你自己去看吧,不过虫子不会死,我算过了,他命里不该死。她就说:你说他不死他就死不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把虫子接回来呢,那个镇子的人都要死了,你这里有粮食啊。她说:想回来呢,天天都想呢,可是回来要翻两座山,山上那么多的人都等着抢粮食呢,怎么能回来?我就说:你说得也对,那些人弄不好连你也吃掉了。你妈倒是挺和善,她说了一会话就给我一个饼子吃。那时候我正打算生气,因为她老是啰里啰唆的。我想着咬她一口,但她给了我吃的,我也就不生气了。我把饼子吃完,要走的时候她说;你碰见虫子就告诉他,让他赶快来找我,镇上的人都要死了,让他赶快跑,赶快跑。哈哈哈,可是你能跑哪里去呢?再过些时候,你还不是照样得死?你妈来不了这里,你也跑不出去这里啦。
我说,我妈在哪里?
他看着我,脸上很迷糊,就好像我不该这么问。
他说,我记不得啦,离这里很远了。
他又说,李有福死了。
他说,我看见李有福了。就翻过山的那边。他被人打死了。我知道他有一天就是这样的。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人把他打死了。我对他们说:这个人我认识。他们说:你认识又怎么样呢?你只是个疯子啊。我说:打死也好,反正他们都要死。他们说啊啊啊。说什么了?我忘记啦,哈哈哈。
他一边说,一边就这么哈哈哈地笑个不停。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听见过笑声了。我碰见的人都在哭。这唯一的笑声就是疯子带来的。也只有疯子在笑。他笑得那么酣畅、舒服,我也就忍不住笑起来了。我先是小声地笑,后来我也就放开嗓门,哈哈哈地大笑起来。我觉得我的声音都要超过他了。
他忽然停住了。他显得很痛苦。就像是我的笑声让他痛苦那样。接着他愤怒起来了。他看着我,脸上的神情非常凶恶。他说,你为什么笑?嗯?谁让你笑的?
他的神情如此痛苦而狰狞,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我害怕极了。我本来想站起来逃跑。结果我发现我的腿根本不听使唤。然后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站起来,伸出双手,就像是一头快要饿死的狼发现了食物那样,朝着我冲过来。
我想,他会把我撕成碎片的。他就是这样的。
土豆
也许就差一个拳头那么大的距离,他的手就能够抓住我的身体。那时候土豆忽然把我从地上拽起来。她就像是突然飞过来的一只鹰。她的力量又是那么强大,因此在最初的时候,我实际上身体悬空,被她带领,在镇子的路面上飞翔。我听见土豆坚强、粗壮的呼吸声。她的身体上有那股我熟悉的青草一样干净的气味。
在我们身后疯狂奔跑的,是一个赤裸着、下体高昂跳动、饥饿至极的疯子。我们在街道上努力地跑啊跑。我听见疯子在我们身后一边奔跑,一边发出快乐的大笑。
那时候其实镇上的人们都看见了。他们害怕疯子,害怕他身体里的鬼魂给他们带来死亡的气息。但是就算不是这样,他们也不会做什么的。他们只是庆幸自己和自己的女人没有被疯子追赶。三个土豆换来的土豆是镇上的贼。另一个快要饿死的人只是一条虫子。就算土豆和虫子没有被疯子撕裂,总有一天土豆会被他们撕裂,因为她是贼;而虫子总有一天会饿死。他们其实正在慢慢地死去,但是在没有死之前,他们总以为自己还有活下去的指望。
因此那是一个非常缓慢、非常狰狞的场景:是这座镇子在死去之前最奇怪和荒诞的一个场景:我们被路面上的石头绊倒在地。然后我被疯子抓住,从土豆的身体上分离开来,进入到高空。土豆躺在地上,被疯子撕裂了她的破烂但是整洁的衣服。从上到下,干干净净。她试图挣扎的时刻,疯子的拳头落在她的脸上。她的脸上出了血。然后她就整整齐齐地躺在地面上。她的身体干净、饱满,在太阳下发出柔和温暖的光亮。然后疯子在她的身体上撕咬和移动。他的身体是那样丑陋,就像是一团臭烘烘的屎。他撕咬的时候还在快乐地大笑。
后来我醒过来了。我身体上也全都是血。我站起来。地上有一块石头,就是那时候绊倒我和土豆的那一块。我抓起来,走过去。我对准疯子的脑袋,用力砸下去。也就这一下。然后我听见什么东西发出沉闷但是彻底的破裂声。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我在土豆身边坐了一会。她还在入睡。她的身体上血迹斑斑。即使这样,她仍然是干净整齐的。她的身体上的气味仍然是干净整齐的。我把她的衣服捡起来。它们已经破烂不堪。我把它们拼凑好,然后把它们铺到她的身体上面。
芳芳
后来我走到古堡里。
就跟我想到的一样,芳芳已经完全腐烂了。
我忽然感觉到很疲惫。因此我就在芳芳身边躺下来。太阳那么温暖,照在我的身上。
我很快就睡着了。
作者简介:
尔雅(1969-),本名张哲。生于甘肃通渭鸡川。17岁开始文学写作并发表作品,迄今在各类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约300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蝶乱》、《非色》,散文集《一个人的城市》,学术随笔集《诗学与艺术问题》等。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8届高研班学员。先后获得甘肃省最高专业文学奖“黄河文学奖”一等奖、二等奖,敦煌文艺奖,及甘肃省重点文艺作品项目资助等。现供职于兰州交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