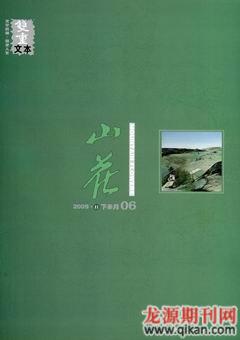大头的一个午后
大头特别想杀死自己的亲爹。他甚至采取过行动。是晚上,清冷的月光拐过窗棂,让屋子里有了凉意。大头被冻醒,感觉口有些渴,就喊他爹。大头说爹我要喝水。爹吧唧一下嘴,舌头舔一下嘴唇,并没有醒来。大头提了提声音,他说爹爹爹我要喝水。爹翻一个身,仍然打着很粗很响的鼾。大头有些气恼,想起爹天天把他锁在屋子里不见天日,再看着爹熟睡的样子,怒火突然从心头升起。大头想我干脆杀了你算了。杀了你,就再也没有人把我锁在屋子里啦。月光下大头盯着爹的喉咙,在那里寻着最恰当的位置。大头偷偷地磨了磨牙,他想让自己的牙齿变得更加锋利。然后,大头张开嘴,迅猛地扑向爹的咽喉。大头没有扑准更没有咬到,他重重地摔倒在爹的身旁,嘴巴磕上炕沿,流出血。爹被他惊醒,含糊不清地说,干什么呢你?又继续睡去。大头静静地躺在那里,流下伤心的眼泪。他想如果杀不死爹,就会被爹永远锁在屋子里了。后来大头哭出了声,声音时断时续。他很伤心。
现在爹下地去了,大头再一次被孤零零地锁在屋子里。他弯下身子,从瓦罐里喝一口水,喷向屋角的蚂蚁窝。滔天巨浪让蚂蚁们惊恐万分,它们争先恐后地从窝里逃出来,在大头面前乱成一团。有几只蚂蚁似乎被淹死,缩在地上一动不动。可当洪水退后,它们抖抖身体,再一次精神饱满地爬开。于是大头不高兴了。没把蚂蚁们杀死,游戏也就失去了趣味。
几年前,大头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英勇地将蚂蚁一只一只地残害。他小心翼翼地把蚂蚁捏起来,再小心翼翼地将它们的腿一条一条地撕掉,然后把蚂蚁重新放回地面。蚂蚁在地上拼命挣扎,用失去腿的躯体爬行。他重新将蚂蚁捏起,用锋利的指甲斩断它们的腰,将它们再一次放回地面。可怜的蚂蚁仍然拼命挣扎,仍然用残缺不全的躯体快速地爬行。这个游戏让大头非常兴奋。后来他不再撕掉蚂蚁们的腿,只是将它们一只只腰斩。被腰斩的蚂蚁们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残缺,反而更显体态轻盈。那时候大头的理想,就是把村子里所有的蚂蚁腰斩。他知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如果不是那次意外,如果不是爹天天把他锁在屋子里。
今天的游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大头仍然没有淹死一只蚂蚁。大头有些不耐烦了,他不得不放弃了对蚂蚁的追杀。现在还是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不久。窗外偶尔有人走动,那是村子里的人们在奔向自己的土地。大头的爹却早已经下地了。他总是天不亮就下地。他说大头我下地了啊,大头说爹爹爹我也要去,门就被锁上了。爹经过家的后窗,一边走一边咳嗽。爹已经咳了好多年,春嫂的白糖水也治不好他。
阳光涌进屋子,大头感觉有些闷热。那阳光是深红色的,是淡蓝色的,是乳白色的,是酱紫色的,是鹅黄色的,是浅绿色的,它们纠缠到一起,扭成漂亮的麻花,在屋子里甩着鞭子。大头喜欢看阳光甩鞭子。有一天他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骑坐在阳光上,手捧一只赭褐色的小茶壶,一边喝茶一边冲大头微笑。他的笑让大头快乐无比,所以大头也冲他笑。后来老头骑着阳光走了,大头把这件事告诉了爹。爹不信。大头说是真的,一个白胡子老头,捧着鸡屎酱色的茶壶,骑着七彩的太阳光。爹说你再胡说八道我就宰了你。
大头突然想起窗外墙角种着的一片鸡冠花。现在鸡冠花肯定开了,爹说它们像春嫂的脸。大头不喜欢春嫂,每一次她来找爹,总会趁大头不注意时躺倒在爹的身下,哎哟哎哟地叫个不停。大头认为春嫂的脸和鸡冠花一点儿都不像。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鸡冠花了。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小孩的巨大损失。
鸡冠花开在墙角,只需把脑袋探出窗外,就可以看到。花丛里也许还藏一只芦花鸡,红的鸡冠和紫的鸡冠花杀到一起,大头就分不清哪个是鸡冠哪个是花了。窗没关,几根粗细不一生满铁锈的钢筋充当了窗棱,把大头一方完整的天空分割成一个一个狭窄的方格。大头痛恨这些窗棱,如果没有它们,大头想,也许自己一个助跑就能够跳出窗子,奔向属于他的快乐。
现在大头特别想看看那些鸡冠花。他把脸贴上窗棱,眼睛努力拐向墙角。可是他只看到一条肮脏颓废的灰色土狗从他面前飞快逃过。那土狗夹着尾巴,一边跑一边笑嘻嘻地看着大头。看不到鸡冠花,大头心中非常失落。他试图将自己斗大的脑袋从窗棱之间的空隙里钻出去。以前他多次这样试过,可是一次也没有成功。现在他想再试一次。他把自己的脑袋往两根窗棱里硬塞,一点一点地增加着力气。他感觉脑袋被挤成椭圆或者不规则的形状。他听到脑袋被挤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他感到太阳穴很烫,眼睛很胀,鼻子很酸,耳朵很痛。他想再使点力气,再使点力气……然后“噗”一声响,大头的脑袋就到了窗外。他似乎得到一种彻底的释放。他感觉到一种天崩地裂的幸福。
大头看到了开成一片的火红的鸡冠花,花丛里安逸地卧着一条翠绿色的蛇。那条蛇长着无数只小脚,每一只小脚上都穿着橘红色的小巧的布鞋。他看到那条土狗不知什么时候偷偷跑回来,此时它趴在花荫里,吐出鲜红的舌头。大头看到那舌头上有两个很大的气泡,两个气泡相互挤压,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气泡。那气泡快速地变换了两次形状,“嘭”一声爆炸。阳光照着大头的脑袋,他感觉很舒服。
这时已是上午了。也许九点多钟,也许十点多钟。夏日的阳光渐渐变得毒辣,让大头方形的脑壳上淌下浑浊的汗水。大头的脑袋在阳光下不停地转动,身体却仍然留在屋子内。两根窗棱将他的脖子卡住,让他很不舒服。他试图把身体也塞进窗棱,然后像挤面团那样慢慢地从窗棱里挤出,拔到屋外。可是他没有成功。事实上他根本不可能成功。大头就那样被窗棱卡着,细细的脖子吃力地支撑着斗大的脑袋,进退两难。人头已经保持了这种姿势太久,现在他开始后悔。他已经把鸡冠花的每一片叶子看了两遍,把那条蛇的每一只脚看了两遍,把那条狗每一根土褐色的毛看了两遍。他感到越来越无聊。可是他还得看第三遍。突然他发现外面其实很虚空,每一样东西都在迅速失去光泽,变成黑白灰三色;每一样东西又都在迅速飘散,像一缕烟,扭曲旋转几下,就不见了。大头眨眨眼,使出全身的力气看那些花,看那条蛇,看那条狗。还好,它们暂时都在。尽管它们的颜色和形状,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
太阳直射着大头的头皮,那里不再舒坦,而是变得很痛。他口渴了。他越来越渴。他从来没有这样渴过。爹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瓦罐清水,刚才淹蚂蚁,他用掉一大半。他知道那瓦罐里还有水。可是他退不回去。他的脑袋似乎永远不可能退出来。可是他仍然在努力。他感觉脑袋再一次被挤成扁平的形状。他听到脑袋再一次被挤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他感到太阳穴很烫,眼睛很胀,鼻子很酸,耳朵很痛。他想再使点力气,再使点力气……可是,没有用。窗棱固执地将他的大头卡住,结结实实。
这时他看到土路的尽头跑来一个男孩。男孩骨瘦如柴,光着脊梁,身体喷发着黑色并黏稠的油脂。那些油脂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男孩像一大块流着焦油的煤的雕像。他在胯下骑一根扒掉树皮的槐树棍,他的身体不断地前仰后合,做出骑马的姿势。有时他
还会从嘴里发出“啾啾”的声音,再喷两下响鼻。直到他跑过来,大头也没有搞明白,到底他是在扮演一位骑手,还是在扮演一匹马。
男孩并没有看见大头,他一边和他的槐树棍搏斗,一边从大头面前疾驰而过。大头不得不喊住他。大头说,小孩!他没有听见。他完全沉浸在骑手或者马的游戏之中。大头再喊,小孩小孩!他吓了一跳,停下来。他朝四周看了看,并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大头不得不喊第三声,小孩小孩小孩!他抬起头,吓得“哇”一声叫。他看到,他的头顶,挂一个很大的彤红的方形的脑袋。
大头说,小孩,我认识你。你认识我吗?男孩说我不认识你。大头说,小孩,你怎么不认识我呢?以前我们常在一起玩。男孩说我真不认识你。大头说,你还来过我家,我们还在一起捉过蚂蚁。男孩说我不记得了。大头感到很失望。他想了想,对男孩说,你帮我把脑袋拽出来,行不行?男孩说那你的身子呢?大头说我的身子还在家里,我的头在这里,你使劲拽我的头,我的身子就会被拽出来啦。男孩说我可不敢拽,万一把你的脖子拽断了,你就死了。大头说拽不断。你快拽。男孩说可是我够不着。大头说你去那边搬两块石头来。你踩着石头,就够着了。男孩说我才不去搬石头。要不,我用这根棍帮你捅两下。捅两下也行吧?大头说不要捅。用棍捅没有用,你得拽。男孩却并没有听他的。他从胯下抽出那根棍子,举起来,瞄准大头的脑袋,轻轻捅了两下。他说行了吗?大头说你别捅,你捅我会痛的。男孩说我问你行了吗?大头说行了。男孩说不。不行。头还没出来呢。差得远啦。
男孩发现了比骑木棍马更让他开心的游戏。他举着那根槐树棍,兴致勃勃地捅着大头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开始他总是捅不准,因为他得仰起脸,白晃晃的太阳让他的眼睛刺痛,看不确切。这让他非常恼火,手上就加了力气。可是他很快找到了诀窍。他将眼睛眯起,只盯着上方那个不停晃动的巨大的红色轮廓。十几下以后,他终于达到了百发百中。大头在狭窄的空间里艰难地躲避,不停地嗷嗷怪叫。后来他把头扭向一边,只留一半脸给下面的男孩。他努力将这个姿势定格,尽量保护着眼睛和嘴巴不受到槐树棍的袭击。他的那一半脸渐渐变得麻木,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热乎乎清稀的鲜血在他的耳根处会聚,滴下来,落进下面操着棍子的男孩张开的嘴巴。男孩曾经试图向旁边挪一挪以便躲开落下的血滴,可是他的棍子马上就戳不着大头的脸了。终于,男孩有些累了,他丢下棍子,冲大头做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他说,看来用棍子捅真的不行。
大头没有说话,他扭过头来看男孩。男孩满脸是血,此时他正用脏兮兮的手去擦。男孩的身体还在向外喷发着黑色的油脂,似乎他的身体就是一个活动的油矿。他热气腾腾,他气喘吁吁。他把脸擦得一塌糊涂。
他对大头说,我是小孩,我没有力气帮你把脑袋拽出来。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个人来帮你。就走了。他走出几步,忽然想起丢掉的槐树棍。他返回来,弯腰,拣起,骑在胯下。他没有再看大头一眼,他奔跑跳跃,发出“吁吁”的叫声。
大头不知道他会不会真找个人来帮他拽头。他希望不要。他害怕这个小孩找到的人拿来一根更长更粗的木棍。
大头的一只眼睛似乎被男孩戳中,钻心地痛。他的眼角被汗水浸泡,面前霞光万丈。他看到所有的鸡冠花都跳起了舞蹈,它们动作整齐,像有人为它们喊了号子;他看到那条狗淡漠地瞅着他,鲜红的舌头吐得更长;他看到那条蛇突然收起所有的脚,然后,从背上张开一对长满金色羽毛的翅膀。蛇慢悠悠地飞起来,划过他的眼前,飞过他的头顶。蛇低头看他一眼,眼睛里燃烧着黄绿色忧伤的火焰。
大头的脑袋疼痛难忍。他再一次想起自己早就口渴了。他想他应该喝一口水。喝一口水,眼睛就能看清了。也许那条美丽的蛇,就会飞回来。
可是大头喝不到水。不但喝不到水,他感到自己沉重的脑袋马上就要从脖子上脱落。大头害怕脑袋掉下来,就开始了哭泣。他不敢大声哭。他怕吓跑那只狗。还怕打断那些舞蹈的花儿。他垂着脑袋,闭着眼睛,压低着声音哭。哭声断断续续,像被人从一只塑料瓶子里挤出来,含混不清。
过了很久,大头才停止了哭泣。不是他不想继续哭,而是实在哭不动了。他睁开眼,吓了一跳。他发现,他的面前,站着一位佝偻着身子的老头。老头正眯缝着眼睛看他,嘴角有节奏地抽动。他不认识这个老头,他想这老头也许是别的村的。老头的脸上满是皱纹,老头的皱纹里满是灰尘,老头的灰尘里满是急急爬行的蚂蚁或者健硕跳跃的跳蚤。老头的手里拿着一根牛鞭,腰间别一个破旧不堪的军用水壶。也许他在附近山上放牛时经过这里,也许他是刚才那个小孩找来的帮手。现在他站在大头面前,不说话,也不动,身体僵硬如一段朽木。
大头说,老头,你是来戳我的脸吗?老头说你说什么?大头说,老头,你是不是来戳我的脸?老头说你得叫我爷爷。谁把你弄成这样?大头说一个小孩。他装成不认识我。老头说他是怎么把你弄成这样的?大头说他拿棍子戳我的脸。老头说,这个狗娘养的。大头说他不是狗娘养的,他爹是村里的会计。老头说他爹是联合国的会计也不行,怎么能这样丧尽天良呢?大头不懂丧尽天良是什么意思,他想了一会儿,没想明白,就不再想了。他说老头,你能不能帮我把脑袋拽出来?老头说你得叫我爷爷。你脑袋怎么回事?大头说,我痛。老头往前迈一步,他说我知道你痛。我问你是怎么把脑袋钻出来的?大头说,我好痛。
大头的脑袋就挂在老头的脑袋的斜上方。他盯着老头的脑袋,盯着那一头白发和跳蚤。跳蚤们在白色的丛林里穿行,彼此打着手势,开辟着属于它们的疆土。然后,那片白色的疆土慢慢向后倒去,大头的面前再一次出现一张遍布沟畔的老脸。一张黑洞洞的嘴从沟畔中突兀出来,像一口废弃的老井,散发着臭哄哄的气味。那口井说,小孩,现在别动。老头努力伸展着自己的弯腰,踮起脚尖,两只手各抓住一个卡住大头脖子的窗棱,咬着牙向两边拉。
可是两根窗棱纹丝不动。老头每拉一会儿,就命令大头退一下脑袋试试。大头严格地按照老头的命令去做,可是他的脑袋就是退不回去。仿佛那两根窗棱变成一只不讲道理的夹子,紧紧地夹住了他的脖子。终于,老头放开窗棱。他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喘了一会儿,又拿一根很粗的草棍抠牙。
大头有些着急。他希望老头继续。他说,老头,我想出去。老头说,你得叫我爷爷。你不是想回去吗?大头说,回去也行。老头说,唉。
老头又试了一次,还是没有成功。他不得不停下这种徒劳无功的尝试。他说要不你就这么待着吧,等你娘回来再说。大头说我没有娘。老头说那等你爹回来再说。大头说我爹下地了。老头说那也该回了。他抬头看了看大头,顺便又看了看太阳。他说,天都晌午了。大头说我不知道爹什么时候回来。我渴。老头说那就这样,你告诉我你爹在哪里,我去帮你找回来……你爹叫什么?老头一边说一边打开他随身携带的军用水壶,把壶嘴塞进大头的嘴巴。大头贪婪地喝一口水,被呛住,剧烈地咳嗽起来,水喷了老头满脸。大
头一边咳嗽一边说,爹叫孙进举。
老头的眼睛马上瞪圆。他说你爹叫什么?大头说爹叫孙进举。老头说就是那个喝酒把老婆喝跑了的孙进举?大头说爹的老婆就是我娘,爹说娘去城里了,不是跑了。老头说就是那个偷了我的牛却死不认账的孙进举?大头说老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渴,我还想喝水。老头说,你喝个屁水。
老头把水壶拧紧,重新挂回腰上。他说你爹去年偷了我的牛。他把牛卖了。我和他闹到派出所。他死不认账。你爹真贱骨头啊。嘴比石头还臭,还硬。派出所说没证据。没证据也是他偷的!你知道那头牛能卖多少钱吗?两千多块啊!两千多块,十个你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
大头说我知道了,老头你去喊我爹回来吧。我好像快要死了。
老头说你死不了。你爹是个坏种,你肯定也是个坏种——如果你不是坏种,脑袋怎么能被卡住呢?坏种都死不了。让你替他受点苦,我心里还舒服一些。也算对得起我那头老牛。你在这里慢慢等你爹回来吧。说完,老头转了身子,要走。
大头看着老头。正午的太阳越来越炽热,大头感觉自己的头发上着了火。不但头发上,整个脑袋都着了火。脸,眼睛,鼻子,嘴。他特别渴。刚才喝下的那口水全都被他喷到了老头的脸上。他盯着老头的后脑勺。他现在,非常需要一口水。
老头突然转过身来。老头仿佛猜中了他的心思。老头说,你渴吗?大头点点头。他的头很痛,似乎马上就要爆炸。点头的动作增加了痛的程度。可是他还是使劲地点头。老头说你想喝水吗?大头再使劲地点头。老头笑了。他说,你喝个屁。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头终于大声哭起来。他把嘴巴咧开,做出痛不欲生的样子。可是他马上停止了哭泣。嘴巴的动作牵动了脸上的肌肉,那里好像有人在拿着凿子不停地凿。眼泪流下来,让他眼角和脸上的伤口雪上加霜。那里似乎已经溃烂,几只苍蝇围着他受伤的半边脸嗡嗡地旋转,它们不时俯冲下来,瞅准机会吮吸着他黏稠腥臭的脓血。也许它们还把蛆虫屙在他的伤口里,他感觉那里有成千上万只软体动物在爬行。
世界暂时安静下来。大头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晕倒。可是他不能晕倒,那样的话,他想,自己会被吊死在窗棱上。他见过吊死的人。死人挂在房梁上,眼睛瞪得很大很圆。那眼珠异常凸起,让大头想起集镇上养在玻璃缸里标价出售的美丽的金鱼。大头还闻到一股又臊又臭的气味。爹说,那是被吊死的人临死前屙在裤裆里的屎,撒在裤裆里的尿。他们为什么要在裤裆里屙屎和撒尿,大头搞不明白。但现在,大头知道,自己正把一泡尿撒进裤裆。那尿也是滚烫的。烫得大头不停地哆嗦。
他把尿撒进裤裆,因为他实在憋不住了;他把尿撒进裤裆,并不仅仅因为他被卡住了脑袋。大头常常把尿撒进裤裆,几乎天天如此。大头的裤子很少有干燥的时间。大头的屁股上长满了红色的有一个小白尖的大疮。大头没有办法,他没有胳膊,没有手。
大头盯着鸡冠花丛。他的眼睛在霎时间有了一种异常的清晰。他看到一条躺得笔直的蚯蚓。他知道那是一具蚯蚓的尸体。确切说是一具干尸。昨天夜里下了雨,这只蚯蚓肯定兴高采烈地拱出地面。地面上的枯枝烂叶肯定让它无比欢愉,可是它想不到太阳出来得这么迅速,这么猛烈,它来不及钻回潮湿的土地深层。它流下伤心绝望的眼泪。它被太阳一点一点地烤干,烤熟,烤焦,烤糊,变成黑色的泥土。想到这里大头忘记了口渴。他想自己会不会也被太阳烤焦烤糊呢?爹回来,他的脑袋已经熟透了。爹轻轻一碰,那脑袋就将滚落地上。大头再一次伤心地痛哭起来,他眼睛以外的肌肉一动不动,他不敢动。那样会增加他的痛苦。他只有眼睛在哭。只有眼睛在哭的大头,淌下了一脸盆的眼泪。
……如果大头还有胳膊,还有手,他想他会攀上窗台,在窗台上坐下。那样他的处境会好很多。其实,如果他还有胳膊还有手,爹肯定不会把他锁在屋子里。他会跟着爹下地,抓几串蚂蚱,或者把爹拔下的杂草抱到地头。也许他还会去村里的小学校里读书,坐在教室里和一群小孩一起念aoe123上中下人口手。可是他的胳膊和手突然间就没有了。烧焦了,锯掉了,扔进了医院的垃圾箱。那一天大头没有恐惧。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他战栗不已。
雨后的村子里到处都是水洼。大头喜欢水洼。他喜欢光着脚在水洼里疯跑,把浑浊的水溅上别人的裤管。他还喜欢把比他小或者比他大的孩子的脑袋按进水洼,灌两口黄泥汤。那时候大头的身体异常强壮。村里有人从城里打工回来,看到大头,说,你真像个小施瓦辛格。大头不喜欢别人这样叫他,他觉得这个名字又长又怪,不好听。大头喜欢爹叫他驴崽。大头见过驴崽。他认为驴崽很漂亮,名字也中听。
那天大头照例在水洼里疯跑。他跑着跑着就跑出了村子,跑到了田野。田野里有一种很浓烈的甜中带腥的气味,那气味让大头深深陶醉。突然大头看到一根裸露的电线,那根电线本来距他很远,静静地躺在地上。可是突然间那根电线就开始了不安的抖动,然后像一条蛇般朝他爬过来。大头惊呆了。他忘记了逃离。他望着那条越爬越快的电线,竟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他甚至向那根电线伸出手,急切地抓住了它高高抬起的头颅。
一霎间大头感到一种极其舒服的烫。他想躺下来美美地睡上一觉。他的眼前五彩斑斓。
目击者后来说,那天,他看到一截被刮断的高压线在地上呼呼叫着冲向一个男孩。那男孩蹲下身子,眨眼间,变成一团火……
突然大头看到了春嫂。在大头接近绝望的时候,他看到了春嫂。春嫂低着头急匆匆地走,并没有注意到大头。春嫂每一次从大头家的门前经过,总是低着头急匆匆地走。大头喊,春嫂。春嫂低着头,却抬了眼。春嫂看见了大头,马上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她用一只手嘭嘭地拍着自己的胸脯,飞快地跑向大头。她说谁把你打成这样?
大头对她的问题并不感兴趣。大头说,我渴。
春嫂说快告诉我,谁把你打成这样?
大头说是一个小孩,他装作不认识我。他拿棍子戳我的脸。现在我想喝水,我好渴。春嫂这才发现了问题的所在。她摸摸大头血肉模糊的脸。她说谁这么伤天害理?大头你被卡住了吗?大头说,我被卡了很长时间。春嫂说你能拱出来吗?你试试能不能拱出来。大头说我拱不出来,我试了很长时间。春嫂说那你试试能不能退回去?你试试。大头说我也退不回去。我的头太大了。春嫂说你没事把脑袋伸这里面干什么?大头说我想看鸡冠花。现在我好渴。春嫂说没事你看鸡冠花干什么?你爹呢?大头说我爹下地了。现在我想喝水。春嫂说你渴吗?大头说,是。春嫂我想喝水。
春嫂并没有着急给大头弄水喝。她踮着脚尖,往屋子里看。她的个子不高,她什么也没有看到。她问大头你被卡了多长时间?大头说我不知道。她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大头说我现在想喝水。春嫂说好,你等着。我去给你弄水喝。
春嫂慌慌张张地跑开。很快,她跑回来,拿着一瓶水,抓了一把草木灰,怀里还揣着一块油饼。春嫂把瓶口对准大头的脑袋,说,你快喝。大头喝一口,再一次被呛得咳嗽起来。春嫂又说,你慢点喝。大头却慢不
下来。他咕咚咕咚地喝着水,表情痛苦并且享受。春嫂随着他喝水的进度慢慢抬高自己抓着瓶子的手,终于,一瓶水被大头全部喝光。他用舌头舔着湿润的嘴唇,眼睛里露出明亮的光芒。春嫂说够了吗?大头说够了。我喝了一条河的水。春嫂说我先给你的脸上抹点药,再帮你去喊你爹。春嫂边说边把草木灰往大头的脸上按,痛得大头嗷嗷地叫唤。大头一边躲闪一边说你别抹啦你别抹啦。春嫂说,不。一定得上些药。
终于春嫂把最后一点草木灰按上大头的伤口。现在大头的脸完全变成了非洲黑,只剩两只眼白闪闪发光。春嫂说还痛吗?大头说痛。春嫂说还渴吗?大头说不渴了。春嫂说饿坏了吧?你先吃块油饼,吃完了,我给你去喊你爹。这个死人怎么都晌午了也不知道回家?她从油饼上掰下一小块,塞进大头嘴里。大头嚼一会儿,却吐出来。春嫂说怎么了?大头说,我吞不下去。春嫂说为什么吞不下去?大头说不知道。春嫂说再来一块试试。就又把一小块油饼塞进大头嘴里。大头贪婪地咀嚼着香喷喷的油饼,尽可能地吮吸着油饼的香味。咀嚼让他的脸变得更痛,可是他不想让自己停下来。这一次他仍然没能把嚼得稀烂的油饼吞下去。大头说我吞不下去。我的嗓子现在跟麦秸管一样细。
春嫂说大头你再稍等一会儿,我现在就给你去喊你爹。这个死人。春嫂每骂一声“死人”,脸就红一下。大头不喜欢春嫂,因为只要春嫂来到他家,爹总会呼嗤呼嗤地忙一阵子。忙完那阵子,爹就会像条死狗一样躺在炕上好久不动弹,连他跟爹要水喝,爹都懒得去舀。爹和春嫂的那事被大头看到过两次。两次都是正午,爹和春嫂都以为大头睡着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睡。一次正忙得快活的爹突然发现大头瞪着眼睛看他们,就甩给大头一记耳光。爹说,你敢说出去,我就宰了你。大头想,哼,我才懒得说出去呢。其实就算大头想说出去,也没有机会。他天天被他爹锁在屋子里。从他被锯断两条胳膊以后,大头过了两个年。由此大头推断,他应该被爹锁了整整两年。
春嫂急急地跑开,大头急急地喊住了她。大头说,你把门砸开吧春嫂。你砸开门。我受不了了,我要死了。
春嫂愣住了。大头说出这样的话让她非常吃惊。她说不能砸门的大头,不能砸门。砸了门,我和你爹的关系,更说不清了。再说也不用砸门,一把锁好多钱呢!我这就去喊你爹,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大头心想他们什么关系说不清呢?大头还没有想明白,春嫂就不见了。春嫂跑起来很快,像兔子。她一边跑一边骂“死人死人死人死人”,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白一阵红一阵。春嫂感觉自己的心蹦到了嗓子眼,她得用一个拳头堵着,那心才不至于蹦出来。
春嫂在半路上遇见了正往回走的孙进举。孙进举扛着锄头,穿着破破烂烂的汗衫。他的身边跟着一个男人,他和那个男人一边走一边说笑。那男人是孙进举的邻居,她知道他们常常在一起喝酒赌钱。春嫂及时地刹了脚步,转过身,往回跑。她不敢走上前。尽管该做的都做了,可是她从来不敢当着别人的面和孙进举说话,她认为那样不好。她的心跳得更慌。
男人捅了捅孙进举。男人怪声怪气地说,春妮子等不及了。孙进举就笑了。他说,一会儿抓紧时间给她来那么几下,她就舒服了。他一边说一边比划,动作形象逼真。两个男人站在午后的田野里放肆地笑。他们每个人点起一支纸烟。
春嫂跑回去,看到大头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春嫂吓了一跳,她说大头你死了吗?大头抬起头,说,我没死。他的脸红得就像刚从猪肚子里扒出来的猪腰子。春嫂说你不用怕,你爹马上就回来了。我刚才见过他,正往回走呢。大头说还有饼吗?春嫂说没有了,明天我再给你做,现在我得走了。大头说你走吧,我不喜欢你,可是我喜欢你的油饼。春嫂就慌慌张张地跑开。她一边跑一边嘀咕,明天,我肯定给你烙油饼吃。
大头看着春嫂的背影,想着明天的油饼,很开心。午后的太阳甩着七彩的鞭子,噼啪作响。一丛一丛的鸡冠花在阳光下开得娇艳。一条灰色的土狗从花丛里站起来,小心地夹起尾巴,懒洋洋地走远。一条蚯蚓被太阳烤焦,它黏在地上,越缩越短。
孙进举看见大头的时候,大头已经死了。他终于踢翻了脚下的凳子,挂死在窗棱上。那时春嫂刚刚转身,刚刚迈出离开的第一步。大头想探探身子嘱咐她千万不要忘记烙油饼,他的腿稍稍用了力,凳子就翻了。大头的身体刹那悬空,舌头霎时吐出很长。大头的世界重新变得模糊不清,所有的一切只剩下一个土灰色的影子。他在喉咙里面、在胸膛里面、在肚子里面、在脑子里面发出一连串奇怪的声音。他一遍一遍地喊着春嫂救我,春嫂救我,春嫂,春嫂,春嫂……可是那时候,鲜嫩的春嫂正在急切地逃离。
春嫂一边跑一边说,明天,我肯定给你烙油饼吃。
作者简介:
周海亮,男,生于20世纪70年代,《读者(原创版)》签约作家。中短篇小说散见于《大家》、《芙蓉》、《山花》、《飞天》、《长城》、《鸭绿江》、《雨花》、《芒种》、《红豆》等,有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选载。国内多家报刊有个人专栏,出版有小说集《刀马旦》,散文随笔集《分钟与千年》等四部。现居山东威海,职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