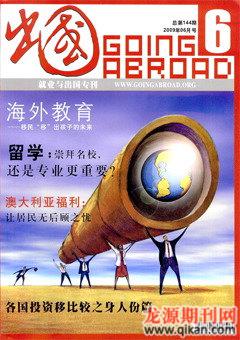我把伏虎罗汉留在了阿姆斯特丹
黄 凌
古物情结
小时候,几乎每周我都要在那个“坛子”冒几个泡,给那些在岁月的“残骸”里活得有滋有味的老头们添点儿乱。当知道和他们一起谈收论藏的居然是个15岁的小女孩后,震动得下巴集体脱臼。后来在那个男性主导的小圈子,我迅速凤毛麟角起来。
顺便说一句,那个坛子有个挺好的名字,叫“收古今藏”。
之所以爱收藏,还缘于我的爷爷。我家算得上是个书香世家,家里那几本泛黄腾灰的族谱上明确记载着“出产”过几个进士。爷爷在文革时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一个小村子,这反而让他如鱼得水,放完牛就偷偷到农民家里看那些当年一文不值的破碗烂盆。据他说,当时有很多好东西,眼睁睁地看着被毁掉,但因为没有钱,更不敢大张旗鼓地买卖,爷爷仅得到一只唐代越窑耳杯和一件明代鸡翅木案几,加起来也不过是个暖水壶的钱,那些日子成了爷爷在“放牛班”的春天。
我从小就是在爷爷收藏的满屋子红木家具里窜大的,感受着几个朝代几百年的岁月,那些古老的红木散发着辛香。爷爷说红木本来就是一味中药,行气、活血、止痛,闻闻味道也让人精神抖擞啊!
在我这辈人里,爷爷最疼我这个从小失去父爱的小孙女。他帮人做鉴赏时,总爱让我陪着,这也不是没来由的,对古物我有种年轻人少有的耐心与悟性,十三岁时我就能通读《金石录》,他想让我来继承他对古物所有的热忱。
在去荷兰读高中前,爷爷送给我一套清乾隆年问的紫檀罗汉。紫檀木至少需要八百年才能成材,心材小但致密,一般用来雕刻成小件艺术品,就连皇宫里都很少见到大件的紫檀家具,因其珍贵而被称为“木中之金”,它还会散发出一种叫做“木氧”的物质,这种物质不仅能够起到安神醒脑的作用,而且长期接触还能够促进细胞再造,预防皱纹的出现!
这套紫檀罗汉通高才8公分,活灵活现,大的褶皱处嵌有细细的金线,深沉古雅,手感温润,每个都被摩挲得泛着黑色的幽光,与金线的光泽交相辉映,简直是太漂亮了!它的价值可见一斑。
爷爷希望它们能保佑我在异国平安,我本来对佛教有种特别的情结,所以一见如故。只可惜,一套整的是十八个,爷爷只找到十七个,我数了数就少了个伏虎罗汉。
丹尼泽
五月的阿姆斯特丹,风还有些微的凉,阳光倒是不-懈怠把四处照得闪亮,难得课业之余的休息,我心痒痒地去了Waterloopiein。
这是个除星期日外都开放、以出售艺术品和古董为主的跳蚤市场。转悠了一上午,只收获了满目精致,想来捡漏的好心情渐渐消失了。疲累的我无目标地跟着一堆人停在一个摊位前。粗略看了下,是卖自行车模型的铺位。小模型确实精巧,居然还带遥控,再看摊主,是个花白头发的老人,也不太招揽生意,自顾自在一推铁皮、铁丝里切切割割。倒也怪,那些生冷的铁在他手里孩子般听话。
他的动作如此轻松,如同裁切的只是一堆纸,再细细地看,Oh,my god!弯月般的刀刃下,荡来荡去的不正是我要寻找的伏虎罗汉吗?只是不知谁在它头顶装了个铜圈,被当作饰物挂在了一柄刀上。想来是入世劝人“放下屠刀”到了极致,已经不顾一切的到市场里悬在刀下,置生死于度外了。这尊挂在现代感极强的银灰色坚毅小刀下的古朴温润的中国紫檀罗汉,许是释迦牟尼深埋在市侩刀身下的佛心。
“小姐?”一个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
“啊!”我一惊,发觉自己的头不知何时,近得几乎要贴上老人的鼻子。
“哦,对不起,我想买,哦,不是,不是买。”我语无伦次,完全忘了捡漏需要的镇定自若。
老人中止活计,兴致盎然地看向我。
我慌忙操持起磕巴的英语:“是这样,我一直在找一样东西,真没想到今天在您这看见。”突然问,怕直接说明来意后,他不让给我,就撒了个谎:“我说的是您手上这把刀,我想您是不是能考虑把它卖给我,对,卖给我,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就在我搜刮词句准备进一步阐明我是如何热爱这把刀,曾经寻找得何其辛苦时,老人已经微笑着给了我一个坚定的摇头:“对不起,这刀可不在我的货品单里。”
“可是,可是,我……”
“对不起,刀是不卖的。”说完,老人低下头重回他的模型世界。
继续纠缠显然不是好主意,我只得退去一旁,远远地看着。
伏虎罗汉像是勾我魂魄的丝线,此后连续两个周六,我早早就去他的摊位旁,充分运用迂回战术,不谈伏虎罗汉,也不谈刀,只聊家常。没多久,我便直呼他丹尼泽,知道他退休前是园艺师,家就在附近。再后来,我主动出击,不只给他打下手,还帮着招揽生意。在我卖力吆喝下,丹尼泽先生的模型销量爆涨。周围不明就里的摊主直夸丹尼泽找了个好帮手,唯独丹尼泽对此反应平淡。
心病
深夜,我醒了,那晚母亲打电话催我回国的声音又一次将我从梦中惊醒,掐指一算,从爷爷离开的日子到今夜,已有一年了。
我想象不到爷爷走后,我的身边会出现那么多表情狰狞的人,五花八门的说辞,只为了把那满房的古董碎尸万段。正如生命中也曾经有过花团锦簇的时光,只是一场大雪就将人生的轨迹抹了去,在相反的方向勾上一笔。
我不知道当爷爷的古董被撕扯着离开老房子时,它们的心情会如何,会像一个饱经人间风霜的红尘女子,不等安身几日,就又一次被人拿去变了烟火钱吗?
我是在突然间又看到了爷爷拿着细软的毛刷柔缓地将它们身上的灰尘轻轻拂去,每一下却都拂在我心里,把尘封的往事都弹拭得清清楚楚,任冲撞而来的人在我左右光影掠过,我又呼吸在辛香红木的过去。
爷爷就躺在那里,但我能看出,他的脸上还有疼爱我的表情。母亲在我身后痛断肝肠,不断呼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让老人家去吧,否则他看到你这样怎能安心?”
我喃喃着:“不会的,不会,他都睡着了,怎么会知道。”
从此世界上少了个爱我的人,对于我而言,爷爷扮演了祖父和父亲两个人的角色,当一个人突然不幸地失去了宠爱时,她就会努力寻找关于爱的支离片断,而我寻找的是双份。
回到荷兰,我梦魇般从丹尼泽的小刀上发现伏虎罗汉,它竟让我介意得夜不成眠。我不休止地想要得到它,要借它的“肉身”凑个整数,给爷爷捎去积攒多时的眷恋,却又不敢声张对它的觊觎,怕一惊动就今生无缘。我磨蹭着自己的来意,有好几次猛地被丹尼泽的顾客打断被它牵走的目光。
赴宴约定
没有了爷爷在经济上的资助,母亲这时已经无力让我在荷兰读书了,我又坚持不肯变卖家里被瓜分得所剩无几的古董。随着回国日期的临近,我对于从这个固执老头手里买伏虎罗汉的信心急速锐减。回国前最后一个周六,已死心的我决定还是去看看丹尼泽,也算一个道别。听他说过挺喜欢吃中餐,我便用上午时间烧了几个拿手的中国菜,盛在小饭盒里带了去。
远远的,就见丹尼泽以他永远不变的姿势窝在摊位后。我悄悄走近,学着送外卖的口吻说:“亲爱的丹尼泽先生,这是您叫的中国餐,请您尽情享用。”边说边打开盒盖。丹尼泽的眼睛猛然亮了下,说了声谢谢就不客气地接过饭盒,以风卷残云之势将
盒内所有固体与汤汁卷入肚中。他吃得如此投入,我不免心生愤恨,这老头,从来当我的付出是应该似的。实在气不过,我便挑高声调:“唉,可惜啊,这么好吃的菜也只能吃这么一次了。”
“为什么?”
这老头,还好意思问。“很简单,我要回国了啊。带着我那颗充满遗憾的、被无情的人伤透的心。”一边说我一边做出痛苦的表情。
丹尼泽见此情形大笑起来,说实话,那次一分钟内帮他卖出7辆车都没见他这么高兴过。
“苏,你的厨艺真不错,今晚,愿意去我家尝尝我做的饭吗?”
“哦?”终于良心发现了?不吃白不吃,我爽快答应。
紫檀伏虎罗汉
“来吃饭吧。”丹尼泽的声音突然在我身后响起。见我在看照片,他低低地说了句,“那是安娜。”就离开了。那一刻,在他略微佝偻的背影里,我只看见深深的落寞,而在鬓角站立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让我想到了爷爷。
刚坐下,丹尼泽先举起杯:“苏,谢谢你能来。”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么一桌菜,真是太丰盛了。”这并非恭维,“半大的孩子吃穷爹”,那天,桌上至少堆了10个盘子。晚餐气氛融洽地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一道甜品吃到接近尾声时,丹尼泽把一个包装好的小盒推到我的面前。
我有些紧张,我已不敢再有什么希望,可又止不住地想要一个希望。我没动礼物,而是紧紧盯住丹尼泽的眼睛,他也看着我,忽然轻松地说:“罗汉终于要回国了,我想你大概就是为了它而来的吧!”
没错,你也一定猜得到,盒里装的就是那把刀和伏虎罗汉。让我诧异的不是丹尼泽会把它们送给我,而是当我扎实地把它们握在手里,内心却突然沉静下来,静得遮蔽了预想中的兴奋、激动、喜悦。我更愿把这样的馈赠,当作一份慎重的托付。我收下了刀,趁丹尼泽不注意,从刀身下取下伏虎罗汉放在桌上,希望它能照顾好这个孤独的老人。
如今,每每用脸颊摩挲那十七个紫檀罗汉做“木氧”护肤时,我就会想到爷爷,想到那些透着红木辛香的年轮脉络,想到那个在异乡入世的伏虎罗汉。想起丹尼泽,想起他花白的头发,浅淡的情绪,想起餐桌旁他举杯说谢谢我陪他过68岁生日时的声音,想起他说“本以为安娜过世后的第一个生日会是一个人和一瓶酒,没想到还能这么美好”时,鱼尾纹里的温馨。
每当有朋友问起那把刀的来历,我会很模糊地说朋友送的,好像要刻意保护好它的背景。不是不知道分享,只是有些东西的珍贵,只有走过那段追寻的旅程,才会懂得。
现在我已经不会再去刻意追寻某件古董,因为我明白它内心的孤独,多少年的岁月里,它与同胞疏离,命运多舛,而又坚强地一路走来,我不过是它见到的一粒微尘,将它放在合适的地方,懂得它,喜欢它,远远地看着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