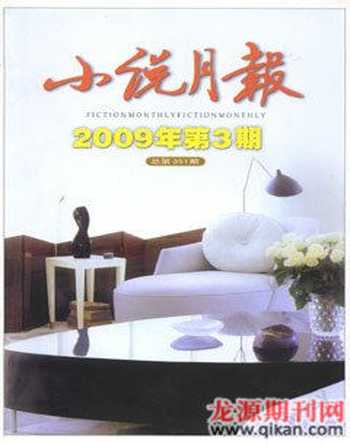夏洛蒂的地毯
雷 娜
连续工作六年之后,夏洛蒂决定辞职,搬家。她在一条新开通的地铁线尽头租了一间公寓。那里是这座繁华都市荒凉开阔的边缘,晴天的傍晚可以看见很美的落日。租金便宜,道路宽阔。
搬去之后,她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整理家居。清洗房间的角角落落,搭起从旧居搬来的黑色铁艺床,铺浅咖啡色的床单。将沾满灰尘的窗帘拆下来清洗,用消毒水擦拭衣柜,将衣服分门别类放置。搁一小瓶薰衣草精油在衣柜中,用来替代樟脑丸。她去宜家订购一些家具,方格子书架,CD架,储物柜,可以放化妆品的琥珀色边桌,向保安借了一把锤子,自己动手安装。从清晨至黄昏,木板和螺丝散落在卧室中央的地板上,场面近乎狼藉,她坐在地上皱着眉研究图纸,内心笃定。到底工作了六年,知道坚持和信心的意义,不将所有的可能都试一遍,她不肯轻易示弱。这项浩大的工程耗费了两天光景,她甚至因此瘦了。
这样一个窝,在她手中一寸一寸充实起来。房东太太留下了浅橘色的纱幔窗帘,质地轻薄,深夜里,窗外的星光灯光会游进来。她害怕黑暗,睡觉时喜欢开一盏灯。这让她觉得安全,世界像是洒满阳光的幽深的树林,她睡在一小片阴影中,但一转身就可以回到光明。
她每天睡到自然苏醒,打量房间里的一切。书架上整齐地摞着书,沙发上歪歪倒倒的靠枕和玩偶,是从少女时代至今的玩伴。墨绿色的围巾覆盖在可以将整个人窝进去的宽大椅子上。那是件镶银丝的美丽织物,流苏从椅背垂落下来,姿态像琴弦一样优雅。
她从床上一跃而起,将需要洗的衣服一件件塞进洗衣机,老式的洗衣机在浴室发出低沉的轰隆声。她俯身清洗地毯,用牙刷和洗涤剂对付每一处污渍。正午的时候,用尽全力将那块白地碎花地毯拖到阳台上,赤足站在上面晒衣服。郊区视野开阔,对面青灰色的高楼与天空的颜色正相宜。她试着打开所有的窗户,风呼啦啦地扑进来。各种颜色的衣服相互击打,像飓风中蝴蝶的翅膀。她心里觉得畅快,连空气也更新了,渐渐不再有经年的暧昧的味道,是来自高空的洁净干燥的空气。
就这样开始新的生活。虽然失业,失恋,藏有隐疾,却有种身处谷底的宁静喜悦。她觉得人的情绪是复杂的,一个人的经历可能不幸,但这个不幸的人拥有的快乐可能比一个幸运的人更多。日子百无聊赖,她不扑粉,裸露着苍白面孔上淡淡的雀斑,穿一件灰色的羽绒服,牛仔裤和球鞋,到楼下乘公交车熟悉周围的环境。那些街边的小店,就像是一格格的蜂巢,外壳黯淡斑驳,里面却流淌着醇厚的世俗蜜意。饭馆、旅社、幽暗的美容店、成人用品商店、五金店、汽车修理铺。她在窗口一格一格饶有兴味地数过去,觉得自己仿佛变回了一个孩子,温顺地瞪着这个和平孤单的世界。这里没有西区的法国梧桐,冬日树叶落尽,影子写在灰白的马路上,也有一份朴素的诗意。有时她看腻了,拉下帽子遮住眼睛靠在车窗上睡觉。她不担心坐过站,这是一段环形的路线,终点就是起点。
她的身体中有一个纤维瘤,痛不可当,终于下决心做手术。她去医院预约了手术时间,回来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什么,问门卫:“这里有介绍钟点工吗?”门卫是位六十来岁的老人,面孔清瘦饱经风霜。夏洛蒂低头看门口黑板上的通知,字体简净有力,像是练习过书法的人写出来的。老人摇头,她说了声谢谢转身离去。“哎,”老人在身后喊住她,“十六楼有一家好像做的,我带你去问问?”“好。”
她微笑,将手插在羽绒服的宽大口袋中,站在原地等待。她和老人一同乘电梯。狭窄的电梯间,老人身上散发出浓郁刺鼻的烟草味。电梯停落时发出清脆的“叮”声,她沉默地跟着,来到一户人家门口,敲门,一位五六十岁的阿姨走出来,老人用带郊区口音的上海话同阿姨交谈了一会儿,转身对她说:“她愿意做的,你把要求和她说一下吧。我先走了。”夏洛蒂看着老人的背影,披着军大衣,腰板挺得笔直,硬是把沉重的衣服穿出了几分轻盈。她掩不住笑意,阿姨一直等待与她交谈,看她笑得灿烂,也同她一起笑起来。这一笑便把两人距离拉近了,人一旦年纪大了,退到社会的边缘,有时神情比成人更加天真。夏洛蒂心想,她应该是个随和易处的阿姨。
她站在门口,轻声交代,她需要做一个小手术,想找一个人帮忙做家务,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做最清淡的家常菜就好。报酬一千元,您看可以吗?”“可以啊。”阿姨脸上的皺纹随笑容荡漾开,夏洛蒂望着她,觉得老成这个样子真好。后来,她渐渐听说,阿姨的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在外地上大学,丈夫前年中风,退休金不多,因此她在楼中做些家政工作补贴家用。但是儿子寒暑假回家来,她是不做的,雇主也帮她隐瞒。夏洛蒂无意与人过分熟稔,但心里对这位阿姨更多了几分善意。
手术的前夜,夏洛蒂费力扑灭了给林恩木发短信的念头。她因此而做梦。她梦见一只鸟,被鲜艳的气球吸引,徒劳地追逐它。距离越接近越恐惧。它们不是同类,不能拥抱和交谈,不能一起结巢一起取暖,鸟觉得累了,于是停落,望着气球飞走了。夏洛蒂在暗夜中醒来,温习刚才梦中的画面。城市淡青色的天空,密密麻麻灰色的水泥森林,因为一只飘扬的气球而显得恍如童话。仿佛是看过这样一幅类似的画作,在一本艺术杂志上。想起来黯然神伤,他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告别,那次分手简单到只有一来一往两条短信,“一切都结束了吗?”“是的,只能这样了。”她本来在工作上就已经心力交瘁,于是辞职,静静地做完了最后一个月的工作,消失。
这个结局一开始时她就料到的。在他们的圈子里,他是个声名狼藉的浪子。最初相遇的时候,她是他的猎物。她想要逃开,却不能够。有一天想通了,径直走过去,对他说,我喜欢你。那是在公司顶楼的阳台上,春末夏初,浓妆艳抹的她在太阳底下像个快要融化的彩色冰淇淋球,他有些诧异,他是想要她的,按照自己设计好的驾轻就熟的方式。她却将一切搅乱了,她不在他想象之中。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拥抱了她。
夏洛蒂以前工作的公司,是那个城区最壮丽的建筑之一。黑色,连玻璃幕墙也是半透明的黑色,楼体被分割成两半,中间以优雅的线条相连接。像天地间一块神秘的矿石,静谧的夜里神灵路过时的歇脚之处。夏洛蒂每天上班,总要向上望一望,楼顶的人看上去就像蚂蚁一样渺小。曾经有一天,她和她爱的男人在那里拥抱了,于是他们的痛苦欢乐在阳光底下也像蚂蚁一样微小。
再见,青春。她对自己说。她赤裸上身躺在手术台上,觉得像是丛林中一只受伤的小兽,恐惧和屈辱像水蛭一样慢慢地贴紧皮肤。她想起以前工作时上司对她说,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可以弱化痛苦。于是她深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滴露水,从树叶上滑落下来,掉在地上,然后慢慢地渗入土壤中。这是个小手术,局部麻醉,过程冗长难堪,终于结束。
在回来的出租车上,伤口开始慢慢苏醒。她对司机说,放些音乐吧。年轻的司机先生打开CD,流淌出的音乐是小田和正的《再见》。夏洛蒂想起他唱的《东京爱情故事》。那时她正在读大学,这中间横亘着十年时光。她看着自己投在车窗上的影,轮廓细致,略显憔悴,不能说不好看了。生命是加法,也是减法,来来往往,不得圆满,也不会在一夕之间崩盘。她开始体会到命运的残忍了,当她弓着背,让伤口悬在衣服底下温暖的空气中的时候。她就这样玩完了。她在疼痛中微笑了。
她回到居室,在浴室的镜子前脱下衣服。切口比她想象的可怕。虽然医生说,会慢慢愈合,到最后会一点也看不出,但却没有告诉她到底要等多久。她对着洗脸池干呕,打开水龙头,幽深的下水道发出咕咚的声音。饱吃蒙睡、忍耐等待,一切都会好的。她对自己说。
她打开电脑,在网上银行查了一下存款数额。数目尚足够她优哉游哉地过上一年半载,可是想到每三个月一付的房租,立刻觉得岌岌可危起来。她打开邮箱,写信给朋友,请他们给她介绍一些兼职来做。每个月做四五次口译,不会很累,又足够支付房租和生活费。剩下的空余时间,她可以去翻译一本小说,这是她大学时代的梦想。她是英文系毕业,除了一口流利外语别无所长。有一天,她看见MSN上艾米莉的签名是:“英语能力于我,犹如性能力之于男人。”她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她们是批量生产出来的同一类人。
只是那个隐秘的伤口,还藏在她身体显要的位置,犹如一个烙印。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这次手术,有种莫可名状的自卑。又过了一个月,艾米莉写信给她,说要来上海找工作。她回信说,过来吧,过来做饭给我吃。
艾米莉是她的大学同学。她们一同参加英文话剧团,她演《简爱》中的简爱,艾米莉演《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她还记得艾米莉在台上演出凯瑟琳和希克厉生离死别的片段,舞台明亮的灯光之下,艾米莉穿月白色的长袍,被男主角捧在双臂上,漆黑蔓长的头发垂落下来。她的美是这出蹩脚剧目唯一的救赎。“那些伤害我的人,我可以原谅他们,可那些伤害你的人呢?让我怎么原谅。”泪水落下,帷幕合上,台上台下的故事依然继续。她和那时的男友在台下观看。那个理工科的男孩子,英文不好,她一句一句翻译给他听。她偷看他的侧影,舞台的亮光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轮廓,非常优美。夏洛蒂每次想起艾米莉,思绪最后总是落在了曾经恋人那里。少时玩伴不懂得隐藏和自我保护,常常把什么都搅和在一起。
夏洛蒂翻箱倒柜,从一堆旧物中找出新的拖鞋、睡衣、牙刷、毛巾。她以前是有恋物癖的,最近在搬家的烦琐中才渐渐体会出简洁生活的好处。她将搜罗出来的物件搁在地毯上,心想应该齐备了,只是家里没有酒。她站起来,换了身衣服,去超市买酒。天色暗了,门卫老人和阿姨正在小区门口站着聊天,看见她愉快地打招呼。两个小女孩在安抚一只怀孕的白色流浪猫。夏洛蒂在货架上选了一种法国葡萄酒,回到家中,用开瓶器缓慢地将木塞旋转而出。她站在阳台上喝酒,对面楼上有一家的窗户闪着微弱的彩色的光芒。她仔细分辨,是一个小孩子在玩悠悠球。小球上下翻飞,技术纯熟。仿佛那个发光的小球是个具体而微的地球,这世界全在他的手掌之中。夏洛蒂想起自己小的时候也爱玩这种游戏,将那个发光的小球推出去,又安妥地回到手心,她那时想起的是灰姑娘的南瓜马车。
艾米莉的航班夜里才到。夏洛蒂将手机开着,留心听楼道的声音,但终究撑不住睡着了。将她吵醒的是门铃声。她跳起来冲过去开门。一个长发纤瘦的女子裹着厚厚的羽绒服逆光站在门口。“亲爱的。”她拉住她的手,递过去那双锦缎绣花的拖鞋,“换上吧。”艾米莉有点发愣,她原以为她们是要拥抱的。但那双精致无匹的拖鞋立刻吹散了她的疑云,她站在门垫上,脱下鞋子,卸下沉重的外衣。“今年上海的冬天也蛮冷的。”“可不是?”夏洛蒂靠着玄关的墙上,端详着她的女友。一头褐色卷发微微干燥,吊儿郎当的宽大毛衣,在昏黄的灯光之下,整个人都有些毛茸茸的感觉。像个娃娃,搁在橱窗里太久有一点点旧的那种。
她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大学开学第一天。她在上铺整理床铺,一对父女走进来,他们长得很像,一个文雅的中年男人和他白皙清秀的女儿。他们站在一起时,就像是一枚银币妥帖到极致的正面和反面的图案,显示着造物主的幽深莫测。女孩束着马尾辫,米色的背带裙,里面衬白色的衬衣,乖巧地站在窗边,她的父亲帮她整理床铺,夏洛蒂忍不住盯着他看,她自幼父母离异,没有见过一个这么有耐心做着琐碎事务的男人。她很好奇。
夏洛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艾米莉。美貌女子大抵分为两种:一种骄傲张扬,仿佛是天经地义的公主;一种低调世故,有着与年龄不符的城府。艾米莉是前者,年轻的女孩子哪里懂得忍耐,室友都不太喜欢她,只有夏洛蒂对她好。一些年之后,她自省,发觉这并不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更宽容大度,而是因为她喜欢她父亲的缘故。大二那年,她们一同恋爱,夏洛蒂的初恋很快无疾而终。艾米莉的恋情却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那是外语系当年最青年才俊的男生,她一毕业就嫁给了他。当时夏洛蒂在上海上班,她特意去苏州买了一件婚纱送给他们。她把它装在白色的漆皮的盒子里,寄了过去。艾米莉没有告诉她收到没有。一年之后,他们离婚了。夏洛蒂没有问艾米莉离婚的原因,因为她的心里有些阴暗的猜测。青春年少的艾米莉其实是个美貌妄为的女子,在大学时代,就曾经有几次秘密的劈腿事件。她想,多半是她没有玩够,又闯出了祸,何况她的缄默也暗合着夏洛蒂的猜想。
艾米莉利落地脱下衣服,对夏洛蒂说:“用一下你的浴室。”“好。”过了一会儿,她探出湿漉漉的脑袋,“过来,一起聊天。”夏洛蒂做了个无奈的表情跟过去。谁让她们是可以裸裎相见的朋友。艾米莉在雾气氤氲的浴帘后滔滔不绝地讨伐前任老板的恶行,夏洛蒂有一句没一句地听,偶尔做出愤怒状。她忍不住观察浴帘之后艾米莉的身体。她很瘦,但窈窕细致。至少在女人眼里,这样的身体是美的。她移过目光,对面的镜子上雾气弥漫,投在里面的影子只剩下淡淡的色块。那个这些天被她观察无数遍的清晰伤口仿佛还藏在里面,只要唤一句咒语,就会浮现出来。“这里太热了。”夏洛蒂打开门,走了出去。
她们俩坐在地上,喝酒聊天。分开的时光是六年,中间唯一的一次相聚,是在夏洛蒂到北京出差的时候。她们聊起毕业后各自交往的男友,语气平淡得就像讨论电视劇中的情节。夏洛蒂犹豫了一下,没有提林恩木,艾米莉也没有提起她的前夫。能够说出口的,都是愿意挣脱,舍得忘记的。夜深了,她们扯下被子在地板上继续聊,累了各自睡着。半夜,夏洛蒂从一团灰蒙蒙的梦境中醒来,懵懵懂懂地抱着被子回到床上。艾米莉在地毯上睡得沉酣,将被子裹得像个蚕茧,面孔也埋进去。夏洛蒂靠在枕头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觉得她纤美外表下其实藏着一个吉普赛女郎的灵魂,带着一小包衣服和一块无印良品的肥皂就冲到她这儿来。仿佛游戏人间,又似乎懂得在万丈红尘中保护自己。夏洛蒂觉得自己在妒忌她,又那么喜欢她,她也分不清自己的感情。有时候,人与人的感情一直推敲下去,都是说不清楚的。
她们的同居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相亲相爱,岁月静好。艾米莉喜欢外出,夏洛蒂乐得将买菜逛超市等工作都交给她,至于逛街,夏洛蒂因为不喜欢所以绝不奉陪。艾米莉形容自己坠入陕西路附近小店犹如蝴蝶飞进花丛中。夏洛蒂笑着说:“蝴蝶采花只是填填肚子,你是整天换翅膀。”艾米莉一袋一袋地往家运衣服,在镜子面前试穿。“这件你穿不错啊,送给你了。”她将自己心生悔意的衣服塞在夏洛蒂手中,直至夏洛蒂打开衣柜,对艾米莉说:“以后我们的衣服放在一起,大家随便穿吧。”“好啊。”身边有个热闹的人,夏洛蒂觉得自己渐渐健康起来,她决心先着手翻译小说。艾米莉也开始找工作了,投出了一堆简历之后,并没有下文,情绪低落。一天,夏洛蒂坐在沙发上,看着艾米莉的背影,若有所思地说:“我以前的公司,我辞职之后那个职位需要招人,你愿意去吗?我帮你问问。”“当然愿意。亲爱的。”艾米莉转过身,朝她做了个鼻子眼睛皱成一团的鬼脸。
夏洛蒂有些后悔,她应该想到,艾米莉是那种强悍的植物,一旦扎根在某种环境中,就会不断地向四周汲取养分。读书的时候她们俩共生共荣,而这次,她不幸成了她的环境。“无论如何,让她工作再说。”夏洛蒂心里暗想,拨通了电话,那个职位真的一直空着,她为艾米莉预约了面试时间。
面试之后,艾米莉变得沉默。“不顺利吗?”夏洛蒂问。“没有,他们录取我了。”“那你還愁眉不展的样子。”“怕做不来,”艾米莉靠着夏洛蒂坐下,把头搁在夏洛蒂的肩膀上,“你以前上班都穿什么衣服?”夏洛蒂放下手中的小说,坐直身体,“都穿职业装,你没有,就穿我的吧,反正我也不穿了。”夏洛蒂有些送佛送到西的心态,因为她的家离公司很远,她想艾米莉一定工作没多久就该想着搬走了。多年的友谊,在短短一个月的相聚之后就变质了,就像是兴冲冲地从柜子里取出一张珍藏的丝绒桌布,却发现上面有了被虫子蛀出的小黑洞,只好把它继续藏起来,但藏起来的结果就是永不再用了。人在社会上待久了,就会心中有伤,发现人人都只能爱自己。夏洛蒂想,她会感伤,因为她当真珍惜过她们的友情。
艾米莉开始上班,夏洛蒂觉得又回到了曾经的单人生活。每天早上半梦半醒的时候,听见水从水龙头流出的声音,刷牙吱吱的声音和窸窸窣窣换衣服的声音。接着她闻到熟悉的香水味道,她们用同一款古琦香水。她在香水的氤氲中睁开蒙眬睡眼,艾米莉已经梳好光洁的马尾,换上高跟鞋,轻轻地打开门,她的背影看上去就像夏洛蒂过去的背影,常常让她生出恍惚的感觉,然后是一声无论怎么小心都会清脆响亮的关门声。夏洛蒂赖一会儿床,她一般会在这段时间里胡思乱想一阵。比如,林恩木会不会遇见穿着她的衣服的艾米莉,他会不会觉得似曾相识,会不会因此而怀念起她。然后又想,事实永远在想象之外,既然想到就不会发生,世间事没有那么巧。她没有料到,事实也可能比想象跑得更快。同在一幢大楼上班,林恩木确实遇见了艾米莉,只是,他没有在她那儿追忆前任女友,而是径直与她相恋了。
如何告诉夏洛蒂自己与林恩木相恋的事,艾米莉的内心颇受了一些折磨。最后她选择用最为直白的方式。“有一天,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馆喝咖啡,有个男人忽然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抬起头看他,一张很干净舒服的男人面孔,他微笑地看着我,仿佛很自信,然后慢慢地变成了惊讶和尴尬的神情。他的表情变化缓慢而流畅,就像是一种魔术,那种过程温吞却没有丝毫破绽的魔术。他说,对不起,认错人了。我说没关系。我转过身继续看资料,但是根本看不进去。我将那杯咖啡喝得很慢很慢,直到咖啡馆只剩下几个人,我的位子对着落地的玻璃窗,他的影子投在里面,我知道他一直还在。我们透过那扇洁净清澈的玻璃窗中的影子打量彼此。然后,他走过来,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真的很像我以前的女朋友。”
夏洛蒂站起身来,动手整理这些日子里她们喝完的红酒瓶,它们都堆在墙角。她一会儿将它们整齐地并排放置,一会儿以一个中心摆成一个圆,一会儿又把它们躺倒垒在一起。空气里只剩下玻璃瓶相互撞击的声音,像杂乱慌张的音乐。她终于排出了理想的形状,转身问道:“后来呢?”艾米莉盘膝而坐的身体向窗口挪了挪,说:“后来,互通姓名,自报家门,聊天,约会,就——成了恋人。”夏洛蒂扭过头去,她觉得自己只是惊讶,不曾难过,但她渴望痛哭一场,因为这次她终于确认自己是不幸的。但是不能在此时,不能在艾米莉面前。“成了恋人之后,我才知道,你是他以前的女朋友。”艾米莉继续说,她的语速加快了,声音却异常清晰,好像是一场电影画面流淌中的独白,让人不得不专注倾听,夏洛蒂的泪水也慢慢地渗回身体的深处。“我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的流言,甚至他自己也承认,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子。许多同事对我说,和他恋爱是浪费时间,因为他根本不想结婚。他从来不缺漂亮的女朋友,大概每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都会认为自己是不一样的那个。不过,我不这样认为。”
“是吗,为什么?”夏洛蒂略带嘲讽地问。“我想,你做不到的,我也一定做不到,而且,我又——离过婚。”艾米莉站起身来,“夏洛蒂,如果你不开心,我可以……”“不用,”夏洛蒂转过身,神色平静,流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宽慰的微笑,“没有必要。我和他已经分手了,我和他只是朋友罢了。”她没有打算和他做朋友,只是这一刻。她的话语却分外轻松,就像是忽然被扔上台的戏子,一刹那天地全无的惶恐之后,仿佛是灵魂脱壳似的入了戏。她甚至觉得艾米莉微微向后退了一步,那双光洁的缎面拖鞋下,显示出一种足背弓起的奇怪姿态,就像是两只受惊吓的小猫。“有空,你带他过来玩。”夏洛蒂微笑着望着艾米莉。
在她们的友谊规则中,喜欢上同一个男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从一开始,她们就喜欢对彼此的男友玩一些暧昧伎俩,作为自身魅力的试金石,以满足如无底深渊般的虚荣心。青春期的女孩子是残忍的。她们对彼此的作为无动于衷,从来不曾因此争吵过。仿佛她们的友谊更像是男人之间的友谊,看似大度,其实虚伪,目光高远,从不任性。又或者,她们之间根本没有友情。但无论如何,这只是青春时代的游戏,夏洛蒂以为一切早已结束,但命运的手又将她推过来,夏洛蒂知道自己输定了。因为她没有力气再争。她难过只是因为她知道自己输定了。在她心里,林恩木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他是个天真得难以捉摸的男人。她爱慕他。因为失去他,她才会自暴自弃去做那个手术。她让他在心里变成神情安顺的雕像,然而,现在他又从雕像变成了一个血肉之躯,恢复了轻薄姿态,拍拍尘土,离她远去。
夏洛蒂给林恩木发了一条短信:“我搬新家了,有空过来玩。和艾米莉。”“好。”林恩木的回复简单迅速。夏洛蒂想,他一点犹豫没有,大约是早已忘情。一个人倘若真的能够做到喜新忘旧倒是好的,至少一直对新人认真,最怕心里闪闪烁烁,每个过客都不肯放下,反而心的空间越来越小,渐渐失去爱的能力。总之,从一开始,夏洛蒂就有无数种方法向自己证明,林恩木不对,他是错的。这些日子艾米莉回来得都很晚,有时夏洛蒂睡了,她才轻手轻脚地进门。她是不敢面对她吧,夏洛蒂想,如果是自己也会和她一样的。一想到她在外面消磨的这些时间都是和林恩木在一起,她的心又隐隐作痛起来。她开始热切地盼望着周末的来临,因为这样就可以见到林恩木了。他们整整有六个月没有见面了。
房间是新的,陈设却是旧的,就像是一幅换了画框的画。林恩木一走进屋子,迎接他的是夏洛蒂无懈可击的微笑,无懈可击的招待。她怎么变成另一个人了,他心里暗想。他走进来,没有忘记紧紧握着艾米莉的手,最开始的时候,他知道她是她的好朋友,只是和她可以攀谈,想打听她的状况,可是这样的美貌女子,他很难不打主意。难道这怪我吗?他无辜地望着夏洛蒂,极其自然地坐在柔软的地毯上,他的眼睛说,我不过是被你扔来的雪球击中了而已。
其实,他们都没有可以做的。因为在优雅的成熟的感情中,人是无法左右他人的。因此他们都非常自在。令艾米莉惊讶的是,夏洛蒂居然没有刻意装扮。她穿一件浅紫色的宽大毛衣,珠灰色的丝绸长裤,头发随意地绾在脑后,甚至连口红也没有涂。当她将最后一道菜端上桌时,皮肤上明显沾了一些油烟的痕迹,她随意拿一张餐巾纸吸了吸,望着林恩木,有些腼腆地笑起来。
“她凭什么这么自信。”艾米莉在心里愤愤地想,在她眼中这样的装扮是一种极大的傲慢。一个女人只有在最亲密的男人面前才会穿家常衣服,脂粉不施。她望着林恩木,心里忽然酸涩,她是看了他和夏洛蒂的合影,有意去勾引他的。她整个青春时代都在玩这种游戏,她的前夫是夏洛蒂暗恋的学长。女孩子常常觉得自己要比好朋友优越一点,方才安心,可是她做事用力过头,因此早早地结了婚,又因为懊悔而匆匆离婚。她把自己的所有青春和所有资本都挥霍在与一个无关紧要的女人的游戏上了。她不应该恨她,抢夺她的一点什么吗?
餐桌上,艾米莉承担起了解决冷场的职责。“夏洛蒂,记得吗?大三的时候,到我家去玩,待了一个暑假。”“记得啊。”夏洛蒂的眼睛发亮,转向林恩木,“她家四周的风景美得不行,在一所小学校里,屋前是小溪,屋后是竹林。市镇上全是旧式建筑,路是石板铺的,一下雨,绝佳的意境。”“我家是个小镇,那里唯一的娱乐场所就是镇上的电影院。”艾米莉对林恩木说。夏洛蒂的目光飞快地掠过艾米莉,有一丝诧异。原来她知道。十九岁的夏洛蒂喜欢上好友的父亲。有一天,这个自恃年轻貌美的女孩子环抱住那个男人,额头靠在他瘦瘦的脖颈上,轻声说,我只想和你去镇上看一场电影。他们去了,在一個下雨的清晨,父亲说要去帮一个学生补课,夏洛蒂说要去看一个好朋友。他们一前一后地离开,又一前一后地回到家里。夏洛蒂收起雨伞望见静静站在面前的好朋友。“外面雨真大。”“你去车站了?”“嗯。”“脚上都没有沾泥?”“我回来路上洗过。”“是吗?洗得真干净。”
“什么时候我也过去玩。”林恩木将手掌盖在艾米莉的手上。“好啊,不过你要小心我爸爸。我爸爸年轻时是个帅哥,不信你问夏洛蒂。”林恩木自然没有问,他只是望着艾米莉。这一天,夏洛蒂的冷淡平静令他幻灭,在他的私心里,他并非是不希望两个女人因为他剑拔弩张的。男人是比女人更虚荣的。
聊天一直持续到深夜,角落的酒瓶又多了几个。最后,林恩木看了看表,对夏洛蒂说:“回不去了。”“那你就住在这里吧,”夏洛蒂打开衣柜,抱出一床棉被,“你睡地上,我们睡床上。”“好。”林恩木乖乖地站在一旁,看夏洛蒂仔细地在地毯上整理出一个床铺来。她的动作非常缓慢,那缓慢的动作仿佛是将流逝的每一秒钟都拉长了。浴室里响着水流的声音,艾米莉不知何时已经溜进去洗澡了。“好了。”夏洛蒂站起身来。她望着林恩木,眼中忽然少了掩饰,周围静得可怕,他走过来,他们拥抱在一起。仿佛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让他们相对了。他不过是个浪子,她已经没有丰厚的青春去玩这场游戏。他们分不清是怜惜彼此还是怜惜自己。
浴室水流的声音终止了,他们分开。艾米莉顶着湿湿的头发走出来,并没有观察这对孤男寡女的神态,而是径直取出吹风机吹头发,低低的轰鸣声吹散了沉默的尴尬。从见面开始就不停地说话,他们都累了,此时仿佛是卸去了盔甲。他们陆续清洁干净,各自沉沉睡去。林恩木躺在夏洛蒂悉心折好的被窝中,空气中有一种静静的熟悉的香味。这是一个女人独一无二的气味,她用的香水,面霜,精油,肥皂,女人生活中无聊的琐碎的不可或缺的点点滴滴,混合成这样特殊的空气。他睡在这样的空气中,觉得抚慰异常,就像是睡在深幽的花草生长的谷底。夜半,有人过来拥抱他,他原以为是夏洛蒂,身体迎过去,又觉得是艾米莉。他吻了吻她的脸颊,发觉她泪流满面。他有些感动,他的心其实是很柔软的,只是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坚强独立拿得起放得下的女子,没有人在他面前流泪,才会令他显得无情起来。如果有个女人用尽力气绑住他,他未必会成了个浪子。
第二天,林恩木很早就起床离开了。在回家的出租车上,他看见很美的清晨的太阳。天空是深蓝色,然后渐渐变成灰蓝,浅蓝,近乎透明的蓝。朝阳在车窗外追着他奔跑,仿佛依依不舍,这新生的太阳并不刺目,并不高远,像个红彤彤的橙子,饱满可爱。他想起生命中那些对他万般眷恋的女人们。活在这珍贵的尘世上,挥霍是可耻的。他叹了口气,第一次,他的心里有了结婚的念头。
【作者简介】雷娜,1980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比较文学硕士。曾任文艺出版社编辑,文学杂志编辑。在《萌芽》等杂志上发表过散文,外国文学评论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