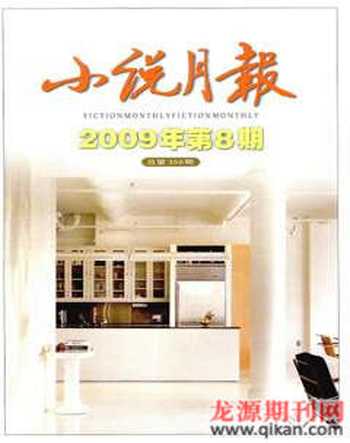寻死无门
一
黄腊梅到家时,刘小富还没见回来。
黄腊梅给刘小富打了电话,说,你是不是还没从医院出来?是不是又在那里和病友摆龙门阵穷磨时间?刘小富说,哪个在摆龙门阵?告诉你老子今天根本就没打吊瓶。刘小富在电话里迟疑了一下,声音忽然小了下来,说黄腊梅你最好来一趟,王大夫有话对你说。
黄腊梅看看表,都快中午了,但还是马上骑着车子去了医院。
从医院回来,黄腊梅腿软得连楼梯都迈不动,但她不愿让刘小富看出什么,嘴上还一个劲儿对刘小富说,“好你个刘小富,结婚二十年你从来都不肯听我半句,这下好,你又吃药又打针又打吊瓶这长时间原来是白花钱,当时叫你好好查一下你不查,你老爸得胆结石你就说你也是胆结石,简直是白痴!这下你还说不说你是胆结石?”走在黄腊梅后边的刘小富不说话,此刻他觉得自己浑身都不舒服,都在冒冷汗,其实最不舒服的是心里的那种感觉,自己一直以为是胆结石在作怪,想不到今天一查竟然是肝里出了大毛病,王大夫说你也不必心慌,只不过是普通囊肿。王大夫不这么说还好,这么一说倒点醒了刘小富,刘小富脑子又不笨。要是普通囊肿,还叫黄腊梅去医院做什么?
进了家,黄腊梅一头去了厨房,她把馒头和昨天的剩菜一样一样放在笼里,愣了一会儿神,忽然说没酱油了,刘小富家的下边就是超市,买什么都很方便。黄腊梅下楼去的时候悄悄把手机拿在了手中。她想到楼下去给刘小富的姐姐打个电话,在家里打怕刘小富听到。黄腊梅有什么事都要请教刘小富的姐姐,仿佛那就是她的守护神。
黄腊梅躲在楼下给刘小富姐姐打电话的时候忽然有了哭音:
“姐……出大事了,小富肝里边长了东西。”
“小梅你大点声。”刘小富的姐姐说你说什么地方长什么东西?
黄腊梅说刘小富一直说胆疼胆疼,今天一查才发现肝里长了东西。
“肝里长了东西!”刘小富的姐姐吓了一跳。
“一个有拳头那么大,一个有核桃那么大。”
“肝里?”刘小富的姐姐又说。
“就是肝里。”黄腊梅说王大夫说恐怕已经是肝癌晚期了。
刘小富姐姐在电话里好一阵子没说话,老半天才说:“怎么会和我妈一样,查错了吧?”
黄腊梅说所以才想下午抓紧时间再到人民医院查一下,“但愿他们查错,姐……”
“你别急,别急,下午我陪你去。”刘小富的姐姐在电话里说。
“我儿子还没成呢!”黄腊梅似要哭出来,但她忍住。
“别急,别急。”刘小富的姐姐又说。
“不会是遗传吧?”黄腊梅说。
“不会吧?”刘小富的姐姐说。
打完电话,黄腊梅跌跌撞撞去超市买了两袋酱油。
这天中午,刘小富的儿子小丰没有回来,小丰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脾气一天比一天大,最近自己出去找了份临时工作,中午一般不回家吃饭,家里就刘小富和他老婆两个人吃饭,吃过饭,黄腊梅在厨房里一边收拾碗筷一边对刘小富说,“要不,下午再到人民医院查一下?”黄腊梅想让自己尽量说得轻松一些,刘小富跟在她屁股后边也进了厨房,他也想让自己表现得轻松一些,顺手抽了一支烟出来,说:“去就去,老子就不信老子肝上真有了东西?”
黄腊梅突然朝刘小富扑了过来,把他手里的烟一把夺了过去,“你还敢抽烟?”
刘小富愣了一下,说抽支烟未必就会马上死人。
“哪个准许你说死说活!”黄腊梅说。
“不说不说,我还怕我死了你再找一个在那里快活。”
刘小富想把话说得俏皮一点,眼圈却猛地一红,喉咙那地方早已哽住,他忽然明白了,自己难受了这大半年,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原来自己是得了正经病!刘小富对这种病再熟悉不过,当年母亲得的就是肝癌,从检查出来到去世还不到两个月。
二
中午过去,下午黄腊梅又陪刘小富去了一趟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在万花南路,离刘小富家不远,中间隔一个体育馆,体育馆旁边是儿童公园,远远就可以看到那个几层楼高的大轮子,因为天冷,这摩天轮没得人坐,只静静待在那里,每回看到这个孩子们最最喜欢的摩天轮,刘小富就在心里想,小丰怎么一转眼就再也不需要自己了?要是小丰再缠着自己带他坐一次摩天轮该有多好。
刘小富的姐姐早早在医院门口等着,风挺大,她围着一条茶色围巾,两眼不知看着什么地方,她的身旁,站著刘小富的姐夫,刘小富的姐夫是个开出租的,早起晚睡,平时忙得很,连过年也难得见着人影,但这一次非同小可,肝里长东西其实就是对一个人判了死刑,所以他放下生意不做也跟上来了。医院门口这天不知为什么插了许多红旗,风从北边吹过来,红旗“哗啦哗啦”响成一片。刘小富姐姐已经和这里财务科的熟人联系好了,来了就检查,不用等,下午看病的相对也少,CT和B超又用不了多长时间,一会儿就好。刘小富上了两回楼,又到地下室放射科去了一下,很快就都一一查完,刘小富姐姐让黄腊梅和弟弟在医院门口等她,她和刘小富的姐夫留下来等检查结果。其实结果早已出来。肿瘤科彭大夫已经看过片子,他对刘小富的姐姐说:
“两边检查结果都一样,已是晚期了。”
“不会有错?”刘小富的姐姐说。
“不会。”彭大夫用手指点点CT片。
“可不可以换肝?”刘小富的姐姐忽然说。
“恐怕不行。”彭大夫说。
“能换最好。”刘小富的姐姐又说一句,心里忍不住一阵乱跳,一个声音在她心里说就是能换小富又去哪里找这笔钱?
彭大夫说这都已经是晚期了,“早就错过了换肝的机会。”
“大概,还能拖多久?”刘小富的姐夫在一旁结结巴巴问了一句。
“三个月到半年吧。”彭大夫说换肝手术你们别想,但介入手术必须马上做,病人已经有了腹水,这里,这里,彭大夫指着片子,所以不能再等,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
刘小富的姐姐顿时在那里愣住。
从门诊楼出来,刘小富的姐姐想尽量让自己装着轻松一点,但她怎么轻松得起来,她想装着轻松,却更显得紧张,她对眼巴巴等在医院门口的弟弟小富说:“问题不大,你放心,是普通囊肿,隔天咱们再到军区医院找专家看看片子。”刘小富的姐夫也想说句什么,张张嘴,却无话可说,忽然望望街对过,说:“要不,咱们在一起吃顿饭吧。”这时候,差不多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医院对过就是万花西路上最有名的“红宝石饭庄”,土菜做得十分地道。
点菜的时候,平时过日子极是节俭的姐姐乱点了许多好菜,要在平时,刘小富不但饭量大,还必要喝酒,这一回,他没提酒,刘小富的姐夫开车不能喝,却忽然问了一句:“要不,我陪你喝两杯?”刘小富的姐姐马上在一边生气地说:“你胡说什么?这么好的菜,你们两个多吃菜!”刘小富的姐夫不再说喝酒,便不停地给小富夹菜。小富想多说几句话,又百般找不出话来,好容易找出一句话,却是:“活多大年纪也是个活!其实都一样!没什么了不起!”
刘小富这么一说,黄腊梅的眼里猛然汪上了泪水。
“哪能一样,我儿子还没成呢!”黄腊梅说。
这顿饭吃得味同嚼蜡,剩下一多半饭菜打了两个包,一包带给刘丰,一包带给刘小富的外甥女小静,小静已经到了预产期,这几天一直住在刘小富姐姐的家里等动静。
这天夜里,刘小富怎么也睡不着,后来他干脆不睡,悄悄去了儿子刘丰的房间打开电脑查肝癌资料。儿子醒来去厕所,吓一跳,说老爸你干什么?怎么这会儿都没睡?看什么好东西?刘小富怕儿子发现自己查什么,忙把电脑关掉,电脑一关掉,窗子那里却猛地白了一大块,想不到外边已是大亮。
刘小富不想再睡,干脆穿衣服去了菜市场。快要过年了,刘小富决定先买些肉回来。刘小富在心里说:“不管老子活到活不到过年,老子先让老婆儿子好好吃顿红烧肉再说!”出现在菜市场的刘小富两眼红红的,一夜间,人老了许多,买肉的时候,刘小富在卖猪肝的那里愣了老半天。
“吃啥补啥。”回来的时候,刘小富提了一副猪肝。
“对,吃啥补啥!”黄腊梅说。
刘小富把自己的拳头放在猪肝上比了比,说,“难道真有这么大?”
“别瞎想,人肝比猪肝大得多!”黄腊梅说。
“我得马上跟霍光芒把欠咱们的钱要回来。”刘小富说。
“要不我去?我不信他养小蜜有钱,给你结账就没钱!”黄腊梅说。
“还是我去!”刘小富说,心里的一句话是:“再不要也许就没机会了!”
“姐姐刚才来了电话,医院那边问了一下,做一次介入手术是一万五。”黄腊梅一边用水龙头冲猪肝一边对刘小富说,这还不算给大夫的好处费,“咱们还是从北京请大夫吧。”
刘小富继续说要钱的事,“亏他还叫什么霍光芒,一点都不光芒!叫霍黑暗算了!现在的人怎么这么黑暗!什么意思,想等到老子死了把这笔钱赖掉!”
“你瞎说什么!”黄腊梅说,“你知道不知道生气对肝更不好。”
“老子已经这样!还什么好不好!”刘小富一屁股坐了下来。
“做完介入治疗就好了。”黄腊梅对刘小富说,咱们的好日子长着呢。
“但愿吧。”刘小富苦笑着说,我总不能比我老子早去那个地方吧。
“做完手术再说别的,要钱的事先往后搁搁。”黄腊梅说。
“要是……”刘小富看着黄腊梅,那半句硬是没敢说出来。
三
做完介入手术,休息了一个多星期,刘小富去了霍光芒的家。
风从北边吹来,天上的云给吹得又薄又平,太阳光灰灰的。
刘小富上楼上得好痛苦,每迈一步身上到处都疼。霍光芒住五楼,刘小富一边上楼一边喘气,还没进霍光芒的家刘小富就看到了立在走廊外的那扇白漆门。刘小富认识这扇门,门是霍光芒的,门上有个大窟窿,没有这个窟窿还看不出厚墩墩的一扇门原来只不过是两张薄薄的合成板做的。刘小富奇怪门上怎么会有一个大窟窿,怎么会卸下来立在走廊里。
霍光芒的老婆在家,开门的一瞬间竟然没有认出站在门外的是刘小富。
“你找哪个?”霍光芒的老婆说。
刘小富说你怎么连我也认不出来了?
霍光芒的老婆这才“啊呀”一声,忙把门打开。
刘小富坐下来,说,外边那是你家的吧?要大兴土木?
霍光芒的老婆马上说,“我这日子没法过了,门是霍光芒这个王八蛋给砸的。”
“他疯了还是钱多撑的?”刘小富说。
“他要跟我离婚!”霍光芒的老婆说霍光芒这个老不要脸的,一点脸都不要,我家老二还没对象,他这样闹,老二还怎么搞对象?
刘小富早就知道霍光芒养小蜜的事,但就是养小蜜也不至于和自己老婆闹成这样。
“是不是小蜜挑唆的?”刘小富说。
“什么小蜜?那婊子都四十七八了!”霍光芒的老婆气不打一处来,差点要跳起来,说他霍光芒要是养个十七八、二十多的也算他有本事,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老烂货,不知给多少人搞过!那婊子说好听点是公共汽车,说不好听的是公共厕所!人人都可以去她那里排泄!
“养了个四十八的?”刘小富吃了一惊,想笑又笑不得。
霍光芒的老婆说我也不怕你笑話,这女的真不知道有过多少男人,你说他霍光芒是不是疯了?还说是为了爱情!一家人现在都不肯跟他说话,他就拿门出气!我倒希望他跳楼!
刘小富想把话引开,说:“听说你家老二在北京打工?”
“你说老二还结婚不结婚,传出去,有这样的公公,哪个姑娘还敢上门?”
“他妈的话他听不听?”刘小富记着霍光芒是个孝子。
“屁!”霍光芒的老婆朝地下唾一口,骂道:“霍光芒已经疯烂了!”
“他妈说话他也不听?”刘小富又问。
“以前还听,现在不听。”霍光芒的老婆叹口气,说他妈也快让他气死了,气得一打嗝就不得停!一个人不要脸就什么都不顾了。霍光芒老婆就又说起去年过年时候的事,说霍光芒连过年都不回家,就待在那个婊子那里点了蜡烛喝红葡萄酒说要找什么情调!两个儿子去找他那婊子还报了警,到后来闹得派出所都批评这老不要脸的。
“真是四十八?”刘小富好像是不太相信。
“差两岁整五十!”霍光芒的老婆说这我还能对你说假话,要是养个二十岁的我也不这么生气,算他有本事!算他流氓流出成果!
刘小富忍不住笑出声,脸色却突然大变,豆大的汗珠马上爆满一脑门儿。
刘小富的样子让霍光芒的老婆吓了一跳,她暂时收起自己的兴奋,问刘小富:“你是不是病了?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
“不好吧?”刘小富说。
“真不好。”霍光芒的老婆说你应该去医院看看。
“还看什么看。”刘小富说。
“人过中年事最多,你要是有点事黄腊梅怎么办?”霍光芒的老婆说。
“我已经是肝癌晚期了。”说这话,刘小富倒显得出奇地平静。
“瞎说!”霍光芒的老婆几乎又要跳起来,“你好好儿一个人,怎么会得肝癌?”
刘小富说,没人愿瞎说这个吧?自己确实已经是肝癌晚期,天地再大也没什么想法了,这次来就是想让霍光芒把欠自己的那两万给结了,刘小富又说,自己刚刚做了一次介入手术,一次两万,马上要做第二次,还有第三次,明知是死也得做,自己这是害人,把老婆孩子都要害死了,上边还有个可怜的老爸!
霍光芒的老婆瞪大了两只眼,说,“真想不到。”
“我这是害人,我把我老婆和儿子害了。”刘小富又说。
“害人的是霍光芒!霍光芒,王八蛋!”霍光芒的老婆又骂起来,一边骂一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忽然站住,“也许是查错了,医院里现在经常出错。”
“错不错我自己还不知道?”刘小富说,“所以光芒不能再把我那两万拖下去了。”
“我打电话他肯定不接,要不,你给他打一个?他总不能连你的电话都不接!”
刘小富说我打他也不会接,上次我用街上的公用电话打给他他才接了一下。
“这个王八蛋!”霍光芒的老婆又骂道,骂归骂,霍光芒的老婆也没办法,她忽然对刘小富说:“要不,我带你去,他这会儿不在单位就肯定在那个婊子家。”
刘小富摆摆手,头上的汗又下来了,“今天我是不行了,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也没几天了,那两万他已经欠了我三年,我就是花不上,到时候也要把它交给我老婆我儿子,我儿子到现在都没找到正式工作,是我害了他们,得这种病就是害人,害人!其实我也是受害者,谁让那几年天天都要陪着农机厂的客人喝酒,别人搞业务是弄钱,我搞业务是给自己弄病,这会儿想找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听说农机厂的地都卖了,好在我老子的那几个可怜工资还能开到手。”
霍光芒的老婆张着嘴,看着刘小富,眼里突然也有了泪水,泪水马上就要流下来了,她突然进了另一间屋子,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了几张人民币:
“家里也就这么些。”
刘小富说:“不不不,什么是什么。”
“你拿去买些营养品。”霍光芒的老婆说这跟那个王八蛋没一点点关系。
刘小富不拿,霍光芒的老婆硬要把钱塞给刘小富,刘小富浑身发软,又一屁股坐下,自从检查出肝里长东西,刘小富觉得自己是一下子就垮了,从身体内部一下子就垮了。他把钱放在茶几上,倒气喘吁吁反过来劝霍光芒老婆,“夫妻还是元配的好,让他疯够了他就不疯了,不过,霍光芒这人真是太自私,他欠我的钱且不说,他都不肯为他两个儿子想一想,他知道不知道到老他靠谁?”
“靠谁?”霍光芒的老婆说就让他靠那个婊子好了!
刘小富离开霍光芒家的时候,霍光芒的老婆又从家里追出来,把手里的钱硬又塞到刘小富的口袋里,刘小富这次不再推推让让,他只觉得自己连一点点力气都没有。从院子里走出来,回头看看,霍光芒的老婆还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自己,刘小富就又往前走了几步,直走到谁也看不见谁,刘小富才找个地方坐下来。刘小富突然笑了一下,想不到霍光芒居然搞了个四十八岁的,多少天来,这倒是一件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想一想,刘小富忽然又伤心起来,就是五十八的,自己也没那个机会了。刘小富把霍光芒老婆塞给他的钱取出来数了数,一共三百块。停一会儿,他又把那钱数了一下。“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刘小富苦笑着对自己说:“要是三十万还差不多。”“三十万?三十万又能做什么?”另一个声音马上在刘小富的心里说,“又要买房子,又要给你儿子找工作,又要给你儿子娶媳妇,三十万能做什么?”这么想着,一个念头突然从刘小富心里蹿了出来,刘小富从心里抖了一下,忽然明白自己现在最最当紧的是想办法给老婆和孩子留一笔钱!这也许是自己最后能想到的事情了!这也许是自己最后要办的最最重要的事了!母亲当年从得病到去世让刘小富太明白这种病是怎么回事。坐在那里的刘小富忽然摸摸自己这里,再摸摸自己那里,摸摸胸,摸摸腰,那天在医院碰到的那个卖血的人的那张脸又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一个想法,突然从刘小富的心里跳了出来。为了自己的新想法,刘小富的两只眼里忽然有了亮光。
“反正也是个死!大不了就是个死!最终也是个死!”刘小富在心里说。
四
从小到大,天气再冷刘小富也没戴过帽子,而现在刘小富不得不戴着帽子出门。
刘小富这天去了矿总局医院。矿总局医院离市区好远,在万花南路最西边,再过去,都快要到梅洛水库了,梅洛水库周围现在盖满了商品房,已经成了很大的一个小区了,人们都奇怪,水库里的水去了什么地方?不少人担心,要是水库里再有了水,那些房子还不被淹掉?
刘小富满脸的疲惫,坐在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姚海泉的面前。
姚海泉是矿总局医院药剂科主任,日子过得肥得很,手下养了一大批跑药的,中秋节那次同学聚会请客,姚海泉只打了一个电话,马上就有人把五桌饭菜订好,原来说好的同学们每人出二百,结果让姚海泉一下子给解决了。姚海泉年轻的时候长得可真是讨人喜欢,想不到一到这个岁数人的模样会起这样大的变化,人胖不说,又早早谢了顶,还是一脸的毛糙胡子,怎么看都一点不可爱。
“刘小富,怎么会是你?”刘小富的样子让姚海泉吓一跳,几乎要跳起来。
“妈的,怎么就不会是我?”刘小富。
“你怎么想起来这地方?”姚海泉说你怎么这么憔悴?是不是女人搞多了?
“没事吧?”刘小富摸摸自己的脸,说自己是想替朋友来问一件事。
姚海泉马上就皱起了眉头,说这几年的药不好做,库里的新药堆积如山都出不去,上边又查得紧,整天苍蝇一样叮在这里。
“我又不跑药。”刘小富说你他妈别害怕。
“那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姚海泉说你是不是想要美国伟哥?可以白送你一盒玩玩儿。
“不是不是,都不是。”刘小富说伟哥和我无关,是有人想问问可不可以卖肾?
“卖肾?”姚海泉大吃一惊,说自己从来没碰过这种犯法的事情。
刘小富说自己只是替朋友打听打听。
“还有打听这的?”姚海泉说自己在医院都没听过有人打听这的。
刘小富说这又不是什么稀罕事,那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留一个自己用就行,卖一个得二三十万还可以派大用场。
“说得轻松,可不是这么轻松的事!”姚海泉说那是人体器官。
刘小富看着姚海泉,忽然又说:“还有,角膜?”
姚海泉就又笑了起来,说刘小富你这家伙是不是入了黑社会,要什么有什么!有没有××!是不是要搞批发?你知道不知道这东西是人体器官,是犯法的,是黑社会!
“你说现在什么事情不犯法?大家都在犯法!”刘小富说。
姚海泉说你说的也是,越是当官的越犯法,带头犯法。
“犯法才能过得好些。”刘小富说。
“也是。”姚海泉说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从来都没好日子过!
“有没有先付钱,到时候再把东西拿走?比如角膜。”刘小富说。
姚海泉一张嘴笑得好大,说到时候?到什么时候,到这人死了再把角膜和肾拿走?
“对。”刘小富说。
“那谁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姚海泉说。
“我就知道。”刘小富的手慢慢抬了起来,猛地一下子把自己的帽子摘了下来。
姚海泉张了一下嘴,当即愣在那里,凭着职业敏感马上明白刘小富可能是得了什么病,并且马上就明白刘小富经过化疗了,要不他的头发不会像现在这样稀稀落落难看得要死。
“你看看我这样子。”刘小富说好看不好看?
姚海泉也不再笑,小声说:“病了?什么病?”
刘小富忽然觉得自己竟然能这样平静地把话一下子说了出来:“肝癌晚期了。”
姚海泉又吃一惊,明白刘小富刚才是在说自己,姚海泉想说些什么,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面对一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老同学,你说什么都不合适。姚海泉想想,站起身把身后的铁皮柜子打开,从里边取出一小沓钱来。
“你什么意思?”刘小富一下子站起来。
“就当我去家里看你,想吃什么你买点儿什么?”姚海泉想开个玩笑,说,“要是没胃口干脆去找个小姐玩玩儿,好好儿打几炮!”
“不是这个意思!”刘小富说。
“同学一场什么意思不意思。”姚海泉把钱硬往刘小富手里塞,说你别嫌少,你快拿起来,待会儿来人还以为你是跑药的,我是受贿的,两下子都不好。把钱塞到刘小富手里,姚海泉转身又从铁皮柜子里取出一盒儿茶叶,“朋友送的日照茶,你拿回去喝。”
“我现在不能喝茶。”刘小富说。
“客人總是要喝的。”姚海泉把刘小富的手按住,刘小富的手冰凉冰凉没一点儿温度。
刘小富想再说几句话就走,便又说到角膜和肾。“我他妈也想开了,一是不能把自己的东西浪费了,二是自己要尽可能给老婆和孩子留些钱,反正也没几天了。”
姚海泉说这种事几乎没有可能,除非你是需要换肾的那个病人的亲戚,角膜的事也不可能,“那是要摘眼珠子的事。”
刘小富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感觉中已经是骨头一把。
“你这真是下下策。”姚海泉说癌症也没什么了不起,也有好的,不可悲观。
“哪有那种可能,要是长在胃和肺那地方还差不多。”刘小富说自己早就上网查遍了。
“好好儿养着,也许一下子就好了,现在许多事情都说不清,你可不能在咱们同学中开这个头儿。”姚海泉说。
刘小富心里忽然好一阵子说不出的酸楚。
姚海泉忽然又对刘小富说,“要是你真那么想,你不妨到网上留一下言,现在什么宣传都没网络厉害,再不你就试着贴些小广告,把电话留在上边,让人们跟你直接联系,不过,你是不是开玩笑……”
刘小富又苦笑了一下:
“我是自己把自己给耽误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胆结石,一直没当回事,岂知儿子和老子并不一样!我也算是让我老子给耽误了。”
和姚海泉分了手,刘小富去“骨里香鸡店”买了些老爸最爱吃的凤爪,他准备去看看老爸,快过年了,他想去老爸家看看都有些什么要做。老爸已经七十三了,有些活儿不能让他再做,比如收拾家,擦玻璃,这都是很危险的活儿,从前这些活儿都是自己和黄腊梅做,今年可以让小丰来做,小丰快放假了。刘小富已经想过了,怎么对老爸交代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自己必须要向老爸有个交代,这需要一个过渡,刘小富想好了,就对老爸说自己有可能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做事,能远到什么地方呢?这么一想刘小富就十分痛恨农机厂,怎么就让自己早早下了岗,要是自己现在还有工作,自己就可以对老爸说自己要出国,去国外搞施工,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以老爸现在的岁数,也许活不过十年了。自己怎么就得了这病,倒让白发人到时候送他这个黑发人?
刘小富忽然蹲了下来,两手一下子捂住了脸,脸上热热的东西流下来。
很快,有人走了过来,对刘小富说:
“哎哎哎,怎么蹲这地方?这不是蹲的地方。”
刘小富把脸上的眼泪擦掉,这才发现自己是蹲在路上,身旁已经堵了一溜车,停在最前边的司机正探出头怒冲冲看着自己,不等刘小富站起来,已经慢慢慢慢把车开动了。
刘小富一下子火儿了,跳起来说:
“轧啊,轧啊,有本事从我头上轧过去。”
刘小富一喊,那车就又停了下来。
“你把老子轧死老子倒有办法了!”
刘小富朝那车走两步,把帽子一摘,又大声说。
那司机果然被吓住,把车停了。
“开呀!你开呀!”
刘小富的脸上都是泪水,头上所剩无几的头发被寒风吹起落下,落下吹起。
五
刘小富去贴广告,马上就要过年了,对联和灯笼还有爆竹已经摆到了街上。
刘小富的棉大衣口袋里,一边是广告,一边是胶水,他一边走一边贴,走走贴贴,也不管周围有人没有人,心里还说“看什么看,老子现在死都不怕还怕你们看我贴广告?”为贴这广告,刘小富一直走到了这个城市的最西边,再往西就是万花路大货场,他计划在西边贴完再到南边。刘小富倒是很怕熟人看到自己,后来他又进了几个小区,把广告直接贴到楼门上。广告上的那几句话倒直截了当:“因为生活所迫,我决定出售自己的肾脏、角膜,本人健康无病,有需要的可与1354603××××联系,价钱面议。”
刘小富贴广告的时候,忽然有个人在他背后说:
“这种广告最好贴在医院门口,贴在这里没用。”
是个胖胖的中年人,手里也拿了一沓子小广告在到处贴。
刘小富想想也是,便又去了几家医院,口袋里的小广告快贴完的时候,刘小富还特意悄悄去了一下霍光芒那里,在他的单元门上贴了一张,又去了一下霍光芒的单位,在霍光芒单位的楼门口也贴了一张。霍光芒的工作单位也就是刘小富当年的工作单位,以前单位外边的法国梧桐都给砍了,现在盖了不少门面房出租,都是温州人在那里卖塑料制品,离老远都能闻见那股子难闻的塑料海绵的味道。
贴完广告,刘小富直接去了老爸家。
刘小富的老爸以前是农机厂的车间主任,说话办事都特别有一套,但自从刘小富的母亲去世后,刘小富的老爸好像是一下子就老了。刘小富一年也难得去几次老爸家,他不愿听老爸总是在那里教训自己,所以去了总是和老爸顶嘴,自从查出肝癌后,刘小富现在是一有时间就去,去了和老爸坐坐,或者就在老爸那里躺一下,刘小富的老爸还住在万花南路的老房子里,刘小富在这栋老房子里长大,结婚后生下小丰才搬走。刘小富对老爸说趁现在还没出国跟您多坐坐,一旦出国去打工说不定多长时间才会回来。“出国?”刘小富的老爸说,“现在这么轻轻易易就让你这样的人出国?要是跑了呢?跑出去再不回来呢?”刘小富笑了一下,不想和老爸讨论这些事,老爸的话是老掉牙,是另一个时代的声音,刘小富说就我,又没搞房地产的老子,就是跑出去也顶多是个要饭的叫花子,还不如不跑出去的好。
“你那头发是怎么回事?”刘小富的老爸瞪瞪眼,问小富。
刘小富说可能是游泳池里不干净,可自己又舍不得扔掉那份工作。
刘小富的老爸说你从小又不傻,自己把头发弄成这样真是白痴。
“还不是像你。”刘小富说明知一个人过日子连个说话的都没有怎么就不雇个保姆?
“我这么大岁数还要什么保姆?”刘小富老爸说,我一辈子自在惯了。
“笑话!岁数大了才要保姆。”刘小富说爸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说话这样颠三倒四!
“我又不是不能动了。”刘小富的老爸说。
刘小富说你那工资一个人又花不了,我们又不花你的,你就是留下我和我姐也不会要你一分,你还是趁早花了,雇个保姆我和我姐也放心。
“雇了保姆你们不来怎么办?”刘小富的老爸说这我还不知道。
一句话说得刘小富无语,老爸不安电话也是这个道理,说安了电话你们就更不来了。
刘小富说我懒得跟你斗这个嘴,一来了就斗嘴也没什么意思,花盆干成这样都不懂得浇一浇。
刘小富的老爸忽然想起刘小富说的过些时候要出国的事,说现在打工的都能出国,要在以前出一趟差都得开证明换全国粮票,没有全国粮票吃饭都成问题。刘小富的老爸又说起旧事,说那年去河南把粮票丢了,整整两天天天吃胡萝卜,吃得直吐酸水。
刘小富的手机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刘小富放下塑料喷壶看了一下号码,想不起会是谁给自己打过来的。接了电话,那边的人马上说:
“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要卖肾的人?”
刘小富吓了一跳,一下子跳起来,怎么会这么快?才把小广告贴出去,电话就打过来了。
刘小富马上去了厨房,关了厨房门,小声问电话里的人,“你什么意思?”
“我问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想卖肾的人?”电话里的人又说了一句。
刘小富觉得电话里的口音有些耳熟,便问:“你是哪个?”
电话里的人说你别管我是谁?我问你是不是刘小富?
刘小富的耳朵里就“嗡”的一声,怎么这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知道了,自己分明没有在那小广告上留名字。正迟疑着,电话里的人又说了话,“你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刘小富的头这才不那么蒙了,他忽然想,这个口音会不会是霍光芒?
“你是霍光芒?”刘小富说。
“算你耳朵好。”电话里的人果然是霍光芒,霍光芒说想不到我那老婆没有说谎,我老婆告诉我说你那天去我家了,说你有病了,而且是正经病。我刚才一去办公室就看到了小广告,我看小广告上的电话像是你的电话,霍光芒在电话里说想不到你真会得这病?你别以为我不急,我这就去想想办法,看看去什么地方把钱挪一下。霍光芒说你倒好,昨天我老婆跑来把我骂个臭死,霍光芒又说,我不是躲你,那些钱我千不该万不该拿去让白家骏这王八蛋去开什么铁粉矿,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你放心,你出了这事,我说什么也得让他先把你那两万挪一下先给你。
“就是给不到我手里,到时候你记着也要把这两万给我老婆孩子。”刘小富说。
“看你说的?”霍光芒说我岂是那种人?我要是那种人还会给你主动打电话?
刘小富想想也是,从小一起长大,霍光芒就是想坏也坏不到哪里。
霍光芒又在电话里说了话:“你是不是专门在我的办公室外边贴了一张?”
“那又怎样?”刘小富说你门口又不是国务院门口,贴不得?
霍光芒说你是个傻×是不是?你怎么留你自己的手机号在上面,认识你的人一下子就都知道是谁了,1354603××××。
“那又怎样?”刘小富说。
霍光芒说你就不怕别人知道?
“我都这样了,还怕什么?”刘小富说知道的人越多越好。
霍光芒忽然没了话,停好一会儿才说这事要是让你老爸知道了呢?
刘小富忽然紧张了起来,小声说我现在正在老爷子家。刘小富侧耳听听外边,老爷子像是还在看电视,只有电视在响。
霍光芒继续在电话里说,“想想也是,要是换了我也许也会想到这主意,一个人一辈子不给老婆孩子留点儿怎么也说不过去,要是有人买你那肾也是好事,你敢这么做就是英雄,真正的男子汉!我的麻烦事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钱借給白家骏这个王八蛋!”
刘小富在心里说你未必就不是王八蛋,你明明知道那两万不是你的钱你怎么还要借给那个白家骏?拿别人的钱风光算什么本事?这么一想,刘小富的心就硬了起来,他对电话里的霍光芒说我也这样了,连自己的肾都敢卖了,那两万希望你尽快给我,那是救命钱,利息我就不说了,那两万,你要是不还,我就是到了那个世界都不会忘记。
霍光芒在电话里忽然没了话,好一阵子,才说:“看样子你不是编了故事给我听,我也不能对不起你,看情况吧,要是有可能连利息一并还你。”
刘小富差点儿叫了起来,“我要是会编故事就好了,那两万就不会让你拖到如今。”
霍光芒在电话里说他会想办法的,说到编故事,霍光芒说我老婆王小琴最会编故事。霍光芒说自己根本就不是乱搞,现在的女朋友是自己以前的女朋友,“十七八岁那会儿就认识了,当时感情好得不得了,还不是因为王小琴的老爸是总工我们当时才没走到一起,既然那时候走不到一起,这时候再走在一起有何不可?”
刘小富说,走到一起走不到一起是你的事,我现在对这些事一点点兴趣都没有,我只关心我那两万块钱。
霍光芒说你得这病,你以为我不难过?人活着谁都不知道谁会得什么病,会什么时候去死,所以我更得和那恶婆娘离婚,我和她离了婚法律会给我做主,看看她还能不能把我的工资卡死死攥在手心。
“你的钱她拿来花未必有什么不对。”刘小富说。
“你不知道我那恶婆娘有多恶!”霍光芒说。
刘小富想劝一句霍光芒,“再恶她也是你儿子的妈!”
“哪个女人做不了我儿子的妈?就现在,我保证一炮一个准。”霍光芒说。
刘小富悄悄把门开了一道小缝朝外看,老爸坐在那里,面对电视,一动不动。刘小富正要把门关上,老爸忽然开了口:“打电话跑到厨房干什么?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你儿子也不小了,不给别人看也要给他看着对头才是。”
刘小富说那天买的凤爪怎么还没吃完,就会唠里唠叨,懂不懂再放就要坏了。
六
这天晚上,刘小富刚刚吃过饭,肚子忽然又不行了,介入手术做完以后他总是拉肚子。他这边刚蹲下,放在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刘小富提着裤子从厕所里冲出来,一把把手机拿到手中,然后又回到厕所里,刘小富按一下键,手机里边马上就传出一声惊呼:“通了!通了!”这个人有点结巴,这个结巴说:“请问你是是不是就是想卖肾的那个人?”
刘小富皱了一下眉头,忙把卫生间的门往紧里推了推,用最小的声音说,“你说吧?”
结巴说,“是是是是就好,那你是什么血型?”
刘小富说,“A,A型。”
结巴几乎是叫了起来,说,“怎么会会会这么巧?”
结巴好像是和刘小富这边说一句话就要和电话那边的人商量一下,停一下,结巴又说了,说,“你今今今今年多大了?”
自从查出肝里的病以来,刘小富脾气一直都不太好,特别容易急躁又特别容易发火。
“四十八!怎么样?”刘小富说。
“四四四四十几?”电话里的结巴问。
“差两个月四十八。”刘小富心里说妈的个×,老子往小了说一百岁你未必能知道!
“好好好,好好好。”结巴在电话里又说:你没没没病吧?
“你说我有什么病?”刘小富说。
“好好好,好好好,”结巴说你怎么想起卖肾?
刘小富忽然答不上来了,为什么?还能为什么?有一股热气好像一下子从下边冲了上来,一直冲到了刘小富的脑门儿那里,刘小富的声音不觉大起来:
“为哪个!为了钱!”
“那那那,那好。”电话里的结巴说那你准备卖多少钱?
刘小富已经想好了,自己的这个肾绝不能卖少了:“三十万。”
电话里的结巴好像不会说别的话,只会说:“那好那好。”
“那好,那好,”结巴在电话里说咱们马上见见面好不好?
刘小富迟疑了一下,说,“好与不好我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等我的电话就是。”
电话里的结巴说:“为什么要等。”
刘小富说我不得想想卖给哪个?今天已经有四五个人都来过电话了。
电话里的人不那么结巴了,说,“咱们先见见面好不好?”
“我得想想。”刘小富又说。
“还,还想什么?”结巴说。
“那是我的腎脏,老子现在要把它割出来卖掉,我不得想想!”刘小富说。
“我老子,我老子再等恐怕就来不及了。”结巴说这是救命的事。
刘小富不再说话。
结巴忽然又说,“可以再给你加些钱,只要你快,咱们明天见见面好不好?”
刘小富刚才的那一点点便意忽然没了,刘小富坐在马桶上,用手摸肾脏那地方,肾脏是不会跳动的,但此刻刘小富觉得那颗肾在“突突突突”跳。刘小富心想明天已经和医院约好了要去做检查,因为马上又要做第二次介入手术。
“明天可以不可以?喂喂喂。”电话里的结巴问。
“行吧。”刘小富说。
“你怎么在卫生间里打这么长时间电话?”黄腊梅这时在外边说了话,你臭不臭?
“我自己拉屎给自己闻,我愿意臭自己。”刘小富说。
“好好好,你变成臭豆腐才好。”黄腊梅在外面说。
“那我就偏偏不再臭,我这就出来。”刘小富说。
“你给谁打电话?”黄腊梅又说。
刘小富脱口说:“姚海泉。”
“水热了,你洗吧。”黄腊梅说洗完用不用我帮你把皮备了,别到时候护士给你弄你又不好意思。
七
第二天,刘小富刚刚醒来,结巴就又把电话打了过来。
“师傅,师傅,今天有没有时间?”
刘小富怕厨房里的黄腊梅听到,小声说你这电话打得真是早,你说去什么地方?
结巴约刘小富去万花宾馆见面,“那地方有茶水。”
刘小富在心里说妈个×!老子未必就没喝过茶!
刘小富出门前都要去一下厕所,最近,刘小富不但总是不停地去厕所,头发掉得也更加厉害,总是一把一把地掉。昨天晚上洗澡,刘小富又禁不住“啊”了一声,手里是一大绺头发。冲头发的时候刘小富又“啊”了一声,手里又是一大绺。“黄腊梅!”刘小富叫了一声。黄腊梅赶过来,站在刘小富身后,也忍不住“呀”了一声,但她只能故做轻松,对刘小富说你干脆把头发剃光算了,现在街上留光头的人不少,还最最新潮,再说你脑瓜儿圆圆的又不难看。刘小富照照洗脸池子上的镜子,嘴上说,“哪个说脑瓜儿圆就好看,好看难看无所谓,你不嫌难看就行。”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说这也许是最后长在头上的东西了,怎么舍得剃光?以后可能连这几根头发都不会长了。想到此,刘小富突然心里一酸,人一屁股在马桶上坐了下来。以后?自己还会不会有以后?如果有,以后又会怎样?刘小富不敢想以后,刘小富只能想以前,以前的事驳杂纷乱没什么可以值得一提。这么多年来,刘小富辛辛苦苦却没挣到多少钱,更不用提有多少积蓄。刘小富一想起这些就忍不住要埋怨自己的老爸,怎么给自己取这样的名字?还当什么屁车间主任,给儿子取个什么名字!什么狗屁小富!还不如索性叫个“没富”!一个“小”字,一下子就把人给小死了,到现在刘小富不但没有小富可言,银行里连一点儿存款都没有。昨天晚上,刘小富又给霍光芒打了几次电话,每次打电话霍光芒总是大骂白家骏,大骂白家骏之后,他也急得没一点点办法。霍光芒那里的两万连一分也讨不到,所以,刘小富想看病还得借钱。
“手术一共花了多少?”蹲在厕所里,刘小富又问黄腊梅,这话他已经问了多次。
黄腊梅现在的耐性十分好:“一共是两万,给北京专家的好处费是五千,加起来是两万。”
刘小富在心里算了一下,说下次干脆就让彭大夫做吧,“还能省下五千。”
黄腊梅马上说:“也是,其实都一样,都是在电脑监控下看着做。”
话还是忍不住从刘小富的嘴里说了出来,让黄腊梅听了鼻子好一阵子发酸。
“哪能一样!北京专家这样的手术一天要做五十多,咱们这里的专家一年也做不了五个!”
黄腊梅说不出话来,她是没话找话,把吃剩下的早餐收拾好,站在厕所外边又问晚上刘小富想吃什么,要不要下去买只土鸡熬汤?
小富在厕所里说什么也不想吃,“没胃口。”
“想不想吃羊肚儿?”黄腊梅知道刘小富最爱吃清水羊肚儿。
刘小富却突然想起儿子小丰,“我这事千万不要让小丰知道。”
“你放心。”黄腊梅说没人告诉他他怎么知道?你好好儿吃你的饭,吃好了身体才会有抵抗力。黄腊梅这几天总是想着办法让刘小富吃得好一些,好像是,只要吃得好,那肝里的病就会好,她想再去给小富买一副猪肝。穷人也只好这样,相信吃什么补什么,其实连黄腊梅自己也知道偏方未必管用。刘小富现在是看见猪肝就想吐。
“吃不吃西瓜?要不,买半个瓜?”黄腊梅又说。
“不吃!”刘小富忽然火了起来。
“好好好。”黄腊梅说我现在什么都听你的还不行。
刘小富想让自己笑一下,但笑不出来。
“要不,弄个箱子去单位请大家捐助一下?”刘小富又在厕所里说。
“要捐款也得过了年。”黄腊梅说眼下人们哪顾得上这些,今天先把检查做完了,有什么事以后再说,也许肝里什么也没有了呢?
这时有人在外边“笃笃笃笃、笃笃笃笃”地敲门,黄腊梅从猫眼里朝外看看,是刘小富的姐姐和姐夫,后边还站着刘小富的外甥女小静。这些天,刘小富的姐姐再忙也要天天过来陪弟弟坐一会儿,她过来还不行,还要把小富的姐夫也拉上,这就让人心里更加难受。黄腊梅忙把门打开,小静挺着个大肚子提着两只烧鸡先进来。刘小富的姐姐随后,手里也提了两个塑料袋,一个袋里是灵芝,刘小富的姐姐不知听谁说灵芝可能对小富的病有疗效。一个塑料袋里是香烟。
“想抽就让他抽吧。”刘小富的姐姐小声对黄腊梅说。
黄腊梅的眼圈马上就一红,她这句话已不知说过多少次:“我儿子小丰离不开他!就是阎王也不会让他死!”
黄腊梅的话刘小富在厕所里听到了,刘小富说我身上的零件哪一件比别人差?哪一件都不比别人差,都是叮叮当当的好货!黄腊梅你放心,我不会给命运先卖了废铁,我不等命运卖它我就先把它处理了。刘小富不想再继续蹲下去,他从厕所里一边提裤子一边出来,对他姐说有事要先出去一下,然后自己直接去医院,“我已经和人约好了。”
“让你姐夫送一送你。”刘小富的姐姐说。
刘小富不让送,说自己活这么大才知道走路原来也是一种享受,就怕哪天连这种享受自己都无法享受了。
“到时候我天天送你。”刘小富的姐夫想把话岔开。
“到时候,就怕你去不了那种地方。”刘小富苦笑着说。
“舅舅你瞎说什么!”小富的外甥女小静说。
“这算瞎说?那地方人人都得去,只不过有迟有早。”刘小富对外甥女小静说。
“你有什么事,不是说好了先去医院做检查。”黄腊梅问刘小富。
“用不了多长时间,办完事我直接去医院。”刘小富说这件事关系着你和小丰今后的日子,是件大得不能再大的事!
黄腊梅看着刘小富,满眼都是疑问。
“放心,我总不会去杀人放火抢银行。”刘小富说。
刘小富的姐姐说,小富你到底要去办什么事?
刘小富说我这身体也干不了非法的事,“你们都放心。”
八
刘小富步行去了万花路的万花宾馆,想不到那些人早已经到了。
房间一进门的地方放了好大一盆鲜艳无比的假花,香得几乎要呛死人。
刘小富想不到那个结巴是个年轻人,长得蛮清瘦漂亮,刘小富一出现,早早等在那里的人都往起站了一下,而且都好像是吃了一惊,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个要把自己肾脏卖掉的人肯定是个身体特别壮的人,想不到站在他们面前的人这么瘦,面色也不好,穿着一件普通的大衣,还戴着一顶棉帽子。但他们顾不上多想,他们请刘小富坐下来,倒了茶水。结巴先说客气话,说无论事情怎么样他们都先表示感谢,总算有希望了:“现在找个肾脏不太容易,所以你是我们的希望。”
结巴说我老爸的一条命也许就在你身上了。
“谁都有老爸。”刘小富说。
“说得好,我们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你身上。”结巴说。
“你们先别这样说,我还不敢先答应你们。”刘小富说。
“那怎么可以,你是我们的希希希希希望。”结巴又急了。
“好。”刘小富说你说吧,我也有老爸。
“那我就把话简短一点说?”结巴说这件事要有许多手续要办。
事情真是没有刘小富想象的那么简单,直到现在刘小富才知道只有亲属之间才可以用对方的器官,如不是亲戚关系,就只能用死体,也就是已经死亡了的人的器官,在死者死亡后二十四小时内把器官移植给需要器官的人。如果不是亲戚关系,活人的器官移植是绝对禁止的,即使是亲戚,也要捐献器官的这一方写一份儿自愿捐献书,并且,还要医院方面的伦理专家开会论证通过。结巴说这些对他们来说都不成问题,只要花钱就办得到,结巴说为救他老爸一命,花一百万不算什么。“你这里我们准备花三四十万,医院那边我们准备花三四十万,这事只求快。”结巴说只要医院那边配型一成功,他们就会先付刘小富二十万,到移植手术做完他们会马上把另外那十万再付给刘小富。
结巴说话的时候刘小富一直不说话,只是两只眼忽然亮了起来。
“现在主要看刘师傅你了。”结巴对刘小富说咱们第一步首先要把关系变成是亲戚关系。
刘小富不知道怎么把关系变过来。“需要什么证明?”
“那好说,只不过是给派出所花钱的事。”结巴说,只要你同意别的就都好办。
“大约需要多长时间?”刘小富说自己也想尽快把这件事办了。
“你是不是急等钱用?”结巴说。
刘小富忽然撒了一个谎,说自己的母亲现在在医院里等着钱做手术。
“钱我们这边不成问题。”结巴说更何况你是为了你母亲。
“我真是急需钱。”刘小富说。
“我就喜欢刘师傅你这样的人。”结巴说那咱们就尽量把事情进行得快一些。
“那好。”刘小富说。
“我先在街道找人开个证明。”结巴说。
刘小富说不是开下岗证明吧?这证明我有。
结巴笑了一下,说这和下岗又没什么关系。
“证明我是你们的亲戚?”刘小富忽然明白了。
“对。”结巴说这事也不太好办。
“什么样的关系?”刘小富说。
结巴说刘师傅以您的岁数最好说是我老爸的兄弟,最好说当年您是我老爸家给出去的,您是A型血,跟我老爸一样,不会有人怀疑的,就是怀疑也不怕,反正是要花钱。您看好不好就说你是我老爸的兄弟?
“这没什么。”刘小富说生在这个世上大家原本都是兄弟。
“说得好,刘师傅你是个好人!”结巴说这也许只是个开头,以后你有什么事我一定会帮忙,一定帮忙,看得出刘师傅你是个孝子,是个孝子。
“我这边呢?”刘小富说需要我做什么?
结巴说你这边就写一个自愿把肾脏捐给我老爸的申请。
“申请?向谁申请?”刘小富说。
“向军区医院。”结巴说医院那边的伦理专家还要讨论通过一下。
刘小富说自己还从来没写过这种申请,不知道该怎么写。
结巴说这事好办,反正都是要打印,到时候刘師傅你签个字就可以,就让我们这边的人来写好了。结巴说中午饭已经安排好了,叫你的家人也过来一起吃个饭?如果肾脏移植成功,咱们就是亲戚,你想想,你的肾在我老爸的身体内工作,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
“中午不行,这事不能让我的家人知道。”刘小富看看表,站了起来,黄腊梅在医院那边也许已经等急了。
结巴说:“中午真不方便过来吃饭?那我下午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刘小富说可以,说话的时候刘小富肝那地方忽然又痛了起来,痛得他脸色都变了,好在他已经走到门口,门口那地方暗,出了门,进了电梯,刘小富痛得一下子蹲了下来,直到电梯停在最下面一层,电梯门开了,有人进来,刘小富才慢慢站起来。
刘小富去了人民医院,等在人民医院门口的却只有黄腊梅一个人。
黄腊梅迎上来,告诉刘小富他外甥女小静马上要生了,“在咱们家里正说着话就突然见了红,姐姐和姐夫现在也都去了那边的妇女儿童医院,所以这边只有我自己。”刘小富说你怎么不跟去那边照应照应,这边我自己也行,还不就是拍片做B超。刘小富说现在自己已经和医院几个科室的人都混熟了,是熟门熟路。黄腊梅说我还是跟着你交个费取个药拿个结果什么的,省得你上上下下乱跑。自从刘小富检查出肝癌以来,黄腊梅的身体倒好像比从前一下子好了许多,上楼下楼也不再喘气,她陪着刘小富先去放射科拍了片,然后去做B超,两项检查很快就完。黄腊梅让刘小富在门诊大厅等着,她自己去取结果。刘小富在外边等了很长时间,坐在那里没事,刘小富就一遍一遍看自己手机里的旧信息,刘小富的手机里存了许多过去的信息,现在看来,每一条都很有意思,每一条都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快一个小时黄腊梅才从里边出来,两手却空空的什么都没拿。黄腊梅对刘小富说放射科的机器不知怎么回事出了故障,片子可能明天才拿得到手。
“片子出来你姐的熟人会给咱们打电话。”黄腊梅说。
出了医院的大门,往北走,经过体育馆的时候,刘小富忽然想起给他老爸买一根拐,说老头儿到时候上楼下楼拄一下也就顶儿子在那里扶他一把。
九
一大早,刘小富被老爸那边打过来的一个电话吓个半死。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刘小富正准备和黄腊梅一道出门去医院。
打电话的人是老爸的邻居,岁数虽然和刘小富差不多大,但刘小富还是叫他刘叔。
刘小富的心已经猛烈地跳了起来,要是没事,这个刘叔肯定不会给自己打电话,事情果然一如刘小富所想,是老爸那边出了事。刘叔在电话里说小富你赶快过来一下,你老爸这一下子摔得不轻。一句话说得刘小富要跳起来,忙问大清早老头怎么就会摔了?人再老,走平地未必也会摔跤?刘叔说他那么大岁数自己踩着凳子擦玻璃,人这会儿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你考虑一下是否送医院。刘小富说,“我老爸开什么玩笑!一大早擦什么玻璃!简直是开玩笑!我老子可真是我老子!——我马上去!”
黄腊梅在一边说,“那你自己还去不去医院?要不……”
劉小富说,“要不哪个!他既是我老子,我能不去?”
黄腊梅自然无话可说,穿起衣服随刘小富便走,临出门没忘了把昨天买的那根手杖带上。
黄腊梅随刘小富打出租赶去了万花南路,偏偏路上又堵车,前边有个骑摩托的被撞了,路上都是血,两只鞋子东一只西一只在路上扔着,出租司机说出了这种事,被撞的人只要两只鞋子都不在脚上,这人恐怕就不行了。因为堵车,平时十分钟的路此时却走了二十多分钟,车钱多了一倍也没得话说。刘小富的老爸住三层,上楼的时候,刘小富直痛出一头的汗。黄腊梅在旁边搀着他,要他不要急,把气喘匀了再上。刘小富扶着楼梯只有苦笑,说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把气喘匀了,“我老子这是要我的命,不过我的命既是他给的,要就要吧,”又说我老爸和我妈当初怎么不多生几个。
“怎么就只生我和我姐两个!想不到这个苦!”
黄腊梅说要不让小丰过来和他爷爷一起住?
“我倒想和老爸住一阵子。”刘小富说这是我心里话,也许都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那你还不天天和你老爸抬杠斗嘴?”黄腊梅想把话岔开。
“能抬杠斗嘴也是一件好事,就是不知道我还能和我老爸抬到几时。”
黄腊梅把刘小富一路从一层扶到三层,刘小富掏钥匙开门的时候,门却从里边一下子打开了,是刘叔。
“我爸好点儿没?”刘小富忙问。
刘叔还没说话,刘小富就听见自己老爸在屋里开了口。
“你放心,你老子一下子还死不了。”
刘小富的火气一下子就冲了上来,“你七老八十也不看看自己,你擦的是什么玻璃,告诉你腊梅过几天就来擦玻璃打扫家,哪个要你自己动手!”
“你也别跟我吼。”刘小富的老爸说我窗帘挂钩坏了我未必就非要等你来。
“总之你要是我亲老子你就最好给我不要爬高。”刘小富说世界上真还再找不出你这样的老子,给你安电话你说怕安了电话我和我姐不来,要你找个保姆你又说有保姆在家里你不自在。
“我要喝水。”刘小富的老爸突然说你少说一句话先给我倒一杯水。
刘小富奔去厨房找来暖瓶,暖瓶提在手里倒不知是要给自己老爸倒水还是给刘叔倒。
“我要喝糖水。”刘小富的老爸又在屋里说。
“刚才真把我吓了一跳,‘嗵的一声。”刘叔跟过来站在厨房门口对刘小富说好在你家老爷子的门总是不插,要是从里边插死了外边的人又进不去多危险。刘叔说人上了年纪没个伴儿真不是一回事。
刘小富倒了两玻璃杯水,一杯茶水端给刘叔,一杯糖水端过去放在老爸的床头。
“坐起来喝口水?”刘小富问老爸摔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痛,什么地方动弹不得,他想要黄腊梅帮个忙扶老爸坐起来。
“不行不行不行!”刘小富的老爸一连气叫起来。
“不行就去医院。”刘小富说黄腊梅你马上去叫出租车。
刘小富的老爸说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骨头不会有事,叫什么出租车。”
刘小富的老爸当车间主任多年,有什么事从来都自己说了算,说先躺一夜看看再说。又说起在农机厂那年工伤的事,要换了别人还不吓死,血都流了够几百毫升,还不是躺了两天就好了,那时候连营养都没有,还不是喝了两天红糖水,红糖水说来真是好东西,最最补血。
刘小富想起老爸最爱吃冰糖的事,便对刘叔说我这个老子硬是与众不同,现在人人都怕得糖尿病,偏我老子天天都要嘴里含块冰糖才睡得着觉。
刘叔说老年人还是少吃甜东西好,“糖不是什么好东西。”
“谁说不是好东西,我们那时候得了病还不是全靠喝糖水?”刘小富的老爸说其实千好万好都不如糖水好,说我这牙疼,都疼多少年了,吃什么药都不好,喝下两碗糖水,一下子就不疼了。
“这也是因人而异。”刘叔说,有人牙疼,只要一抽烟就好。
刘小富的老爸继续说他的:“我在农机厂那时候,谁得了肝病,卫生所开证明就可以供应他二斤白糖,喝了白糖水人就好,你说糖不好,糖连肝病都能治。”
刘叔说这倒没听说过,“糖居然对肝有好处。”
黄腊梅马上拉了—下刘小富,要他跟她到厨房说话。
关上厨房门,黄腊梅对刘小富说你喝喝白糖水看看?我也好像听老人们说过这事,说肝病见糖就好,说着就给刘小富冲了一碗白糖水要刘小富喝。刘小富端起那碗糖水,说糖水要是能治了我的病普天下的医生还不都气死!又说我老爸摔这一下就是骨头没事,筋骨也不会轻松,你赶快去买些排骨炖排骨汤给我老爸补一补。刘小富说医院你上午就不必去了,去了也就是挂吊瓶,待会儿我自己去,挂完吊瓶我自己会回来,干脆中午饭就在我老爸这里吃,我也好久没喝你炖的排骨汤了。
黄腊梅说炖排骨汤还不是一会儿的事,我先陪你去医院,我看你老爸好像没事。
“有事没事你先陪他一上午。”刘小富说要想让我心安你就这么做。
黄腊梅说事情怎么都凑到了一起,还不知道你外甥女那边生了没有。
刘小富说自己力不从心管不了那许多,“我老子既然没事我就不多想了,我现在能多想想的就是怎么才能给你和小丰留下些钱,我爸这边我倒不多想了,他那点退休金也够他花了,看病还有公费医疗。
从厨房出来,刘小富又问老爸好点儿没?
“你给我搽搽碘酒。”刘小富的老爸说你小时候踢球把脚脖子崴那粗,搽搽碘酒就好。
给老爸搽完碘酒,刘小富去了医院。
十
刘小富是顺着万花路走,穿过万花南路的十字路口,风一下子大了起来。结巴的电话也就是这个时候打了过来,结巴说他那边把该办的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说现在这个世界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只要花钱就可以把一切事都办了。结巴说了一句玩笑话,说他们现在是在用金钱和死神赛跑,但愿能得到刘师傅的合作一起跑过紧紧跟在他老爸屁股后边穷追不舍的那个死神。听着结巴在电话里说话,刘小富在心里说你们是用金钱和死神赛跑,我可是为了金钱加速走向死亡。结巴又在电话里告诉刘小富,医院的伦理专家今天就有可能把论证弄出来,到时候有可能要刘小富出现一下,回答一下医院伦理专家们的问题,然后,就可以做配型了。
“然后,是不是我就可以拿到钱了?”刘小富说。
结巴在电话里说:“你母亲那边怎么样?”
“正等着钱做手术,我是不是可以先拿到二十万?”刘小富说。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结巴在电话里说二十万是小事情。
刘小富说现在已经有人要出到四十万了。
结巴在电话里忽然没了话,停了好一会儿,小声说:“不可能吧?”
刘小富没说话,心怦怦怦怦跳起来。
“这样吧,如果配型成功的话可以再给你加五万。”结巴在电话里说,“我知道你也是为了你母亲,我这边是为了我老爸。”
刘小富长出了一口气,“那就三十五万?”
“对。”结巴在电话里说虽说是这样,但对外边最好说一分钱也没拿,是捐献,“因为咱们对外是亲戚,你是我老爸的兄弟。”
“要是我把两个肾都给了你们呢?”刘小富忽然说。
结巴在电话里大吃了一惊,连说那不可能那不可能,要是那样你可能连命都会没了,医院也不会答应!除非你长有三个肾,长三个肾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太少了,太少了。
“不是可能不可能,我他妈马上就要没命了!”刘小富在心里说。
刘小富忽然站了下来,他面前是医院旁边的那家花店,店里满坑满谷都是鲜花,还有用黄色菊花扎好的大花圈,又不知是什么人死了。刘小富的鼻子忽然酸了起来,结巴在电话里还在说什么,他连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电话再次响起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好一会儿,这次是黄腊梅打过来的,黄腊梅对刘小富说,“你外甥女小静生了,生下个男孩儿,是剖腹产,八斤九两,你姐说一定要你给他取个名字。”
刘小富说我又不是什么取名专家,要我取的是什么?
“也算是个纪念。”黄腊梅这话一出口马上就在心里后悔。
“有什么好纪念。”刘小富说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你当舅姥爷了。”黄腊梅在电话里又说。
刘小富的脑子里忽然一片空白,他听见自己在对电话里的黄腊梅说: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能给你和小丰挣到三十五万。”
黄腊梅在电话里给吓了一跳,“你说什么?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花店跟前。”刘小富说。
“花店?哪个花店?什么三十五万?”
“人民医院跟前的花店。”刘小富说。
“你说什么三十五万?”黄腊梅再次说。
“我可能给你和小丰挣到三十五万!”刘小富又说。
黄腊梅忽然不再做声,她想问,又不便当着刘小富的老爸问,刘小富的老爸就在她身边。
刘小富听见自己老爸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还没出国就说自己挣到三十五万,这小子是在做美梦!告诉他早早回来喝他的排骨汤!我还要他给我搽碘酒。”
十一
许多年了,刘小富和黄腊梅很少回到他老爸这边老房子住,就是过年过节,刘小富总是吃了饭拍屁股就走,最多陪老爸打一下五角钱的小麻将,再晚也不会超过晚上十二点。黄腊梅按照刘小富的吩咐炖了排骨汤,在里边放了一些牛蒡,把火开到最小让它炖着,腾出手来把自己和刘小富住了八九年的那间北面的房子收拾了一下。这个家黄腊梅是最熟悉不过,被子和褥子都放在那个立柜里边,现在一一取出来。黄腊梅想好了,离过年也没多长时间了,从现在开始她就要和刘小富住在这里,也算了结刘小富一桩心愿。她和小富睡北边屋,让小丰和他爷爷住爷爷那屋,那屋里的大沙发看上去土头土脑,打开来睡人却又宽畅又舒服。黄腊梅在这边收拾,刘小富的老爸在另间屋说了话,说腊梅你做什么?黄腊梅说爸你这大岁数摔一跤真是吓人!我和小富在这里睡几天侍候您几天也算是孝敬,省得您再摔一跤我给您吓死。晚上我打电话让我姐也过来一块儿吃个晚饭。
“她不在医院里陪小静?”刘小富的老爸说。
“医院现在不让任何亲属陪床。”
“那小丰是不是也不走?”刘小富的老爸说。
“他是你孙子,你以为他是哪个!”黄腊梅说正好我那边暖气这几天没一点点温度。
刘小富的老爸“哦”了一声,说其实暖气费蛮贵,下边的话没再说。
黄腊梅像是已经知道了刘小富老爸肚子里是什么话,说,“明年干脆我那边就不交暖气费,住到这边过一冬还会省下两千多。”
“好啊,懂得节约就好。”刘小富的老爸说厨房里是不是你的手机在响?
厨房里黄腊梅的手机果然在响,是刘小富的姐姐打过来的,刘小富的姐姐声音有些不对头,她问黄腊梅是不是在家里,小富在不在旁边,身边有谁。
黄腊梅说自己现在正在老爸这边,小富不在,身边没人。
刘小富的姐姐说人民医院那边打过电话了,结果出来了。
黄腊梅忽然有一种不祥之感,心怦怦乱跳起来。
“怎么样?”
“小富那上边又长了一个,有栗子那么大。”刘小富的姐姐在电话里把话说了出来。
“这么快?转移这快?”黄腊梅说。
“这还不能叫转移。”刘小富的姐姐说。
黄腊梅说小富知道怎么办?我是不是要告诉他一时取不上片子。
“那就先别告诉他。”刘小富的姐姐想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他要看片子怎么办?”黄腊梅说。
刘小富的姐姐也想不出办法,只说一句:“你先别让他知道。”
“怎么辦?”黄腊梅说。
刘小富的姐姐又能怎么办。
两个人都在电话里静了好一阵子。
和刘小富的姐姐通完话,黄腊梅的身上一下子软得像是连一点点力气都没了,她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忽然想起来灌水,水已经开了好一会儿了,水壶已经疯狂地叫了好一阵子了。
“小富怎么回事?”刘小富的老爸这时突然在屋里说了话。
黄腊梅回过神来,忙说还不到出国时间,听说过了年就差不多了。
“我的儿子我知道。”刘小富的老爸说你看看他的头发都掉成个什么样,游泳池又不是镪水池,还能把头发弄成那样?我知道他有事,他有事不跟我说我也不问。他说他出国,我又不是白痴,我怎么说当年也是车间主任,我现在还能看电视,他出国?他出国做什么?他凭什么技术?他又没力气,他几时这样关心过我,又来看我又给我买手杖。
刘小富的老爸不再说话,却把放在床边的手杖拿起来看了又看,黄腊梅自然也不敢说话,拎着个空壶在厨房的凳子上坐下来。炖排骨的味道很香,但这一刻却好像连一点点味道都没有了。刘小富的老爸忽然在屋里又说了一句:
“小富不会挣钱,但他人不坏。”
黄腊梅心想,除此之外,自己还能要求小富什么呢?
中午的时候,刘小富和他姐姐都回他老爸这里吃饭,医院那边有小静的婆婆守着。
黄腊梅的排骨汤炖得很香,她先给小静那边盛过了一饭盒,然后把一碗端给躺在床上的刘小富老爸。刘小富喝得也像是很香,连说像这样的好汤只有我老婆黄腊梅才炖得来。“富人喝燕窝汤,穷人喝排骨汤,要说养人还是排骨汤。”刘小富说喝得起排骨汤的不能说是穷人吧?生病以来,刘小富难得像现在这样开心过,但开心也只是瞬间的事,一顿饭没有吃完,刘小富又捂着肚子去了厕所,吐完即拉,人坐在马桶上满头是汗已经是百般站不起来。刘小富在厕所里的时候又有电话打了进来,黄腊梅把手机拿到厕所里让刘小富接,电话是结巴打过来的,说明天上午要刘小富去军区医院那边做一下配型前的检查。
“军区医院这边都安排好了。”结巴说检查没事就可以马上做配型了。
“如果配型可以,是不是先把那二十万付一下?”刘小富说。
结巴在电话里说这个你只管放心,“没问题,但也要有一个合同。”
“只要我一上手术台,不管成功不成功那十五万必须给我。”刘小富又说。
“这个也不会有问题。”结巴在电话里说配型成功先给你二十万,上手术台再给你十五万,分两次打清。
“那咱们明天一早见。”刘小富说。
结巴说我去接你,我自己开车。
刘小富想想,说那咱们在木棉花宾馆门口见面好不好?
木棉花宾馆就在刘小富家门南边。
刘小富虽然身上难受,但心里忽然好像舒畅起来,他已经想好,给老爸留五万,三十万给黄腊梅,再加上霍光芒欠的那两万,黄腊梅手里就有三十二万,房子,小丰结婚就住自己现在那一套,老爸的这一套迟早还不是黄腊梅的?就是自己过到那个世界去重新投胎,也算是一个交代了。
“你没事吧?”黄腊梅在厕所外边小声问了一句。
刘小富的老爸说了句什么,黄腊梅忙说小富不知吃什么坏了肚子,吃点儿药就好。
十二
第二天一大早,结巴把刘小富接到了军区医院。
结巴对刘小富说真是对不起,让你早饭也没得吃。
少吃一顿也饿不坏。刘小富说,做这种检查谁敢吃饭。
结巴说那中午刘师傅咱们一起去吃饭好不好?“我请你,吃什么都可以,鱼翅都行。”
刘小富说吃饭就不必了,自己还有事。
“刘师傅你真是天底下最最大的孝子。”结巴又说。
刘小富这几天精神有些恍惚,加上昨夜一夜没睡,一时想不起说什么了。
“像刘师傅这样卖肾给母亲治病真应该报道一下。”结巴说只可惜此事不能报道。
刘小富忽然想起问结巴他父亲住在哪个医院。
结巴说他老子在北京,这边检查好,送北京去做,“这边做不好。”
“军区医院条件总算可以了吧?”刘小富说。
“差远了,只是让他们检查检查,正式手术还是要去北京做。”结巴说现在只有没办法的人才会在军区医院做手术,有办法的人都去北京。
刘小富忽然没话,紧闭了嘴看车子外边。
在刘小富的记忆里,军区医院是市里最好的医院,那些年一般人都很难在军区医院挂号看病。医院在万花路的西边,那一带风景如画,既可以看到北边的山峦,西边的梅洛水库正好挨着医院的疗养区,有人说那个水库当年就是为军区医院修的,为的是让军区首长在里边游泳。还有一种传说,说是梅洛水库下边有一条战备暗道一直通着北京。当年每年“八一”的时候刘小富都会与厂里的人到梅洛水库来游一次泳,霍光芒有一次还差点儿给淹死。但现在一切都变了,随随便便哪个人都可以到这个医院里来看病,在这里看病也好像是对病人的一种安慰,不管怎么说,军区医院还是市里最好的医院。医院的大门在刘小富的记忆里像是永远有两个军人在那里守卫着,但现在守卫大门的军人永远不见了,那大门也像是一下子变小了。刘小富还记着老农机厂的书记当年为了来这里住院还特批给军区医院两辆当时买也买不到的小四轮。现在真是世界大变天翻地覆,小四轮没人要了,工人下岗了,农机厂也早已塌台,更加让刘小富想不到的是自己要在这里把自己的肾活生生卖掉!
“刘师傅,你母亲要是想在这边找人你跟我说。”结巴对刘小富说。
“不必了。”刘小富说。
“不用客气。”结巴说。
“谢谢。”刘小富又说。
结巴已经在军区医院这边安排好,一到医院,刘小富就开始做检查,过B超、拍X光片、验血、查尿,还有大便,这种检查到哪里都是一样。刘小富此刻变得木头木脑,脑袋仿佛一下子没了知觉,仿佛身子和脑子已经分了家,好像将要和身体分开的不仅仅是那个肾,而是刘小富生命的全部!刘小富生活的全部!
十三
快到中午的时候,刘小富才慢慢从军区医院大门出来。
从军区医院里出来的刘小富双目无神,捂着胸口靠着医院的门柱站了好一会儿。
刘小富觉得自己已经实在没有力气上对面的过街天桥,但要到马路对过他又别无选择。刘小富慢慢上了天桥,此刻正是下班时间,桥下车很多,车上人也很多,刘小富呆呆站在天桥上,朝下看了好一会儿,恨不能当着桥上来来往往的人即刻就一头从上边栽下去,从小他老爸就常常对他说人不能光想好事,光想好事到最后就只有难受,但刘小富觉得自己不是在想好事,而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努力,想不到事情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刘小富只想是检查肾脏,想不到做彩超的时候,那个李主任忽然吃惊地叫起来,说“小黄你来小黄你来。”直到此刻,刘小富才知道那个结巴姓黄,他的父亲就是人人皆知的煤运的黄局,就这个结巴,和医院里的人上上下下都混得很熟。那个做彩超的李主任马上拉结巴到外边去说话,他们都说了什么刘小富不知道,直到结巴又带他去拍了一下X光片,拍完片子,结巴要刘小富在走廊里等着,他和那个做彩超的李主任在肿瘤科的柴主任的诊室里边说了老半天话。后来,刘小富给那个柴主任叫到了门诊室里,肿瘤科柴主任眉毛特别浓,让刘小富好想一笑,因为这个柴主任让他想起以前看过的勃列日涅夫的照片,但这个柴主任待人和气,请他坐下,关心地问了一些刘小富身体方面这里那里的事,还问刘小富身上都什么地方不舒服?后来对刘小富说明天让你家人陪着你来一下好不好?我给你再做个检查好不好?你一定来,你的身体好像有些问题。军区医院的柴主任这么一说,刘小富马上明白自己的病情已经被彩超给超出来了,想隐瞒也隐瞒不住了。柴主任对刘小富说话的时候,站在一边的那个结巴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失望还是惊恐,只是一动不动看着刘小富,钱已经花出多少且不说,打通各个关节费了多大劲儿且不说,令他吃惊的是眼前的这个刘师傅竟然肝上长了两大块恶性肿瘤。柴主任悄悄对结巴说这个病人已经活不了多少天了,怎么还敢做肾脏移植?现在应该做的是,他应该安排他自己的后事了。
虽然结巴对刘小富说“刘师傅等一下我送你。”但刘小富哪还能让人家再送。
刘小富好不容易从军区医院出来,好不容易爬到了过街天桥上,此刻他再也走不动,即使是想从天桥上跳下去,恐怕也攀不上天桥上的那道栏杆。
这时旁边突然有人开口说,“咦,刘小富?”
说话的是蹲在旁边卖光盘的那个人。
刘小富掉过脸去,马上认出是老农机厂的武青,武青的个子又高又大,却长了一张刻薄嘴,嘴刻薄心地也不宽厚,再加上娶的又是乡下老婆,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刻薄之外又加上了无边无际的怨气。他还有个坏毛病,常把车间里的东西偷偷摸摸弄出去卖掉,有一次拿了车间的一段铜料受了处分,恰好那时刘小富的父亲是那个车间的主任。
“你来这儿干什么?”武青说。
“看病。”刘小富说。
“你还会有病?”武青像是开玩笑,说你和你父亲要得也只能是心病。
一句话说得刘小富想抬腿马上走开,腿上却没得一点点力气。
“厂子被你们吃没了,不得心病也怪。”武青又说。
一股火忽然从刘小富心里直冲出来,“武师傅,你说哪个错!”
武青说当然错总是在我们这边,你们不会有错。
“我再正确还不是照样下岗!”刘小富说。
“我以为你永远不会下!”武青说。
刘小富不再说话,浑身的难受让他把脸掉向了另一边。
农机厂的武青又开了口,“你想什么呢。”
“想死!”刘小富突然说。
武青吃了一惊,但马上笑了,他以为刘小富是在开玩笑:
“真想死?真想死怎么不从这里跳下去?”
刘小富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他看看天桥下边,在心里问自己,“如果一下子跳下去呢?”
“看来你还是不想死。”武青笑着说。
“我是没力气去死。”刘小富说。
武青说:“笑话,死还要力气?没听说过!”
“哈,你帮我一把看看!”刘小富说。
“我再爱助人为乐也不会帮助别人去死。”武青说。
刘小富说武师傅我确实没见过你助人为乐过。
“那是因为别人都比我活得快乐!”武青说。
刘小富忽然在心里同情起面前的这个武青来,武青说得对,那时候好像是农机厂里的人们都比他活得快活,几乎是,什么快活事都轮不到他,只有倒霉的事跟他有份儿。
刘小富说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去医院?
“为什么?”武青说。
“我也让你高兴一下,这一下子,我永远不如你了!”刘小富说为什么我不如你,因为我已经是肝癌晚期了,肝癌!
“你是取笑我?”武青说在农机厂那会儿你还没拿我开过心,你是不是现在想补上,武青忽然停下来不再说话,因为刘小富已经慢慢把戴在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刘小富的头发更加稀少了,化疗之后的脱发和正常脱发不同的地方是头发脱落得完全没有章法,那种杂乱无章让人心打寒战,是一派死亡气息。
“你问我去医院做什么?”刘小富说我是想去把我的肾脏卖掉给孩子和老婆留些钱。说话的时候,刘小富的眼泪流了下来。“你说我取笑你,我是在取笑我自己!我想把自己的肾脏卖掉,但我的肾脏这会儿恐怕喂狗狗都不会吃,当垃圾都不是好垃圾!扒出来白给人家人家都不要!”说话的时候,刘小富又把帽子戴了起来。“你说别人都比你活得快乐,这一下,武师傅,至少你是比我快乐了。”刘小富指指下边:
“我真想跳下去,我真想死。”
“你这样死还不是白死!”武青说。
是武青的这句话突然让刘小富打了个大寒战。
“就是死也不能白死!”武青又說。
“不能白死?”刘小富说。
“拿两张碟回去看,算我送你,万事想开点儿。”武青说。
“我还看什么碟。”刘小富说你留给别人看吧。
“我扶你。”武青说。
“不用了,我要谢谢你,你说得对,我不能白死!”刘小富又说。
从天桥上下来,刘小富忽然觉得有些后怕,自己刚才要是一冲动从上边一下子跳下来怎么办?那自己岂不是真正落一个白死。刘小富现在明白了,就是死也不能白死!死也要死得有用,死也要给黄腊梅和儿子弄一笔钱,从这一刻起,刘小富不再是等死,而是为了钱自寻死路了。
这一夜,刘小富吃了两颗药才睡着,睡到后半夜两点又疼醒来,再吃两颗,又睡到凌晨四点,睡着后却不停地做梦,梦中都是南来北往疾驶的汽车,梦做到后来,也不知自己是在梦里还是醒着。最后一次醒来,刘小富不再睡,又吃止痛药,吃过止痛药,他眼睁睁躺在那里把自己所熟悉的每一条路都想了一个遍,刘小富现在想明白了,要想弄到一笔钱,跳楼不行,吃药不行,跳河也不行,触电也不行,只有让汽车撞自己,撞死就是三十万!对自己来说,寻死也要抓紧时间,要是像自己老妈那样一旦肝昏迷再有什么想法也办不到了。刘小富选定了一条寻死之路,那就是万花路,这条路上车最多,而且人也多,如果选择一条没多少人的路,司机撞完自己开车跑掉怎么办?
刘小富想好了,就去万花路寻死!
十四
很长时间刘小富都没去过公共澡堂洗澡了,这天吃过早饭刘小富拖着虚弱的身子去公共澡堂洗了澡,他对黄腊梅说,马上又要做介入,洗个澡干干净净别让人们讨厌。刘小富这次洗澡用了一个多小时,回到家,忽然对他老爸说您的脚也该洗一洗了吧,从那天摔跤到今天都三天了,这么大人三天没洗脚了,你不臭别人也臭。不由老爸分说,取了洗脚盆倒了水便过来给老爸洗脚。刘小富这是第一次给老爸洗脚,洗完脚,又替老爸把趾甲剪了一下。
“小时候我带你洗澡你还记得不记得?”刘小富老爸说你那时候一见水就哇哇哭,一点儿也不像个男孩子,从小就没什么大出息。
刘小富说洗澡倒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次我踢球回来你说我脏,把我没头没脑按在盆里就给我洗,说实话老爸你那时候有几分像希特勒!
“我带你去公园打滑梯你总记得吧,你总是说再打一次,再打一次,我休息一天倒要陪你打半天滑梯。”刘小富老爸说你打滑梯打累了倒要骑在我脖子上回家。
“那就对了,你是我老子我不骑你脖子还能骑哪个!”刘小富说,“说起这一辈子我最最不满意的就是您给我取了个‘小富的名字,到现在我是既无大富也无小富。”
“你有儿子,还不到说没富的时候。”刘小富老爸说。
“你孙子至今连个工作都没有,我不知道他的富在什么地方?”刘小富说。
“你向我学习,活到七十三熬到儿子给洗脚就是富!”刘小富的老爸说。
刘小富的眼里突然有了泪花,他低下头装作给老爸剪最后一个趾甲,嘴上却说,你以为我想给你洗啊,还不因为你是我老爸,我是没办法。
“那就对,你没办法就好,谁让我是你爸。”
刘小富的老爸说我这一跤还是摔得好,要不你一出国,谁来给我洗这个脚。
刘小富给老爸剪完脚趾甲,然后又去给儿子小丰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儿子有一件东西在花瓶下边的那个抽屉里,是下边那个抽屉,儿子小丰说老爸你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事?什么要紧的东西?
“你看了就知道了。”刘小富说晚上要早睡,别盯着电视一看就是后半夜。
儿子小丰说我又不是七岁八岁,你和我妈在那边好好照顾老爷子就是,老爷子没事吧?没等刘小富回答,儿子那边电话已经放下,电话里已是一片忙音,刘小富张张嘴,眼泪已经顶了上来。
刘小富上了路。刘小富知道自己不能对黄腊梅多说什么,话一多,黄腊梅就会察觉,再说,一辈子跟她也说得太多了,要是说,再说十年二十年也说不完,索性不说。从老爸那里出来,刘小富在商店门口破天荒打了辆出租,出租车司机黑不溜秋,很胖,不太爱说话的样子。刘小富却忽然非常想跟他说说话,说,今年天气不冷?出租车司机好一会儿才开口答话,说是不太冷。刘小富说快过年了,过年的时候你们能挣个好钱。出租车司机又停了好一会儿才说:“不下雪还好,下雪车跑不开,也不好挣。”刘小富说下雪容易出事,一到下雪天,医院里的病号就多,不是断胳膊就是断腿。出租车司机说最怕那种不会骑车的女人,左拐右拐右拐左拐往往就摔到车轮子下边。
“轧死怎么办?”刘小富说。
“怎么办,倒霉的还不是那骑车的人,司机怕什么,有保险公司。”
“轧死一个人现在是多少钱?”刘小富说。
“三十万。”出租车司机说要是轧不死就说不定多少钱了。
“三十万也不算多!”刘小富又说。
“轧死是三十万,没轧死就无法说,如果再碰上一个赖在医院不肯出院的话。”出租车司机说到时候倒霉的就是他们司机。
“三十万不多。”刘小富说那是一条命!就是五十万他也花不到一分!
“好在现在有保险公司,要是没保险公司三十万还不要了司机全家的命!”出租车司机说你怎么还说三十万不多?
“就是不多!那是命换来的!”刘小富说。
“多!”出租车司机说。
“不多!”刘小富说。
“你这个师傅像是很有钱,要不不会这么说话!”出租车司机说。
“就是不多,那是一条命!”刘小富忽然生了气,要求下车,万花路也到了。
“我要下车!”刘小富说,下了车,刘小富又对出租车司机说:“告诉你,就是一百万也不多,那是一条命!一条命!”
“我也告诉你,出租车司机又不是富人!”出租车司机也跳下车大声对刘小富说。
刘小富忽然不再说话,这个司机说得对,出租车司机也不是富人!
十五
刘小富双脚站在了万花路上。
万花路路两边是一盆盆的塑料假花,红红绿绿也不难看。
刘小富上中学的时候就来过这里修路,当时这条路是万花公园后边的一条土路,北边是一家生产轴承的厂子,现在厂子不见了,商店大宾馆倒是一家连着一家,最高那个楼是希尔顿,比它矮一些的是卡宾斯基,都是住一晚要大几千的地方。刘小富小时候还好,对富人就那样,你富你的,我不富也照样在太阳下该吃饭吃饭该拉屎拉屎!你奈何不了我那一泡屎!可现在刘小富不知怎么突然仇恨起富人来,好像他们口袋里的钱都是他身上的脂肉膏肝!刘小富慢慢走到了希尔顿宾馆的门口,他昨天晚上已经想好了,要死就在这里死,因为在这里出出进进的都是些富人,寻死是一件晦氣得不能再晦气的事,这晦气应该留给富人!既然他们活得那么滋润,既然他们活得那么得意,既然他们想要什么有什么!那就让他们晦气一下!希尔顿宾馆门口出门朝西就是万花南路,是一个坡,一个转弯,车从宾馆里开出来必须要猛转一个弯,如果有人在转弯的坡下猛地出现车还真不知能否刹得住。
刘小富站在了那里,人一站在那里,眼泪就禁不住开始哗哗哗哗往下淌,身子也跟着一阵紧似一阵地发抖,抖得刘小富只好蹲了下来。这时候有车从宾馆里边开了出来,这是辆刘小富叫不上牌子的好车,车身特别长,车从离刘小富不到两三米的地方开过的时候把地上的枯叶一下子卷了起来。在那一瞬间,刘小富只要往起一跳,把身子往那边一冲一切就都解决了,但刘小富抖得更厉害,死是让人恐惧的,死永远不可能让人欢欣鼓舞。长这么大,刘小富只亲眼看到过一次车祸,那天早上他去菜场,过十字路口的时候猛地听到“嘭!”的一声,是声音先过来,然后才看到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老头给一辆出租车撞得飞了起来,然后又落下去,重重落在出租车的挡风玻璃上,那辆车的挡风玻璃当下就碎了。刘小富跑过去的时候看到了血,血从老头儿的鼻子眼睛耳朵里很快流了出来。出租车司机是个年轻人,慌慌张张从车上拿来一卷卫生纸,那一卷纸马上全部被血浸透。
又有一辆车从宾馆里开了出来,刘小富还蹲在那里。
有五六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推着一辆车也朝这边走了过来,刘小富想站起来,但疼痛让他马上又龇牙咧嘴地蹲了下去,一个年轻人朝刘小富紧走几步,问:“师傅你没事吧?”
刘小富说:“没事,谢谢。”
“要不要帮忙?”这个年轻人又说。
刘小富想站起来,疼痛却让他一屁股又坐在了那里。
“你是不是什么地方不舒服?”这个年轻人伸手搀了一下刘小富。
另外那几个年轻人已经把车停在离刘小富不远的地方,他们开始搭一个宣传架子,架子搭好,又把一个小桌子摆在了那里,刘小富看了看宣传架子上的标语,“全球血压日”。
刘小富站起来,把脸慢慢慢慢朝南边掉过去,身子跟着也慢慢慢慢掉了过去,刘小富慢慢慢慢离开了希尔顿宾馆,又朝卡宾斯基那边慢慢走过去,去卡宾斯基要过到街对过去,过街的时候刘小富等了一下从东边过来的车,车从他身边开过去的时候刘小富的脑子忽然清亮了一下?这岂不是个好机会?只要把身子朝那边一斜一切就都结束了。但刘小富还是慢慢走到了街对过,站在了卡宾斯基大饭店的门口。当年他还在老农机厂的时候,厂里在卡宾斯基饭店开过订货会,当时卡宾斯基还叫东方红宾馆,这家宾馆是英国人盖的老宾馆,刘小富记得饭店的大门往左是两丛树丛,但让他失望的是当年那两丛大树丛现在不见了,大树丛那地方现在是广告牌。卡宾斯基对过是民航售票处,再旁边是金税宾馆,过去,是卫校。这时候街上人正多,刘小富看看两边,前边不远的地方有人正朝这边看,可能是茶馆的服务生,还在招手,是在招呼一辆车,在帮顾客泊车。刘小富站在了广告牌子的后边,他想好了,只要一听到汽车的响动就从广告牌子后边闭着眼睛冲出去。只有这样,自己才不会白死,只有这样,自己才能用自己最后的努力给黄腊梅和儿子小丰弄到三十万!也就在这时候刘小富听到了汽车的声音,汽车正从自己左边开过来。
车快开过来的时候,刘小富把一只脚猛地迈了出去,但他没敢迈第二只脚,却再次脸色煞白地蹲了下来,冷汗顿时出了一脑门儿,在这个世界上,没人不怕死!死是令人恐惧的,不可能有人会欢欣鼓舞地面对死!好一阵心跳过后,刘小富慢慢慢慢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了那瓶白酒。这瓶酒刘小富昨天就已经准备好了。
刘小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喝酒了,从小到大,他从来都没有喜欢过酒,过去他喝酒都是为了讨别人喜欢,或者是,为了农机厂的生意,现在没有人再需要他为了生意喝酒,他也不必要为了别人高兴而把酒灌到肚子里,这一次,他是为了自己,为了黄腊梅,为了小丰。
没人看见刘小富在那里把酒瓶的盖子咬开,也沒人看到刘小富把瓶子举起来,也没人看到刘小富举着酒瓶大口大口地喝酒,喝到后来酒呛得他咳嗽起来,刘小富在那里咳嗽了好一阵,然后举起瓶子继续喝,一瓶酒很快就让刘小富喝下去了一大半儿。很快,刘小富就天旋地转起来,刘小富扶了一下广告牌,想吐,却吐不出来,早上吃的止痛药还在那里起作用。在天旋地转中,刘小富的耳边响起了汽车开过来的沙沙声,听声音是辆小车,这辆车开得很快,也许是刘小富的动作太慢了,他还没往那边冲,这辆车已经开了过去。
当汽车声音再次响起来的时候,刘小富看清了,是一辆黑色小车,从卡宾斯基大饭店里开了出来,刘小富看清了开车的是个中年人,刘小富还看清,这辆车的挡风玻璃上挂着一个什么亮晶晶的东西在一晃一晃。酒让刘小富的胆子忽然变大了,车开到刘小富的面前时,他一下子松开了抓着广告牌的手,身子猛地一荡,人跌跌撞撞朝路上一下子冲了出去,万花路的路面在去年刚刚修过,是既平整又好,脚踩上去真是舒服。松开手的刘小富一下子没了可依持的东西,他本可以一下子冲到那辆开过来的汽车的前边,但跌跌撞撞的刘小富由于跌跌撞撞却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感,车上的司机发现了从路边突然冲出来的人,猛地把车往路那边打了一下,车猛地往那边打方向盘的时候,恰恰躲过了冲过来的刘小富,但汽车的后屁股却把刘小富猛地带了一下,刘小富只觉被猛地一拽,人一下子变得轻盈起来,一下子飞了起来,没有一点点痛苦,也没有一点点难受,人一下子就飞了起来,但这个飞翔极其短暂,然后是落下去,一下子落在万花路路边的长青树矮墙上,冬天的长青树,灰不溜秋没一点绿色。
刘小富落下去的时候听到了一声尖叫,那声尖叫才是怕人,这辆车为了躲刘小富,却撞到了另一个骑自行车的人。
十六
刘小富还是在人民医院里又苏醒了过来,黄腊梅坐在病床旁边。
“我怎么没死?”刘小富问黄腊梅,声音低得不能再低。
刘小富的声音太低了,黄腊梅没有听到,黄腊梅坐在那里睡着了。
“我要去万花路。”刘小富又说,他用了最大的力气。
这一次黄腊梅听到了,刘小富那边像是有了动静,她睁开了眼。
刘小富的嘴唇在一动一动:“我、要、去、万、花、路——”
“你说什么?”黄腊梅说。
“我、要、去、万、花、路——”
“你说什么?”黄腊梅又说。
刘小富的嘴唇在一动一动,他用了最大的力量:
“我、要、去、万、花、路——”
黄腊梅顿时泪流满面,她忽然一下子把脸贴在了刘小富的脸上,她不知道那湿漉漉的东西是自己的泪水还是刘小富的泪水,但她明白此刻苏醒过来的刘小富根本就不知道他现在除了面对死亡,还要面对那辆车,面对那个人,面对更多更麻烦的事!但再多的麻烦事加在一起都要比死亡小,只要活着,哪怕活一天,就会有希望!
只要刘小富活着,黄腊梅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空空荡荡。
【作者简介】王祥夫,男,辽宁抚顺人,1958年生。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屠夫》、《乱世蝴蝶》、《种子》、《生活年代》、《百姓歌谣》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永不回归的姑母》、《西牛界旧事》、《谁再来撞我一下》、《城南诗篇》、《狂奔》等八部,散文集《杂七杂八》等四部。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等文字在国外出版。曾获首届、二届赵树理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现居山西大同,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