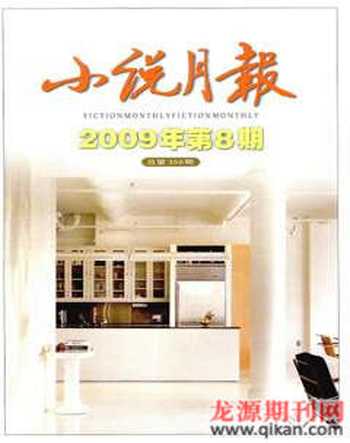轮盘赌
1
星期六晚间,我在单位办公室接到黄纵的电话,他打的是手机。
“在哪儿呢?”他问,“忙什么大事?”
我还能忙什么大事?在单位加班扶贫。他清楚的。
“领导怎么突然关心我了?”我问他,“有好事?”
“当然。”他说。
他向我打听单位里还有谁一块儿加班,我告诉他没有别个,就是本人庄昭平。他放心了,让我继续加班,少动点脑筋,多花些时间,不要急着完成任务关门走人。他准备马上赶过来,陪同我一起扶贫。
“你在家吗?”我问。
却不是。此刻他没在市区家中度周末,人还在县里。今天上午省里有一重要部门领导到他们县走访慰问,他留在那边,陪着跑了一天。晚饭后客人们返回,没他事了,可以回家了,这时忽然想起我,便打了这个电话。
“这些日子事多。”他说。
我问他是不是陪上级领导走访慰问上瘾了,手中的慰问金没花完,需要找个谁接着花,所以要到我这里继续走访。他即批评,说庄昭平你这家伙没治,想哪里去了?没事不能去看看你吗?非得先讨点回报,问个明白?
我不由笑,承认自己心里有些纳闷儿:“领导这么关心让人很不安。”
这当然就是说笑。
黄纵在下边县里当副县长,他那个县城离市区不远,就二十几公里,坐上轿车,算上出城进城时间,不必开快车,半个来小时就能过来。当领导的有车,跑这么点路不困难,问题是他对我不需要这么关心,我断定他找我一定有事,尽管他含糊其辞,语焉不详。会是什么事呢?来了自然知道。
半小时后他到了,根据时间推算,肯定是放下电话就抬腿走人。
那时我已经把自己的事情做完了,也就是做一个领导急要的信息专报,不是什么大事。任务完成后本可关门走人,为了接受黄副县长的意外走访慰问,我只能继续坚守于工作岗位。
当晚黄纵在我这里坐了一个半小时,如他自己调侃,亲切看望了周末加班工作的机关工作人员。一个半小时里他跟我东拉西扯,把我们所在的市政府办公大楼里的张三李四问了个遍,这个如何,那位怎么样,走访得十分广泛。我注意到他显得很轻松,谈兴很浓,话题东跳西跳,充分表明并无特别事项要跟我单独交流。但是有一个细节没逃过我的眼睛:他一直要喝茶。我们办公室有一套精致的紫砂茶具,我们用它给客人沏茶,茶具用的茶盅不算太小,足供客人品尝,于黄纵却不够。当晚我不断给他续茶水,几乎每续一次,他都会在一两分钟内把茶杯里的茶水喝光。
我对黄纵有一定了解,知道一旦该同志情不自禁不停地喝水,他心里一定有事。他一直不说,显然这件事不好开口。
我们俩在办公室里耗到近十二点,他终于站起身告辞。
“不早了,回家吧。”他说。
我感到非常意外。
我把他送到楼层电梯间,他提出让我一起走,用他的轿车送我回家。我告诉他我还得把办公室收拾一下,然后骑自行车回去,以便明天上班还有交通工具可用。他点点头,不加勉强,独自乘电梯下楼去了。
没有开口。
我回办公室关窗关电脑,把散乱于桌上的材料归拢。埋头打扫之际,没提防“啪啦”一响,有个东西突然落在我的桌面上。当时不免大惊,赶紧抬头,一见竟是黄纵,原来他没有走人,终究又回来了,当然不是为了喝茶。
“給,收着。”他说。
他往我办公桌上丢了一个信封,土黄色,不太大,有点鼓。信封上除了上下两处印有填写邮编的空格,没有任何其他文字,印刷的没有,手写的也没有。
“这是什么?”我非常吃惊。
他笑了笑:“慰问金。你要的。”
“别开玩笑!”
他把笑容一收,决定不开玩笑。
信封里装的是人民币,跟各位领导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时送上的人民币一样。这些人民币并不是要慰问庄昭平,是烦请转交给程家驹的。黄纵今天亲自陪同上级领导到处走访慰问,为什么不能顺便亲自上门慰问程家驹?因为有所不便。由于以往的一些原因,他请我替他做这件事,对我表现出极大的信任。
“想了很久,只好劳驾你。你比较合适。”他说。
我发觉这事怪怪的,有点蹊跷。
“这什么事啊?”我问。
他笑笑,让我不要多打听,帮忙转交就是了。
“怎么回事总得告诉我呀。”
他说:“以后我会告诉你。”
我注意到扔在办公桌上的信封已经封得严严实实,不撕开封口,无法知道里头的究竟。要我帮忙,又不让我帮得明白,这种拜托方式挺怪异。
“里边真是钱吗?”我问黄纵,“不会包了一卷卫生纸?”
他肯定那是钱,人民币,与扶贫慰问红包里的东西完全相同。
“有多少?”
他还是那句话,让我不要问了。如果我非要搞个明白不可,尽管把它打开。不过他还是劝我不必那么好奇,知道了不一定好。
“放心,没什么大事。”他说,“以后我告诉你。”
2
黄纵跟我谈论过国外的一种恐怖游戏,叫轮盘赌。该赌不赌筹码,赌的是性命,使用的赌具不是电影里大赌场那种大转盘,是一支左轮手枪。
左轮枪怎么做游戏呢?它有一个轮盘,起弹夹作用,轮盘上有装子弹的洞槽,装满子弹后,打一枪轮盘转一下,直到全盘子弹打光。玩轮盘赌时,左轮枪的轮盘里只装一颗子弹,其他弹槽洞轮空,赌命者轮流拿手枪对准自己脑袋开枪,一人只扣一次扳机,碰到轮空没装子弹的弹槽洞,他就活,谁碰上那颗子弹谁倒霉,一枪毙命。
“很恐怖很刺激。”他说。
我不解:“这有什么好玩?找死嘛。”
我俩真不在一个水准上。
当年我们常在一起聊天,讲过的事情有的早就忘记了,有的至今记忆犹新,例如轮盘赌。我们俩是老同事,当年我们就在眼下我这间办公室相识,此前我在市农业局,他在市经贸委,彼此并无关系,后来同时被抽到市扶贫办,一起共事,他的办公桌和我的办公桌背靠背,我们俩上班时面面相觑。当年同为年轻干事,普通公务员,两个白丁,属于需要提早上班,擦桌子洗茶杯打开水的小字辈,彼此相处不错,很有共同语言。那时黄纵在一群机关小字辈里已经显得出类拔萃,他很聪明,为人处事很周到,有气魄,见多识广,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像轮盘赌。他还是那种心里特别有数的人,我们成为同事之初,他就告诉我,扶贫办干一段时间可以,久待不行,找到机会要赶紧走。
我说:“在哪儿都得干活儿呀。”
他摇头:“那不一样。”
他认为人经常需要做出选择,得知道自己要什么,什么对自己有利,什么不利。
我跟黄纵共事了近两年时间,黄纵做什么都心里有数,知道权衡利弊,知道抓住机会,机会当然总是与他这种人同在。扶贫办属临时机构,与市领导的联系却比较直接,黄纵在此间努力表现,很快就让领导注意到了。有一位副市长对他挺中意,把他调去当秘书,让他走上了一条快车道。几年后他又碰上时机,给派到县里任职,当副县长,成了领导。而我则一直没有挪窝儿,始终还在这间办公室这张办公桌边扶贫,屡屡让他批评,让我多努力。他曾经为我找过我们单位的头头儿,说庄昭平是正经人,不能亏待人家,得给个位子,不久后我被领导委为科长。这事让我挺感激。
他不在意:“别客气。彼此老交情,以后说不定也要请你帮助。”
黄纵虽然一路顺风,跟我却始终保持联系。这人会做人,并不一阔变脸,当了领导,到政府大楼开会办事时,有空还愿意到老地方转转,见了旧日同事还知道握手寒暄,问东问西,笑模笑样,让人感觉不错。几年里我曾找他办过些事,他也因为若干事情找过我,机关工作人员与基层领导干部,地位不同,各自都有些对方不具备的资源和便利,可以互相关心帮忙。但是认真回顾总结,盘点一下,几年里大家彼此相烦的都是些小事情,状况都比较自然,绝对正常,不像今天这般蹊跷:厚厚一个封了口的信封,嘴巴也封了,语焉不详,云山雾罩。
细究起来,黄纵如此古怪地让我处理这件事情,当然有其理由,除了因为两人是老同事,还因为事情牵扯到程家驹,跟我有关系。
程家驹是我老婆的远房亲戚,年纪比我老婆小,辈分似乎还比她高,仔细画一张关系线路表,可能推算成我老婆的表舅什么的。我在私下里跟老婆管这个人叫“程家狗”,自嘲因为本人文化程度不够,一不留神把“驹”和“狗”两字搞混,忘记它们偏旁不同,一个属狗,一个属马。其实我是故意那么叫,因为该小子给我印象特别不好。这人长得歪瓜裂枣,从小惹是生非,成人后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不务正业,东遛西逛,喝酒赌博,不时招惹麻烦。
几年前,有一天程家驹到市里,找上我家,我见了他大吃一惊,因为他穿上西装,打了领带,进门还会脱下皮鞋,几乎让我认不出来,变得有些人模狗样。
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原来人家已经成了某工程公司的经理。
“其实就是个包工头。”他自己承认,倒也干脆。
当时我们已经有几年不见,程家驹找上门来,却不是要来展示自己浪子回头,人生巨变,弃狗返马,也不是因为忽然想起我老婆是他的表外甥女,想来续续家谱,叙叙亲情。他有事情求我帮忙,并非什么天大的事情,就是让我把他介绍给黄纵。他听说我跟黄纵曾为同事,彼此挺熟,他正好用得上。
我老婆的老根在乡下,到我岳父那一辈才离乡进城,到市区生活工作。程家驹则一直是乡下人,从早年斗鸡走狗,到眼下当包工头,活动区域始终在他们老家一带。那一块区域属黄纵那个县,黄副县长管得着。
我对程家驹有些提防,没打算跟他牵扯太多。我告诉他我与黄纵虽是老同事,人家现在是领导,我已经不太够得着,恐怕没用,帮不上什么忙。程家驹却咬着我不松口,还像当年那种狗样子。他堅持让我给黄纵打个电话,说不管有没有用,还请帮助说一声,都是亲戚,这点小忙不帮一帮,实在说不过去。
“你什么事找这个黄县长?”我问他。
他声称眼下没什么事,就是想认识一下,多一条路。黄纵在县里管建筑,权力很大,大家都千方百计跟他搞关系。搞熟了,今后用得着。
老婆说:“庄昭平你就给打个电话吧。”
关键时刻,老婆的胳膊肘还得受血缘牵制,尽管这个程家驹的DNA跟她隔得够远了,早就八竿子打不着。迫于老婆的压力,我给黄纵打了电话。
“是你亲戚啊?”黄纵答得很爽快,“行,让他找我。”
事情到此为止,剩下的归他们俩自己,与我再无牵扯。
后来程家驹很稀罕地又到我家访问一次,这一次不仅穿西装,还开来了一辆车。小子混得不错,在当地包了几个工程,赚了点钱。他给他表外甥女即我老婆送了一份礼物,就是一袋茶叶,包装一般,看上去并不贵重,也就是比扶贫的档次稍微高一点儿吧。小子在我家坐了会儿,发了句感慨,让我老婆鼓捣我想办法,不要死待在一个地方加班加点干活儿,应当想办法到下边当个头儿,掌点权管点事,那就不一样了,一两袋茶叶算个啥?几万十几万拿也是行情。
“像人家黄县长,”他说,“多少人求他。”
“都拿钱给他吗?”我追问。
他笑笑,称那种事只好去问老天爷,恐怕老天爷也未必都清楚。
“你自己呢?给没给?”
他起身告辞,开玩笑说不能再坐了,表外甥女的老公不像搞扶贫,倒像审案子。
当时我是没事找事,私下办案,未有结果,不了了之。哪会想到眼下案子忽然自己找上门来。黄纵跑到办公室陪我加班扶贫,嘴上没事,手上忽然扔下一个信封,内装人民币,数目不详,让我转交给程家驹。别说我这种自觉加班多年的机关干部,街上踩三轮开出租的听了这事也都能猜出个大概。包工头程家驹不是黄纵副县长发放慰问金的合适对象,黄纵让我转交的人民币只可能是程家驹给他的礼金,或许还是贿金,他要通过我把这笔钱退还。黄纵找我代理,却不把事情说白,显然其中有些不便。这种不明不白的事情我当然可以拒绝,但是毕竟与黄纵关系一向不错,加上程家驹为我老婆这边的亲戚,是我打电话让他攀上黄纵的,所以此刻我不好拒绝相帮。把这个事情搞明白并不太困难,旁人不清楚,两位当事者自己心知肚明,黄纵不提起,找程家驹问问也就清楚了。
我感觉需要问个明白。
3
这事居然挺复杂。
我给程家驹打了电话,意外发现这个人消失了。手机关机,家里电话停机,人不知去向,马跑了,狗也不见了。
我非常吃惊,决定把老婆推出来参与办案。当年要不是她胳膊肘出了点问题,过分受到DNA影响,替程家驹说话,给我施加压力,今天这起案子也不会自动找上门来。所以她没有表示不满,愿意积极配合,将功补过。我把黄纵丢给我的信封丢给她,她收起来放进自己的小包里,依计行事。
“这好像也不是太多嘛。”她对信封表示了看法。
我老婆跟我一样,对黄纵的信封有些好奇,她很想把它打开看个究竟,末了听从我的劝告,没有撕开封口。但是她还是克制不了好奇,不能用直接方式,她就采用间接方式侦查那个信封。做这种事不需要太聪明,也不需要动用核磁共振X光机之类高科技侦查设备,老婆有一只弹簧秤,她用它称出黄纵那个信封的重量,然后找来另一个信封,装入我们家自有的人民币,假设黄纵信封里全部都是百元大钞,她在自己的信封里也一概采用百元面额人民币,不让小面额进入。经仔细验证,黄纵信封的重量大体相当于百张百元面额人民币之重。这就是说,里边大约有一万元。
相对一位副县长身份,这笔钱时下确实不算大。也许就因为不够大,所以可以请我代为转交。一旦数额足够大,恐怕再怎么也不好让旁人插手。
由于电话找不到人,也不好四处打听随便张扬,我让老婆赶紧回乡走一回亲戚,设法把钱送到,同时就近了解一下情况。老婆的外婆还在世,已经九十高龄,一直住在乡下老家,老婆回去看看老人,不仅是办案需要,也属人之常情。
结果她白跑了一趟。老人当然是探望了,案子却没办成。程家驹没见到,老婆回乡之前,我们曾共同分析案情,推测各种可能,探讨应对策略,我们也曾估计该小子关手机停电话,一时可能找不到,我建议老婆找他的家人,把信封脱手,这也算数,不一定非要慰问程家驹本人。但是老婆没有办到,因为程家驹已经没有家人。他在一年前与元配离了婚,他们的儿子归前妻,目前住在乡下。程家驹自己在县城既包工程,也包小姐,他在那边有一套房产,金屋藏娇养了个年轻女人,此刻他消失了,小姐也不见了。
程家驹除了前妻、儿子和小姐,毕竟还有其他近亲,血缘和DNA跟他更接近,我老婆却不敢把信封丢给他们转交,如黄纵把它丢给我一样。为什么呢?她听到了一些消息,觉得不能轻易行事,只怕有麻烦。
原来程家驹可能是犯事了。最近一段时间,他们那个县出了一起经济大案,涉及到官商勾结、工程舞弊、权钱交易等等,听起来相当厉害。目前已经有几个包工头被拘,牵连到十几个官员,几个政府部门要员涉案,案情还在发展。
我听了大惊:“涉及到黄纵吗?”
老婆不清楚。她的消息是从一个堂姐那里得到的,她堂姐在该县教育局工作。据堂姐介绍,那里发生的是流感型案子,以交叉感染的方式迅速扩散发作。案子起于县一中几个头头儿私分一笔教辅材料回扣款,有关部门接到举报,着手调查,学校分管基建的一位副校长入案慌张,说出一大堆其他事项,包括其收受某工程队一笔贿款。工程队老板被查后也交代出其他事项,涉及到县里几大部门要员,于是查了两个局长,这两个局长分别又交代出与之进行过权钱交易的若干包工头,这些包工头被办案部门叫去追查,又牵扯出其他官员和线索。官员和包工头两种人物交叉感染,案情呈现燃烧之态,在十数位局一级官员涉案之后,火势向上蔓延,似乎马上就要烧到县一级领导那里。眼下该县被该案搞得人心慌乱,有事的官员心怀鬼胎,一边忐忑一边还得坚守工作岗位。有事的包工头则表现得活络一些,一看风声不对,拔腿走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一躲再说,程家驹是其中之一。
我老婆只觉头大了。程家驹要是没事,他跑什么跑?这么一跑当然格外引人注目。这种情况下哪里好去寻访慰问程家驹?要让办案部门听说有人专程前来找程家驹还钱,他们能放过不查吗?无异于引火烧身。所以信封没有出手,经过一番旅游,它装在老婆的包里又回到了我的身旁。
这时候我有些明白了。黄纵托我办这件事,除了因为程家驹跟我有关,也因为黄领导可能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如果可以自己悄悄退掉这笔钱,他肯定要亲自去办,不会劳驾他人,哪怕那个人可靠得有如亲爹老子。显然他无计可施,这笔慰问金需要尽快退掉,包工头程家驹却又跑得不知去向,于是不得不想起我这个老同事。
我发觉黄纵这个信封挺烫手。如果是在平常时候,出于与当事者双方的瓜葛,我来帮黄副县长转交一笔慰问金也无不可。眼下却不一样,那边有案子在酝酿发作,这钱可能有涉,介入其间可能让我在一起流行性感冒窝案中脱颖而出,成为其中一个人物。本来我并无资格,哪怕有心要挤进去凑个热闹,也还条件不够,对不起观众。现在不一样了,我举着一个信封,夹在黄副县长和程包工头之间,他们俩一旦涉案,我将与他们相伴,没有条件成为共犯,起码有些像志愿者。即使不被怀疑参与作案,不被追究是否从中谋得什么私利,对我肯定不是好事。
我对老婆说:“看起来不对。”
我给黄纵打了电话。
“没找到人。”我告诉他,“黄领导这事我恐怕办不了。”
他竟问:“什么事呢?”
我没含糊:“程家驹的慰问金呀。”
他认真了:“我在开会。晚一点儿我给你回电话。”
当天上午他没有回,下午也没有,直到半夜。
我感觉紧张,不知道黄纵是不是突然出事了,或者他事情大了,竟然不再坚守领导岗位,已经学习程家驹等包工头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很巧,晚间十点,本市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一条消息,黄纵出现在新闻里。有一位市领导到黄纵那个县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县若干官员陪同参观考察,其中有黄纵,他有一个特写镜头,在镜头里站在市领导身边指指点点,形象很突出。
我注意了新闻发生的时间,是本日。这就是说,黄副县长没事,今天好着呢。黄纵在县里管经济,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似乎不归他,怎么他在该新闻里也能露脸?估计该同志是主动参与。这种现象经常可以看见,当外界盛传某官员出事而该官员其实暂未出事之际,只要有可能,这位当事者通常会找一切机会出头露面,努力做重要讲话,到处走访慰问,千方百计曝光以正视听,黄纵看来也一样,不能免俗。
但是他没给我打电话,他不会没有机会,却置之不理。
我再次打手机找他,对方拒绝接听。
我觉得不行,不能这样玩。
4
我说:“没关系,我等会儿。”
他们给了我一杯茶。
我带单位里一位年轻干事下乡调研,到黄副县长的地盘走访,实地了解该县几个扶贫重点村近期情况。按早先计划,本次调研重点在另一个县,我提出若干理由,把这边也纳进来,一并开展。这使我可以顺便回访慰问黄副县长。
我把他给我的信封放在包里,拟完璧归赵。这件事我帮不上忙,只怕耽搁了不好,还是请黄领导自行处置为宜。我知道他不会因此感到愉快,但是只能这样。
我打听了情况,知道那天上午他在办公室,没有外出,于是我找上门去。我没提早给他打电话,以防止他突然有事消失了。不料谨慎至此,上门还是扑了个空:人家领导果真临时有事,集中在会议室开会,让我在外头干瞪眼。
我对政府办值班人员说:“能帮我给黄副县长说一声吗?”
该值班员不错,借进门给领导送茶水之机,帮助我告知了。黄纵让他带话出来,表示对不起,会议很重要,不能离席出来看我,有事回头再联系。
我决定留下来等。所谓回头再联系可能靠不住,我已经有体会了。任何会议无论多么重要,总有完的时候,与会人员无论多么投入,时候到了总要吃喝拉撒,所以不妨守株待兔。这个县的政府办值班室设于会议室前厅,出入会议室必经值班室,把住这个关口就行了,除非兔子变成苍蝇,否则溜不过去。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如愿以偿,与黄纵欣然相逢。
他表情正常,没有表现出惊讶。
“好哇,欢迎。”他跟我握手,“到我办公室喝茶。”
一直到走进他的办公室,我还没想清楚该怎么开口。因为条件所限,我还缺乏收受或者退还各种慰问金的经验,所以总在斟酌怎么说比较合适。不想人家很干脆,门一关不再兜圈子,既不解释为什么不回电话不接电话,也不明知故问打听我为什么在政府会议室外守株待兔。
“东西带来了?”他直截了当问。
我点头。
“给我吧。”
我从包里取出那个信封奉还,他把信封扔在自己办公桌上。
“松口气了?”他看着我笑。
我也笑,点点头。
他表示理解。他相信我一定尽力了,但是无能为力,所以回头找他。事实上那天晚间他跑到办公室请我帮忙时,心里挺矛盾,也很犹豫。彼此老同事老交情,实在很不愿意把我拖进这种事里,如果有其他办法,他不会那么干。之后他心里还挺后悔。
他说得我都内疚了,比较起来,倒像我很不够意思。
“你一定听到一些消息?”他问我。
我告诉他是听到了一些传闻。我没跟他具体讲到什么,也不打听他本人是不是有麻烦,因为这种事不好多问。如果他别无问题,只牵扯程家驹这笔慰问金,事情也许不会太大,如果这笔人民币只是他需要摆平的多项钱款之一,麻烦当然不会小。以我推测,他可能是后一种,所以我不想多问。
没想到他主动跟我谈了些情况。
“传闻有真有假,今天是真的。”他说。
原来今天上午他们开的会比较特别。这是个打招呼会,市纪委领导专程前来,召集几套班子成员开会,其实不是一般的讲情况打招呼,已经是敲山震虎,直接敦促了。领导前来开会为的是该县正在查处的案件,会上提到,经办案人员认真努力,该县这个案子已经取得重大突破,发现掌握了一批重要线索。从现有情况看,案子涉及面很宽,问题很严重,上级极为重视,决心一查到底。为了体现政策,特地召集大家开会打招呼。与会各位领导中已经有人涉嫌,上级决定给三天时间,有问题者三天之内向有关部门交代并采取实际行动,今后可按主动坦白从轻论处,拒不交代者将从重处罚。
“口氣很重。”黄纵告诉我,“要下手了。”
“那——那,怎么办?”
我要问的是“你怎么办”,黄副县长是不是准备马上去坦白并采取实际行动,例如把程家驹的这笔慰问金拿去上交?话到嘴边,我又情不自禁地把“你”字删去,以免太刺激对方。但是这一来倒像是我俩在共谋对策了。
“不说不是办法,”他说,“这个大家清楚。”
他跟我分析,谈的却不是自己怎么样,他假设了一个对象,叫做“这个人”。他说今天领导打招呼讲到这种程度,不可能纯为吓唬,他们手中一定有些东西,已经有人进入他们的视线。这个人不管是谁,此刻不坦白不是办法。为什么?如果说了,可能念这个人主动坦白,到此为止,不再往深里挖,到头来给个处分,严重的话降个职,其他还能保住。这个人如果不说,人家已经掌握线索了,当然要查。待到把他弄进去,不说行吗?有的人以为可以咬住不讲,死不认账,人家没办法。其实不行,没有谁抵挡得住,最后总是要开口的。一旦开口,很少有人能够打住,总是交代了这个交代那个,加在一起,数额之大,能把这个人自己吓死。
“这才悔不当初。”他说。
我表示赞同,看来争取主动为好。
他笑,问我打算如何争取主动。这个人如果拿人钱了,不太可能很挑剔只拿一笔。一旦风吹草动,他一定千方百计试图补救,能退的退,能遮的遮,但是总会有些退不了遮不住的。事到临头,不知道哪一笔被人家掌握了线索,他怎么去说?如果一笔一笔都努力讲到,加起来数额大了,跟弄进去的结果也差不多。
“所以没治。”他说。
“这就完了?”
他问我,记得轮盘赌吗?我说记得,是一种拿手枪对准自己脑袋的玩法。
他再阐述,说轮盘赌的左轮手枪里有一颗子弹,扳机一扣,可能枪响,也可能轮空。眼下这个人好比进了轮盘赌局,拿起了那支左轮枪。
他在谈论“这个人”时很超脱很放松,可能因为设定为他人。但是我注意到他情不自禁又在不停地喝水。
他感叹说,其实不必扣扳机,这个人的脑子里已经全是枪声了。枪声真的一响,对他可能是一种解脱。
“不必再接着玩了。”他说。
5
几天后该县一位重要官员被办案人员带走。却不是黄纵,是他们县长。
听到消息后我忍不住想给黄纵打个电话,几经踌躇,这电话没打。
我不知道黄领导感觉如何。很遗憾没有解脱?脑子里的枪声停了没有?还打算接着玩吗?
原刊责编 王 霆
【作者简介】杨少衡,男,祖籍河南省林州,1953年生于福建省漳州,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1969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7年起,分别在乡镇、县和设区市机关部门工作。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发表小说二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危险的旅途》,中短篇小说集《彗星岱尔曼》、《西风独步》、《红布狮子》、《秘书长》、《林老板的枪》等。中篇小说《尼古丁》获本刊第十二届百花奖。现在福建省作协任职,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