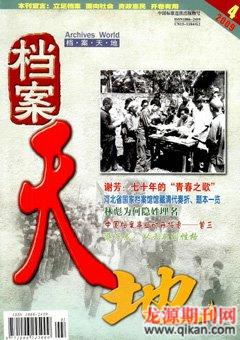七十年的“青春之歌”
谢 芳

编者按:
谢芳,原名谢怀复,1935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后迁居上海。1951年毕业于汉口罗以女子中学,考入中南文工团,任歌剧演员。195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青春之歌》,谢芳被著名导演崔嵬选中,扮演林道静而一举成名,轰动了中外观众,从此步入影坛。1962年由文化部推选为新中国22位电影明星之一,1989年被中国电影周报评为建国四十周年十大影星之一,1995年获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2005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
颠沛流离中的童年
我是1935年出生的,1935年可了不得啊,伟大的爱国主义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就是在这一年发生的。那时候我才一个多月,一个多月的小女孩,躺在床上瞪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咿咿哑哑,动手动脚的,她能想得到她长到23周岁的时候去演一部表现这一伟大运动的电影《青春之歌》吗?1935年,我家住在湖北省黄陂县滠口乡的彭家湾,那时候天灾人祸不断,妈妈说:有一次乡亲们遭饥荒,难民中有兄弟二人被分到两家去吃饭,我母亲为那位哥哥做的饭吃的好好的,可那个弟弟在另一家吃饭却被撑死了,真可怜。
我妈妈怀着我的时候,还遭过一次土匪的干扰,我爸爸的同事王敬轩教授还被土匪砍掉了一根手指,就在那天,我妈妈怀着我就往山里跑,吓得哆哆嗦嗦的,两只手控制不住直捶自己的肚子。据我妈妈讲,就是因为这次跑土匪,我提前上班了。那时候,因为进城不方便,同事的太太们便都相互帮忙接生,替我接生的是一位胖胖的师母,性情开朗随和,所以我长大了也是马马虎虎的。
我出生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为收复国土,取名谢怀复,数月后,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再数月后又辗转上海,当时因为我的大哥和大姐、二姐均在湖南上学,父亲又去了外地出差,我妈妈只好独自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奔赴上海,当时人荒马乱的,去上海的轮船码头上水泄不通,我妈妈找来一个箩筐,先把10岁的小哥和2岁的我放进筐内,用绳子坠了下去,然后再拿着行李抱着只有几个月的小妹妹进船舱,到达上海后,我母亲最高兴的是见到了父亲,半个家团圆了,就这样,我们在上海住了9年。
我们家住在上海市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51号的二层楼上,一层楼住的是一位日本的牙科医生,三层楼住的是一家绸缎铺的老板。我从小病多命大,我和比我小一岁的妹妹一块儿出麻疹,我的脸发红,大夫说是发出来了,我妹妹脸却发白,大夫说是憋在里头了,我妹妹太小了,没有扛得过那场疾病的磨练,不幸窒息而亡。我还有个妹妹,她很小便离开了我们,我对她没有什么印象,然而此时,我却忽然很想知道,她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她比我更像妈妈一点,那就也是一张瓜子脸,杏仁眼,肯定比我会念书。
我3岁时得了伤寒症,住在上海法国医院里,他们是不让家属陪住的,所以每次母亲去看我的时候,我都会突然地号啕大哭起来。因为一个3岁的孩子怎么能读懂这个世界上还有社会,还有社会的种种规矩。伤寒是很危险的疾病,我却被外国人治好了,如今背上还留有他们治疗的痕迹。我8岁时又得过一次肺炎,后转为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炎”管了我一辈子:你只要用嗓子唱歌演戏,它就要来捣乱,好在我的肺部却永远“未见异常”。我5岁的时候,还被父亲抱到圣诞节的晚会上唱过一首英语歌曲,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登上舞台。不过以上所写的这些都不在我的记忆之中,我都是听我妈妈讲的。
我的记忆开始得很晚,那是在我亲爱的小哥哥谢怀民离开我们的时候。我看见小哥的脸很白,头发很长,都竖了起来。小哥是个乖孩子,临死时,他对妈妈检讨说他不该对妹妹发脾气,他还自己朝着基督耶稣的画像说:“主啊!成全你的旨意吧!”
我的小哥太痛苦了,也太聪慧了,一个18岁的孩子便懂得在最后的时光寻求精神的解脱。我的小哥长得更像我的母亲,也是瓜子脸,杏仁眼,在校各门功课都好,他的大哥哥姐姐们都在外地上学,他就成了家中主要的劳动力,每次去影院看电影,都是他背着我。这么漂亮懂事已经长到18岁的儿子突然离世,这是做母亲的难以忍受的,在这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只要一提起他就哭,这是我童年时主要的记忆。
我3岁时和我的小哥谢怀民照过唯一一张照片,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为了正义与和平晚会的序幕中,当戴玉强先生唱起《松花江上》,当我百感交集,愤然举起这张画像时,很多人都哭了。小哥去世后,因为大哥和大姐、二姐都在外地上学,家中除了父母之外,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到了我的学龄时期,在上海那样繁华的都市里,没有专人送小女孩子上学,家人是不放心的,而我们家又请不起保姆,所以我爸爸只好把小学的课本买回家,由我母亲教授,我是属猪的,我爸说:“你就在家当猪养着吧。”
因为我不用去上学,我的自由时间自然会多一些,我们家有一架脚踩的风琴,我妈妈是基督教会的风琴手,我可以从她那儿学弹琴、学习简谱、五线谱,寒暑假,哥哥姐姐放学回家时,我还能从他们那儿学到歌曲,我大哥教我英文歌《昨夜》,二姐教我《梅娘曲》,我还看过不少的中外名著,好像八、九岁的时候就看到《飘》,看过《基督山恩仇录》、《悲惨世界》、《红楼梦》、《雨》、《家》、《春》、《秋》等。

每天早晨我常背着小书包和小朋友们一起去上学,等走到叉路口后又灰溜溜的回到家中,在弄堂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过家家时,我最喜欢当老师,假装在上课,我会把解放前那种黄颜色的草纸撕成一块一块儿的发给大家当作业本,演起来特别自信、自然,没有想什么,这不就是戏剧的初胚吗?后来当我住在九龙道风山上时,我还学会了游泳,这些技能都用在了我日后的艺术生涯之中。
1946年,我随父亲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湖北滠口,由于母亲生下我不到半年就离开了这个地方,自然一切是陌生的,也是新鲜的,这里是农村,小集镇的纯朴情绪、大自然的优美风光常常让我流连于山峦之中,湖泊之滨,在我的作业本上,又增添了几篇打了好分数的文章,但这却不是母亲给的了,这时我已经进了一所由教会办的学校。从小过惯了孤单生活的我,视野开始扩展了,我和女友们穿着一样的蓝布褂、黑裙子、白袜、布鞋,去参加学校举办的郊游和运动会。
夏日里,大场上那种独有的甘草香味和由于穿得整齐而显得格外炎热的感觉,至今仍十分清晰的留在我的记忆中,可是那些在小学毕业时,我为取得全班第二名而曾经做过的种种努力、种种温课备考的情景我却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我来说,凡是感性的属于形象思维的东西,我趋之若鹜;而对于一些理性属于逻辑思维的东西,却大有高不可攀之感,这大约是我日后走上表演艺术大路的主要原因。然而在那时,对于未来职业的选择,我并不一定了解,在初中毕业作文《我的理想》中,我的志愿是学医当大夫,立志免费为穷人治病,虽然这只是处于一时的热情,一种连自己都感觉十分渺茫的幻想,然而一种同情贫民、蔑视权贵的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意识却已在我的脑海里产生了。
1948年初,解放战争的炮声还在远方隆隆作响,每天晚间,父亲和他的几位好友都要议论形势,政治这个往往在两种团体、两股力量进行激烈较量时显得尤为活跃的东西,条条的渗透到我的头脑之中,并且还显得十分强烈、新鲜。从他们的议论中,我得到这样一个为12岁的孩子所能够接受和理解的真理,父亲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在交谈这些问题时,他往往非常激动,或大声争辩,或为自己的论点取得胜利而纵声大笑。即便如此,当父亲所执教的这所神学院决定搬迁到九龙道风山时,父亲仍然跟着去了。
解放前夕,在九龙、沙田、道风山的半山腰间,我们住在一所名叫“禅悦林”的寺院里,院内有个名叫“细姑”的出家人,每天早晚香烟缭绕,木鱼声声,住房旁是由一股山泉续成的游泳池,街下有两个对称而立的小亭子,这个小亭子也就成了我每日自修功课的地方,除了自修功课以外,我还去姓王的教授家中练习钢琴,加上睡觉前的例行渠道,这三件事成了我每天必须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每天去做一些实际上并不能引起多大兴趣的事,而且要天天如此,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总是强迫自己去做,并且把它作为一种锻炼和验证自己红心和毅力的标志。

就这样,在“禅月林”那幽静的寺院里,我又度过了虽然比起学校生活要来得轻松自由,却又不断地与自己的情绪进行斗争的一年。在这期间,我曾在九龙的志贤中学上过半年学,志贤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坐落在九龙的一条街面上,院内秀美整洁,报考时感觉英文程度比国内要深,大概是其他功课考得尚好,我仍被录取了。我每天从风山上走到沙田镇,然后乘一刻钟火车到九龙去上学,我喜欢站在车厢的连接处,以显乘车之熟练与不在乎,我们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父亲的薪俸,虽然能维持温饱,但远远算不上富裕。我平日穿的衣服常常是母亲亲自设计缝制的,服装淡雅略带土气,每日上学的午餐是到临近学校的一个食品店里买一圆面包加一小条黄油,夏天黄油成块状,和着面包咽下去的那种滋味并不十分好受,虽然吃腻了,但饭钱只有这么多,小孩子又不知调配花样,也无可奈何。
最令人难忘的是足下的那双球鞋,为了多穿几年,母亲给我买了一双至少大出两、三号的高腰蓝球鞋,因为脚小且瘦,鞋前面的空余部分自然向一边弯了过去,这一形象在香港九龙穿着入时的中学生中间所产生的自惭形秽之感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却依然乐观,很少计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父亲把我从沙田送过深圳罗湖桥,到广州的宝安县里中学去念初二下学期,在回来的路上遇上飞机轰炸,我和父亲躲在一个只能容一个人的洞里,为了让父亲的头能进到洞里,我把自己的头伸出洞外,炸弹在离我们数十米远的地方炸开。宝安县里的记忆是和水桶、冲凉、奖状等事物连在一起的,因为进校时正值夏天,妈妈给我买了一只铁桶,十分结实耐用,中学校长是一位60来岁的长者,初次见面,父亲让校长用英语跟我对话,记得简单的词汇还对付得过去,陌生处免不了要连蒙带唬,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外住,有些寂寞。
记得宝安县附近的那不算大也不算整洁的街道和商店,也记得那炎热的中午,乘凉的夜晚,记得在过堂里参加比赛的情景,每次放假回家路过罗湖桥时都要检查行李。有一次,当警察打开我的箱子时,首先露出来的是讲演比赛的奖状,此事成为母亲日后非常喜欢提起的话题。
与文艺结缘
1950年夏天,我重新回到了湖北,1951年的夏天,我在汉口罗以中学念完了初中三年级,因为临近毕业,顾不得搞更多的文艺活动,我们只演出过一个独幕剧叫《爱什么》,一个叫王佩珍的同学女扮男装,而我则扮演剧中的女主人公,同学们用生火用的炉钩子帮我烫了头发,又抹上口红,画上蓝眼窝,穿上从同学的妈妈那里借来的旗袍,拎着手提包坐在沙发上,表演时,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在另一次全校举行的联欢会上,我还独唱过《黄水谣》,但那时,不够轻松自如。这时的我对于文艺只不过是尚有兴趣而已,至于将来做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甚至不知道还有专门从事文艺的学校和团体,但是无巧不成书,当时我们家住在汉口胜利街52号的楼上,而刚刚南下不久的中南文工部音乐部的一些人正好住在楼的下面,他们经常在那里排练节目,大概是因为我每日上下楼路过那里,无人时也哼上两句歌曲的缘故,引起了文工团领导的注意,那时中南文工团的团长骆文、程云、莎莱,戏曲部主任汪洗,音乐部主任姚汉光、杜平等同志正值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时候,为了党的文艺事业,他们极其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择,他们委托汪洗同志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文工团,我因惧怕数理化,本来就不想继续上高中,便答应可以试一试,因为考的是音乐部,负责考试是杜平同志,只是测验了一下我的识谱能力,和用钢琴弹了几首曲子,就这样,我被录取了,开始了曾经令多少人为之倾倒的并感到深奥莫测的艺术生涯。
我是1951年7月1日正式参加中南文工团的,当时还是供给制,进团后每人发一套列宁式的灰布制服,每月生活费是四万元,有的同志还发有卫生费,伙食由公家供给。吃饭时,八个人围着一大碗菜,还得站着吃。而我由于从小在家孤单惯了,不好意思,常常面壁而食。我们一起考进去的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15周岁;一个是13岁的男孩子,名叫何大滨,后来是武汉歌舞剧院舞蹈演员;另一个是11岁的女孩子,名字记不清了。刚去无事,我们几个便天天坐在一起读报,学习文化。不久,文工团新址建成,我们便搬到渣甸路一号住下。文工团的房子建造得很不错,院内有灯光球场、小剧场、俱乐部、排演厅、食堂以及单人、集体宿舍。我参加的第一次公开演出是在苏联话剧《曙光照耀莫斯科》里扮演一个只有很少几句台词的女工。既然是演外国人,就得用石油灰把鼻子垫起。到了夏天,剧场里热到三十多度,鼻子尖上的汗水被捂在石油灰里像许多条小虫在那里爬,弄得怪痒痒的。我们不得不把石油灰捅个小洞,让里面的汗水流出来,好叫鼻子透透气。除了跑群众之外,我还被分配管理服装。有一次,我把电熨斗放在袜子上走开后忘记了,等我想起来时,袜子已被烧了个大窟窿。为此,我主动写了检讨书,对自己的失职行为和“剥削阶级思想”进行了狠狠的批判。
当时,全国人民还都沉浸在获得解放的狂热之中。党、政、军各级干部和战士面对着来之不易的胜利,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文工团的生活充满了朝气,同志之间、官兵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充满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感。文工团经常举行球赛和周末晚会,届时,俱乐部或球场的四周挂起彩色灯泡,乐声悠扬,笑声不断,院子里一派欢腾喜悦的景象。1952年冬天,我刚满16岁,文工团去湖南道县参加“土改”。副团长汪洗同志和我在一个队里,他熟悉戏曲,是文工团的导演,他是一个做事一板一眼、有条不紊的人。临出发前,他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提出各种要求,如:某火车站须在一分钟内上车完毕,等等。他还给我们画了如何打背包的图样,连鞋子和茶缸子应放在背包的什么部位都画上了。年轻人是无忧无虑的,我们没有卧铺,便用报纸垫在地板上,钻到火车的座位底下睡觉。每逢火车停站时,便下车去买各地特产来吃。
日常的开会、填表、斗地主、分发浮财等事,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记忆了,可有些事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过去生孩子多的家庭给孩子们取名,为了图省事也为了便于排辈,常常用一个字作为名字的开头,然后依次排列下去,如:建军、建华、建民等等。由于我的大哥出世时,祖父已经故去,为了纪念老人,父母亲为他取名谢怀祖。因此,后来我的哥哥、姐姐以及叔伯姊妹们均以“怀”字打头。而等到我出生的时候,由于爆发了抗日战争,为寄托兴复国土之心,母亲为我起名谢怀复。为了这个名字,还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故事呢。
那是文工团搬进新居的第一天,集体宿舍是四人一间,女同志在楼上,男同志在楼下,每间房的房门上均已贴好了名字。当时我抱着行李兴高采烈地上了楼,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经过仔细探寻,终于在楼下找到了,原来分房子的同志把我当成是男同志了。由于当时参加革命者多取单名,在“土改”中,汪洗同志便建议我改个名字。我记得他在三张小纸条上各写一字:一是“军”,一是“方”,再是“筠”字,并说明以抓阄定夺,随即我就抓了个“方”字。谢方自然比谢怀复叫起来顺口响亮,因此当土改结束回到武汉后,在团里便很快传开了。
到了1955年,为电影《青春之歌》撰写演员表时,负责字幕工作的执笔者认为既是女性,方字必然要有草字头,于是“谢方”就变成了“谢芳”了。至今,武汉老同事中男性者仍有写谢方的,这个谢方不过是一个历史误会的产物而已,可见世上偶然之事也多有既成事实的,不过在方字上加个草字头也有避免重名的产物,因为谢和方二字本身是相矛盾,方是可以和很多姓连在一起的,唯独和谢在一起则不好,因若将其用在形容词,则有花落去之意,倘若做动词,岂不是有摧残繁华之嫌呢,所以想必世上很少有人叫这个名字。到目前为止,除了古时有个叫谢方的以外,尚没有听到重名者,这又是题外之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