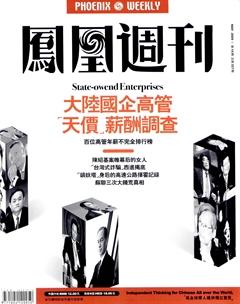“本”“外”一家人
编考按:台湾月前的一场风波。将“郭冠英”这个名字推至各大报纸的头版大标题位置。由于一位笔名为“范兰钦”者在各媒体及网络上发表多篇被岛内独派认定为“辱台”的文章。民进党人在网络上发动人肉搜寻,将目标锁定为台湾前“新闻局”驻加拿大多伦多新闻秘书郭冠英。郭氏遂被“新闻局”由海外遣回。接受调查。最终承认自己就是“范兰钦”,并被撤职查办。
这段风波一时引发岛内外各方对于言论自由与族群纷争的不同意见。反对者。若台当局“监察委员”钱林慧君。直至4月20日仍不依不饶,认为虽郭遭记两大过并免职。但她还是不排除提案弹劾郭冠英;而同情者。则认为郭氏已成悲剧人物,因为“令人惊讶者,郭冠英在李陈时代对台独口诛笔伐。尚且相安无事,反而是在马英九执政时期中箭落马”。
面对人生最大低谷的郭冠英,近日投书本刊,坦陈自己由加拿大返台后风波过身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前半生和形形色色的“本省人”与“外省人”纷纷纭纭的结缘。
他于信中强调:“我不是要讨好本省人。我的事为言论自由。毫无错。”——其实。正如他文中所述,“外省人”、“本省人”从来不是任何一个台湾入生命中抽象的族群概念。更不是若非朋友便是敌人的政治道具。
我从加拿大被紧急召回台北,飞抵台湾上空时,一片白云,只有中央山脉突起在云端。我看着圣陵线的最北端,那是大霸尖山,我最喜欢的山,我爬了两次,意犹未尽。我想,退休后一定要做一次圣陵线纵走。但我怕我在国外一呆5年,回来已老,腿不行了,这个愿望达不到了。所以,我现在回来,或许反可圆梦。
每次走在这些高级的地方,看到那些和善的山友,我就觉得,这里真是美丽。
“婆娑美丽的美丽岛……”我是最早唱着李双泽这首歌的人,还在电视节目“六十分钟”把它记录下来。当时,我们真是这么想、这么看,可是后来,这里不再美丽。
我一直盯着那个酒桶山顶看,直到飞机穿云落地。一出机场,闪光灯此起彼落,我到了现实的台湾省,被追问:“你爱不爱台湾?”
我想说:“我不爱,一点不爱。”但我爱大霸尖山,我爱山东的太鲁阁,我爱山壁下的苏花公路。我在去年7月间,还一个人在这里走了一趟。我用走的,一路搭便车,我搭了贷车、卡车、摩托车、轿车,司机有平地人、原住民、小商人、工头、学生、军官,还有警察,他违规地载我这个没有戴安全帽的路人一程。这些人,我都喜欢,我都感谢,谈不上爱,但他们确实可爱。我把这段旅程写成了两篇文章。
当那位原住民军官一家,送我到花莲车站,他那可爱的小孩向我说“一路保重”时,我接到台北办公室里长官的电话,他问我愿不愿接多伦多新闻主任。那位长官是本省人,我们并不亲。
我生在新竹,出国前,我特地去那里走了一遍。我的老家在文化中心旁边,已夷平成了一块小公园。我在保留下来的大榕树下,坐了很久。
从小学到高中,我读的都是新竹最高级的学校。我的小学——竹师附小,更是有名。我和同学们感情很好,毕业了快50年,我们还每3个月就聚会一次。这次我出了风波,同学们马上问:“我们是不是再办一次同学会,为他打气?”这些同学中,大多是本省人。
如果“高级”,是指生活富裕,那我这外省中级军官的孩子,实在比不上我的本省同学,他们多来自新竹的仕绅家庭,是医生或殷商。他们弹钢琴,我则不懂五线谱。他们住在两层的水泥洋房里,我家只是竹篱笆围起来的日本榻榻米房子,四家分住。他们的便当打开是干干净净的鸡蛋肉片,我的则是些杂乱的五花肉,我还记得打开自己便当时的羞惭感觉。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比其他学校的人好,他们是光脚,我们有皮鞋。我们同学间经济虽有高低,但感情仍然很好,维持50年,直到我们终老。可是一直到去年,有位同学拿出她刚逝的父亲的照片,她父亲也是我小时的医生。照片上写着她父亲与日本行政长官后藤新平的关系,我这才感到,我们之间的差异,不是外省、本省,其实是中、日之别。我们小学的感情,是克服了省籍差异,但国族的差异却仍然潜伏着,一旦有人挑起来,我们的感情、认同,就会受到冲击,这就是台湾过去20年来的发展。
小时我们认识一家,与我们很亲,他们是外省人中最“高级”的,高到不能再高了,但在时代的变迁中,他们的生活却很低级,或许这么说,“困苦”吧。他们的生活还要靠我家送点小东西而有点欢乐。后来这个人又回到了那最“高级”的环境,他可能不再回新竹看了,也不再认我这个儿时朋友了。但他在我这件风波中,竟骂我变态,我真有相煎何急之痛。如果台独把我调侃的“高级外省人”说法当真,那我是当之无愧,正如詹宏志所说,我们确实是“知书达礼,安分守己”。但看到这个外省人的表现,我实在感到脸红心虚。
在我小时,台北是多“高级”的地方,我坐着父亲的吉普车,顺着省道晃两小时来到台北,真是兴奋。我到了圆环,吃了蚵仔煎,视为人间美味,所以我才会对圆环有份感情,才会对它的没落感到失落,才会写《绕不出的圆环》,就像我写《中华商场》一样。这些怀旧喟叹,怎么会扯到我是“高级”,因此瞧不起那些自认“低级”的人呢?
“九二一”地震第二天,我就到了现场,我也写下了我的感受,那是地震后第一篇上报的长文。我又怎么会不关心这块土地?看着一位高大的外国记者在拍放在冷冻棺材中罹难者的脸,我还真想叫他别拍了,这些痛苦的画面不要再拍了!我这时会想躺在那里面的是本省人或外省人?是,我是有厌恶的时候,当我看到满山的槟榔树,被震得一片片的大滑坡。我会想,种这种对水土保持不好、又对身体有害的植物,做什么呢?
我积极支持戒烟,抽烟加槟榔,口腔癌是一般人的5000倍,这多是本省人嗜为。如果我是“高级外省人”,那我为何要管本省普罗大众的健康呢?
我还有个老师,后来做到“最高级”的台湾人,但他一生其实是想做个日本人,因此我没与老师来往,否则我早做最高级的文官了。这老师以前对我很好,还鼓励我去追他女儿,如果我做了,很可能成为个日本人的驸马爷,那是不是比台湾人“高级”了呢?
我最好的朋友,是个“最高级”的外省人。我认识他时,他父亲已因经济上高级,被一位政治上高级的朋友疏远了。我写此文的这几天,这还是个高级的话题。他的第一个女友,是位秀美的本省人,他那高级的父母有天私下找我去,说高低不配,叫我劝那女的不要与他儿子来往。我勉为其难地做了,约她出来,绕着那时还有的复旦桥,告诉她我约她出来的目的。我不敢正视她,我记得的只是她那双鞋子。
过了几天,我朋友约我到他家,在门口很严厉地对我说:“你是交我这个朋友,还是我爸爸?”我听了很惭愧。后来他们还是分手了,我朋友娶了一个外省女孩,但他似乎并不快乐,那女孩要适应他那高级的家庭也不快乐。我想,如果我朋友的初恋维系下来,他会不会比较快乐?他一直记得她,想见她。
因为这位好友,我认识了一位最“本省”的本省人,“本省”到与我讲话常冒出一大段闽南语,让我如鸭子听雷。他现在也是位最高级的中国人,结果又被台独给骂死了。这个人对我说:“我爸爸从小对我说,不要与外省人来往,他或许是受了‘2·28的影响。所以我小时候根本没外省朋友。像你这种人我根本不交。但我后来认识了他,我才知外省人中也有好人。直至他父亲死了,我去参加葬礼,冠盖云集,才知他父亲是大将军。早知他父亲的地位,我是不会与他相交的,我怕怕。”
现在,我们这两个原来绝不会有交集的人续缘成友。我们都是中国人,不分哪一省。
还有一个“最高级”的本省人,堪称本省王子。我们一起带着小孩激流泛舟,一起累了把车停在路边睡觉,我们一见如故,可惜他喝酒抽烟早逝,我们的友情无续。
还有个外省人,非常的“外省”,“外省”到我知他是漳州人,大吃一惊。他说他父亲是军官,在“2·28”后派来台,因为会说闽南语。他们住在新竹机场旁的日本仓库里,以前,我会把他视为“低级”外省人的。他混太保,坐过牢,后来才发迹。现在,他是“外省”还是“本省”,是“低级”还是“高级”呢?他想叫他的儿子与我女儿来往,那他是“高攀”,还是“低就”呢?
我家那分住的日本房子与隔壁只隔张纸板。他们家的女儿嫁了一位很有钱的外省人,后来经济犯罪逃到国外去了,闹的新闻不比我的小。她属“高级”还是“低级”?若算钱,她现在还是很“高级”,但若穷得只剩钱,似乎不算“高级”。
我的太太是赵耀东的堂妹,赵耀东死了,有位本省人立刻来家致悼,坐了好久,后知马英九要来,他就走了,王不见王。他是施明德。赵家不知怎搞的,很支持施明德。我以前知道,还向大哥说我反对,施明德搞台独,不应该支持这种本省人。但后来,在施明德选立委,他最失意的时候,我经过他那冷清的竞选总部,还是去捐了一点钱。我不同意他的理念,我敬佩他至死不改的坚持。这点,他高级。
我一直想送施一个东西,这本来是属于他的。1980年代末,我在新闻局做最简单的“回复人权信函”的工作。这些来函大多是呼吁要释放施明德的。我都以制式函回复,上面写:“施氏有害国家安全,此与言论自由无关”云云。没想到,现在这种回复,可能要适用到我身上了。我把来函的邮票收成了两本集邮本,本要送给两个儿女,后来,我想还是应该送给施。我甚至想义卖个百万元,捐给他。
当我第一次外放结束,离开纽约时,来接我的是个本省人。他一直支持台独,从未隐藏他的想法,后来他做到副局长。当局里很多人嫉评他升得太快,我为他辩,说他其实升得慢。他对台独不改坚持,比你们这些见风转舵、人鬼言殊的人好多了。2008年蓝赢,他辞职,我追出去向他说“再见”,他已隐入夜色中走了。
还有一个本省人,绝对的台独。当我那些同事,包括些外省人,阻挠我外放时,我拿着我的成绩去与他谈。我隐藏了我大统派的立场,等于欺骗了他。他接受了我的说词,直接点我外放。他是叶国兴。这些年来,我一直想去看他,说“谢谢”。
姚文智,现在恨得我牙痒痒,若他知道他要关TVBS时是我代表新闻局同仁在报上投书反对,他不知会怎样想。我还配合退休的处长们,在新闻局内筹钱给TVBS代缴罚款。这些匿名的捐款者,多是本省人。后来,法院判决新闻局这项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是错误的,TVBS拿回了缴交的罚款,则我们的那些作为又有何不对?
还有黄智贤,本省人。蒋夫人死了,我写评论批评这位“最最高级”的外省人、中国人,甚至美国人。黄智贤大不以为然,写文章为蒋夫人辩,不打不相识,我们反而成了好朋友。
还有张超英,也算是个本省王子。他与我很好,因为我俩都懂电视,都爱摄影机。我们从纽约就熟识。他每次从日本回来,都要约我见面,谈谈一些计划。后来我知他倾独,比较不与他往来了。他死了,回忆录写了他在中华民国西,偷偷搞台独,推翻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那我不也是一样吗?我是在他们快达成的目标下,偷偷地在保卫中华民国啊!他以叛国被颂,那我何以爱国受罚呢?
张超英的爸爸反日,一元租其屋给中华民国领事馆,以见青天白日旗在他家升起为悦,但“2·2”后,他又对国府失望,终身不再参加政治,儿子成为联日求独的人。但张超英死了,在葬礼上把政府褒扬令交给其家属的竟又是陈仪(“2·28”时的台湾省主席)的后人,历史是如何的吊诡?
我在新闻局的最后这4年,有4位同事常在一起,两位是本省人,一嘉义,一宜兰,一位是外省人,就是那位具名投书而被申诫的潘舜昀。我们4人常中午吃饭,一天谈的话比与太太谈的都多。
有天,我们到西门町吃饭,吃完了走回局。潘舜昀说:“我小时候,父亲带我来看电影,都要到新公园旁去喝杯酸梅汤。我想去回味一下,好不好?”于是我们都去喝了杯标准的外省美味,溽暑全消,大感满意。那位嘉义的说,他大学第一次来台北,路过新公园,看到一个外省老兵,下摆皆湿,他以为他掉到池塘里,后来才知那是血,因为同性恋纠葛而被人所杀。我回去后写了《同志四人》一文,记下我们那值得回忆的一天。
最后,说这段事作结束。1990年代,我调派在温哥华时,那里有很多“台湾之子”,他们父母来报到做加拿大人后,又回去爱台湾,把他们丢在高级的异邦。他们是我儿女的同学,把我家当活动中心,整天到我家来吃喝,我太太把他们当自己小孩。我虽然向儿子笑说他们是“歹仔”,但我出去玩,去露营、去爬山、坐飞机、划木舟,都带着他们。我的车里能装多少就带多少。他们的青春,有我家的深刻印记。他们读完了书,有的回到台湾,有的去了大陆,少数留在加拿大,一直与我家保持联系。这次我风波出来,他们非常关切,写电邮给我太太说:“郭妈妈,不要怕,我们共同养你。”
有一个歹仔,从南极回来,给了我们一封信,他说想为延续2041年到期的“南极公约”而奋斗。信中说:“在旅程中,有人说,调查显示,会关心并致力于保护环境的人,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小时候曾经接触过大自然。接触的频率越高越深,对往后的影响越大。所以感谢您和郭爸爸之前去哪都带我去,没有小时候的启蒙,我也不会有今天,更不会因为想要为这世界带来改变而参与一堆学校的活动,进而争取到去南极的机会。也就是说,没有你们,就没有我这次的南极之旅。”
在南极,他会想到本省外省,谁高谁低吗?他想到的恐怕只是我在野餐桌上的叫喊:“吃饭了!”
我们,不过就是多摆了双碗筷而已。
编辑 涂艳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