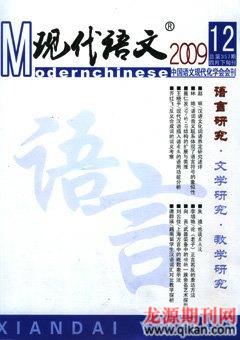简论诗歌创作中通感辞格的运用
摘 要:诗歌创作利用通感这种感觉的挪移进行形象思维,创造了很多“不合生活常理”的句子。而往往正是那些“令人费解”的字眼,使诗句顿时神灵活现、含义隽永,给人以无穷的回味。通感与比喻有很多相似之处,但通感是在两种或更多种感觉之间打比方。因此,它比一般的比喻表意更加痛快淋漓,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
关键词:诗歌 修辞 通感 运用
杜牧《阿房宫赋》中有这样两句诗:“歌台暖响,春光融融。”从字面看,是说“人们在台上唱歌,歌声是温暖的,如同春光那样融和。”“歌声是温暖的”,这是不合生活逻辑的。声音怎么能给人以温暖的触觉感呢?这就关涉到一种修辞手法——“通感”。
按照逻辑思维,人体的五种感官各有分工,任何一种感官都不能跨越自己的职责范围,去代替另一种感官进行工作。“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附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耳不能坚,手不能白”(《公孙龙子·坚白论》)。这就是说触觉和视觉是井水不犯河水的。陆机在《演连珠》中也说:“目无尝音之察,耳无照景之神。”实际上,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融,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譬如我们说“光亮”,也说“响亮”,把形容光辉的“亮”字转移到声响里去。又譬如“热闹”和“冷静”。钟子期能从俞伯牙的琴声中听出伯牙“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列子·汤问》)。孔子鼓琴时见到一只老鼠,其弟子便从其琴声中听出杀气。这些都是生活中感觉沟通的例证。用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种现象就叫“通感”,或者叫感觉挪移。
一
诗人们进行诗歌创作时正是利用这种感觉的挪移进行形象思维,造出了很多“不合生活常理”的句子。往往又正是那些“令人费解”的字眼,使诗句顿时鲜活起来,含义隽永,给人以无穷的回味。诸如“小星闹若沸”(苏轼《夜行观星》),“山花焰火然”(庾信《奉和赵王〈隐士〉》)等。诗歌创作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为了便于理解,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举例分析:
(一)触觉向视觉的挪移
(1)已同白驹去,复类红花热。(庾信《八关斋夜赋四城门第一赋韵》)
(2)仍怜风月太清寒。(范成大《亲邻招集·强往即归》)
(3)杨花扑帐青云热。(李贺《蝴蝶飞》)
(4)促织灯下吟,灯光冷于水。(刘贺《秋夕》)
(5)无风生翠寒,未夕起素阴。(杨万里《过单竹洋径》)
在上面的例句中,“热”“清寒”“冷”“寒”这些触觉中的感觉被应用于“红花”“月”“青云”“灯光”“翠”这些视觉形象中,使这些视觉中的形象给人以触觉的感受。
(二)触觉向听觉挪移
(6)寒磬满空林。(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
(7)残照背人山影黑,干风随马竹声焦。(《永乐大典》卷3579《村》字引《冯太师集黄沙村》)
(8)已觉笙歌无暖热,仍怜风月太清寒。(范成大《亲邻招集·强往即归》)
(9)鸟抛软语丸丸落。(黎简《春游寄正夫》)
(10)霜重鼓寒声不起。(李贺《雁门太守行》)
在这类句子中,“寒”“焦”“暖热”“软”“不起(重)”这些触觉中的感觉都被应用于“磬(声)”“竹声”“笙歌”“(鸟)语”“(鼓)声”这些听觉形象中,给人以听觉的感受。
(三)嗅觉向听觉的挪移
(11)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陆机《拟西北有高楼》)
(12)枝头便觉层层好,信是花相恼,觥船一醉百分宝,拼了如今醉倒闹香中。(王灼《虞美人》)
(13)雨过树头云气湿,风来花底鸟声香。(贾唯存《登螺峰四顾亭》)
(14)人皆待三嗅,余独爱以耳。(张羽《听香亭》)
在这类句子中,“馥”“香”这些嗅觉中的感觉都被应用于“哀响”“闹”“鸟声”这些听觉形象中,给人以嗅觉的感受。最后一例中以“耳”去“嗅”物,更是造意奇崌。
(四)听觉向视觉的挪移
(15)色静深空里。(王维《过清溪水作》)
(16)隔竹拥珠帘,几个明星切切如私语。(黄景仁《醉花阴·夏夜》)
(17)银浦流云学水声。(李贺《天上谣》)
(18)剪剪轻风未是轻,犹如花片作红声。(杨万里《又和二绝句》)
(19)视听一归月,幽喧莫辩心。(阮大铖《秋夕平等庵》)
(20)水北烟寒雪似梅,水南梅闹雪千堆。(毛滂《浣溪沙》)
(21)寒窗穿碧疏,润础闹苍藓。(黄庭坚《奉和王室弼寄上七兄先生》)
(22)山气花香无着处,今朝来向画中听。(李慈铭《叔云为余画湖南山桃花小景》)
(23)两地发钟声,子夜挟一我;眼声才欲合,耳色忽已破。(释澹归《南韶杂诗》之二三)
(24)月下听寒钟,钟边望明月,是月和钟声?是钟和月色。(释苍雪《杂树林八百首》之五八)
在这类句子中,“静”“切切如私语”“学水声”“作红声”“听”“闹”“和钟声”这些听觉中的感觉都被用于“色”“明星”“银浦流云”“花片”“月”“梅”“苍藓”“画”“眼”这些视觉形象中,使人从这些视觉形象中获得听觉的感受。
(五)视觉向听觉的挪移
(25)促织声尖尖似针。(贾岛《客思》)
(26)呖呖莺歌溜的圆。(汤显祖《牡丹亭·梦惊》)
(27)鸟抛软语丸丸落,两翼新风泛泛凉。(黎简《春游寄正夫》)
(28)商气洗声瘦,晚阴驱景劳。(孟郊《秋怀》)
(29)剪剪轻风未是轻,犹吹花片作红声。(杨万里《又和二绝句》)
(30)避人幽鸟声如剪。(《永乐大典》卷5345《潮》字引林东美《西湖亭》)
(31)柳边深院,燕语明如剪。(卢祖皋《清平乐》)
(32)月凉梦破鸡声白,枫霁烟醒鸟话红。(李世熊《剑浦陆发次林守一》)
(33)风随柳轻声皆绿,麦受尘欺色易黄。(严遂成《满城道中》)
(34)歌声青草露,门掩杏花从。(李贺《恼公》)
(35)戏拈生灭后,静阅寂喧音。(钟惺《夜》)
(36)耳色忽已破。(释澹归《南韶杂诗》之二三)
(37)是钟和月色。(释苍雪《杂树林百八首》之五八)
在这类句子中,视觉形象中的感觉“尖似针”“溜的圆”“丸丸落”“瘦”“红”“剪”“白”“绿”“春草露”“阅”“色”“月色”都被用于“促织声”“莺歌”“软语”“鸟声”“燕语”“鸡声”“鸟话”“歌声”“寂喧音”“耳(听到的)”“和(声)”这些听觉形象中,使人从这些听觉形象中获得了视觉感。
在各种感觉的相互挪移中,听觉和视觉间的挪移为最多。
其他还有听觉向味觉的挪移,如“香声喧橘柚,星气满蒿莱”(王贞仪《张兆移酌根遂宅》);视觉向嗅觉的挪移,如“数本菊,香能劲;数朵桂,香尤胜”(吴潜《满江红》)等等。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声音不但会有气味——“哀响馥”“鸟声香”而且会有颜色——“红声”“鸡声白”“声皆绿”。“香”不但能“闹”而且能“劲”。“银浦流云”会“学水声”。花色和竹声都有温度:“热”“焦”。鸟有时快如“剪”,有时软如“丸”。看月兼而“听月”,看星也觉私语,五官感觉可算得有无相通,彼此相生了。这些都不是按照逻辑思维所能理解的。
二
我国古代的诗人词人们是最讲究炼词炼字的。的确,有时一个好字会使全句顿时神灵活现,甚至使全诗骤然生辉。这一字便是“诗眼”。而实际上诗眼有相当数量都是在通感这种修辞手法下产生的。
北宋文学家宋祁《玉楼春》中有一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作者也曾因此而获得“红杏尚书”的美誉。而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李渔对此提出了不同见解。他在《窥词管见》第七则中说:“此语殊难著解。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炒”“斗”“打”字皆可用矣!”可见李渔是以自然主义的观点,以逻辑思维的方法来看待这一诗句的。对于这一批评,已故700年的作者宋祁,当然是不能作任何申说的。然而,李渔的同时人方中通则为宋祁作了有力的辩解。方中通在《与张维四》的信中说:“试举‘寺多红叶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之句,谓‘烧字粗俗,红叶非火,不能烧人,可也。然而句中有眼,非一‘烧字,不能形容其红之多,犹非一‘闹字不能形容其杏之红耳。诗词中有理外之理,岂同时文之理,讲书之理乎?” 既然“非一‘烧字不能形容其红之多”“非一‘闹字不能形容其杏之红”,着此一字,自然是恰到好处的了。
通感这种修辞手法的童年,大抵是比喻。到了后来,逐渐发展,它便从比喻这一家族中分离出来。因此,我们说它们之间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亚里士多德说:声音有“尖锐”和“钝重”之分,那是比拟着触觉而来的(亚里士多德《心灵论》)。培根说:音乐的声调摇曳和光芒在水面浮动完全相同,“那不仅是比喻,而是大自然在不同事物上所印下的相同足迹”(培根《学术进展》)。从其中的“比拟”“比喻”几个字,我们可以得到旁证。
任何一个含有通感手法的诗句中,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先天性的比喻成分。所不同的是,比喻只是在一种感觉(或视觉或听觉等)内的打比方,而一旦在这一种感觉内打比方不能尽情表意时,作者便突破一种感觉的局限,在两种或更多种感觉之间打比方,这便成了通感。如同样写星,“星如撒沙出”(卢仝《月蚀诗》)只写视觉范围里的固有印象,即以视觉形象喻视觉形象,这是比喻。“小星闹若沸”则是超越了视觉本身的局限,而领会到听觉范围里的印象,即以听觉形象喻视觉形象,这便成了通感。
再如,白居易《琵琶行》中写音乐:“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只是用各种事物发出的声息(雨声、私语声、珠落玉盘声、鸟声、泉声),来比方“嘈嘈”“切切”的琵琶声,并非以“急雨”“珠落玉盘”之状来比琵琶声。换言之,白居易只是从听觉联系到听觉,并非把听觉沟通于视觉,这只能是比喻。
元稹《善歌如贯珠赋》写歌声:“美绵绵而不绝,状累累似相成。……吟断章而离离若间,引妙啭而一一皆圆。小大虽伦,离朱视之而不见;唱和相续,师乙美之而谓连。……仿佛成象,玲珑构虚。……似是而非,赋《湛露》则方惊缀冕;有声无实,歌《芳树》而空想垂珠。”听歌声而使人从中看到了各种状貌,这可以说是对通感的绝好解说。
另外,李颀《听董丈弹胡笳》,以“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来喻胡笳声的纵控抑扬。韩愈的《听颖师弹琴》,以“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来喻琴声的飘逸激越,徒然升高,急降而下。这些都超越了听觉本身的局限,而领会到视觉范围里的印象。把那些虚幻无形的笳声、琴声化作可观可玩、可触可摸的视觉形象,这些都是通感的典型例证。
通感既然是超越了一种感觉的两种或者更多种感觉之间的比喻,因而,它要比一般的比喻表意更加痛快淋漓,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文学家们正是利用这点,创造突出的、典型的艺术形象,去调动人们的各种感官,让人们在视觉里获得听觉的感受,在嗅觉里获得味觉的感受……人们往往从一个形象上听出声响,看到状貌颜色,触到温冷,嗅到气味,尝到甘苦。从而对事物有更全面、更深入、更本质的感知。这样,作者的思想、情感便自然而然地传达给读者了。这就是那些“令人费解”的字眼会使诗句顿时精神起来、活跃起来的原因。
三
通感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文学创作中被广泛运用。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已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比如《礼记·乐记》中有一段极美妙的文章,把听觉和视觉很好地拍合在一起:“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即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对这节文章,孔颖达在《礼记·乐记》中作了扼要的解释。他说:“声音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形状如此。”马融《长笛赋》讲得更简明。他说:“尔乃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象飞鸿。”
另外,孔颖达《毛诗·正义》说:“使五声为曲,似五色成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为之歌《大雅》,曰:‘曲而有直体。”这些都让人从听觉形象里获得了视觉感。尤其是《乐记》里的那一串体贴入微的“类型”描写,要算是通感的典型例证了。它和“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遥相印证,可以说是惊人地相似。
声音有肥有瘦,更是儒家音乐理论的惯语。如,“肉好顺成之音作”,语出《礼记·乐记》,郑玄注:“‘肉,肥也”。“广则容奸,狭则思欲”,语出《礼记·乐记》,郑玄注:“‘广谓声缓,‘狭谓声急”。把时间上的迟速听成空间上的大小,这些都是通感的古例。后来的作家或者是模仿,或者是表达的需要(恐怕大多是表达的需要吧)用“通感”手法的数不胜数,这点从前半部分的例举中就可看出。
通感在西方作家的诗文里出现得也是很早的。并且比我国的通感表现得更突出、更大胆。例如,荷马有句诗:“像知了坐在森林中一棵树上,倾泻下百合花似的声音”(详见斯丹福《希腊的比喻》)。这句话曾经使很多翻译者搔首搁笔。至于用“大声叫吵的”“怦然作响的”等词来形容太鲜明或太强烈的颜色,用“珠子”般来形容音调,更是很平常的了。如“一群云雀儿明快流利地咭咭呱呱,在天空里撒开了一颗颗珠子”(意大利作家贝利语,见普罗文扎尔编《形象词典》第23页引)。到了后来,通感应用之广,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一阵响亮的香味迎着你父亲的鼻子叫唤”(见约翰·唐《香味》),和我国诗人“闹香”“香声喧”“幽芳闹”差不多。巴斯古立名句:“碧空里一簇星星啧啧喳喳像小鸡儿似的走动”(见巴斯古立《夜里的素馨花》),和“小星闹如沸”十分相近,和“几个明星,切切如私语”就更相合了。
通感,作为一种修辞格,是诗人们创造独特意境的一种手法。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夫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塑造典型,创造意境,通过个别高于生活的突出形象反映一般,启发读者想象,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了解了这种修辞手法的特点,就不会对“歌台暖响”觉得费解了。
参考文献:
[1]唐铁惠.文论专题[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7.
[2]周煦良.外国文学作品选[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3]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文学研究室古代文学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4]徐中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李新平 郑州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45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