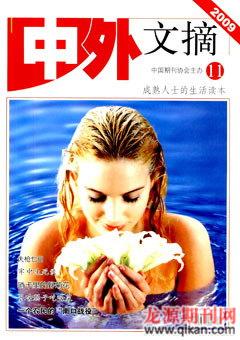种在陶罐里的太阳花儿
梅 寒
他给她的第一印象,是毛手毛脚,他做事大大咧咧,有点让人生厌。
开学第一天,他到她的办公室报到。彼时,她已在那所学校教务主任位置上稳稳地坐了两年,他是新调到学校的语文老师。
一声脆响,是在他起身离开她办公室的时候响起的。伴随着那声响,她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那只漂亮的青花瓷瓶,在他风风火火的一转身问,从她的案头掉落。一地碎片,凌乱的几枝残荷,加上她的惊呼,屋子里顿时乱成一片。他慌乱地俯身去拾,连声说对不起。她无力地向他摆手,示意他出去。那一刻,如果能够,她恨不得吞了他。
是在那以后的第二天,他就捧了一只同样的花瓶还有大束艳红的玫瑰到她的办公室来谢罪。好话说了很久,她依然没有收下。她让他带回去,临走轻轻地抛给他一句:我这里不需要玫瑰,谢谢!态度很客气,也冰冷。
捧着那瓶兀自妖娩的玫瑰,他在她的门外,沉思良久。
都道她是一个冰冷的美人,其实她也不过是老套故事里的可怜女主角。她曾有过一个爱得死去活来的男友,那个男人最终却选择了与另一个女子双宿双飞。忧伤自此像她的影子,日日萦绕不去。那个青花瓷瓶,就是当初那个信誓旦旦的男子带她到很远的古玩市场上淘回来的宝贝。是他留给她的唯一念想,如今也碎了。就像她碎了的心一样干脆。
碎了的终究碎了,什么样的补偿都于事无补。她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他赔偿的好意,可她却没有办法阻止他的脚步。两个人的办公室,仅有一墙之隔,他常常在课余时间到她的屋里来。还是一贯的大大咧咧。在众人吃惊的目光里,他大大方方地将一瓶可乐饮料扔到她面前,不管她乐意不乐意。他也会当着同事的面,细心地询问,为何脸色那么苍白,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没有休息好。自男友弃她而去冰冷成了她最好的保护伞。可他的真诚与温暖,还是在不经意间,一点一点将那层冰冷融化了。脸上有淡淡的笑意,下班后也开始跟着他和同事们到茶吧里浅饮小酌。可她知道,那些,与爱情无关。
他把那只古朴笨拙的陶罐捧到她面前,在她二十八岁生日那天。一只咖啡色的陶罐,上面绘有挑着水桶的村姑,还有井台、瓜架,整个画面看起来简洁又生动,淳朴又空灵。她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继而又暗淡下去。她不是不懂他的那份情思,可她却再不敢接受。
依旧那么不远不近地走着。她把那只笨拙可爱的陶罐放在自己的案头,就在那只青花瓷曾经站立的地方。只是如她说的,她的案头,从不需要玫瑰。一捧又一捧的爱情玫瑰,一律被她轻轻拒之门外。那只陶罐,寂寞如她。
他知道她的心结,所以,他从来不把心事寄托给玫瑰。他只是在她身边,充当着亦父亦兄亦友的角色。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借给她肩膀哭泣,她笑容灿烂的时候,他就按动自己手中相机的快门,永远地把那些笑容留存。
他也过了而立之年,却将自己对老人的承诺一推再推。谁都知道,他在等她。
女人的三十岁是一道门槛,门槛的这边是风华正茂,门槛的那边就已迈步朝向明日黄花。她终于在自己三十岁那年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他。新婚大喜日,闹洞房的众友起哄,让她讲讲他们的罗曼史。她没说什么,而是款款地从身后的花架上捧下那只陶罐。就是他曾送她的那一只,不同的是,那个陶罐再不是寂寞空空的,一簇五颜六色的小花,在里面开得正艳。她说,她曾接到过很多男人送来的花,但送花种给她的,他是唯一一个。
那是一种普通的小花儿,学名马齿笕,俗名太阳花儿。在乡野间的田间地头,农家院落,郡种花耔儿落地就生根,生根就发芽,不怕干旱,也不怕水淋,从初夏到深秋,一路开得摇曳生姿。他就是捧着那样一捧花籽儿向她求婚的:过去的爱情就是那只碎掉的青花瓶,碎掉了就碎掉了,而爱情却不会死,给一片土壤,撒下一拄种子,平凡的陶罐里也能开出幸福的花。
(摘自《人生与伴侣》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