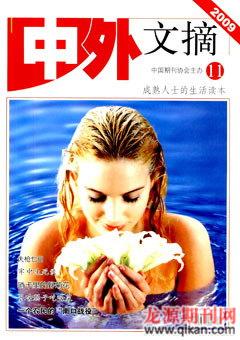牢中生死录
黄秀丽
牢头狱霸的社会之痛绵延古今中外,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又纠结产生于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若干不足。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官员也坦承“牢头狱霸长期存在”,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打击。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专项检查”方案,从4月20日起在全国看守所排查严惩“牢头狱霸”,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郑言水,曾在某看守所蹲过5年冤狱,后被无罪释放。他在看守所从“新收”(黑话,指新进看守所的人)混到了号长(即俗称的牢头),几历死生。2009年5月下旬,他向记者作了口述。
号里,一个丛林法则的小社会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号里如果是软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
2001年3月9日上午9点多,我被警察带进了看守所。警察检查完身体,按规定搜走了我的腰带、皮带后,我拎着裤子、光着脚进了“仓”。福州将监舍称作“仓库”,嫌疑人入监、出监称作“进仓”、“出仓”。
大铁门里面,房间有二十几平方米,呆了二十七八个人,大家忙着做灯花、编织、穿珠子,后来我知道这是看守所规定的劳动任务。房间有六七米高,只有一个窗户,几乎不见阳光。
我的到来让大家很兴奋。“脱衣服,浇头。”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说,后来我知道他是号长。屋里有个天井,我被叫到天井中央“过关”。凉水浇了二三十桶,3月份还很冷,我全身都冻硬了。还有二十多个人围着我,盯着我看,我脱光了站在那里,恐惧到了极点……
后来我知道“浇头”还算好的,我们这里是干部号,关着公务员、外籍人员、老人以及一些托人关照过的嫌疑人。看守所里有两个干部号,其他都是大号,关的就是杀人、抢劫等刑事犯罪嫌疑人,新入号的犯人过关方式就是挨打,类似《水浒传》里的:“杀威棒”。
浇完头,号长叫我过去问案情。他听完了之后说了声“很麻烦”,就叫我去劳动。穿了一上午珠子,中午一口饭没吃下去。晚上10点多,大家陆续睡下了,50厘米高的大通铺上挤挤挨挨地睡了十几个人,连一只脚都插不进去。这时号长发了话,你睡“海山”吧。我就拿了生产用的纸皮铺到“海山”边。“海山”原来是本市最豪华的宾馆,在这里指的是茅坑,故意讽刺的。因为铺位有限,有一半的犯人要睡到通道和“海山”边。人多的时候,连“海山”边都睡不下,只能在墙上靠着,或者轮流值班,轮流睡觉。
刚开始几天很害怕,后来慢慢适应了,发现这是个很特殊的社会。号里有28个人,分为3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为“一斤”、“二斤”、“三斤”。“一斤”是号长和当头的几个人,即“高层”;“二斤”是中层。“三斤”是新来的和地位低下的嫌疑人。号长通常是干部(指警察)指定的,其他“一斤”、“二斤”和“三斤”是自动形成的。决定等级高低的因素有多种,包括拳头有多硬,和干部、号长关系好坏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案情,诈骗,强奸等嫌疑人被认为人品有问题,是混不上“一斤”、“二斤”的。
起初也有人欺负我,有天轮到一个合同诈骗嫌疑人值班分饭菜。菜是煮土豆,他分给我的只有汤。我火起:“你不要狗眼看人低!”他说:“你新来的要怎样?”两三个人就围了过来,我这边也有两三个人,打起来了。几分钟之后,干部来了,用警棍在铁门上敲,警告我们。号长也过来调解。
打了一次架,人家就不敢小看我了。在“海山”边睡了半个月,就去睡通道,差不多睡了一年。在号里如果是软蛋,那就有洗不完的衣服,洗不完的碗。有一个房管局的前科长就比较软蛋,总是受人欺负,这种人是多数。如果你有钱,可以买些东西来孝敬“号长”以及其他“一斤”、“二斤”,这样的日子就好过点。要是既没钱又没身份,只能扫地,帮人捶背,洗短裤,非常痛苦。
号长,微小的权力被无限放大
并不是所有的牢头(号长)都是狱霸。只有当牢头太凌厉霸道,警察又不够负责任时,才会变成“狱霸”。
在这个看守所,一个警察要管两个号,每个号都有二三十个人,直接管理是不可能的,都通过号长来遥控。所以,一个号长素质高低,对看守所的秩序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比如新来的犯人能否“服水土”,关键要靠号长的调教。
做号长意味着有利益上的好处。在外面,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资源在这里被无限放大,成为人人羡慕的东西。号长,吃东西会多一点。看守所里不许给家人写信,只能寄明信片,但号长就有每月给家人写一两封信的“特权”。这些在外面都是很小的事情,在里面就不得了。多写张明信片有什么?在里面都是一根根救命稻草,你想捞都捞不着的。
当号长还有一个长处,每天都“出仓”两次,向干部汇报工作。这是了不得的待遇,绝大多数的犯人,无论关几年,只有进仓、出仓两次。
老号长走了之后,干部就觉得我威信还行,让我当号长。我就是为了出去透透风,才同意当号长的。在仓里呆着只能看三四米远的地方,眼睛都半瞎了。
我能出去,还能打听一些外面的信息,嫌疑人与世隔绝。我回来讲给他们听,人家都很羡慕。
号长也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比如睡觉,每天晚上,睡床上和海山,天差地别。晚上值班分成早、中、晚三班,中班正好是半夜,是最难受的,怎么排班,也是号长一句话;饭菜很差,一菜一汤,青菜都煮黄了。可是能否吃到一口菜,也得是号长说了算。
号长可以决定你能否给家里邮寄明信片。干部把明信片分给号长,要是号长给使点小动作,就会根本寄不出去。点点滴滴的权力,外人看起来很可笑,但对嫌疑人来说就很重要。
号长和干部的关系很微妙。干部利用号长来管犯人,需要给号长一些好处。如果干部向犯人索取一些利益,或者犯人要跟家里人取得联系,都得号长“牵线搭桥”。号长跟干部合伙搞这些事是违法的,我在这里呆了3年,有好几个警察进去了。
到了后期,我们吃上了“干部菜”,这是干部给我们做的大好事。一个月交800到1000块,中午和晚上能吃上5块钱的那种盒饭。号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吃,其他的人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吃,吃剩下的他们就分了。
并不是所有的牢头(号长)都是狱霸。牢头要维护监管秩序,也要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有的号长在外面捞,在里面也捞,太凌厉霸道,如果警察又不够负责时,号长就会变成“狱霸”。不过号长要是民愤太大,警察也怕出事,会把你换掉。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死人
看守所死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生存环境太恶劣了。除了纯暴力打死的,还有两个原因,犯人精神极度紧张、营养极度缺乏。
我只当了一年的号长,就坚决不再当了。二十多人呆在一个房间里,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哪能不打架?如果号长威慑力不够,就管不
住犯人。通常干部会派几个比较凶悍的犯人给号长撑腰。遇到事了,是打还是不打?很为难。
号里有一个“小山东”,身高一米八二,二十七八岁,以前是当保安的,很壮。他在大号里被人把脾脏打坏了。脾脏摘除后,瘦了好几十斤,每天弓着腰,饭量一点点。他给我们看伤疤,有十几厘米长。他要是再放在大号里,就被人打死了。干部号这种事比较少,就是冲突起来强度也比较低。干部才把他调过来。大号很恐怖,打架的,斗殴的,强奸的,抢劫的,都有。
白天干部盯着监控屏幕,号里发生异常立刻就赶过来;晚上就是犯人自己管犯人。晚上出了事情,比如打架要把人打死了,或者有人病得很重,号长就带领大家拍床板“喊号”,干部就会跑过来处理。“喊号”天天都有的,经常听见隔壁发生骚乱的声音。
号里莫名其妙地死人很常见。每隔一段时间,看守所的医生就来发维生素B、D呀,我们问怎么回事呀?医生说又死了一个人,解剖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号里营养不好,赶紧给大家补充些营养,以防万一。
看守所里两三年都吃不到一口青菜。这里关了很多处级、厅局级的人物,大家经常谈拌空心菜,都会流口水。我在这里呆了半年头发就白了,一方面是因为愁案子另一方面营养太差。
看守所死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生存环境太恶劣了。除了纯暴力打死的,还有两个原因,犯人精神极度紧张、营养极度缺乏。比如说刚进来的嫌疑人生命是最脆弱的。经过审讯的高压,嫌疑人身心俱疲,没吃没喝,精神极度紧张,不堪一击,在外面可能20拳都打不死,进来一个指头就戳死了。我是当兵出身,身体棒棒的,那么残酷的训练都经受得起,进来却连续7天盗汗,极度虚弱。要是适应不了环境,没调整好,就走了。
我们在这里从不放风,一个个皮肤雪白雪白的。晒太阳怎么晒?冬天的上午,有一缕阳光从窗户射进来,总共也就十几分钟,大家就轮流晒一会儿。这是最让我刻骨铭心的。
干部是不会进号的,除非搜查违禁品。那时候武警手持冲锋枪冲进号里,大家抱头蹲在角落,要是哪个人抬起头,橡皮棍就敲过来了,那真是奇耻大辱。我们这些人还不是犯人,是嫌疑人哪。
一个与世界隔绝的世界
我们最羡慕的是一个外籍华人。他是个诈骗嫌疑人。每个月,该国领事馆驻广州的领事都会飞过来看他,我们感到他们把人看得最重。
“坐牢”3年,我脑海里经常会浮现《水浒传》描写狱卒的细节,一千年过去了,狱卒除了衣服穿得不一样,有多少本质区别呢?
在号里所有的信息外面的人都不会知道。按照规定,嫌疑人不可以会见家人,就是律师我也是三个多月后第一次见。出来之后我才知道,这都是律师申请了好多次看守所才同意的。一年大约只能见一两次,每次都高兴得不得了。会面大约有半个小时,除了案子,没法谈别的。警察在旁边,提到别的就会打断。再说,这些东西跟律师讲了有什么用呢?
我们最羡慕的是一个外籍华人。他是个诈骗嫌疑人,关了两年。诈骗罪是最让号里人瞧不起的,但他属于“一斤”、“二斤”的人物,连警察都畏惧他三分。因为,每个月该国领事馆驻广州的领事都会飞过来看他,雷打不动,他每次都很骄傲地出去。我们问他,每个月都看你,哪有那么多话说?他说不过就是问是不是挨打之类的,就是一句话不说,人家也来看,这是规矩。这个形式代表了很多很多内容。我们感到他们把人看得最重。
(应当事人要求,郑言水为化名)
(摘自《南方周末》)
链接
牢头狱霸的今与昔
何兵
因为云南牢头狱霸殴人致死一事——“躲猫猫”事件,我重温了清初散文家方苞的《狱中杂记》。他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的代表作家。方苞因为给好友的书写序,身陷文字狱,被押进刑部大牢。初定绞刑,后被营救释放。《狱中杂记》便是他在监牢的所见所闻,
作者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监狱每天有三四个犯人死去,被从墙洞里拖出去。一位在押的知县告诉他:“这是瘟疫发作啊。现在气候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每天十多人。原因是牢房没有窗户,关押的犯人却有二百多人,屎尿味同食物气味混在一起。贫穷的犯人在地上睡觉,很少不生病的。”奇怪的是,大盗们往往精气旺蛊,鲜有死去的,死去的都是罪轻的人或者证人。
方苞纳闷地问:“刑部监狱为什么关押这么多人呢?”那位知县犯人告诉说:“官员和小吏们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与案件稍微牵连,就想办法弄进来,戴上脚镣手铐,让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导他们找保人,花钱疏通关系。弄来钱,官员和小吏就瓜分了。有钱人出几十两银子,就可以去掉脚镣手铐,并住进好监室。贫穷无依的犯人,戴上刑具关押,作为标本,警告其余的犯人。结果,罪轻的、无罪的遭受枷锁之苦,重犯反倒住在外面。”
方苞问小吏:“狱吏跟犯人没有什么仇恨,不过希望得点财物,如果确实没有,就宽容宽容他们,这不是善行吗?”回答说:“这是立下的规矩,不然人人都会有侥幸心理,到哪里去弄钱?”又问:“犯人贫富不一样,何必按出钱多少,分别对待呢?”回答是:“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由此可见,狱吏们对于潜规则,倒是奉行执法必严的原则。
有些奸诈的人,长期关在监狱里,同狱卒内外勾结,很能捞钱。有个杀人犯,每年能弄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他被大赦出狱,失去了好营生。几个月后,同乡有人杀人,他就代替那人承担了罪名。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不是故意杀人的,不会有死罪。康熙五十一年,他运气不好,被发配到边疆戍守。他遗憾地说:“我再没机会待在这里啦!”他几次写呈文,恳求推迟发配,没有得到批准,让他很失望。
看完清代狱中见闻,我在网上搜索当代狱中见闻,看看监狱或类似机构有无变化。下面是搜索的一些结果:上海的作家韩寒在博客中转载了一篇纪实散文——《嫖娼启示录》。
故事是这样的:作者的一个朋友,经不住诱惑被小姐拽上床,被北京的公安拘押起来。本来以为罚款就行了,谁知不仅拘留十五天,而且可能直接转收容教养半年。托朋友打听,说要花十五万,还最少要在收教所待三个月。律师朋友说,现在是年关,警察任务比较重。任务完不成,直接影响他们的考评,所以没人敢放。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位在北京犯事的人不知为何被转移到河北邯郸的收教所——据说是收教所从北京买的。个中原因是,在河北嫖娼不算个事,派出所直接罚款五千元放人。收教所在本地搞不到学员,只好从北京购买。这次买来的一百六十个学员中,有十六个是画钧的,意思是这十六个人是可以出钱的。故事的结局是,大家花了十二万七千元,将人捞了出来。
这个故事如果方苞听见,他会觉得与康熙五十一年间发生的类似。
下面这个故事,是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四川省阆中市第二看守所四名在押犯,打伤民警逃出看守所。盖子揭开后发现,这个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得经常出去卖酒。酒是看守所自己酿的,几乎每个人都得出去卖,挣的钱交回看守所。看守所规定,卖酒超过二十五公斤,可以出去玩一天。有时,在押人员卖酒,警察根本不在场。除了外出卖酒,警察心情好的时候,还带着犯人去娱乐场所按摩。
这样的故事,方苞没讲给我们听。他可能没见到,或者没想到。云南“躲猫猫”事件,如果讲给方苞听,他可能会这样想:李荞明和其他五个村民在山上偷砍几棵树,被晋宁县森林公安收押,是因为“官员和小吏们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纵容牢头狱霸行凶,是“让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导他们找保人,花钱疏通关系。弄来绒,官和小吏就瓜分了”。李家一直不交保,当然不能宽容——“不然人人都会有侥幸心理”。犯人贫富不同,必须区别对待——“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
至于弄死人,并上了互联网,这倒是牢头狱霸和方苞万万没有想到的。
(摘自《济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