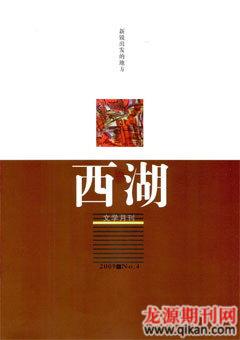关于鲁迅研究
李冬木 刘 涛
刘涛:李老师您好。2008年9月,在费正清中心偶然遇到您,此后与您多次接触,多次请教,受益良多。于是希望和您正式谈一次,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现在已经深夜了,我们算是“波士顿夜话”了。
您近几十年的研究基本集中在鲁迅研究,尤其集中于鲁迅和日本的关系。一方面笔耕不辍写了大量鲁迅研究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向中国翻译和介绍了大量日本学者研究鲁迅的著作。其中很多在鲁迅研究界引起重大反响,认识您之前就读过您翻译的竹内好《鲁迅》。您几十年研究的重心集中于鲁迅,可否先谈谈为什么如此倾心于鲁迅?
李冬木:我中学的时候已经开始接触鲁迅,不过都是在教科书中,比如读了《故乡》、《孔乙己》等。那位教师后来还讲过《狂人日记》,我们那个时候不能理解,觉得不可思议。现在印象最深的是《孔乙己》,那位教师讲课很生动,模仿着说:“哎,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前些日子我还在国内寄来的去年同学会的录像里见到了那位教师。
之后我本科读的是中文系。当时学习现代文学,鲁迅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教师讲得非常细。我就随着教师的进度自己阅读。教师有他自己的问题意识和着重点,而我阅读之后有不同的兴奋点。久之,我开始觉得鲁迅跟文学史中谈的鲁迅很不一样。二者差别非常大,以至于很多人不敢认同真正的鲁迅,只是接受教科书中的鲁迅。
我对此不满意,于是大二的时候,开始通读《鲁迅全集》。从大二到大四,两年间读完。我觉得鲁迅是现代留给当代的遗产,我们还没有很好吸收,这也是我要读研究生的主要动机。研究生我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毕业论文是写鲁迅的文明观。以他早年留学的几篇论文为主,分析日本留学时期鲁迅思想的基本框架。我发现鲁迅的核心是文明冲突的问题,他谈中国文化衰落的问题,文化衰落的本质是现实中人的精神衰弱。中国近代对西方的了解经历了一个过程,先是被“坚船利炮”吓到,此后魏源他们已经意识到除枪炮外,西方尚有长技,于是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又有洋务运动。严复他们已经意识到西方除此之外,尚有哲学和思想,于是大兴翻译。鲁迅则更综合地看这些问题。鲁迅的一些想法跟福泽喻吉很近似,后者有一本书,叫做《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50年代即作为名著翻译出版。这部书指导了日本的近代意识。福泽将文明分为两种,一是有形的,一是无形的,无形的即指人的独立精神。鲁迅的《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篇,即是在喧嚣的“有形”世界中对“无形”的洞见与强调。鲁迅认为东西文明之差异“犹水火然”,其本质的不同即人之“精神”的有无。强调确立“人格”或“精神”是鲁迅早期的主要思想。这也是我二十多年前写硕士论文的思路。那篇论文的题目是《文明、历史、人、文学——论鲁迅的文明观》(吉林大学研究生论文集刊,1987年)。我写了五大章。其时写作只用了十二天,连续好几天几乎没吃没喝,是爆发式的,觉得要将几年的积累爆发出来。理解了鲁迅之后,觉得鲁迅和自己特别接近。
刘涛:呵呵。鲁迅已经化入您的气质之中了。您后来或写或译了大量鲁迅与日本关系的论文与专著,为什么后来集中于鲁迅研究的这一领域呢?
李冬木:大学期间,给我引导的是已故的蒋锡金先生。他也是我父亲的老师。蒋先生一般不上课,我常去他家拜访,他边喝酒边给我讲鲁迅。那时,我们学校迎来了首批学习汉语的日本留学生。有一位同学来自仙台,送了我一本书《鲁迅在仙台的记录》。日本鲁迅研究界为了弄明白《藤野先生》这一篇文章,动员了专家学者等共四百多人。这本书完全是史实调查,涉及鲁迅在仙台的大量信息,比如什么时候到了仙台,住在什么地方,房东是谁,跟哪些同学交往,是否有漏题事件,为什么离开仙台等。足见日本学者之认真。这本书后面有一篇《藤野严九郎年谱》。当时我正在学日语,在蒋锡金先生的鼓励下,我试着翻译了这个年谱。当时日语不太好,蒋先生帮我改了很多。后来送到《东北师大学报》发表。这是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我读大三,特别受鼓励。
后来我报考了吉林大学刘柏青先生和刘中树先生的研究生。其时是1983年,刘先生被教育部派到日本访问,历时三个月。三个月间,刘先生访问了大量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并购买了大量的日文书籍。我们当时四个人考取了他的研究生。刘先生第一次见我们就问,你们觉得自己的日语考得怎么样?记得那一年的考题格外难,我考了四十多分,还算是高分。刘先生对我们说,你们的日语都还不够。我这里有一些日文鲁迅研究专著,你们带回去阅读,读完了过来见我。我当时挑了《鲁迅与日本人》一书。阅读了很久,但还是模模糊糊。一次我去教师家里请教问题,刘先生帮我解答完之后,我豁然开朗。于是问老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刘先生给了我充分的肯定,并鼓励我试译一下。其时刘先生与伊藤虎丸先生合作主持一个翻译项目“日本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于是将我的翻译的一章收人,这是我发表的第二篇论文。
其时刘再复先生提倡“三论”,1985在扬州主持“现代文学与新方法”讨论会。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现代文学研究与系统科学方法移植》,于是在刘先生的鼓励下奔赴扬州。开会规定每个人十五分钟发言时间,我讲了三十分钟。会后,刘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徐中玉先生。刘再复先生让我将这篇文章呈给徐中玉先生。我回到吉大不久,即收到徐先生的信,说此文在《文艺理论研究》下一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上发表。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我毕业留校之后,有机会到日本关西学院访学,我报的题目是《鲁迅与福泽喻吉》(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1992年)。两年后,我考取了大阪市立大学片山智行先生的博士生。片山智行先生是增田涉的弟子。当时正值他的又一重要著作《鲁迅<野草)全释》出版,我即将此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
在读期间,通过资料以及和各种学者接触,我开始让自己介入到研究史里来,并对按照某种预设框架来进行阐述性研究的方法感到不满。此后经过摸索,逐渐认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是以正确的史实关系为前提的研究。毕竟还有那么多基本史实都还没弄清。实证研究的原则是没坚实的史实支持,就不能随便下结论。如果灯笼能够照射三米,我只要这实实在在的三米,绝不越界。我们应该知道人本身的界限。我希望做完一方面的论文之后,对后人有所帮助,少一些修正或少走些弯路。论文或著作少不要紧,要实实在在。我从事实证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即是研究日文版的《支那人气质》。这里要提一下张梦阳先生。
刘涛:我看过张梦阳老师的一篇文章,他谈过你们两个人认识的过程。1999年在云南昆明举行一个学术会议,会后聚餐你们坐在一起。张梦阳老师到处向别人打听,“谁是李冬木?”你也向别人打听“谁是张梦阳?”其实你们
就坐在一起。
李冬木:对。就是这样。我非常感激梦阳先生。他对英文本史密斯《支那人气质》的研究给了我非常多的启迪。但是我也向他指出一些不足,因为鲁迅读的日译本的《支那人气质》,不是英文原文。梦阳先生对此早有洞见,但苦于一直没找到日译本。于是,我便从寻找这个日译本人手,最终在增田涉的文库中寻得。译者是涩江保,但关于出版社和译者的情况,一概不知。于是我开始研究博文馆和涩江保。明治时代的博文馆出过四千多本书,我一本一本数过。日本大百科全书关于博文馆的数字是错的,他们说是四十几年间出了三千多本,我估计作者只是估算而已,其实是二十几年间就出了四千多本书。此书的译者涩江保留下一百六十多种著作,但是名字没有留下来。我认为这是因为涩江保跟出版社关系不好,写博文馆史的作者有意地抹杀了他。博文馆在日清战争时,出过二十四本“万国战史”,后来被日本知识界评为“白眉”。“白眉”典出于《三国志马良传》,意为“最好的,最出色的”。“万国战史”读物二十四本。涩江保一个人就有十本。我将其发掘出来,这是对日本研究涩江保领域的一个开拓。日本东方学会定期将本国的研究译成英文向西方介绍,我的这篇文章也被列入介绍计划当中。
刘涛:我们一起吃饭或者聊天的时候,我注意到您时常会提起国民性问题。关于国民性的问题,你的研究亦已有十几年。为什么这么持久地关注这个问题呢?
李冬木:这是鲁迅那里的重要问题,也是近代思想史的重要问题。汪晖的那本书《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没有讨论“国民性”与“进化论”这两个问题,在构成思想史史实的意义上,我觉得是个遗憾。
刘涛:汪晖的这本书有特殊的针对性,主要是指向了西方汉学,故他的问题域和引用文献基本集中于西方汉学。我觉得此书的长处和不足都在此。
李冬木:不论针对什么,既然谈近代思想史。我觉得这两个问题,绝对不能回避。我近十年的研究即集中于这两个方面。思考国民性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近代化或者现代化本质就是人的提升过程。研究人的性格和精神气质是重要角度。学习西方不是原罪。但国家的个性并不会那么轻易丧失,我对此充满信心。比如以商品为喻,日本的商品无论如何带着日本人的痕迹;中国的商品亦有中国人的痕迹。
鲁迅那代人在进化的尺度上看待问题,但是“进化”的核心是人。他追求的目标是人的极大程度的提升。他不是拿中国优秀的与西方抗衡,而是拿最差的与西方比较。尼采拿出一个超人,鲁迅拿出一个“狂人”,甚至后来拿出一个“阿Q”。我们必须正视阿Q,正视人格的弱点,阿Q的本质就是“奴性”。
刘涛:2008年12月6日,王德威老师主持“族裔认同”问题研讨会时,您的演讲是《一本书的旅行》,即谈这个问题。以涩江保的这本书为切入点,展现了思想史的丰富内涵。我想您对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固然是研究鲁迅,是否也想以此为契机,讨论思想史的大问题呢?
李冬木:对。我通过国民性的研究,希望展现思想史、文化史关联和交往的丰富性。我希望还原到当时的语境,展现历史的复杂。此前的历史教科书或者通史,一方面固然让我们知道了大体轮廓,另一方面也简化了我们的历史,误导了我们。只有前前后后捕捉到一些信息,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历史。《一本书的旅行》是我这本书的导言,这本书不久会出版。
刘涛:您为什么要研究进化论的问题呢?
李冬木:这是思想史另一个重要问题。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其时影响非常大。赫胥黎的原文很简单,严复的译文却非常古奥,吴汝伦亦为之叫好。严复要通过这本书向国人说“适者生存”。严复给了其时知识分子非常大的鼓舞,但是关于进化论本身其实并不懂,只是觉得严复文章非常好。周作人说:“他读懂进化论,是在宏文学院,学了日语之后。”但很少有人拿周作人的话当真。我于是去探讨这个问题。后来找到了丘浅次郎,鲁迅关于进化论以及其它很多想法,都来自此人。丘浅次郎留学德国,懂十三门外语。我注意到了鲁迅与之相关的大量思想。举几个例子吧。鲁迅有一个“眼睛画”的说法,即是来自丘浅次郎的进化论讲话。鲁迅全集对此的注释说是来自东晋顾恺之,这太远了。鲁迅说的不相信“黄金世界”,这亦是丘的思想。鲁迅还讲过农夫农妇的想象皇帝皇后的生活,说“拿一个柿饼子来”或挑粪桶的扁担都是金子的等例子,都与丘用过的例子很相像。鲁迅的“示众”思想亦来自丘的关于猴子也有好奇心,喜欢围观的思想。鲁迅无形中消化了很多人的思想,化为无形;周作人不一样,他大半在引用。
刘涛:您现在的这些研究。就是要从无形之中找出有形,看鲁迅的思想来源和知识背景。
李冬木:对。只有真正这么做,才能找出思想的真正源流,而不是没有基础的胡思乱想。现在很多研究没有根基,我提倡的实证研究,即是要注重根基。
刘涛:看一个人阅读的书,即可见出这个人的思想境界。鲁迅毕竟曾留学日本,其思想资源亦多与日本学术界相关。您这些年持续向中国翻译解释日本学者研究鲁迅的著作,或许就是出于这层考虑吧。您可否谈谈翻译竹内好《鲁迅》的前前后后,以及为什么又重译《鲁迅》?
李冬木:我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即译完《鲁迅与日本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后来很久才出版。当时黄源先生主持一套译丛,我这本书本来列在其中,但最后只出了竹内好的《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这本书只印了1000册,非常紧俏。译者是李心峰。他是我吉大的前辈,是孙歌的同班同学。李心峰先生的这个译本我一直没有读过。2005年12月在上海为竹内好的第一本中文版评论集《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其中包括我重译的《鲁迅》)举行“鲁迅与竹内好国际讨论会”,会上郜元宝先生跟我说他读过以前的译本。我就问谁有这个译本,可否帮我也找一本。三联的叶彤先生也去了,回去就复印了一本寄给我。那时候我才看到李心峰先生的译本。我大概读了一下,这个质朴的译本当时在中国知识界发生那么大的影响,真是令人感慨。
我很早就开始接触竹内好。当时刘柏青先生访日归来之后,带回非常多的日文书籍。我就是那时候通过书籍和刘先生的讲授开始知道的竹内好。日本战后的鲁迅研究,无论如何跨不过竹内好的《鲁迅》。原神户大学教授山田敬三有一本书叫做《鲁迅的世界》(1977年),他在序言中即说日本战后的鲁迅研究者面前都耸立着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墙,这就是竹内好。可以说,日本战后的中国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竹内好开始的。我当时在读伊藤虎丸,他的书里不断提到竹内好,亦在不断修正竹内好的框架。当时我非常好奇,伊藤虎丸与竹内好搏斗得这么痛苦,引发了我强烈的兴趣,于是开始阅读竹内好的《鲁迅》。我1985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发表在《吉林大学学报》
(1984年第4期,后收《中日比较文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上叫《关于“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鲁迅与战后日本文学》,这一篇即是关于竹内好研究的论文。
当时读竹内好非常吃力,翻译也没有勇气。在日本读书时,我下决心认真读竹内好《鲁迅》,前后读了不下五遍。竹内好的语感我基本上已经很熟悉了。
竹内好的问题意识抓住了我。鲁迅国民性、文化、政治批判,落实于一个核心问题,即“奴隶性”批判。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阐发鲁迅“奴性”以及“循环史观”最好的是竹内好。竹内好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抓住这个问题。其时他处于日本军部的强烈压制之下,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有力的支撑。竹内好在北京时见到很多次周作人,但是对周作人没有什么好印象。因为他所要寻求的东西,周作人给不了。平和冲淡并不是竹内好想要的精神品质。竹内好强调“主体性”,奴性恰是没有主体性。前几年我在《读书》2006年4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竹内鲁迅”三题》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后来之所以要翻译此书,和孙歌有关。孙歌希望译此书用意很深。2003年赵京华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们想请我翻译竹内好的《鲁迅》。我当时正在研究丘浅次郎,但是我立即答应了。放下电话,《鲁迅》的第一句话立刻涌上心头。我力图译出竹内好的语气。孙歌对竹内好有自己的理解,此前她引用竹内好时,已经译过很多段落。但她的语感与我不一样。为了译此书,我们几乎对每一个词都有一番推敲上的“攻防战”,前后通过数不清的电子邮件。我两个月基本上把原文译完,八个月作注释,因为竹内好的思想背景太复杂了。竹内好的书第一次有注释,日文版亦没有,因此日本人也觉得竹内好很难读懂。有日本学者和我开玩笑说,今后我们读竹内好得要看中译本的注释了。
刘涛:对。我当时读此书的时候,即惊叹于译本注释之详细和认真。记得有一条关于“回心”,我与周围同学还讨论过。
李冬木:对。“回心”与“转向”是竹内好的两个重要观念。但是“回心”这一注释,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伊藤虎丸先生生前,我曾直接向他请教过。就此问题曾与伊藤先生通过好几封信。
刘涛:上次张业松老师来哈佛访问时,带了您最近的译作《鲁迅与终末论》。上次在您这里聚会,也见到过这本书。您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呢?
李冬木:实际上,伊藤研究鲁迅的核心是这本书。伊藤先生认为《鲁迅与日本人》只是一个普及本,那本书通俗易懂。伊藤实际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他面临着日本战后严重的大学问题,这其实与当下中国大学亦非常相似。他提的实际不是鲁迅的问题了,而是日本大学的问题,可见鲁迅对伊藤影响之深。大学没有了主体性,完全细分化。伊藤面临着这个问题非常苦恼,于是向鲁迅求助。伊藤甚至说,鲁迅的问题无所谓,我希望关注现实的问题,鲁迅是他的思想资源。
这本书的解说和译后记原计划是发在《读书》上,后来因故没有发表。“终末论”一词非常有歧义。在译著的封底页我写了一段话,可以解释“终末论”:“作者所用‘终末论,并非预告世界末日的流行语,而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终末论意义上的个的自觉。所谓‘终末论,并不是预想当中这个世界走向最后的事件,而是这个世界本身,在根柢上就是终末的。‘终末论实际是要‘确保乃至恢复历史,以作为个体的‘个去爱和决断的场所”,因此“终末论是希望之学”。
刘涛:我们的谈话就以您的这段话为结束吧。非常感谢李老师。
冬木1959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1979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现代文学专业。1986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留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1988年留学日本,先后在关西学院大学、京都产业大学做客座研究员,自1990年起在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攻读日中近代文学比较研究博士课程,1994年课程结业离校。现任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
专业领域为中日近代文学比较研究。专著有《鲁迅の研究——<造化>ぅ<国民>》(佛教大学、2002年)。近年来的研究课题是“鲁迅与日本书”,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涩江保译<支那人气质)与鲁迅(上、下)》、《(支那人气质>与鲁迅文本初探》(《关西外国语大学研究论集》第67号[1997]、68号[1998]、69号[1999]。《涩江保译(支那人气质>与鲁迅(上、下)》的压缩版亦连栽于《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4~5期。昆明·建国五十周年鲁迅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关于(物竞论)》(佛教大学《中国言语文化研究》第一期,2000年。绍兴·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丘浅次郎と鲁迅(上、下)》(佛教大学《文学部论集》第87号[2003]、88号[2004])、《“国民性”一词在中国》、《“国民性”一词在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论集》第91号[2007]、92号[2008])等。
翻译有《鲁迅<野草>全释》(片山智行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伊藤虎丸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鲁迅》(竹内好著,收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竹内好文集《近代的超克》,2005年)、《鲁迅与终末论》(伊藤虎丸著,三联书店2008年)以及学术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