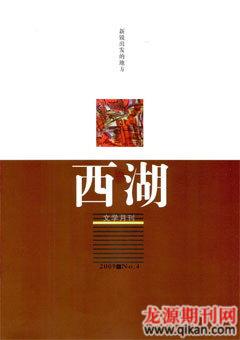山中发红萼
王继军
读到《燕声莺语》的时候,正逢木芙蓉花开。我居住的附近,木芙蓉大多被种植在小河边上,虽然离马路不远,而且,木芙蓉花花色妍丽,但是,因为现代人的忙碌加上车辆的速度,那些正怒放的花也显得比较落寞,可能还落了一层灰尘。但是,只要你看到了——你看到的就会是妍丽的意象,因为是秋天,它还会带给你温暖的感觉。它粉红的颜色因为季节的缘故,又因为花瓣略有褶皱,虽鲜艳却不轻佻。而这正是我读《燕声莺语》后慢慢酝酿出的一种印象。木芙蓉就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豆芽儿的形象,是氤氲在豆芽儿心底的一种热烈又隐秘的情感。小说将这种情感写得活泼而又寂寞。
这是一篇写山村生活的小说,不知作者是否受了沈从文《边城》的影响,但是现在的山村肯定不会受《边城》的影响,虽然看上去它很偏僻,但是还没有偏僻到没有村支书的地步。不过这里的村支书,大概因为偏僻,也没有成为恶霸的象征,至少从豆芽儿的眼里没有看到这一点,而且——也是从豆芽儿的眼里看——他们一家是通向文明的通道。支书家的儿子周子善到城里读了书,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还是可以做一个教书先生的。对于豆芽儿来说,周子善的白球鞋都是香的。这显然是一个通感式的表达,读起来有点别扭,但是因为周子善能用木炭在墙壁上写下这样的诗词:“燕飞忙,莺语乱,恨重帘不卷,翠屏平远。”再加上家世好,身材好,对于怀春的略通文字的农家少女,教书先生周子善可以说是通体发光了,在幻觉中,飘香的白球鞋也完全是可能的。这样通体放光的人去豆芽儿家提亲,对豆芽儿来说,自然是天神下凡。在原型上,这是王子与灰姑娘的山村版。只是,如果仅是这短暂的下凡,要引出一段醇厚绵长的爱,显得有些牵强。小说在这里很好地把握着分寸,天神不仅要下凡,凡女还到天神家里走了一趟,按当地的风俗说是去“看家”。姻缘虽然没有成,但是一来一去,却不多不少地在豆芽儿身体里埋下了一颗发育饱满的爱的种子。我觉得豆芽儿的爱情是虚幻的,她可能爱的不是周子善这个人,但细究起来,即使城里的年轻男女已经有了肌肤之亲,相互爱起来的时候,是否能真的爱上“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形象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植入豆芽儿身体里的种子却是真的。它将要在她的身体里膨胀、发芽,抽穗直至结果和凋落。耗尽她孤单而短暂的一生,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好像马克思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果你在爱别人,但却没唤起他人的爱,也就是你的爱作为一种爱情并不能使对方产生爱情,如果作为一个正在爱的人你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被人爱的人,那么你的爱情是软弱无力的,是一种不幸”。这也许是对的,但却只是“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男女之间追求平等和自我。也就是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只是男女之间的一种关系,不再跟他们生存的世界有关,一旦男女之间没有实现爱情交换,爱情的意义就会削弱,甚至丧失殆尽。现代男女从世界中独立了出来,有了更清晰和具体的自我意识,但也失去了“世界”的呵护,很难在世界中提升,在交换失败后,暴露在空旷的水泥广场上,显出孤单无助的本相。但是对于生活在“山村”中的豆芽儿来说,她和山村是一体的,山村及其风俗给了她一种朴实性,并且将她融入其中。她孤单地养育了这颗几乎是飞来的种子——没有享受到爱情的甜美,但种子开出的花、结出的果子,也回报了她的辛劳。她比其他的山村姑娘多了一个秘密,这秘密使她变得敏感,使她的嗅觉听觉触觉都灵敏起来,可以捕捉单调的山村生活中细微的变化,这使她的淳朴摆脱了单调性,变得更丰盈活泼。山村里的一切,不仅山和水是自然的,连风俗也是自然的。这种自然性给了她一种顺天应命的美。她自然地接受了周子善同会唱歌的美好女子的婚姻,自然地跟木匠能手但长着龅牙的常来结了婚。她甚至带着惭愧的心喜欢周子善的新媳妇,她跟常来的婚姻可能没有像与周子善结合会带来的战栗,但是也没有龌龊,常来操持手艺活,豆芽儿则照顾家里家外;她还喜欢支书一家,放自己的孩子去支书膝下承欢,她心中没有权势的概念,只是去慰藉他们的寂寞。后来周子善跟他的媳妇关系破裂,远走他乡,临走托付她照顾自己的父母。周子善的媳妇并不贤良,她跟别的男人通奸,并且恶待婆婆,村支书下台并且意外死了。她一边安慰婆婆,一边也并不厌恶周子善的媳妇,并且还希望周子善也不要厌恶她,因为她心里也有她的苦衷……最终,她孤独隐秘的爱情通向了爱,这爱弥补了她那有缺陷的爱情,同时也使山村更富有人情的气息。她的死亡也是自然的,她迷迷糊糊地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看到的却是周子善媳妇的死。她就像一朵木芙蓉一样在地震中消失了,这不是说她死得美丽,而是死得悄无声息。但是,也正是因为悄无声息,有一种美让人缅想。
对于当代中国,这只能是一篇发生在山村的故事,而山村还须是偏僻的。游人所到之处,比如《边城》的发源地风凰,都已经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了。如果不是山村,如果山村不够偏僻,豆芽儿就不真实,或者说不能写真实。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故事,因为没有山村自然性的支撑,豆芽儿就是一个可怜愚笨生命麻木的形象,她的顺天应命就无法发展成更厚实的存在。村支书对于庙儿湾也就是故事发生的地方来说,还只是通向“文明”的一个窗口,而“文明”普及的地方,人们或者说作家们已无力虚构一个真善美的故事了。作家变得更擅长实际上是更容易编写一个揭示人性丑陋的作品,写“恶”成了作家们的宿命。但当作家发现仅仅写“恶”不够的时候,同时也发现中国已经很少有地方可以承载一个善的形象了。但要找这样的地方,却无法靠勤劳的双脚去寻觅,更重要的大概是要改变对世界和自我的看法。人性不是总在“发展”的,沈从文从大都市回到了凤凰,福楼拜找到《一颗淳朴的心》,不时有人会回到源头去寻觅更真实的生活,这种生活也许并不能在我们的社会中实现,但它可以作为一种光返照我们的生活。我觉得《燕声莺语》也具有这方面的努力,给人以启迪。只是,落实到语言和人物,作者的技巧和认识并不是很成熟。豆芽儿少女时的心思写得很细腻和微妙,但豆芽儿从少女变成中年,心理的变化层次不够分明。豆芽儿的丈夫常来,快到结束时好像突然被通电了一样,写得活了,写出了一个和自己的手艺融为一体的人所具有的灵光。但是前面却失之于粗略,比较黯淡,而且他的暗也使豆芽儿的一侧隐没在阴影中,减少了主人公的立体感。大约现在要写好乡村生活是更难的了,废名是读了西语系,懂得了莎士比亚,再回头写成了《竹林的故事》的。